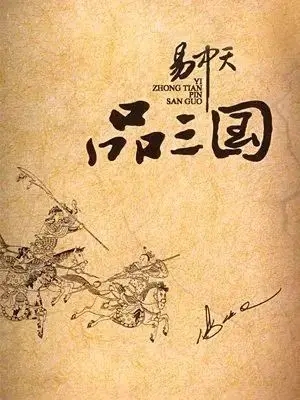第二章 尼莫船长的新提议
1月28日正午,鹦鹉螺号在北纬9.4°处浮出了水面,我们望见了在西面8海里远有一块陆地。我率先注意到那是一群海拔约2000英尺高的连绵起伏的山峦。我测定好方位,就回到客厅里,在地图上对比了一下,才意识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锡兰岛——印度半岛这片叶子下的一颗明珠。
我回到图书室寻找一些关于这个岛屿——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的书籍,恰好找到了一本H.C.希尔先生编写的,名为《锡兰和锡兰人》的书。我一回到客厅,就记下了锡兰的方位。在古代,这个岛屿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称呼。它的地理位置在北纬5.55°和9.49°、东经79.42°和82.4°之间。岛长275英里,岛的最宽处有150英里,周长900英里,面积24448平方英里,也就是说,比爱尔兰岛略微小一点。
这时,尼莫船长和船副出现了。
船长看了一眼地图,然后转身对我说:“锡兰岛是一个以采珠业著称的地方,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想不想去看一看它的采珠场?”
“那还用说,船长先生。”
“好,这并不难。只是一年一度的采珠季节现在还没开始,我们只能看看采珠场,却不能遇到采珠人。不管怎么样,我会下令把船向马那阿尔湾开去的,夜里我们就能到达那儿。”
船长对船副说了几句话,船副就马上出去了。不一会儿,鹦鹉螺号又潜入了水中,压力表指示在30英尺深处。
我两眼盯着地图,搜索着马那阿尔湾。这个海湾处于北纬9°,锡兰岛的西北岸,是马那阿尔小岛延伸而形成的。要到马那阿尔湾去,就必须沿着锡兰岛的西岸向上溯。
“教授先生,”尼莫船长接着对我说,“在孟加拉湾、印度海、中国海、日本海、美洲南部沿海、巴拿马湾、加利福尼亚湾,人们都在捕捞珍珠,但就是锡兰的珍珠捕捞业最卓有成就。我们或许来早了点儿,这里的采珠人三月份才齐集马那阿尔湾。到那时,在30天之间,他们的300只采珠船就会不断地从事着采集大海宝藏这一有利可图的工作。每只船有10个桨手和10个采珠人。10个采珠人分成两组,轮流潜入水中。他们把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拴在一块大石头上,两脚间夹着石头潜到12米深处。”
“如此说来,”我说,“他们还是一成不变地使用这种原始的采珠方法吗?”
“是的,”尼莫船长回答说,“尽管1802年《阿米恩条约》签订后,这些珠场就属于世界上最工业化的英国人所有,但原始的采珠法还是沿袭使用着。”
“喏,依我看,您使用的潜水服在采珠这样的作业方面似乎大有用武之地。”
“是的,这些可怜的采珠人毕竟不能在水底下待太久。英国人佩斯瓦尔在他的锡兰游记中提到,有一个卡菲尔人可以在水下憋气15分钟,但我认为这不太可信。我知道有些潜水者可以在水中坚持57秒钟,功底深一些的可以坚持到87秒钟,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的;而且,这些不幸的人一回到船上,鼻子和耳朵都淌着血水。我认为采珠人在水中平均可以待上30秒,在这30秒中,他们得拼命地把他们抓到的珍珠贝往网袋里装。而且,这些采珠人一般不能活到老,他们的视力衰退,眼部溃疡,身体多处创伤,更有甚者,他们经常在海底中风。”
“是的,”我说,“这是一种悲惨的职业,它只是为了满足某些骄奢淫逸的人的需要。可是,船长,请告诉我,一只船每天能采到多少珍珠贝呢?”
“有四五万只吧。我甚至听人家说,在1814年,英国政府为了谋求高额利润,雇人采珠,在整整20天里,采珠人共采集了7600万只珍珠贝。”
“可他们会付给采珠人足够的佣金吗?”我问。
“雇金少得可怜啊,教授先生。在巴拿马,采珠人每周才赚到1美元。而且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摸到一个含有珍珠的珠贝就得一个苏,可是他们抓到的珠贝里毕竟多数是没有珍珠的啊!”
“这些可怜人养肥了他们的主子,到头来自己才得一个苏,真是可悲啊!”
“这样,教授先生,”尼莫船长对我说,“您和您的同伴一起去参观参观马那阿尔滩吧,说不定会碰到提早来的采珠人呢,我们就看看他们如何作业吧。”
“好啊,船长。”
“随便问一句,阿罗纳克斯先生,您不怕鲨鱼吧?”
“鲨鱼?”我叫了起来。
对于这个问题,这还用说吗?
“如何?”尼莫船长追问说。
“老实说,船长,我对这种鱼还不太了解。”
“我们这些人对它早就习以为常了,”船长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也会的。何况,我们还会带上枪。在途中,说不定能捕杀到角鲨呢,这种打猎很有趣的。就这样吧,教授先生,我们明天一早见。”
尼莫船长从从容容地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客厅。
请想想,假如有人请您到瑞士山上猎熊,您或许会说:“妙极了!我们明天要去猎熊了。”如果有人请您到阿特拉斯平原狩狮或到印度丛林里打虎,您或许会说:“啊!啊!看来我们要去打老虎或狮子了。”但如果有人请您到鲨鱼的老巢里去捉鲨鱼,在接受邀请之前,恐怕您是得三思而行。
我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几滴冷汗。
“让我们再想想吧,”我心里想,“我们得抓紧时间,到水下森林猎水獭,就像我们在克莱斯堡森林一样,那还可以。但在深海里游来荡去,而且还有可能碰到鲨鱼,这可就是另外一回事啊!我清楚地知道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安达梅岛,黑人们会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拿着绳索,毫不犹豫地去攻击鲨鱼。可我也清楚地知道,在这些去迎战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的人中,许多都是有去无回的。再说,我又不是一个黑人。如果我是个黑人的话,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犹豫,就太不应该了。”
于是,我心里想象着鲨鱼的样子,想象着它那硕大的颌部,武装着的一排排牙齿,能把人一下子咬成两段。我已经感觉到腰部隐隐作痛。再说,我不明白船长为什么这么不客气地提出这种糟糕的邀请!这难道是去树下抓一只不伤人的狐狸吗?
“对了!”我想,“龚赛伊怎么样也不会去的,这样我也可以不陪船长去了。”
至于尼德·兰,老实说,我不能肯定。这么大的风险,对他好斗的本性来说,总是一种引诱。
我重新拿起希尔的书,但我只是机械地翻着。在书的字里行间中,我看到的尽是一个个张大着的、硕大无比的鲨鱼颌。
这时,龚赛伊和那个加拿大人走了进来,他们神情平静,甚至还有点儿高兴。他们还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等着他们呢。
“天哪,先生,”尼德·兰对我说,“您的尼莫船长——去他妈的——刚刚跟我们提了个友好的建议。”
“啊!”我说,“你们知道了……”
“请别见怪,先生,”龚赛伊说,“鹦鹉螺号船只的指挥官邀请我们明天陪同您到锡兰美丽的采珠场去参观。他言辞得体,举止堪称一位真正的绅士。”
“他没跟你们说其他的?”
“没有,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没说其他的。除了他跟您说过的散步外,没说其他的。”
“说真的,”我说,“他没跟你们提过任何细节,有关于……”
“一点儿也没有,博物学家先生。您和我们一起去,不是吗?”
“我嘛……当然!我看您对这很感兴趣,兰师傅。”
“是的!这很新奇,很令人惊奇。”
“可能危险点儿!”我旁敲侧击地说。
“危险,”尼德·兰回答说,“在珍珠贝滩上走一趟也会有危险!”
显然,尼莫船长觉得没必要向我的同伴提醒鲨鱼的事。我局促不安地盯着他们,好像他们现在已经四肢不全了。我要不要提醒他们呢?要,当然要,但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先生,”龚赛伊说,“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采珠的细节?”
“是关于采珠本身,”我问道,“还是关于事故……”
“关于采珠的,”加拿大人回答说,“去现场之前,知道一下也是好的。”
“那好吧!请坐吧,我的朋友,我就跟你们说说我刚从英国人希尔那里了解到的所有知识吧。”
尼德和龚赛伊坐在了沙发上,加拿大人首先发问:“先生,珍珠是什么?”
“我憨厚的尼德,”我回答说,“在诗人眼里,珍珠是大海的眼泪;在东方人看来,它则是一滴凝固了的露珠;对于妇女,它是一种椭圆形的首饰,晶莹剔透,珠光宝气,她们戴在手指上、脖子上或耳朵上;在化学家看来,它是有点胶质的磷酸盐和碳酸钙混合物;最后,在博物学家看来,这是某些双壳软体动物分泌螺钿质器官的病态分泌物。”
“它是属软体动物支,”龚赛伊说,“无头类,甲壳属的。”
“对极了,聪明的龚赛伊。但是,在甲壳类中,鲍子、大菱鲜、砗磲、海珧,一句话,所有分泌螺钿质的动物,即那些内瓣充满蓝色、浅蓝色、紫色或白色螺钿质的动物,是不能产出珍珠的。”
“贻贝也一样吗?”加拿大人问。
“是的。在苏格兰、加勒地区、爱尔兰、萨克、波艾米和法国,这些地方的某些河流里的贻贝都不能产出珍珠。”
“好哇!那我们以后得注意点儿。”加拿大人回答说。
“但是,”我又说,“像贝母、乳白珠贝还有珍贵的小纹贝,就特别能产珍珠。珍珠仅是一种圆形的螺钿质凝聚物而已。它或是黏附在珠贝的壳上,或是嵌在珠贝的肉缝里。在壳上的珍珠是黏着的,而含在肉里的则是活动的。但珍珠的形成总是要有一个坚硬的东西作为核心的,这可能是一个石卵,也可能是一颗沙子,螺钿质在沙石的表面常年不断地、一层一层地累积。”
“在一个珠贝里可以同时找到几颗珍珠吗?”龚赛伊问。
“是的,小伙子。有一些小纹贝简直就是珠宝盒。有人甚至说见过一个珠母,它至少含有150只鲨鱼,我是对此表示怀疑。”
“150只鲨鱼!”尼德·兰喊道。
“我是说鲨鱼吗?”我也叫了起来,“我是说150颗珍珠,说鲨鱼就文不对题了。”
“确实是这样,”龚赛伊说,“可是先生,您现在可否和我们讲讲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取珠的呢?”
“有好几种方法,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当珍珠是附在贝壳上的情况下,采珠人就用钳子把珠贝夹出来。但最普遍的方法是把小纹贝摊在铺有草席的海岸边上,让它们在露天中死亡。10天之后,小纹贝就腐烂得差不多了。人们再把小纹贝倒进一个大海水池中,然后打开冲洗。接下来就开始两道取珠的工序。人们先把在贸易中称为‘纯白’、‘杂白’和‘杂黑’的珍珠分别盛到125千克到150千克的小匣子里,再把珠贝的腺组织摘下,煮一煮,再筛一筛,直到看到最小的珍珠。”
“珍珠的价钱是按大小而定吗?”龚赛伊问。
“不仅根据大小,”我说,“而且根据形状,根据水色,也就是颜色,还根据光泽,也就是肉眼看上去柔和绚丽的色泽。最漂亮的珍珠被称为贞珠或范珠。它是单独在软体动物的纤维上成长的,白色,通常是不透明的。但也有的是乳白剔透的。最常见的是球形或梨形的珍珠。球形的可以用来做手镯,梨形的可以做耳坠。因为很贵,所以论颗来卖。其他附在贝壳上,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则按重量来卖。最后,那些被称为小粒珠的小珍珠是低一级的珍珠,买卖时是按斗算的。这些小珍珠主要用来绣在教堂的装饰品上。”
“可是,把珠子按大小分开这活儿,肯定又费时又麻烦吧?”加拿大人问。
“不,朋友。这道工序使用11种筛孔大小不同的筛子。留在20至24孔的筛子里的珍珠是上等的,剩在100至800孔的筛子里的是二等品,最后用900至1000孔筛出来的是小粒珠。”
“太巧妙了,”龚赛伊说,“我明白了,分珠的方法很机械化。先生,再讲一讲有关珍珠开采的情况好吗?”
“据希尔的书上说,”我答道,“锡兰珠场每年的利润丰厚。”
“大量的法郎收入。”龚赛伊说。
“是的,大量的法郎收入!300万法郎,”我重复说,“可是我认为,这些珠场现在不会有过去那样的好收入了。美洲的珠场也一样,在查理王朝统治时,年收益为400万法郎,而如今呢,减少到了三分之二。总之,估计目前珍珠开采总收入为900万法郎。”
“那么,”龚赛伊问,“您能不能说一说一些价值连城的珍珠呢?”
“当然,小伙子。听说恺撒曾经送给塞维利亚一颗现价高达12万法郎的珍珠。”
“我甚至听人家说过,”加拿大人说,“古代有一位贵妇人把珍珠泡在醋里。”
“那是克娄奥巴特。”龚赛伊说。
“这可不太好。”尼德·兰补充说。
“是糟透了,尼德,”龚赛伊说,“这样一小杯醋酸就值15万法郎,可谓价格不菲啊!”
“真遗憾我没能娶到这个贵妇,”加拿大人说着,挥动着手臂,神色令人不安。
“尼德·兰,娶克娄奥巴特!”龚赛伊喊道。
“我早就该结婚的,龚赛伊,”加拿大人严肃地说,“可我没结成,这并不是我的错。我甚至已经买了一串珍珠项链给我的未婚妻凯特·唐德,可她却嫁给了别人。瞧!这条项链整整花了我一块半美元,教授先生,您好歹得相信我,项链上的珍珠可是20筛孔筛子里头的啊。”
“老实的尼德,”我笑着说,“那是人造珠,是一颗外表涂着东方香精的玻璃珠。”
“咦!东方香精,”加拿大人说,“也应该很贵吧。”
“分文不值。它是欧鲌壳上的银白色物质,从水里采集到,保存在氨水中,没有任何价值。”
“可能正因为如此,凯特·唐德才嫁给了别人。”兰师傅通达地说。
“不过,”我说,“说到价格昂贵的珍珠,我想没有任何一位帝王的珍珠可以和尼莫船长的珍珠媲美。”
“是那颗。”龚赛伊指着玻璃罩里华丽的首饰匣说。
“当然啦,我没估错的话,它价值2000000……”
“法郎。”龚赛伊急切地说。
“对,”我说,“2000000法郎。尼莫船长也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采到它。”
“喂!”尼德·兰叫起来,“谁说在明天的散步中,我们不能像尼莫船长一样撞彩呢?”
“做梦!”
“为什么不?”
“在鹦鹉螺号船上,有1000000法郎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在船上,不,”尼德·兰说,“是……在别的地方。”
“什么!别的地方!”龚赛伊摇摇头说。
“确实,”我说,“兰师傅说得有理。如果我们能带着一颗价值几百万的珍珠回到欧洲或美洲去,这起码能证明我们这次历险的真实性,并增加传奇的色彩。”
“我相信。”加拿大人说。
“可是,”龚赛伊说,他总是想到事情会有教训的一面,“采珠危险吗?”
“不,”我赶快说,“特别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就更不会有危险了。”
“干这一行有啥危险?”尼德·兰说,“顶多是多喝几口海水呗。”
“确实如此,尼德。不过,”我尽量像尼莫船长那样,用从容不迫的口气说,“你们害怕鲨鱼吗?”
“我,”加拿大人说,“一个职业捕鲸手,捉鲨鱼正是我的老本行。”
“这可不是用鱼钩把它们钩上来,拖到甲板上,剁掉尾巴,开膛剖腹,掏出心脏扔到海里啊。”我说。
“这么说是……”
“没错。”
“在水里?”
“在水里。”
“我的老天爷,得用一只好鱼叉!先生,您知道鲨鱼这些畜生身体有缺陷,要翻过身来才能咬人,就在它转身时……”
尼德·兰做了一个“咬”的动作,让人感到脊背上都凉飕飕的。
“那,你呢,龚赛伊,你怎么想呢?”
“我,我要坦诚地和先生谈一谈。”龚赛伊说。
“是时候了。”我想。
“如果先生要攻击鲨鱼,”龚赛伊说,“他忠实的助手是没理由不和他一起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