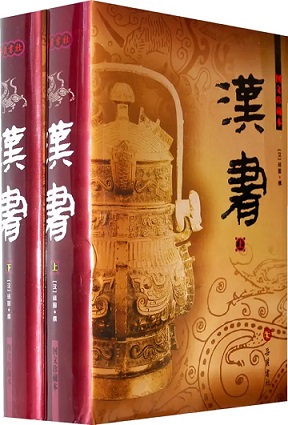第九章 消失的大陆
第二天,2月19日早上,加拿大人走进我的卧室,我正等着他的。他看上去十分沮丧。
“先生,怎么样?”他开口问我。
“尼德,昨天晚上,我们可真倒霉。”
“真是倒霉。这个该死的船长偏偏在我们要去偷他的小船时命令鹦鹉螺号停了下来。”
“是的,尼德。他去找他的银行家有事。”
“他的银行家?”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银行。我是想说,他的财富放在这大西洋里比存在国库里还保险。”
于是,我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加拿大人听,希望他听了之后能回心转意,不再想要离开尼莫船长。可是,适得其反,尼德·兰只是为没能亲自去维哥湾古战场走一趟而后悔不迭。
“总之,”他说道,“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只不过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成功。如果需要的话,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现在鹦鹉螺号正朝哪个方向行驶?”我问道。
“不知道。”尼德·兰回答说。
“那么,中午,我们去看看它的方位。”
加拿大人回去找龚赛伊了。我一穿好衣服就来到了客厅。罗盘所指示的航向令人担忧。鹦鹉螺号现在的航向是西南偏南,我们正背朝着欧洲航行。
我略显焦急地等待着潜艇航行的方位被重新标注在海图上。11点30分左右,储水舱已经被排空,我们的潜水船又重新浮出大西洋洋面。我匆匆登上平台,可尼德·兰已经赶在了我的前头。
一眼望去,陆地已经无影无踪,只能看见茫茫大海。天边有几片帆影,想必是去圣罗克角等待适航的风再绕过好望角的帆船。天空阴沉,要起风了。尼德大发脾气,试图望穿雾气弥漫的海平线,希望在浓雾中能发现我们如此期盼的陆地。
中午,太阳露了一会儿面。船副利用这瞬间的晴天测量了太阳的高度。接着,大海变得波涛汹涌。于是,我们回到了舱里,嵌板又重新被关上。
一个小时以后,当我查阅海图的时候,我发现海图上标明的鹦鹉螺号的方位是在北纬33°22′,东经16°17′,距离最近的海岸有150法里。看来逃跑已经没有可能了。当我把我们所处的位置告诉加拿大人时,他那悔恨的模样读者们可以自己去想象。
我倒并没有过分懊丧,反而觉得像是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被搬掉了,并且又可以平静地继续进行我的日常研究工作了。
夜里11点左右,尼莫船长意外地来到了我的卧室,非常和蔼地问我昨天熬了一夜是否感觉累。我说不累。
“那么,阿罗纳克斯先生,我建议您去进行一次有趣的观光。”
“船长,去哪里观光呢?”
“您还只是在白天有阳光的情况下参观过海底。您是否愿意在一个月黑之夜去看看海底呢?”
“非常愿意!”
“这次海底远足会很累,我先提醒您,要走许多路,还得爬一座山,而且,路也不好走。”
“船长,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我这就想跟你走一趟。”
“那就走吧,教授先生。我们去换潜水服。”
我来到了更衣间,这才发现,这次远足我的两个同伴和船员们都不跟我们一起去。尼莫船长甚至没有向我建议带上尼德或龚赛伊。
不一会儿,我们就换好了潜水服,有人帮我们把灌得满满的储气舱背在我们的背上,但是没有准备电灯。我提醒了船长。
“我们用不着电灯。”他回答说。
我以为他没有听清我说的话,但又不好再提醒他,因为船长的脑袋已经钻进了金属头盔。我也戴好了头盔,并且觉得有人把一根铁棍塞进了我的手中。几分钟以后,等做完了这一套程序,我们的双脚就踩在了300米深的大西洋海底。
这时已临近午夜,海底一片黑暗。不过,尼莫船长给我指了指远处的一个浅色红点,那是一大片微弱的光亮,距离鹦鹉螺号大约有2海里。那是什么光呢?是用什么点燃的呢?它为什么又是怎么在水体中发光的呢?我说不上来。不管怎么说,它为我们照明,光线的确很弱。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特殊的黑暗,并且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用不着兰可夫照明灯。
我和尼莫船长相距很近,径直向那光亮走去。平坦的海底在不知不觉中上升。我们拄着铁棍,步子跨得很大。但总的来说,我们前进得很慢,因为我们的双脚常常陷入长满海藻和布满扁石的淤泥当中。
我继续向前行走,听到头上有一种轻微的噼啪声,有时候,这种声音很密集,形成连贯的噼噼啪啪的响声。我很快就明白了产生这种响声的原因。原来是大雨瓢泼,雨点打在海面上噼啪作响。我本能地想到,自己要被淋湿了。在水中被雨淋湿!我不禁为自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而感到可笑。不过,说实在的,由于身上穿着厚实的潜水服,因此根本就不觉得是在水里,只感觉自己是在比陆地上的空气密度略大的大气中行走,仅此而已。
走了半个小时以后,海底地面上的石头多了起来。水母和小甲壳动物等发出的微弱磷光把海底照得有点光亮。我朦胧地瞥见一堆堆长满植形动物和海藻的石块。我的脚常常在黏糊糊的海藻层上打滑,要不是手里拄着铁棍,恐怕早就不止摔倒一次了。我不停地回头,始终都能看到远处鹦鹉螺号舷灯的光亮,只不过变得越来越苍白。
我刚才说到的一堆堆石块在海底按一定的规律排列。对此,我无法解释。我发现一条条长度难以估量的大裂缝,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之中。此外,其他一些特别的东西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觉得自己脚上沉重的铅底靴踩在一层骨骼上,发出清脆的断裂声。脚下这块辽阔的海底平原是什么呢?我正想问问船长。可是,我对于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海底旅行时使用的手势语言仍然一窍不通。
这时,那个为我们引路的浅色红点在渐渐变大,像火焰一样映红了远处。水里出现这么个光源,使我感到极其惊讶。这难道是电发出的光亮?难道我面对的是一种仍没有被地球上的学者所知道的自然现象?甚至或者是——因为我的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这个火团掺杂着人为的因素?是人类导致的一场火灾?在这么深的水层,我是否会碰到像尼莫船长一样过着这种古怪生活的同伴或朋友呢?船长是去拜访他们吗?我难道会在那里遇到一大帮受够了陆地上的苦难,来海底寻求独立的逃亡者?这些不可理喻的古怪念头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我又不停地受到映入眼帘的海底奇观的过度刺激,即使真的在这里遇上尼莫船长梦寐以求的海底城市,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
我们的前面越来越亮。这道白光是从一座大约800英尺高的礁石顶上发射出来的。不过,我所见到的仅仅是水中折射的反光,而光源,发射这道亮光的地方则在礁石的那边。
在大西洋底错综复杂的礁石迷宫里,尼莫船长毫不迟疑地向前走着。他熟悉这条阴暗的道路。显然,他过去经常来这里,因此不会在这里迷路。我觉得他仿佛是一个海神,于是以不可动摇的信任紧跟在他的身后。当他走在我前面时,我欣赏着他的背影,他那黑色的影子把远处明亮的背景一分为二。
凌晨1点,我们来到了礁石的头几道斜坡前。不过,要爬上这几道斜坡,还得冒险从崎岖的羊肠小道穿过一片树林。
是的,是一片没有叶子、缺乏生气的死树林,已经在海水的作用下被矿化了的树林。树林里到处是高大的松树。这里就像一个靠扎根在海底泥土里的树根支撑而站立着的煤矿,树的枝杈犹如精致的黑色剪纸清晰地倒映在树林上面的水中。这令我不禁想起了位于山腰的哈茨山森林,可这是一个被大海吞没的森林。林间小道上长满了海藻和黑角藻,海藻丛里有无数的甲壳动物在爬行。我攀登岩礁,跨过横躺着的树干,扯断了攀附在树干上的海藻,吓跑了在林间转悠的鱼群。我跟在这位不知疲倦的向导后面,兴致勃勃,也丝毫没有感到疲惫。
多美的景色啊!我该如何描绘它呢?如何描绘这水中的森林和岩石呢?它们的底部显得黑暗而又荒凉,它们的上面因那团光亮及其反光而被笼罩在红色之中。刚刚被我们踩过的一块块岩石,在我们的身后一片一片地坍塌下去,犹如雪崩一样发出沉闷的轰隆声。我们的左右到处是深不见底的黑乎乎的沟壑,眼前却呈现出一片似乎是所谓的林间空地。有时,我不禁自问,这里的海底居民该不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吧。
尼莫船长始终在向上攀登。我也不甘落后,勇敢地跟在他后面。我手中的铁棍帮了我不少忙。在两侧都是深渊的崎岖小道上行走,踏空一步将摔得粉身碎骨。我步履坚定地走着,一点儿头晕目眩的感觉都没有。时而,我纵身一跃,跳过一道裂缝,要是在陆地冰川之间,这么深的裂缝说什么我也会望而却步的;时而,我在一根横躺在深渊两侧、不停地摇晃着的树干上冒险地走过,而且能不看两脚一眼,双目只顾欣赏这一带荒凉的景色。那边,仿佛在垂头顾盼自己不规则的基座的巨大岩石好像是在向平衡规律挑战,岩石丛中生长着一些生命力顽强的树木,它们相互支撑着。一些形似摩天大楼的岩石,各边就像城堡碉堡之间的护墙那样陡峭,要是在陆地上,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绝不可能倾斜成这样的角度。
当我身穿笨重的潜水服,头戴钢盔,脚踩铅底靴,攀登陡峭的斜坡犹如山羊或羚羊一样敏捷时,我自己不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由海水的高密度所造成的差异吗?
一说起在海底旅行的这段经历,我自己也觉得简直不像是真的!我可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可能的,而确实实实在在、无可争议的事物的见证人。我根本就没有做梦,我确实看见了,真实地感觉到了。
离开鹦鹉螺号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穿过了林地。这座礁石的顶峰就矗立在我们头顶100英尺的高处,它的投影遮挡住了礁石那边的光辐射。石化了的灌木东倒西歪地铺满了地面,我们每走动一步,一群群鱼像野草丛中受惊的鸟儿一样四散开来。岩石堆坑坑洼洼的,行走困难。在岩石下面幽深的岩洞和深不可测的洞穴里,我听到了可怕的东西发出的声响。当我看到一根又粗又长的触须横挡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或听到一只大螯虾在黑洞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时,我全身的鲜血都涌到了胸口!数以千计的亮点在黑暗中闪烁,那是蜷缩在巢穴里的巨大的甲壳动物的眼睛。大鳌虾犹如持戟的卫兵严阵以待,挥舞着双螯,发出金属般的响声:大海螯像是一门门瞄准了目标的大炮;可怕的章鱼扭动着触角,活像几条缠绕在一起的活蛇。
这个我素昧平生的超凡世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这些仿佛是把岩石作为自己的第二甲壳的甲壳动物又是属于哪一目的呢?大自然是在哪里发现了它们无性繁殖时期的生活的呢?它们在大西洋底层已经生活了多少个世纪了呢?
不过,我不能停留。尼莫船长已经对这些可怕的动物习以为常了,因此对它们毫不在乎。我们登上了第一块高地,有许多令我惊奇的东西在等待着我。这里横亘着许多景色美丽的废墟,留下了人工所为的痕迹,而不是造物主造物的杰作。从这垒成堆的石块中,昔日的城堡、寺院依稀可辨,现在已被鲜花盛开的植形动物占领。海藻和墨角藻,而不是常青藤,成了这里的主人。
这部分因地壳剧变而被淹没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是谁把这些岩石和石块堆砌得像史前的石棚一般呢?现在,我又是在哪里呢?尼莫船长心血来潮,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
我想询问尼莫船长,但我无法问他。于是,我拽住尼莫船长的胳膊,叫他停下来。可是,他摇了摇头,用手指了指前面一座礁石峰,好像是在对我说:
“走吧!再往前走!一直往前!”
我鼓起最后的勇气,跟着他继续向前。几分钟以后,我登上了比这块礁石其他地方高出十来米的顶峰。
我俯首眺望我们刚才爬上来的这一侧山坡。这座礁石只比海底平地高出七八百英尺。但是,礁石的另一侧则距离大西洋海底的高度是这一侧的两倍。我举目向远处眺望,一块由强烈的闪光照耀的广袤空间一览无余。原来,这座礁石是一座火山。在距离顶峰50英尺的地方,雨点般密密麻麻的石块和岩渣丛中,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正在喷射急流般的熔岩,散落在海水中成了熔岩的瀑布。这座火山就像一把巨大的火炬,照亮了整个海底平原,一直到海底地平线的尽头。
我刚才说过,海底火山口在喷射熔岩流而不是火焰。火焰的产生需要空气中的氧气,在水里产生不了火焰。不过,熔岩流本身就有白炽的成分,能够产生白色的火苗,一旦与海水接触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把与之接触的海水化为蒸汽。湍急的流水带走了这些趋于扩散的气体,熔岩流一直流淌到这座礁石的脚下,就像维苏威火山的喷出物一直流淌到另一侧的拖雷德尔格雷科城一般。
事实上,我的眼前到处是废墟、沟壑和废弃物,一个被摧毁的城郭:屋宇倾覆,寺院坍塌,拱门散架,梁柱倒地,不过从中还能感觉到托斯卡纳建筑比例匀称的构造;稍远处横亘着一个巨大的输水工程的废墟。这边是一座护城的加固墙,还有潘提翁神庙式的浮坞;那边是码头的遗址,好像是一个古代的沿海港口,有可能停泊过商船和战舰。更远处,是一道道长长的坍塌了的护城墙和大街废墟,尼莫船长带我来看的简直是一座沉入大海的庞贝城!
我是在哪里?我不顾一切,想问个究竟。我想说话,想脱掉套在头上的铜头盔。
可是,尼莫船长做手势阻止了我。接着,他捡起一块白垩石,走到一块玄武岩前写了一个词:亚特兰蒂斯(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没大海)。
我的头脑豁然开朗!亚特兰蒂斯,泰奥庞波斯(古希腊演说家、历史学家)笔下的梅罗彼德古城,柏拉图所说的亚特兰蒂斯岛,奥利金(古代基督教希腊神甫之一)、鲍尔菲里奥斯(原籍叙利亚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让布利克斯(原籍叙利亚的古希腊作家)、德·安维勒(法国地理学家)、马尔特·布朗(丹麦地理学家)、洪堡等人不承认它的存在——他们把它的消失归咎于神话传说,而波塞多尼奥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普林、安米阿纽斯·马塞卢斯(希腊籍用拉丁语写作的历史学家)、德尔图良(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恩格尔·歇雷、图尔纳弗尔(法国植物学家、旅行家)、布丰(法国博物学家)、德·阿乌扎克等却认为它确实存在,这片陆地现在就展现在我的眼前,而且仍带着它曾遭受过天灾的、不容置疑的痕迹!因此,这个沉没了的地区存在于欧洲、亚洲和利比亚,以及直布罗陀海角以外,强大的阿特拉斯人民就是在这里繁衍生息,古希腊发动的头几次战争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历史学家柏拉图本人把这个英勇时代的丰功伟绩写入了自己的著作。他的《泰迈奥斯与克利蒂阿斯对话录》,可以说,是受诗人和立法者梭伦的启发而撰写的。
一天,梭伦与萨伊城——当时已经有八百年的历史,铭刻在古城神庙圣墙上的年表可以证明这一点——几个年长的圣贤聊天。其中,一位长者讲述了一个比萨伊城还要古老1000年的城市。那就是雅典最古老的城市。在建城900世纪那年,这座城市被阿特拉斯人攻陷,而且毁坏了部分建筑。据这位长者说,阿特拉斯人占领了一个比亚洲和非洲之和还要辽阔的大陆,其面积跨越北纬12°到40°。阿特拉斯人把他们的统治势力甚至扩展到了埃及,还想强迫古希腊人接受他们的统治,但因遭到希腊人不屈不挠的抵抗而不得不退却。几个世纪过去了,发生了一次地壳剧变,洪水、地震接踵而至。一昼夜之间,亚特兰蒂斯便销声匿迹了,只有几座最高的山峰仍然露出海面,即现在的马代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
尼莫船长在白垩石上写下的那个名词在我的脑海里唤起了这么多的历史回忆。我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脚踩着这块大陆的一座山峰!我用手触摸着这些具有上千世纪的历史、与地质时期同时代的废墟!我在与盘古同时代的人走过的地方行走!我脚上沉重的靴子的铅底踩碎了传说时代的动物的骨骼,而现在已经矿化了的大树曾经荫庇过它们!
啊!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儿时间!我真想走遍这座山的陡坡,走遍这个无疑连接着非洲和美洲的辽阔大陆,游览这些挪亚时期大洪水前的城郭。也许,就在那里,我的眼皮底下,曾经是崇尚武力的马基摩斯城邦和虔诚的尤西比乌斯城邦的遗址。它们的剽悍居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几个世纪,他们不缺乏力量来修建这些现在还能抵挡海水的城郭。也许,有朝一日,这些被海水吞没的废墟还会因火山喷发而重新露出水面!有人已经指出,在这一带大西洋海域有许多海底火山。有许多船只在这片多灾多难的海底上面经过时感觉到过特别的震动。有的船听到了海底地壳碰撞发出的沉闷响声;另一些船收集到了喷出海面的火山灰。这个地带,一直到赤道,迄今仍受到地下深层力量的作用。有谁知道,在遥远的将来,由于火山喷出物和熔岩的日积月累,一些火山顶是否会不断增高,最终会露出大西洋洋面。
我正浮想联翩千方百计地把这一壮观场面的各个细节引入自己的脑海时,尼莫船长却用胳膊肘倚靠在一块石碑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雕一样心醉神迷。他是否在思念这些永逝的先辈,在向他们请教人类命运的奥秘?这个怪人来这里是否为了再次接受历史遗迹的洗礼?他这个不喜欢现代生活的人来这里是否为了重温古代生活的旧梦?我怎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和他一起探讨他的思想,从而理解他的思想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整整停留了一个小时,凝视着这片被熔岩光亮笼罩着的广袤平原。有时,熔岩喷发的强烈程度令人吃惊。地核内部的沸滚使山体的地表发出阵阵震颤。这种深沉的响声在水体中传播,放大以后发出响亮的回响。
就在这个时候,月亮透过水层露了一会儿面,在这块被淹没的大陆上投下了几缕苍白的光亮。虽然只是几缕微弱的光亮,但却产生了难以描绘的效果。船长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向这块广袤的平原投去了最后一瞥。随后,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跟上他。
我们很快下了山。过了化石树林,我就看到了鹦鹉螺号上像星光一样闪烁的舷灯。船长径直向潜水船走去。当我们回到船上时,大西洋洋面上已经露出了第一缕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