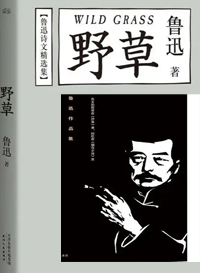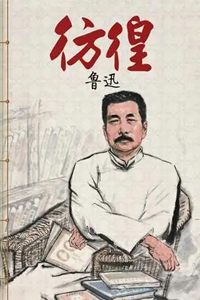第十章 海底煤矿
第二天,2 月 20 日,我起得很晚。夜晚的劳累使我一直沉睡到早上 11点钟。我赶快穿上衣服。我很想知道鹦鹉螺号船的航向。而仪器显示出它总是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在100米的深度向南行驶。
这时龚赛伊走了进来。我向他讲述了我们晚上的旅行。刚好嵌板是开着的,他还可以眺望到那沉没的陆地的一部分。
实际上, 鹦鹉螺号船只此时正贴着离大西洋城平原地面仅仅10米的水层行驶。它就像陆地草原上一只被风吹送的气球一样疾驶着,更恰当地说,我们在客厅里就像是坐在一列特快列车的车厢里一样。最初从我们眼前闪过的景象,是那些形状各异的岩石;接着是那片从被植物占据过渡为被动物占领的树林,它那一动不动的影子在水中丑态百出;还有覆盖在轴形草和银莲花地毯下的沉没的大岩石,上面竖起无数长长直立的蛇婆;然后是形状怪异的熔浆块,这些熔浆块证明了地球内部活动的强烈性。
当这些奇怪的景象在我们的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时,我向龚赛伊讲述了阿特拉斯人的故事,拜伊(法国作家、政治家)纯粹从想象的角度出发,为他们写下了多少动人的篇章。我向龚赛伊讲了这些英雄人民的战争史。我谈论亚特兰蒂斯城的问题,对此我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但龚赛伊心不在焉,他根本没听进去,他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无动于衷,我很快就会做出解释的。
原来,他的眼光被无数的鱼群吸引住了。当鱼群游过时,龚赛伊便开始忘我地对它们进行分类。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随着他,着手开始我们的鱼类学研究。
其实,大西洋的鱼类和我们以前观察过的并没什么明显不同。身材庞大的鳐鱼,长达5米,天生身强力壮,能跃出水面;各种各样的鲛鱼,其中有长15英尺,长着尖三角牙的海蓝鲛鱼,身体透明,在海水中几乎看不出它来;还有栗色的萨格鱼;棱柱形,长着癞皮甲壳的人鱼;与地中海中的同类很相似的鲟鱼;长1英尺半,黄褐色,长有灰色小鳍,没牙齿又没舌头,像柔软的蛇一样爬行的喇叭鱼。
在骨质鱼类中,龚赛伊记录了:浅黑色,长3米,上颚长有一把利剑的帆船鱼;色彩鲜艳的龙,即亚里士多德时代著名的海龙,其背鳍上长着尖刺,捕捉尤为危险;还有褐色的背部缀满着小蓝纹,镶着金边的哥里菲鱼;美丽的鲷鱼;犹如一只反射蓝光的碟子的月亮金口鱼,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些银色的小点;最后是长8米,成群结队行走的旗鱼,它们长有浅黄色、镰刀状和长剑状的鳍,这是一种无畏的动物,与其说它们是食鱼动物,不如说它们是食草动物更为恰当,它们对雌鱼发出的一个即使是最小的信号,都表现得像温驯的丈夫一样言听计从。
在观察海里各种动物种类的同时,我还不停地审视着亚特兰蒂斯广阔的平原。有时,因为海底的地表起伏不平,鹦鹉螺号不得不放慢航速,它像一条鲸鱼般灵巧地在这些丘陵形成的狭窄水道中穿行。遇到走不出的迷宫,它便像气球一样升起,越过障碍后,它又回到距海底仅几米的深度中行驶。多么令人羡慕、令人陶醉的航行,这使人想起了气球飞行的情形,不同的是,鹦鹉螺号是被动地受它的舵手的操纵。
下午4点钟左右,总是由厚厚的夹有化石枝叶的淤泥构成的地表开始慢慢地变化;石块越来越多,好像是砾岩和玄武凝灰岩,中间夹杂着一些熔岩和硫黄黑曜岩。我本以为这个山区很快会连接上一片辽阔的平原的。但事实上,鹦鹉螺号前进了一段路程后,我发现了南边的海底地平线被一堵高墙挡住,好像所有的去路都被堵住了。墙顶显然高于海平面。那堵高墙可能是一片陆地,至少是一个岛屿,可能是加那利群岛的一个小岛,也可能是佛得角群岛的一个小岛。这时,船的方位没标出来——这可能是有意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位置。但不论如何,这么高的一堵墙让我觉得我们是走到了大西洋的尽头了,我们没有走过的,总之,应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夜幕降临了,可我的观察并没中断。龚赛伊已经回到他的船舱去了。我独自一个人。这时,鹦鹉螺号放慢船速,在地面上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上低旋。它有时擦地而过,好像要在上面停留似的,有时却心血来潮地浮出水面。此刻,我透过晶莹的海水,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天上一些璀璨的星座,并清晰地辨认出排在猎户座后面的黄道带星座中的五六颗星星。
在嵌板关闭前,我还在玻璃窗前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欣赏着美丽的大海和天空。不久,鹦鹉螺号来到了那堵高墙耸立的地方,并停下来不走了。它要做什么呢?我猜不到。接着我便回到房间里,上床睡觉,并希望睡几个小时就能醒过来。
可是,第二天,我回到客厅里时,已经是早上8点钟了。我看了看压力表,就知道鹦鹉螺号是浮在水面上。另外,我还听到平台上有脚步声。可是船并没有摇晃,而是一动不动。不知道海面波浪的情况如何。
嵌板是开着的,我走上嵌板边。但是,眼前我看到的不是我期待的大白天,而是一团漆黑。我们在哪里呢?我没弄错吧?还是晚上吗?不!没有一颗星星在闪烁,再说夜晚也不会这么漆黑。
我干愣着,这时,一个声音对我说:
“是您,教授先生?”
“啊!尼莫船长,”我回答,“我们在哪里呢?”
“在地下,教授先生。”
“地下!”我叫道,“可鹦鹉螺号是浮着的?”
“它是一直浮着的。”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
“等几分钟,我们的探照灯就会亮,如果您愿意弄清楚情况的话,您会满意的。”
我走上平台,等待着。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甚至看不到尼莫船长。然而,在正对着我头上的天顶,我捕捉到了一丝摇曳的光亮,一种射进圆洞里的朦胧的光线。这时,探照灯突然亮了。它强烈的光线使这丝模糊的光亮黯然失色。
强烈的灯光使我感到有些目眩,我闭了一会儿眼睛,才睁眼来看。鹦鹉螺号是停着。它靠在一处像码头一样的陡岸边。它目前所处的这个海,是一个被高墙包围着的,直径2海里,周长6海里的湖泊。它的水平面——按压力表所示——是应该和外面海水的水平面一致的,因为这湖和海洋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条通道。这些高墙,下部倾斜,上面呈圆拱形,像一只倒扣的大漏斗,高约500至600米。顶上开着一个圆孔,我刚才看到的那缕光线就是从这个孔透进来的,那显然是白天的日光。
在更仔细地观察这个大岩洞的内部结构之前,和在我自己考虑这是一个天然的洞穴还是一个人工的洞穴之前,我朝尼莫船长走去。
“我们在哪里?”我说。
“就在一座熄灭的火山中,”船长回答说,“一座由于地震而海水入侵的火山中。教授先生,您睡觉时,鹦鹉螺号就通过海平面10米下的一条天然水道进入了这个咸水湖。这里是船籍港,一个安全、舒适、神秘、可以避开任何风暴的港口!您能在你们的大陆海岸或海岛海岸边找到一处能与这个安全的避风港媲美,并能防御飓风袭击的海港吗?”
“确实不能,”我回答说,“在这里您是安全的,尼莫船长。谁会到这火山中来侵犯您呢?但是在它的顶端,我不是看到了一处开口吗?”
“是的,那是火山的喷火口。以前,这是一个充满熔岩、蒸气和火焰的喷火口,而现在,它成了为我们提供新鲜空气的通口。”
“那这座火山是怎么样的?”我问。
“它是遍布在海洋里的一个小岛。对于船只,它只是块暗礁;而对于我们,则是个大洞穴。我是无意中发现了它的,而且就这样,它无意中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
“但人们不能从这座火山的喷火口下来吗?”
“就像我不能从这里上去一样。这座山内下部到100英尺高度是可以通行的,但超过100英尺,山壁就很陡峭,这样的陡坡是走不上去的。”
“我发现,船长,大自然总是待您不薄。您在这个湖上很安全,除了您,没有人会进入这个水域,但这个避风港有什么好处呢?鹦鹉螺号是不需要港口的。”
“不,教授先生,它需要电力来发动,需要原料来发电,需要钠来补充原料,需要煤来产生钠,需要煤矿来开采煤炭。而正是这里,海水淹没了一整片在地质时期就埋入泥沙中的森林,现在这片森林已经矿化,变成煤矿。所以对于我来说,这里是一个取之不竭的矿藏。”
“那您的人在这里就成了矿工了?”
“正是。这里的矿就像纽卡斯煤矿一样在海里延伸着。在这里,我的人穿着潜水服,手拿镐铲就可以去采煤,我甚至用不着去找陆地上的煤矿。而且当我燃烧这些燃烧物来制造钠时,烟雾就会从这个火山口飘出去,这使这座火山表面看起来还处于活动期呢。”
“我们可以看看您的同伴干活吗?”
“不,至少这次不行。我想赶着继续我们的海底旅行,因此,这次我只是把我储存的钠拿出来用就行了。装船的时间也只是一天,然后我们就继续赶路。如果您想在这个洞里走走,在咸水湖中兜一圈,那就好好儿地利用这一天吧,阿罗纳克斯先生。”
我感谢了船长,就去找我那两位还没离开他们船舱的伙伴。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的位置,而是请他们跟我走。我们登上了平台。对任何事都不感到惊奇的龚赛伊,认为在水下睡觉后,醒来却在山底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尼德·兰则只顾着搜寻这个洞穴是否有某个出口。
吃过早饭后,约10点钟,我们下船到了岸上。
“瞧我们又一次到了陆地上了。”龚赛伊说。
“我不能把这个叫作‘陆地’,”加拿大人回答说,“再说,我们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
在山壁脚下和湖水之间,延伸着一片沙堤,最宽处有500英尺。沿着沙岸,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绕着湖走一圈。但陡壁的下部地势起伏不平,横卧着一些堆放得生动别致的火山岩和大浮石。这些风化了的石堆,在地下热源的作用下,镀上了一层光滑的珐琅质,在探照灯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岸上的云母尖粒,被我们的脚步扬起,一点点像火星似的飞扬。离湖边的冲积地越远,地面的起伏就越明显。我们不一会儿就到了长长的曲折的斜壁边,那是一处真正的斜坡,人可以沿着它慢慢往上爬,但在这些没有用水泥粘砌起来的砾石之间行走,还需谨慎为好,而且在这些长石和石英晶体形成的玻璃质岩石上走,脚是会打滑的。
各个方面都证实了这个大洞穴是一个天然的火山。我向我的同伴们指出了这一点。
“你们试着想象一下,”我问他们,“当这个漏斗装满熔浆,而且当这种炽热的液体上升到山口,像熔铁在熔炉里一样时,这个漏斗会怎么样呢?”
“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是怎么样的情形,”龚赛伊回答说,“可是先生能否告诉我,那位伟大的铸炼者为什么半途而废呢?而他又怎么把这个熔炉换成了一湖平静的水呢?”
“龚赛伊,这很可能是因为海面下的某种变动而形成了鹦鹉螺号通过的那个通口。大西洋的水便由这个通口涌进了山的内部。于是水和火这两种东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以海王的胜利告终。但自那以后,经过了不知多少个世纪,沉睡的火山就变成了平静的岩洞。”
“太妙了,”尼德·兰说,“我赞同这种解释。但从有利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真感到遗憾,阿罗纳克斯先生说到的那条通道不是在海平面上。”
“可是,尼德朋友,如果这条通道不是在水下,那鹦鹉螺号就进不来了。”
“我也补充一句,兰师傅,如果这条通道不是在水下,那海水也就不能涌进山里,这座火山还是火山。那您的遗憾也就是多余的了。”
我们继续向上攀。斜坡越来越陡,越来越窄。我们把腹部贴在斜壁上向前爬。斜坡上有时切进去了一些深深的山洞,要跃过去才行。半路还会杀出一些凸起的大石块,要绕过去才行。但是,有龚赛伊的敏捷和加拿大人的帮助,所有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
在约30米的高度上,地表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变得更难攀行了。地面先是砾岩和粗面岩,接着是黑色的玄武岩,后者一块块摊着,上面布满气泡;前者形成一些有规则的菱形,排列得像一根根支撑着这大穹窿的拱底石的石柱,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此外,在这些玄武岩中间,蜿蜒长垂着一些冷却了的熔岩,嵌着一些沥青线纹,而且到处铺着一层厚厚的硫黄地毯。一道更强烈的光线从上面的火山口射进来,炫目的光亮笼罩着所有这些将永远埋藏在这熄灭的山中的火山喷出物。
然而,不久,我们攀到了约250英尺的高度处,就遇到一处无法穿越的障碍,只好停步不前了。在此处,穹隆的内部向外突出,要向上攀就得兜圈子走。在这最后的一个平面上,植物开始和矿物争相斗艳。有些小树,甚至一些大树,从石峭的坑洼处破土而出。我辨认出几株流着腐蚀性浆汁的大戟树。一些名不副实的向阳草——因为阳光根本照不到它们——凄凄地垂下一串串褪色的、香味散尽的花朵。一些菊花羞怯地星星点点地点缀在忧郁的病恹恹的长叶芦荟脚下。但是,在下垂的熔岩中间,我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紫罗兰,还微微散发出芳香,我不得不承认,我满怀快乐地去感受它的香味。
因为花香,是花的灵魂,而海中之花,那些艳丽的水草,是没有灵魂的!
我们来到一株茁壮的龙血树下,它粗壮的树根力排丛石,使树拔地而出。这时,尼德·兰喊道:
“啊!先生,蜂窠!”
“蜂窠!”我应道,做了一个完全不相信的手势。
“是的!蜂窠,”加拿大人重复说,“好些蜜蜂在周围嗡嗡飞着呢。”
我走到近前,眼见为实。那龙血树树干上的一个洞口,果真有着成千上万只辛勤的昆虫。这种蜜蜂在整个加那利群岛很常见,它们产的蜂蜜在那里备受推崇。
很自然,加拿大人就想到要储存一些蜂蜜。如果我反对的话,那就似乎不近人情了。于是,加拿大人用打火机点燃了一些夹杂着硫黄的干草,开始熏蜜蜂。蜜蜂的嗡嗡声慢慢地停息了,蜂窠被剖开了,里面有好几公斤香喷喷的蜂蜜哪。尼德·兰把蜂蜜兜进了他的背囊里。
“我把这蜂蜜和面包树的粉和在一起,”他对我们说,“就能给你们做出一道美味的糕点。”
“把蜜饯面包搁一边吧,”我说,“继续我们的有趣之旅吧。”在沿途小径的一些拐弯处,我们看到了整个湖的面貌。探照灯照亮了整个平静的湖面,没一丝涟漪,没一点儿波浪。鹦鹉螺号也一动不动。在船的平台上和堤岸上,船上的人员正在忙碌着,光亮的空气中,清晰地映出他们黑色的身影。
我们绕过了支撑着穹隆的前几堵岩石中的最高峰。这时,我发现蜜蜂并不是这个火山里唯一的动物。还有一些猛禽从它们高筑在岩石尖的巢里飞出来,在黑暗中四处翱翔、盘旋。那是一些腹部白色的鹰和一些叫声尖利的隼。在斜坡上,还有一些漂亮的胖大鸨迈着长得像高跷般的脚,快速地奔走着。我可以想象得出,一看到这些美味的野味,加拿大人又嘴馋了。他真后悔手里没有一把枪。他试图用石块代替铅弹,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他终于打伤了一只美丽的大鸨。说他不惜冒20次生命危险来弄到这只鸟,是一点儿也不言过其实的,而且他干得漂亮极了,这只动物终于被他兜进他的包里,和那些蜂蜜放在一起。
此处的岩脊变得无法通行,我们该回到岸边了。在我们上面,火山口像一个宽大的井口一样张开着。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外面的天空。我还看到了一片片被西风吹得零乱的云块,云雾的碎片一直拖到山顶上。可以肯定,这些云彩并不高,因为这座山高出海平面也至多是800英尺。
在加拿大人打完鸟的半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内湖岸上。这里的植物以织成大地毯的海鸡冠草为主,这种草又名钻石草、穿石草和海茴香,泡醋很好吃。龚赛伊采了好几把。至于动物,有数不胜数的甲壳动物,像螯虾、大螃蟹、手臂蟹、苗虾、盲蛛、加拉蟹,和数量惊人的蚝蛤、磁贝、岩贝和帽贝。
这个地方还有一处奇妙的洞穴,我和我的同伴兴致勃勃地躺在洞中的细沙上。火光照亮了熠熠发光的珐琅质洞壁,洞壁上满是云母石粉屑。尼德·兰拍打着洞壁,想估出它的厚度。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话题又转到他那不死的逃走计划上,我想在不操之过急的情况下,可以给他希望:就是尼莫船长往南行驶只是想补充他船上的钠燃料。我希望尼莫船长现在会返回欧洲或美洲海岸,这样或许可以使加拿大人更有把握地重施他那流产了的逃跑计划。
我们在这个绮丽的洞里躺了一个小时。开始谈话还很活跃,但渐渐地便没了生气。我们都感到昏昏欲睡。我想没什么理由要抵制睡眠,便让自己进入沉沉的睡梦中。我梦见了——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梦的——,我的身躯缩成一只植物性的普通软体动物,这个洞穴变成了我的两片介壳……
突然,我被龚赛伊的叫声惊醒了。
“当心!当心!”这位老实的小伙子喊着。
“什么事?”我半坐起身问。
“水漫上来了!”
我跃起来。海水像洪水般向我们的藏身之所涌来,显然,既然我们不是软体动物,我们就应该逃走。
几分钟之后,我们安全地逃到了岩洞顶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龚赛伊问,“又是什么新现象?”
“哦不!我的朋友,”我回答,“这是海潮,只是海潮把我们吓了一跳,像华尔特·司各特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海洋外面涨水,由于自然的平衡规律,湖水也跟着涨起来。我们半身都湿透了,回鹦鹉螺号换衣服吧。”45分钟后,我们完成了环湖旅行回到船上。这时船上的人员也完成了装钠工作,鹦鹉螺号船一会儿就要出发了。
然而,尼莫船长并没有发出任何命令。难道他想等天黑,再从他的海底通道悄悄地出去?有这可能。
不管怎样,第二天鹦鹉螺号就离开了它的港湾,它又会远离陆地,在大西洋的水波下几米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