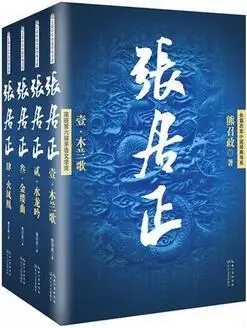第十二章 抹香鲸和长须鲸
3月13日晚上到14日,鹦鹉螺号继续朝南行驶。我想,到了合恩角的高纬处,它会掉转船头向西走,返回太平洋,完成它的周游世界之旅。可它一点儿也没这么做,而是继续向南极海开去。它究竟要去哪儿呢?难道去南极吗?真是发疯了。我开始相信,船长的鲁莽行动足以证明尼德·兰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好些时候,加拿大人不再跟我谈起他的逃跑计划。他变得寡言少语,几乎是沉默了。我明白这种无限期的囚禁对他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压抑。当他碰到船长时,他的眼睛里燃着阴沉的怒火,我能感觉到他满腔的怒火,我总是担心他暴躁的本性会使他走极端。
那天,3月14日,他和龚赛伊到我的房间里找我,我询问他们来拜访我的原因。
“来向您提个简单的问题,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我说。
“请说吧,尼德。”
“您认为鹦鹉螺号上会有多少人?”
“我说不来,我的朋友。”
“我觉得,”尼德·兰说,“驾驶这船不需要很多船员。”
“确实如此,”我回答,“按目前的情况,顶多十来个人就够了。”
“那好!”加拿大人说,“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人?”
“为什么?”我反问道。
我盯着尼德·兰看,我不难猜出他的意图。
“因为,”我说,“如果按我的猜测,根据我对船长生活的了解,鹦鹉螺号不仅仅是一条船,应该是他们那些人——像他们的船长一样与世隔绝的人——的一个避难所。”
“可能是吧,”龚赛伊说,“可鹦鹉螺号最终只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先生能估计一下它的最大容量吗?”
“怎么算,龚赛伊?”
“按算术推算,按先生所知的这艘船的容积,推算出它能容纳的空气,另一方面知道每个人呼吸所消耗的空气量,将这些结果和鹦鹉螺号每 24小时就要浮出水面换气这一情况相比……”龚赛伊话没说完,但我很清楚他想说明什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这种推算很容易,但只能得出一个不确定的数据。”
“那没关系,”尼德·兰坚持着说。
“是这样计算的,”我回答,“每人每小时消耗100升空气中的氧,那24 小时就消耗掉 2400 升空气中所含的氧。因此,还必须知道鹦鹉螺号含有多少倍2400升空气。”
“正是。”龚赛伊说。
“不过,”我回答,“假设鹦鹉螺号的容量是1500吨,1吨容积是1000升,鹦鹉螺号含有 150 万升空气,除以 2400 升……”
我用铅笔快速地算出来:“得到625,鹦鹉螺号所含的空气完全可供625人在24小时内呼吸。”
“625人!”尼德重复说。
“可你们要知道,”我补充说,“这么多的乘客加上水手或管理人员,我们还没够这个数的十分之一呢。”
“这对于三个人来说还是太多了!”龚赛伊喃喃地说。
“因此,我可怜的尼德,我只能建议您忍耐一下。”
“不仅仅是忍耐,是顺从。”龚赛伊回答说。龚赛伊用词真是恰如其分。
“总之,”他接着说,“尼莫船长总不会一直向南走的,他必须停下来,哪怕是到了大浮冰前面,他也总得开回开化的海域里的!那么,我们总会有时间实施尼德·兰的计划的。”
加拿大人听了摇摇头,他用手摸摸额头,然后一言不发地退出去。
“先生,我冒昧说说我对他的看法吧。”龚赛伊于是对我说,“可怜的尼德·兰老想着一切他不能有的东西。他回想起他过去的一切生活,就对我们被禁止做一切事情感到遗憾。以前的回忆老是纠缠着他,他感到很难过。我们应该理解他。因为在这里有什么可做呢?没有。他又不像先生那样是个学者,所以不能跟我们一样对海里所有奇妙的东西有相同的品味。即使为了能走进他家乡的一家小酒馆里,他也宁愿冒一切危险!”
很显然,船上单调的生活,对于习惯过自由和活跃生活的加拿大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事情太少了。然而,有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重温了他作为捕鲸手的那段美好日子。
那天早上11点左右,在海面上,鹦鹉螺号撞到了一群鲸鱼中间去。我对遇到这些动物并不觉得惊奇,因为我知道它们受到了大肆猎杀,都躲到了高纬度的海域中来。
鲸鱼在世界航海中的作用和它对地理发现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正是鲸鱼,先后使巴斯克人、阿斯第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大胆地和海洋的危险做斗争,并引导他们从陆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鲸鱼喜欢在南极和北极海中游弋。一些古老的传说甚至告诉人们,这些鲸类动物曾把渔人引到距北极只有7里的地方。如果说这种传说有误的话,那总有一天它会成为真实的,因为当人们到北极或南极地区捕鲸时,会有可能就这样到了那不为人知的地球极点的。
当时我们正坐在平台上,海面上风平浪静,而在这一纬度上,十月份正值美丽的秋日。这时加拿大人——对此他是不会弄错的——指出在东边海平线上有一条鲸鱼。我们仔细一看,在距鹦鹉螺号5海里处,有一条鲸鱼的灰黑色脊背在水波中时隐时现。
“啊!”尼德·兰喊道,“如果我是在一条捕鲸船上,这次相遇会让我很高兴的!这是一只大家伙!瞧它的鼻孔喷水汽时多有劲儿!真见鬼!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束缚在这块钢板上呢!”
“什么!尼德,”我回答,“难道您还没打消您打鱼的旧念头?”
“先生,一个捕鲸手能忘记他的老本行吗?他会永远厌倦这种捕猎所带来的快感吗?”
“您还从没在这一带打过鱼,尼德?”
“从来没有,先生,只是在北极海打过,在白令海峡和戴维斯海峡也打过。”
“这么说,南极鲸鱼对您来说还是陌生的。至今,您捕捉到的只是那些一般的鲸鱼,它们不敢贸然穿过赤道温热的水域。”
“啊!教授先生,您这是说什么?”加拿大人用相当怀疑的口气反问道。
“我说的是事实。”
“啊!我跟您说,两年半前,在北纬65°,我就在格陵兰岛附近捕捉到一条肋部还插着鱼叉的鲸鱼,它是被白令海峡的一条捕鲸船叉到的。那么现在我问您,这动物在美洲西岸被击中,如果它没有绕过合恩角或好望角,穿过赤道,那它怎么会在东岸被杀死?”
“我和尼德的想法一样,”龚赛伊说,“我等待着先生的答案。”
“我的朋友们,我会做出回答的。根据鲸鱼的种类,它们是有区域性的,在某一海区生活,它们就不会离开。如果有一条鲸鱼从白令海峡游到戴维斯海峡,很简单,是因为在美洲海岸或亚洲海岸存在着一条从这个海通到那个海的通道。”
“我们要信您吗?”加拿大人眯着一只眼睛问。
“应该相信先生。”龚赛伊说。
“那么,”加拿大人回答,“既然我从没在这一海域捕鱼,我也就不熟悉在这里出没的鲸鱼了。”
“这我对您说过了,尼德。”
“那就更有理由去熟悉它们了。”龚赛伊说道。
“瞧!瞧!”加拿大人声调激动地喊道,“它游近了!它朝我们游来!它在嘲弄我!它知道拿它没办法!”
尼德跺着脚。他的手颤抖地挥动着一根想象中的鱼叉。
“这些鲸类动物,”他问,“和北极海的一样大吗?”
“差不多,尼德。”
“我见过的大鲸,先生,长竟有100英尺喔!我甚至得说,在阿留申群岛的胡拉莫克岛和安加里克岛一带的鲸鱼,有的竟超过150英尺长。”
“我觉得这太夸张了,”我回答说,“这些动物不过是鲸科动物,有脊鳍,诸如抹香鲸,总的来说,它们比一般的鲸鱼小。”
“啊!”加拿大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海面,喊道,“它来了,它来到鹦鹉螺号附近了。”
接着,他又说:
“您说,抹香鲸就像小动物一样!可我能说出一些巨大的抹香鲸,这是些聪明的鲸类动物。有人说,有些抹香鲸身上长满海藻和墨角藻,人们还把它们当成是小岛呢。人们在它上面扎寨,在上面安居,生火……”
“还在上面建房子。”龚赛伊说。
“是这样的,俏皮鬼,”尼德·兰回答说,“然后,有一天,这动物潜入了海底,把所有的居民都带进了深渊。”
“这就像水手辛巴达历险记里说的一样。”我笑着说。
“啊!兰师傅,看来您喜欢这类离奇的故事!您的抹香鲸是怎样的抹香鲸啊!我希望您不要相信这些!”
“博物学家先生,”加拿大人严肃地说,“应该相信关于鲸的一切!——您看,它会走!它会藏起来!——有人还断言这些动物能在15天内绕地球一周呢。”
“对此我不能置否。”
“可是,您可能不知道,创世之初,鲸鱼游得比现在还快呢。”
“啊!真的,尼德!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它们的尾巴是横着游动的,像鱼一样,也就是说,它的尾巴是扁直的,左右、右左地拍水。但造物主发现它游得太快了,便剪掉了它们的尾巴。从那时起,它们只好上下拍水,这就影响了它们的速度。”“好,尼德,”我做了一个和加拿大人一样的表情,说,“我们要信您吗?”
“不要太信,”加拿大人回答说,“如果我对你们说,存在一些长 300英尺,重10万磅的鲸鱼,就更不要信。”
“确实,这太离谱了,”我说,“不过应该承认,某些鲸类动物还是发育得很可观的,因为有人说,它们竟能提供120吨油脂。”
“这个,我见过。”加拿大人说。
“我乐于接受这个观点,尼德,因为我相信有些鲸的重量相当于100头大象。看看这头巨大的动物直冲过来能产生的后果吧!”
“它们真能把一些船撞沉吗?”龚赛伊问。
“一些船,我不相信,”我回答,“可是有人说,1820年,正是在南部海面,一头鲸直冲向‘爱塞斯号’船,使这艘船以每秒4米的速度向后退。(海水涌入船的后部,‘爱塞斯号’顷刻间沉没。”)
尼德用一种嘲讽的神态看着我,他说:
“至于我,我受过鲸鱼尾巴的一次袭击——不用说,就在我的小艇里。我和我的同伴被抛到了6米高,但我们遇到的鲸鱼走在先生的鲸鱼身旁,只不过是一条幼鲸而已。”
“这些动物寿命长吗?”龚赛伊问。
“一千年,”加拿大人不假思索地说。
“您怎么知道,尼德?”
“因为人们都这么说。”
“为什么人们都这么说呢?”
“因为人们知道。”
“不,尼德,人们不知道,人们只是猜测,他们猜测的依据是:400 年前,当渔夫第一次捕捉鲸鱼时,这些动物的身形比他们现在捕捉到的鲸鱼的身形要长。于是人们便相当合乎逻辑地猜想,现在鲸鱼变劣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完全的发育。正是如此,布封说,这些鲸类动物能够,甚至应该活上1000年。你们明白吗?”
尼德·兰没听明白。那条鲸鱼不断向我们靠近,他也不想再听下去,只管眼睛发直地盯着它。
“啊!”他喊道,“不只是一条,是10条、20条,整整一群呢!可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在这里手脚都被束缚住!”
“但,尼德,”龚赛伊说,“为什么不问问尼莫船长可否捕捉呢?”
龚赛伊话还没说完,尼德·兰就从嵌板跑下去找船长了。过了一阵子,两个人来到了平台上。
尼莫船长观察了一下在距鹦鹉螺号1海里处嬉耍的鲸鱼群。
“那是南极长须鲸,”他说,“它们可以使一整队捕鲸船发大财。”
“那好!先生,”加拿大人问,“即便不是为了不忘记我的捕鲸手老本行,我还是不能捕杀它们吗?”
“这有什么好处呢?”尼莫船长回答说,“捕杀只会导致毁灭!我们船上要鲸鱼油做什么呀?”
“可是,先生,”加拿大人又说,“在红海,您允许过我们追打一头海马!”
“那是因为那时能给我们的船组提供鲜肉。而在这里,是为了捕杀而捕杀。我很清楚这是人类的一种特权,但我不允许这种残害生命的消遣方式。消灭像一般的鲸鱼一样无辜善良的南极长须鲸,您的同行,兰师傅,他们的行为是要受谴责的。他们就是这样使整个巴芬湾的长须鲸绝迹,而且他们将毁掉一种有用的物种。让这些不幸的鲸类动物平平静静地生活吧。就是您不去搅和,它们也已经有够多的天敌了,像抹香鲸、箭鱼、锯鲛等。”
不难想象出,在上这堂道德课时,加拿大人脸上的表情如何。跟一个捕鲸手讲这样的道理,简直是白费口舌。尼德·兰看着尼莫船长,显然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不过,船长的话是有道理的。捕鲸人野蛮无节制的杀戮总有一天会使海洋中的最后一条长须鲸都消失了。
尼德·兰把手插在口袋里,背朝着我们,用口哨吹起了美国国歌。
这时,尼莫船长观察了那一群鲸,对我说:
“我有理由这么说,除了人类,这类鲸鱼还有相当多别的天敌。不一会儿,这群长须鲸就要碰到强敌了。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有没有发现,在下风8海里处,有一些灰黑色的点在动?”
“有,船长。”我回答说。
“那是抹香鲸,一种可怕的动物。我有几次遇过它们,一群竟有二三百条!至于这些抹香鲸,是一种残暴有害的动物,我们有理由去消灭它们。”
听到这最后几句话,加拿大人迅速转过身来。
“那好!船长,”我说,“从鲸鱼本身的利益出发,时间还来得及……”
“用不着去冒险,教授先生。鹦鹉螺号足以去驱散这些抹香鲸。它装有钢铁冲角,我想,可与兰师傅的鱼叉相媲美。”
加拿大人很自然地耸耸肩膀, 用船的冲角去袭击鲸鱼! 以前有谁听说过?
“等着瞧,阿罗纳克斯先生,”尼莫船长说,“我们要让您见识一下一次您还没见过的追捕。对于这类凶残的鲸类,丝毫用不着怜悯。它们只不过是嘴和牙而已!”
嘴和牙! 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词语来形容这种体长超过25米的大脑袋动物了。这种鲸类的大脑袋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身体。长须鲸的上颚只有一缕鲸须,而抹香鲸比长须鲸武装得更好,它们的上颚镶着25颗20厘米高、圆筒状而尖顶圆锥形的大牙,每颗足有2磅重。就在那颗巨大的脑袋上部,由软骨隔开的部位,装着3至4公斤被称为“鲸鱼白”的珍贵鲸油。抹香鲸是一种丑陋的动物,按弗雷多尔的观点,他认为说它是蝌蚪类比说它是鱼类更为恰当。
另外抹香鲸的形体结构有缺陷,就是说它的骨骼左上部有缺陷,只能用右眼看东西。可是,这群巨物不断地向我们靠近。它们已经发现了长须鲸并做好了攻击的准备。我们事先就会断定,胜利是属于抹香鲸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更善于攻击它们无辜的敌手,而且因为它们能够更长时间地待在水中,不用浮出水面呼吸。
去援救那些长须鲸的时刻到了。鹦鹉螺号沉入水里,我、龚赛伊和尼德坐在客厅的玻璃前。尼莫船长回到领航员的身旁,以便亲自操作他那台毁灭性机器。不一会儿,我就感觉到机轮的拍动速度在加快, 鹦鹉螺号的速度也加快了。当鹦鹉螺号到达时,长须鲸和抹香鲸的战斗早已经开始了。 鹦鹉螺号从抹香鲸群中间冲过去。一开始,那些抹香鲸看到有新来的怪物加入战斗,并没显得很在意。但不一会儿,它们就不得不对鹦鹉螺号的进攻加以防备。
这是一场多么激烈的战斗啊!就连尼德·兰不久也狂热起来,拍手称好。鹦鹉螺号恰如船长手中一支妙不可言的鱼叉。它投向那些肉堆中,把它们一块一块戳穿,它所过之处,只留下两段躜动的动物躯体。那些打在它船侧的猛击,它没有感觉到。它袭击抹香鲸时产生的撞击,它也没有感觉到。歼灭了一头抹香鲸,它又冲向另一头。为了不错过目标,它瞄得很准,在舵手的操纵下,它前进后退,当抹香鲸潜入深水层中时,它也潜进去,当抹香鲸浮出水面时,它也跟着上来,给它们迎头一击或侧身一击,把它们斩断或撕碎,并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速度,用它那可畏的冲角刺穿了它们。好一场厮杀!水面上多热闹啊!这些受惊的动物发出多么尖利的呼啸声和特殊的吼叫声!在平时何等平静的水层中,它们的尾巴搅动出真正的波涛。
这场史诗般的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那些大头怪物无一幸免。好几次,10或12头纠集起来的抹香鲸想抱成一团把鹦鹉螺号压碎。透过玻璃窗,我们还看到了它们那布满牙齿的大嘴和巨大的眼睛。再也不能自持的尼德·兰,威吓着它们,诅咒着它们。我们感觉到它们像狗在矮树丛下看小猪一样,纠缠住船体。但鹦鹉螺号无视它们巨大的体重,也无视它们强大的压力,它加大马力,把它们带过来,拖过去,或者把它们拉到海水上层。
最后,这群抹香鲸一哄而散,水面又恢复了平静。我感觉到我们又回到了水面上。嵌板打开了,我们急忙跑到平台上。
海面上布满残缺的尸体,就是一次强大的爆炸也不可能有如此的爆炸力,把这群巨物如此炸开、撕碎、扯烂。我们的船浮在那堆背部浅蓝、腹部灰黑、长着大疙瘩的庞大尸体中间。剩下几条受惊的抹香鲸向天边逃窜。好几海里内的水都被染红了,鹦鹉螺号浮在血海中。
尼莫船长上来和我们会合。
“怎么样,兰师傅?”他说。
“太好了!先生,”加拿大人回答说,他渐渐从狂热中平息下来了, “确实是一幅可怕的场面。但我不是肉店老板,我是捕鲸手,而且这里也不开肉店。”
“这是对有害动物的屠杀,”船长回答说,“再说鹦鹉螺号也不是一把肉刀。”
“我宁可要我的鱼叉。”加拿大人反诘道。
“人各善其器。”船长直盯着尼德·兰回答说。
我真担心尼德·兰会克制不住做出过激行为,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但当他看到鹦鹉螺号此时向一条鲸鱼靠近时,他的怒气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是一只没有逃脱出抹香鲸的牙齿的动物。我认出是一条南极长须鲸,它头部扁平,全身黑色。从解剖学角度看,它和一般的鲸鱼以及北卡彼岛的鲸鱼的区别在于,它颈部的七根脊骨是接合的,并且比它的同类多出了两根肋骨。这条不幸的鲸鱼侧浮在水上,腹部上满是伤洞,它已经死了。在它残缺的鳍部一头,还浮着一条没能从屠杀中获救的小鲸。它的嘴巴张开着,水从鲸须中潺潺流出。
尼莫船长驾驶着鹦鹉螺号驶向那动物的尸体旁。他手下的两个人跃到了长须鲸的身侧上,我无不惊奇地看着他们把它乳房里饱含的奶水都挤出来,足足挤了2至3吨。
船长递给我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奶。我不得不向他说明我对这类饮品反胃。但他一再向我保证说这种奶很好喝,它和牛奶没有任何两样。
我把它喝了后,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这便成了对我们有益的储藏品,因为,把这种奶做成咸奶油或奶酪,可以为我们的日常饮食增加一道美味的食品。
但自那天起,我忧心忡忡地注意到,尼德·兰对尼莫船长的态度越来越差,我决定密切留意加拿大人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