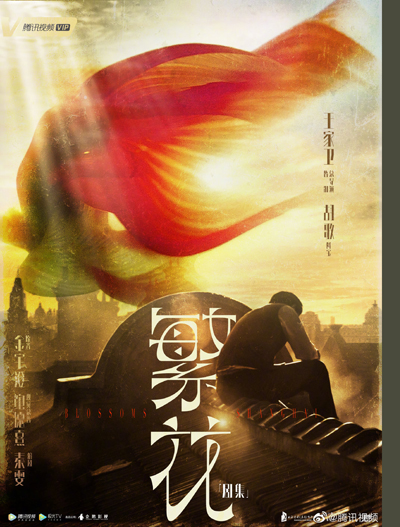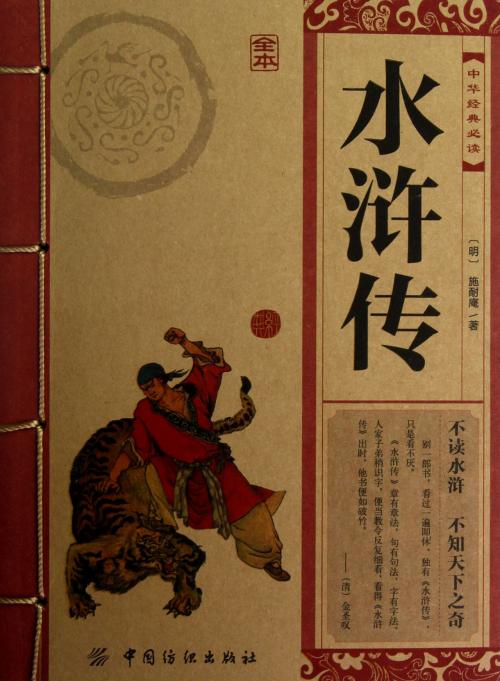第十一章 萨尔加斯海
鹦鹉螺号的航向始终没有变。那么所有返回欧洲的希望只能暂时放弃了。尼莫船长一直朝南行驶。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我想象不出来。
那一天,鹦鹉螺号通过了大西洋一片奇特的海域。众所周知,在大西洋存在着一股名叫“海湾”的大暖流。这股暖流从佛罗里达湾出来,直逼斯匹司堡。但在流进墨西哥湾之前,这股暖流在北纬 44°左右分为两股;主流向挪威和爱尔兰海岸流去,而分流向南迂回流到阿索尔群岛;然后,受到非洲海岸的阻挡,划成一个长长的椭圆形,又流回安的列斯群岛。
然而,这支分流——与其说它像一只手臂,不如说像个项圈——的暖水圈把海洋这部分冰冷、平静、静止的水域包围起来,这个水域被称为萨尔加斯海。这是大西洋中的一个真正意义的湖,暖海流绕萨尔加斯海一周至少要用 3年。
萨尔加斯海,更确切地说,覆盖了整个沉入水中的大西洋城。某些作家甚至认为,海面上分布着的无数的水草,与这片古老的陆地的草原有关。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些产自欧洲和美洲海岸的草叶植物、海藻、墨角藻,是被“海湾”暖流带到这个水域中来的。这也是使哥伦布猜测到有一块新大陆存在的原因之一。当这位大胆的探索者的船队到达萨尔加斯海时,他的船只在这些水草中举步维艰,水手们因此谈草色变,他们整整用了三个星期才穿过这片水草。
此时,鹦鹉螺号漫游的海域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有一片真正的草原,海藻、海带和热带海葡萄织出一条精致的毛毯,那么的厚,那么的结实,船只的冲角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它撕开。因此,尼莫船长不想让他的机轮陷入这堆水草中,他让船保持在几米深的水下行驶。
“萨尔加斯”这个名字是来自于西班牙语“sargazzo”,意思是海藻。这种海藻、浮水藻或海湾藻,是这带海水中的主要藻类。按学者莫利,《地球物理地理》一书的作者的观点,为什么这些海产植物能聚集到大西洋这带平静的海域中来呢?他阐述如下:
“我认为我们能提出的解释,是来源于一种众所周知的经验。如果我们把一些软木塞碎片或其他漂浮物体的碎片放在一盆水里,并让水作周循运动,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那些分散的碎片集中到水面的中央,也就是说,集中到运动最小的一点上。在我们留意的这个现象中,水盆,代表大西洋,‘海湾’暖湾,就是作周循运动的水,而萨尔加斯海,就是漂浮物体的集中点。”
我赞同莫利的观点,而且我能在这片船只很少行驶进去的特殊水域中观察到这一现象。在我们上面,漂浮着各处漂来的物体,掺杂在那些淡褐色的海草中,有安第斯山脉或落基山脉上的树干,被亚马孙河或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冲到这里来;还有无数的遇难船只的漂流物,残存的龙骨或船身,捅破了的船板,上面坠着沉甸甸的贝壳和茗荷贝,重得浮不出水面。总有一天,时间也会证明莫利的另一个观点,就是这样几个世纪累积下来的物质,在海水的作用下,将发生矿化,从而形成了取之不竭的煤矿。这是一份珍贵的储藏,是卓有远见的大自然为人类耗尽陆地上的矿藏时准备的。
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海草和墨角藻丝中,我注意到了一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海鸡冠,以及拖着长长的触须的海葵和绿色、红色或蓝色的水母,特别是提过的浅蓝色的伞膜上镶着紫边的大型根足水母。
2月22日一整天,我们就泡在萨尔加斯海里。那些爱吃海草和甲壳动物的鱼类,在这里可是丰衣足食的。第二天,海洋恢复了它往常的面貌。
从这以后,2月23日到3月12日,整整19天,鹦鹉螺号都待在大西洋海域中,它以每24小时100里的恒速载着我们前进。尼莫船长显然想完成他的海底计划,我不怀疑他绕过合恩角后,还想返回太平洋南端的海域里。
因此,尼德·兰有理由担忧。在这片没有岛屿的浩瀚大海里,根本不能有逃跑的打算。反抗尼莫船长的意志更是行不通。唯一的做法就是屈服。但是,人们不能指望靠武力或狡诈来解决的事,我希望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我想一旦旅行结束,如果我们以我们的人格担保,发誓永不泄露他存在的秘密,尼莫船长难道还不同意让我们自由吗?但这个微妙的问题还需和尼莫船长商讨。可是,如果我去要求自由,会受他的欢迎吗?尼莫船长本人,当初不就是正式宣布, 他生活的秘密要求把我们永远囚禁在鹦鹉螺号船上吗?这四个月来,他不就是把我的沉默当作对这种情况的默认吗?如果以后出现了有利于我们逃跑的良机,我现在和他提起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他的疑心,而致使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呢?我反复掂量着,思考着所有这些理由。我和龚赛伊商量,他心里一点儿也不比我好受。总之,尽管我不容易丧失勇气,但我明白,再见到我的同胞的机会正日益减小,特别是在尼莫船长冒失地向大西洋南部奔走的这个时候!
就在我上面提到的19天内,我们的旅程中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我几乎见不到船长。他在工作。在图书室里,我时常看到他摊在那里的书籍,特别是自然历史书。我的海底著作,他翻阅过了,空白处注满了他的批注,其中有些看法与我的理论和体系背道而驰。但船长仅仅是这样帮助我的工作,他很少和我讨论。有时,只是在夜晚,在最寂静的黑暗中,当鹦鹉螺号在荒无人烟的海洋中沉睡时,我才听到他的管风琴发出的忧郁的琴声,他满怀情感地弹奏着。
在这段旅行中,我们整天在水面上航行。大海好像被遗弃了一样,偶尔才见到几只印度群岛的船,朝着好望角开去。有一天,我们遭到了一条捕鲸船的追踪,显然,他们把我们当作某一种高价值的巨鲸。但尼莫船长不想让这些正直的人们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让船潜入水底,结束了这次追踪。这一意外事件激起了尼德·兰极大的兴趣。我想我是不会估计错,加拿大人看到我们这条钢板鲸鱼没有被那些渔人的鱼叉叉死,一定很遗憾。在这段时期,我和龚赛伊观察到的鱼类,和我们在别的纬度研究过的没多大差别。主要有几种可怕的软骨属鱼类品种,分为3个亚属,不下32种。其中主要是条纹角鲨,长 5 米,头扁而且比身体还宽,圆形尾鳍,脊上有 7条平行的纵向黑纹;其次是炭灰色的珠形角鲨,有7个鳃孔,在身体稍微正中有一个脊鳍。
海面上也游过一些大海狗,一种贪食无厌的鱼类。我们有理由不相信渔夫们的故事,可他们讲道,他们在一条大海狗的肚子里找到了一个水牛头和一整只牛犊;在另一条大海狗的肚子里发现了两条金枪鱼和一个穿着制服的水手;在另一条的肚子里呢,有一个佩着军刀的军士;最后一条,是一匹马和它的骑士。这一些,说实话,并不可信。加上因为一直没有一条海狗落入鹦鹉螺号船上的渔网,我也就无从证实它们的贪吃性。
这些天来,一群群优雅调皮的海豚陪伴着我们。它们五六只一群,无声地猎食,像田野中的狼群一样;而且,它们一点儿也不比海狗吃得少。我相信哥本哈根的一位教授,他曾经从一只海豚的胃里取出13只鼠海豚和14头海豹。海豚这种鱼实际上是一种逆戟鲸,是已知的最大鲸类,它们身长超过24英尺。这些海豚家族有六属,我看见的那几条属逆戟属,特征是喙特别窄,而且比头长4倍。它们身长3米,上面黑色,下面粉白色,散布着一些罕见的小斑点。
在这带海区,我也记录下了棘鳍类和石首鱼科的鱼种。有些作者——与其说是博物学家,不如说是诗人——断言,这些鱼能唱出悦耳的歌声,它们和音合唱与人声合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我不能断言。但我们路经这里时,这些石首鱼并没为我们唱过任何一首小夜曲,我对此深表遗憾。最后,龚赛伊对一大群飞鱼进行了分类,以此结束考察。在这里,没有比观看海豚极准确地捕猎飞鱼更有趣的事情了。不论飞鱼飞得多远,飞成什么曲线,甚至飞到鹦鹉螺号上方,这些倒霉的飞鱼总是发现海豚们正张着大口等着它们。这些飞鱼不是海贼鱼,就是鸢形鲂,它们的嘴能发光。在夜晚,飞鱼用嘴在空气中擦出道道火光,然后就像流星一样坠入昏暗的海水中。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兼程的,一直到了3月13日。那天, 鹦鹉螺号进行了一些勘测实验,这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我们从太平洋远海出发至今,已经走了约13000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南纬45.37度,西经37.53度。这里就是莱哈尔号船上的船长邓哈姆曾做过14000米深的探测,但还没够到海底的海域。也是在这里,美国驱逐舰议会号船上的帕克大尉,做过了15140米深的探测,但还是没够到海底。
于是,尼莫船长决定让他的鹦鹉螺号潜到最深的海底去,以检验一下这些不同的探测数据。我做好记录所有的实验结果的准备。船上客厅的嵌板打开着,要到达深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海层的实验开始了。我们想,用储水器充水使船下潜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也许储水器不能使鹦鹉螺号船只的比重充分增大。再说,要浮上来,还必须排掉多余的水,水泵可能无法抵御外部强大的压力。
于是, 尼莫船长决定尝试一下船上的纵斜机板。 他把纵斜机板调到与鹦鹉螺号的吃水线成45°角的位置,再让鹦鹉螺号沿着这条对角线潜入海底。然后,推进器开到了最大速度,它的四层机叶以无法形容的强度激烈地拍打着水波。
在如此强大的推动力下, 鹦鹉螺号的船体像一根弓弦一样倏倏颤抖,匀速地潜入水中。我和尼莫船长站在客厅里,注视着飞速转动的压力表指针。鹦鹉螺号船一会儿就超过了大部分鱼类生活的那层海层。如果说鱼类中的某一些只能生活在河里或是海面上,那么,能生活在如此深的海层中的,数量则更少。至于后者,我观察到了六孔海狗,一种有六个呼吸孔的海狗;还有眼睛巨大的望远镜鱼;和靠浅红色的骨片胸甲来保护灰色的前胸鳍和黑色的后胸鳍的带刀甲板鱼;最后是生活在1200米海深,因而要顶住120个大气压的榴弹鱼。
我问尼莫船长,他是否在更深的海层中发现过鱼类。
“鱼?”他回答说,“很少。可按目前的科学水平,人们能预测到什么呢?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瞧,船长。人们知道,越往海洋的底层,植物就比动物消失得越快。人们知道,在底层中还能碰到一些动物,而见不到任何一种海产植物。人们还知道,肩挂贝、牡蛎类是生活在2000米深的海水中,而两极海的探险英雄麦克·克林多克, 曾在2500米深处抓到一只星贝。 人们甚至知道, 皇家海军猛犬号船上的船员,曾在2620英尺深,也就是1海里深水中,采到一个海星。可是,尼莫船长,您怎么能对我说人们什么都不知道呢?”
“不,教授先生,”船长回答说,“我是不能这么不客气。可是,我要问问您,怎么解释这些生命能在这么深的水中生活呢?”
“有两个理由,”我回答说,“首先,因为那些垂直运动的水流,受海水的咸度和密度不同影响,产生了一种足以维持海百合类和海星的基本生活的运动。”
“没错。”船长说。
“再者,因为,如果说氧气是生命的基础的话,我们知道溶解在海水中的氧气是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不是减少,而且底层的压力又有利于对氧气进行压缩。”
“啊!你们知道这个?”尼莫船长口气略带吃惊地回答说,“那好,教授先生,既然这是事实,人们就有理由知道,而且的确也是这样。我还要补充一句,当鱼在水面被捕获时,鱼膘里含的氮多于氧,而在深水中被捕获时,情况恰恰相反,氧多于氮。这也为您的论点提供了论据。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观察吧。”
我把目光移回压力表上。仪器指到了6000米深度。我们的下潜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鹦鹉螺号沿着纵斜机板不断地往下滑。荒凉的海水清澈透明得无比绝伦。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13000米深处,而海底仍然还没有出现的意思。
然而,在14000米处,我发现水中冒出几座黑色的尖峰。这些山峰可能属于喜马拉雅山或勃朗峰那一类高峰,而此时海底深渊的深度还是无法估计。
鹦鹉螺号还是顶着巨大的水压,往更下层潜。我感觉到嵌板螺丝衔接的地方都在颤动着,船栏铁条都弯成了弧形,舱壁在呻吟着,客厅的玻璃在水压下好像都快翘起来了。而这架牢固的机器,如果不是像船长说的那样,像一块实铁一样坚不可摧,恐怕早就被压扁了。在贴着那些直插海底的石壁下潜时,我还发现了一些贝类、蛇虫、活刺虫和某些海星种类。但过了一会儿,这些最后的动物代表都消失了。在 3里下, 鹦鹉螺号超过了海底生存的极限,它就像一只上升到可呼吸的空气层以上的气球一样。我们到达了16000米,即4里的深度,此时鹦鹉螺号的两侧承受着1600个大气压的压力,也即是它表面每平方厘米就承受着1600公斤的重量!
“这是怎样的情形啊!”我叫道,“穿过这片深无人烟的区域!瞧,船长,看看那些形状奇妙的岩石,那些无人居住的岩洞,地球的最后几个藏身之处,但生命却不可能在此存活!多么不为人知的景象,为什么我们只能把它们保存在记忆中呢?”
“您愿意把它们保存得比记忆更好吗?”尼莫船长问我。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没有比照一张这一海区的照片更简单的事了。”对于这一新建议,我还没来得及表达出我的惊奇,尼莫船长就一声吩咐,一台仪器被推到客厅里来了。通过宽敞地敞开着的嵌板望出去,受到电光照射的海水中完全光亮,没有任何阴影,而我们的人造光也没有一丝减弱的迹象。进行这种性质的操作,阳光恐怕都不如这种光线更便利。鹦鹉螺号船只的推进器转动着,而纵斜机板固定,船停住不动了。于是这台仪器对准海底的景色,几秒钟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些极清晰的底片。
我这里展示的是正片。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那些从未受到阳光照射的基岩,那些形成地球坚实的基底的底层花岗岩,那些石堆中镂空的深岩洞,还有那些无比清晰的、镶在黑暗中的轮廓,就像出自于某些佛朗德艺术家的手笔。接着,在上面,山的尽头,有一道漂亮的曲线,构成了这幅风景的背景。我无法描述这堆光滑、黝黑、光亮、不长苔藓、无一斑点、形状怪异的岩石堆,它们稳稳地站在反射着电光的沙毯上。
然而,尼莫船长结束了他的操作后,就对我说:“我们上去吧,教授先生。这种地方不宜待太久,也不能让鹦鹉螺号在这种压力下耽搁过长的时间。”
“上去吧。”我回答。
“您站稳啊!”
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船长这么叮嘱我,就摔倒在地毯上了。随着船长一声令下, 鹦鹉螺号船上的推动器合上了,纵斜机板竖起,鹦鹉螺号像空气中的气球一样,闪电般迅速向上升。它冲破水层,发出响亮的颤动声。任何东西都看不到。40分钟内,它就穿过了与海面相隔4海里的水层,像飞鱼一样跃出水面,又落回水波中,溅起了惊人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