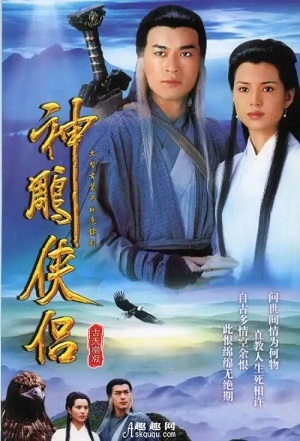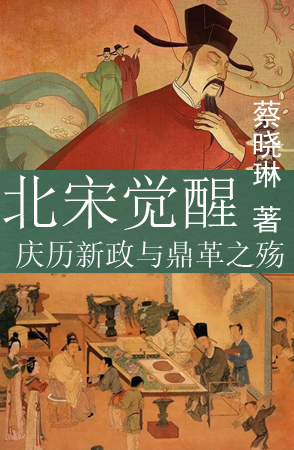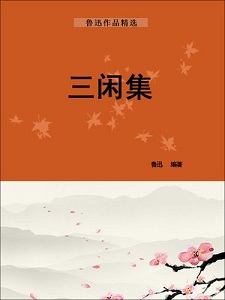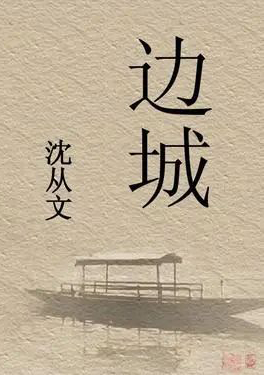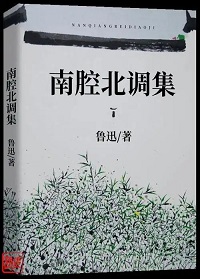三十五 周恩来醉酒的背后
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赋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全部撤出朝鲜回国。祖国人民隆重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以杨勇、王平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全体人员等,并合影留念,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高的荣誉和莫大的鼓励。同日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协、市抗美援朝分会联合举行宴会,欢宴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全体人员。周恩来、朱德、陈毅、郭沫若以及首都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欢聚一堂,畅饮胜利酒,畅谈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
这一天,周恩来特别高兴,以致在宴会上醉了酒。
是啊!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日理万机,不仅在外交斗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军事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从战场作战指导到后勤保障以及朝鲜停战谈判指导,涉及方方面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主持组建东北边防军
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后,中共中央适时决策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1950年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国防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央军委于7月13日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了东北边防军的组成、东北边防军的组织指挥机构、东北边防军的后勤准备、兵员补充、政治动员等问题。随即确定了东北边防军的供应办法。
在边防军向东北集中的过程中,已确定的东北边防军领导因病因事一时都难以到任,并且边防军25万大军的补给供应也是个大问题。为避免边防军的指挥脱节和保证供应,周恩来在与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褛研究后,于7月22日与聂荣臻一道向毛泽东提出报告,建议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原拟边防军后勤机构与东北军区后勤部合并。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稍后,又指定第13兵团部为边防军的军事训练组织领导机构。使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后能迅即展开整训和后勤保障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8月中旬以后,朝鲜战局形成了相持局面。8月26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督促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种准备情况。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一种情况是朝鲜人民军一鼓作气,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至少是告一段落;另一种情况是战争持久化,要准备在长期化的战争中逐步消灭敌人。“在第一种设想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现在看来第一种设想情况已经过去,第二种设想情况将成为现实,我们应很快地积极准备。同一次会议上,还确定了军兵种的参战准备。
此外,8月下旬,周恩来还多次召集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开会,商谈加强东北边防军问题,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为边防军计划了第二、第三批部队。
从7月上旬组建东北边防军到10月上旬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整个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包括抽调部队、部队集中时的运输组织、训练工作、装备编制的调整、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等,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由于东北边防军的及时组建和突击准备,使得东北边防军在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出动到朝鲜作战,一开始就连续取得胜利。
参与出兵决策并保证决策的顺利实施
1950年9月中旬,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发生逆转,朝鲜人民军被迫实施战略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上,于9月20日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致电金日成,对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指导提出了建议,指出:“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作战最忌平分兵力,而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做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金日成对此十分欢迎和感谢。
当金日成和朴宪永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后,在10月4日和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讨论出兵援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弊得失,认为出兵对于长远经济建设、对解决台湾问题、对国际影响均利大于弊,积极支持出兵援朝的主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后,为使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得以顺利实施,10月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具体研究部署了志愿军出国作战事宜。10月8日,周恩来又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与林彪秘密前往苏联,向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通报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情况,争取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援助并出动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和协助中国防空。此后,从10月下旬至1951年1月,周恩来在多种场合对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做了宣传、解释,阐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正义性,动员政府各有关部门、全国各行各业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此外,还协助毛泽东进行各种战略筹划和部署,全力保证战争的胜利、保证国内防务万无一失和尽可能进行经济恢复。这些,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略决策的实施。
协调中、朝、苏三方部队的作战指挥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时,朝鲜人民军主力已遭到严重损失,正在从三八线以南向北后撤转移中,新组建的部队18个师,有9个师9万余人在朝鲜靠近中国的边界地区整训,另有9个师9万余人在中国境内整训。在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也有个别部队参战,但由于与志愿军缺乏统一协调,曾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
11月,苏联协助中国担负国土防空任务的空军部队出动到鸭绿江上空作战,朝鲜人民军新组建的部队也将陆续整训完毕准备投入作战,人民军空军尚有一部分部队可以参加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也将有一部分部队参加实战练习,这样中、朝、苏三方部队的作战协调指挥,特别是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统一作战指挥问题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彭德怀请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同金日成协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统一指挥问题,但由于苏联驻朝鲜大使和驻朝鲜的军事顾问对此问题认识不一致,而影响了金日成的决心。11月11日,彭德怀将有关情况电告毛泽东并高岗,提议由金日成、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与作战有关的协调指挥、军事政策等问题。此事涉及苏联方面,并且苏联对朝鲜更具影响力。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致斯大林的电报,转去了彭德怀的建议,征求斯大林的意见。电报中说:“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史蒂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斯大林接电后,于16日同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同时电告了金日成和史蒂科夫。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也赞成斯大林的意见。11月17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的电报,将此情况通报给彭德怀和高岗。
从此,凡与作战有关中、朝、苏三方需协调的事宜,均由周恩来出面与苏联政府或军方领导人、朝鲜的金日成协商,或由周恩来委托聂荣臻出面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协商。
12月3日,金日成来北京,就朝鲜战争有关问题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讨论。此时,人民军有5个军团完成休整或整训,将与志愿军并肩作战。关于中朝两军的统一指挥问题,金日成说斯大林来电报同意中朝两军统一指挥,因中国同志有经验,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已同意。讨论中商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合司令部应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铁路的运输和维护也归联合司令部指挥。联合司令部的命令,经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下达。推任彭德怀为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12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协议,并征得金日成的同意,中朝联合司令部顺利成立。后来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也为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
在中朝联合司令部之下,1951年3月中旬,成立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8月成立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管理维护战时朝鲜铁路运输和铁路的抢修;9月成立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两个联合指挥机构。
这些联合性质的指挥机构的成立,统一了中朝两军的作战指挥和战时朝鲜铁路的运输管理。
指导志愿军作战
志愿军参战后,在第一至第三次战役期间,毛泽东高度关注志愿军的作战,对志愿军的作战指导极为详细具体。在第三次战役胜利后,特别是第四次战役开始以后,对于志愿军的作战指导,毛泽东一般均委托周恩来、聂荣臻处理,直至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此期间,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反“绞杀战”、反细菌战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的斗争。周恩来和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除对志愿军的作战给予许多具体指示和指导外,还对志愿军的作战指导做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如下两点:
一是主持中央军委确定志愿军实施轮番作战的方针。
在志愿军组成之前,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检查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时,就曾设想边防军出动参战后的补充问题,“一种是从各部队抽出十万人来补充,一种是用建制补充,后一种办法较好。另一种是采用换班的打法进行补充,即准备第二线部队作为后备,待第一线部队一个军或一个师作战后需要补充时,可以开第二线整补,而以第二线一个军或一个师调前线作战,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中央军委同时为边防军出动作战,准备了第二、第三批部队,为后来志愿军在朝鲜实行轮番作战做了组织准备。
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特别是第三次战役后的战场情况表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依靠优势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在遭到志愿军的攻击时其组织撤退快,在志愿军停止进攻后其组织反扑也快,不容许志愿军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战场休整。志愿军已连打三个战役未得休整补充。如何解决休整补充的问题成了志愿军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重大战略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确定志愿军“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1951年2月8日,周恩来主持制定以三番部队进行轮番作战的具体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告志愿军和各大军区。经对具体轮番的部队进行调整,于2月18日最后确定以21个军分三番作战,即以正在朝鲜作战的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在朝鲜休整的第9兵团3个军为第一番作战部队;以第一番部队中的第9兵团3个军和准备入朝的第19、第3兵团的各3个军共9个军为第二番作战部队,准备4月中旬前后接替第一番部队作战;以第一番部队中的第38、第39、第40、第42军和国内尚未入朝的第47军、第20兵团两个军及西南军区第二批北调的3个军共10个军为第三番作战部队,准备6月中旬前后接替第二番部队作战。
2月下旬,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讨论战争形势问题,建议将战场情况和中央军委采取的轮番作战方针通报给斯大林,周恩来又起草了以毛泽东名义致斯大林的电报,3月1日,将战场情况和上述轮番作战方针计划通报给斯大林。
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就是按此计划以第二番作战部队为主进行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第三番作战计划未再执行,但第47军和第20兵团的两个军,于4月和6月先后入朝,第47军于6月接替第一线的防务,第20兵团的两个军也于9月接替第一线防务。
1952年5月以后,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只剩战俘遣返问题一项议程,由于美方违反《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顽固坚持“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迫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而未能达成协议,并且美方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故意拖延,致使战争继续延长。鉴于这种战争形势,同时为使长期在战场上的志愿军部队得到较好休整和按国内国防军的编制进行整编,使国内更多部队得到现代战争的锻炼,5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确定了以国内完成整编的部队轮换战场部队的方针,责成总参谋部与在北京治病的彭德怀进行协商,制订第一期以国内3个军轮换战场上3个军的计划,并于当年9月开始实行。此后,还组织了第二期轮换以及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指挥机关的轮换,炮兵、装甲兵、工兵部队和指挥员也进行了轮换。
轮番与轮换作战方针的确定和实施,既有效地解决了志愿军在战场上作战与休整的矛盾,保持了强大的作战力量,又使国内更多部队得到现代战争的锻炼。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指导中的一个新创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一个新内容。
二是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主持中央军委确定作战要“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的方针。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场上的打和谈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战略的角度说,打是为了谈,打也促进谈,谈制约打,谈为打提出任务和目标。因此,这期间的打,从战略上都要根据谈判的需要进行,打的规模大小、打击目标的选择和打的时机的确定,都需考虑到谈判的形势。鉴于这种战争形势的出现,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于8月19日就志愿军计划的第六次战役问题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志愿军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使休战谈判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并准备谈判不成,破裂的责任落到敌人身上。……在作战上,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从而明确了停战谈判期间志愿军作战与谈判的关系,明确了这期间志愿军作战的重要指导方针。志愿军贯彻这一方针,在整个停战谈判期间的作战,有力地适应和配合了停战谈判。
筹划新军兵种建设和参战
早在东北边防军整训期间,为准备同完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军作战,周恩来即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确定了制定空军、海军和各特种兵三年建设规划事宜。
8月26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国防会议上指出,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战争长期化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朝鲜进行长期战争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的。但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看来这个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肩上”“我们这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美军是依靠大炮、飞机等火力,……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美帝国主义总是想将世界大战一步步地推动起来,但现在还不能发动,主要原因是还没有准备好。……但其总企图是不断地由一个一个的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在我们方面,就要将它发动起的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使它不能发展为大规模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建设应该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如果今天订不出长远计划,也必须先订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建军计划,作为准备阶段的计划”。
这次会议确定,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军兵种分别制订一个三年建设计划, 1951年开始实施。据此,空军、海军和各特种兵机关均制订了三年建设计划。
会议确定,空军在已有7个航空兵团的基础上,到1951年1月底,再增编3个轰炸团和1个海军飞机团,1951年下半年再增大编制,具体计划责成空军司令部拟制,空军至迟到1951年1月底开始出动参战。
装甲兵在1950年编成3个旅共9个坦克团,共360辆坦克,9月底前编成,年底前完成训练,准备1951年出动参战。3个旅9个团的编成及所需坦克、汽车、汽油、器材、人员编制、干部配备、部队训练、聘请顾问等,责成装甲兵司令部制订计划。
炮兵,高射炮编成18个团,中小口径高炮428门,3个月内分两批完成训练;榴弹炮、野炮、火箭炮、战防炮等以配足10个军的队属炮兵计算,所需火炮、汽车、器材、弹药等责成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在3天内做出详细计划,这些部队组编后,1950年年底前完成训练,1951年开始参战。
接着,周恩来与军委有关部门研究,于8月31日对炮兵和空军的建设计划做了进一步调整。
经过多方努力,计划基本得以实现,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且也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起步。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空军和特种兵部队何时能参战,能出动多少参战,也都是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或责成总参谋部与有关军兵种机关协商做出具体计划,组织实施。由于空军和特种兵部队于1950年和1951年陆续参战,使志愿军的作战能力逐渐增强,到1952年秋季已经完全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直至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统筹战争后勤保障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
早在周恩来主持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决定任命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专事负责边防军的后勤工作。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就专门有一项是后勤准备,其中包括弹药基数准备、交通运输工具准备、粮草汽油准备、服装准备(改穿人民军式服装)、卫生医院准备、担架及担架队准备等,并责成有关部门具体落实。
东北边防军改为志愿军参战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供应事宜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周恩来对总后方基地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1950年11月5日,周恩来致电高岗和李富春(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分工主管后勤保障工作),指出:
对于东北全部支援部队工作,我们已想见其繁重。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但你们仍可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声,当由中央追认。凡能统一于东北者,我们无不赞成统一于东北。
事实上,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所需干部、部队、车辆、司机、物资、经费、在国内的铁路运输等,都是由周恩来与政务院有关部门、全国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协商解决的。还由周恩来起草电报以毛泽东名义致电斯大林或周恩来直接致电斯大林或布尔加宁,与苏联领导人协商从苏联订购中国不能生产的武器、汽车等,解决志愿军所需。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以志愿军名义出国作战,并且是以劣势装备同最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这给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直接关注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后勤保障问题,组织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东北军区等研究解决的措施。
在志愿军入朝初期,周恩来亲自点将,由东北军区派出后勤机构负责战场保障,先后筹划组建了7个后勤分部(后缩编为5个)负责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后勤工作。
根据战场上保障作战的需要,周恩来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军委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多次协商后,中央军委于1951年5月19日做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确定在志愿军首长领导下,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取代东北军区派出的后勤指挥所,组织在朝鲜境内的后勤保障。根据这个决定,组成以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同时从军到团各级均以一名能力强的副职兼任本级后勤部(处)的主官,加强了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组织领导。
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前期,后勤保障的最大问题是在朝鲜境内的运输补给不适应作战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1年1月下旬,周恩来率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运输司令员吕正操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由东北军区组织召开的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会议确定把运输工作作为志愿军后勤保障的中心工作来抓,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同时确定增调铁道兵和工兵部队入朝抢修铁路、公路,增加运输汽车以增强运输力,增调高炮部队入朝掩护交通运输。
为保证战时朝鲜境内铁路运输,周恩来主持与朝鲜政府协商,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建立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之下,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
1951年8月18日,美国空军发动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给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采取许多重大措施:命令志愿军空军出动掩护平壤以北铁路运输;指示志愿军将在朝鲜境内的高炮部队主要力量集中用于担负铁路系统防空作战;加强铁路抢修力量;将国内准备用于修建黄河大桥的钢材和即将从苏联购进的钢材运入朝鲜,以保证朝鲜境内的铁路抢修。周恩来还指示,为保证战场急需,重点运输粮食和被服,缓运正待入朝的特种兵部队,减少弹药和杂品运输,改善物品打包办法,车辆增载三分之一,保证完成9月下半月至10月底的运输任务。采取这些措施,加上志愿军后方各军兵种部队和机关的共同奋战,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志愿军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从而解决了志愿军战场运输一直困难这一战略上的重大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为人民解放军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停战谈判的主要指导者
朝鲜停战谈判虽然是战争双方司令官派出代表进行的关于实现朝鲜停战的军事谈判,但由于双方参战国众多,并且是在战争双方战场力量旗鼓相当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朝中方面的谈判对手是推行强权政治、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军队的代表,因此,这场谈判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鉴于此,朝中方面对这场谈判斗争极为重视。
为有力地进行谈判斗争,朝中方面建立了三线班子:第一线班子,是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团进行面对面的唇枪舌战;第二线班子,是停战谈判的前方指挥部,由周恩来挑选有谈判斗争经验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直接坐镇指挥,并由中国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协助。李克农直接与毛泽东和金日成、彭德怀联系,报告谈判情况,获得有关指示,并根据这些指示制定代表团在谈判桌上的谈判方案;第三线班子,是最高决策层,由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协商,并征求斯大林、彭德怀的意见,确定谈判的总体方案、方针和原则,根据谈判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发出指示。最高决策层的工作,毛泽东基本是委托周恩来进行具体操作的。有关停战谈判问题以毛泽东名义发给金日成、斯大林征求意见的电报,以毛泽东名义发给李克农和谈判代表团的指示,以金日成、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声明及给“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信函,朝中方面谈判首席代表的声明及给美方首席代表的信函,甚至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的一些发言稿,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起草或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但最高决策层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指导工作一直由周恩来负责。据不完全统计,在2年17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中,由周恩来亲自起草或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文件、指示等达300余件。这些文件和指示有力地指导了朝中方面的谈判斗争,既体现了谈判斗争原则的坚定性,又体现了谈判策略的灵活性,体现了高超的谈判斗争指导艺术,使朝中方面在谈判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取得了谈判斗争的胜利。
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主持外交斗争,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具体负责停战谈判指导,协助毛泽东进行战争指导,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周恩来伟大一生中光辉的一页。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巨大军事贡献,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和研究现代局部战争战略指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