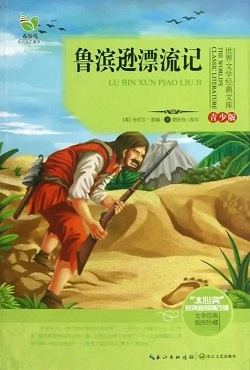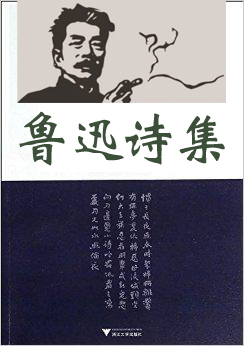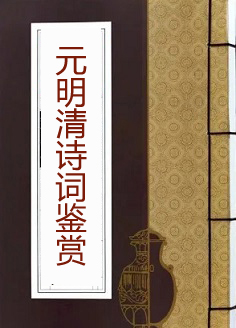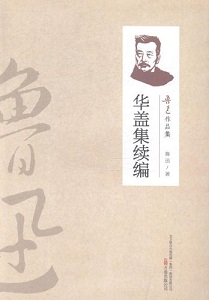六 盛世经济与历法之争
康熙皇帝即位后,前前后后忙活了不少事,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征服噶尔丹,澄清吏治,减轻赋役,招纳贤士。而完成这些大事,都需要国家经济的支撑。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自农业。农业是国家存亡的根本,百姓的生命之源。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虽然,满人起源于游牧,善骑射,不善农事,但从建国时起,在努尔哈赤倡导下,已把农业生产列为重要的部门。特别是皇太极时期,把农业置于社会经济的首要地位,反复开导他的不善农业的兄弟子侄及其本族臣民,灌输重视农业的思想,具体讲解农业之重要及耕作方式方法。
这之后,以农为国本的思想,已成为历朝皇帝及统治集团的传统国策。如顺治帝与多尔衮,都不忘农业这个根本,在进行统一战争中,仍不废农业生产,攻克一地,便迅速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
入关以后,顺治皇帝效仿历代帝王,在京南设立先农坛,把祭先农列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同时,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一亩农田,叫作籍田,专供皇帝每年春天到这里来行“籍礼”。
而在清朝的12位皇帝中,若论重视农业生产,并将其付诸实践,做得最好的,非康熙皇帝莫属。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以往的皇帝那样,把重农仅仅体现在每年春天的“籍礼”上,而是切切实实地对某些植物、土壤及栽培技术进行调查研究,并做了一些有效的实验。
据记载,康熙皇帝研究考察过的植物多达二十余种,如黑龙江麦,御稻、吐鲁番西瓜、葡萄、果单、菱角、杨柳、枫树、竹子等。他对这些植物的产地、生长期及根、茎、叶、花、果的性能、用途、味道等,都做过比较深入的考察。在考察过的20多种植物中,亲自试种过的有10来种,如稻麦、人参、花木等。
康熙皇帝南巡时,十分喜爱江南的香稻和菱角,他便带了一些种子回京试种。结果没有收获,试种失败了。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悟出种庄稼不能生搬硬套,“南方虽有霜雪,然地气温高,无损于田苗。”之后,康熙留心改良土壤,提高地温水温,他的栽培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在康熙皇帝进行的苦干栽培试验中,最有成效的是御稻的培育。他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试种御稻,到晚年时,还曾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在江宁、苏州等地进行推广。据史书记载,御稻第一季亩产在四石左右,与当时苏州稻田的亩产量接近;第二季亩产量一般都在两石至两石五斗,两季加起来,比原来增长了五成左右,所以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御稻在江南曾流行过一段时期,但当时还没有解决在一块土地上不倒茬、连种的弊端,同时农民也缺乏长期栽种双季稻的积极性,御稻慢慢就绝迹了。
康熙重视农业、关注农民,不仅体现在他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上,还体现在他的农业政策上。众所周知,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就是在康熙朝彻底废止的。当时还规定,奖励垦荒,地方官如能招来垦荒者晋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予种地的农户,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康熙朝曾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9省田赋普免一周;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由于实施重农政策,全国耕田面积由顺治时代的5.5亿亩发展到康熙时代的8亿亩,农业得到显著发展。人口随之迅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
康熙皇帝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功业,就是大规模整治黄河。
清初的水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苏北地区,当时水患的主要特点,不仅是黄河频繁泛滥,淹没大批良田,更导致了连接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阻断。
当时主持治河的,是17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水力学家靳辅。靳辅的治河理念,延续了明朝人潘季驯的“束水冲沙法”,而他别具突破性的创举在于:他认为应该把黄河当作一个整体去治理,如果仅仅是哪里闹水灾,就去治哪里,那无疑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超前眼光的治水理念,也一度引起清王朝的质疑。
靳辅于康熙十七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五年多次治理黄河。他的压力巨大,因为他眼光超前的治水思路,是要对黄河进行全面的整修,这势必就要耗费巨额的投资。而且,这种治水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工期长,见效慢。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他至少有五次,因为黄河决口,而遭到同时期一些“专家”们的质疑。但最后的结果证明,靳辅是对的。在这次大规模的整修后,黄河大约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大型的水患。
康熙不仅在南巡的时候,对治理黄河的工程进行了规划和检查,还利用亲征噶尔丹的机会,在宁夏从横城口乘船顺黄河而下,体验黄河的汹涌激荡。
康熙四十三年,曾派侍卫拉锡等人前往黄河的源头进行考察。《康熙政要》中,记录了康熙皇帝对拉锡等人的指示:“黄河之源,虽名古尔班索罗谟,其实发源之处,从来无人到过。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
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这一年的四月初四,拉锡奉谕旨率随员西行,到达青海的时候,是五月十三日。他们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之下,对黄河发源地的星宿海、扎陵湖和鄂陵湖的大小与形成情况,进行了考察,并绘制了黄河从鄂陵湖流出的路线图。在此之后,康熙皇帝在拉锡奏报的基础上,写了一篇短文《星宿海》,记叙了黄河之源的情况。
从此次考察的奏报可以看出,其考察结果,与现代地质学家对黄河河源的地理环境考察基本是一致的。康熙皇帝在300多年前组织的一次黄河河源考察,可以算得上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壮举。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不仅在安邦治国上,大有作为,还特别提倡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封建君主,怎么会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呢?这要从一次历法之争说起。
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本来是很高的,可到了明末,由于腐朽没落制度的束缚,科技水平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明朝的历法,用的是大统历。所谓大统历,就在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到明朝时改称为大统历。
大统历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到明末已经很不准确,需要修订了。当时,西方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皇帝的重视,都想方设法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华。
明朝有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从传教士利玛窦那里学了很多东西,又把一个叫汤若望的传教士推荐给明朝皇帝。前文提到过,这位叫汤若望的传教士,后来在顺治朝受到重用,官居一品,三代荣受皇封,孝庄皇太后还尊他为义父。
汤若望根据比较先进的仪器和数学知识,推算出来的日食、节令都比大统历准确。明朝决定推行汤若望的新历法,还让汤若望主持在北京修起了一座观象台。然而,新历法还没来得及推行,明朝就灭亡了。观象台也在兵荒马乱之中被毁坏。
清朝入关后,汤若望又写信给顺治皇帝,说用新历法推算,这年八月初一将出现日食,请求派官员测验。到了八月初一,摄政王多尔衮派人一看,果然不错。多尔衮很满意,马上宣布实行新历法,还让汤若望当了负责天文、历算的钦天监监正。
顺治皇帝亲政后,更加信任汤若望,授给他“通玄法师”的称号。而钦天监那些靠推行大统历混饭吃的守旧派官员,都被冷落到一边去了。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官员,认为只要靠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什么都好,外国传进来的就什么都不好。于是,他上疏说,清朝要子子孙孙传下去,可是汤若望推行的新历法只有二百年,可见他居心不良。
康熙皇帝即位初期,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权,他们认为,凡事按祖宗的老一套办法做,才稳妥。就下令严惩主张推行新历的一派人。汤若望因为有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讲情,才被免除了死刑。年老多病的汤若望,不久后就死在了狱中。其余的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负责新历的汉族官员也受牵连被处死。杨光先一跃成为钦天监监正。
康熙皇帝除掉鳌拜后,发现杨光先推算节令常常出错。可是,究竟是旧历好,还是新历好,康熙皇帝一时难以决断。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的一天,康熙皇帝让杨光先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一同参加了御前会议。康熙皇帝让二人分别拿出证据,来证明旧历和新历哪一个更好。
杨光先拿不出证据。而南怀仁却胸有成竹,说,请皇上摆出两个日晷(用日影来测定时刻的仪器),让杨监正和我分别算出明天正午日晷投影的位置,看看谁的准确。
康熙皇帝认可了,让礼部尚书等人到时当场验视。次日,礼部尚书带领众官员到达午门,等待验证。
杨光先本来不懂历算,推算节令要依靠别人。这时候虽然标出了一个投影的位置,但心里根本没有把握,南怀仁懂得代数、几何,因此很镇静。
到了正午时分,日晷果然准确无误地投影在南怀仁标明的位置上。而杨光先推算的却差得很远。杨光先看到这个情况,十分尴尬,却不服气,口称:“宁可无好历法,也不可使大清国有洋人!”
南怀仁不慌不忙地说,今天是冬至,投影应该在二百四十度这个位置上。继而又问杨光先,今年应该是十二月闰月,可是按您的历法,却在明年一月。除此之外,您还把明年算成两个春分,两个秋分,不知是何道理。
南怀仁滔滔不绝地讲着,前来验视的官员,包括杨光先,个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回答。康熙皇帝很感慨,大清王朝这么多大小官员,难道都不懂历法推算?至此,他决定采用新历法,还下令钦天监的官员学习新历法。
其实,康熙皇帝下令让钦天监官员学习之前,自己已经开始学习了。他把南怀仁请到宫里,详细地询问西方科学。南怀仁每天到宫里,用满语和汉语给康熙皇帝讲解天文学、几何学和静力学。
康熙皇帝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和阿基米德定律,还学会了使用一些主要的天文学仪器和数学仪器。后来,每逢行军打仗,康熙皇帝都让侍卫随身背着一些仪器,以便随时测量太阳子午线的高度,和周围地形地物的高度和方位。
康熙皇帝还组织编纂了一本《数学精蕴》。这部书集中了当时中国和外国数学的代表作,成为清朝最重要的数学著作。有一次,康熙皇帝到南方巡视,有人把数学家、天文学家梅文鼎的一部数学著作献给康熙。两天以后,康熙皇帝对献书的人说:这本书写得很细致,议论也公平,朕要带回宫里去仔细研究。
后来,康熙皇帝再次南巡,就指名要见梅文鼎。梅文鼎当时已经年逾七十,被请上龙舟,连续三天,从早到晚和康熙一起研究数学。梅文鼎辞别的时候,康熙皇帝依依不舍,说朕留心天文历算,像您这样有学问的人,实在太少了。可惜您年纪太大了,不然朕一定把您留在身边,早晚向您请教。说罢,又提笔当场写下“积学参微”四个大字,赐予梅文鼎。
次年,康熙皇帝把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召到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学数学。过了几年,康熙皇帝又编纂了介绍音律知识的《律吕正义》,书刚印好,康熙皇帝就拿出一部叫给梅瑴成说,你祖父学识渊博,把这部书寄给他,让他看看,能指出错处就更好了。
梅瑴成出生在数学世家,本来就有家学的底子,再经康熙皇帝指点,学问长进很快。康熙皇帝亲自把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代数“借根法”传授给他。
虽然,康熙皇帝推崇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数学,但是又决不墨守成规。每到一个节令的头一天,只要有条件,他都拿日晷亲自验证。那次历法之争过去四十多年以后,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夏至午时三刻,康熙皇帝亲自验看日晷投影,发现了误差。他对周围人说:西方历法大致准确,但时间久了也不能没有差错。你们看,今年夏至按西方历法应该是午时三刻,实际是午时三刻九分,再过几十年就会差得更多了。
康熙皇帝对待科学和科学家,能高度重视并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很少见的。在康熙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一些发展,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人才。正因如此,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中,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国家。康熙在位期间,除了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之外,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充分展现了其圣明的一面。而清朝正史的史料中,还有一个对他普遍的评价,那就是“宽容”。
《清史稿》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有大臣认为,在征粮食的时候,如果不去控制火耗,就会给官员贪污提供便利。康熙回答说,官员们的俸禄本来就比较微薄,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捞外快的机会,对那些工作努力的官员,也是一种补偿。
正是因为这种“宽容”,使吏治松懈、腐败横生,甚至国家财政也入不敷出。作为一国之君,康熙皇帝使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增强,然而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又因为自己的“宽容”使经济下滑。到了他去世的那一年,国库存银只有八百万两。而就在他去世的前三年,国库存银尚有近五千万两。
而国家的财政问题,仅仅是康熙皇帝在晚年头疼的事情之一,还有一件让他烦恼不堪的事,就是选择谁来接替他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