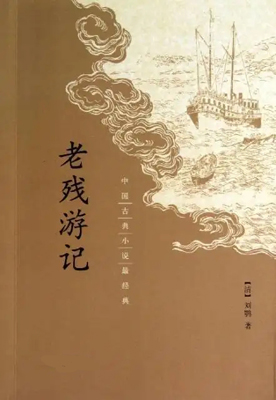朱仙镇战役结束的第二天,一部分义军开始返回开封城外。李自成和罗汝才的老营尚未移营,而朱仙镇一带仍驻有很多人马,多是追杀官军回来的部队,奉命要休息到明天才拔营去围困开封。
五月二十四日这天晚上,李自成在他的老营大帐中召集少数亲信文武,研究朱仙镇大战以后的新局势和围困开封诸事,同时也研究了今后同曹营的关系。这次机密会议直开到三更以后。当大家退出时候,李自成对牛金星说:
“启东,明天到阎李寨,应该继续讲《通鉴》了,还有《贞观政要》这部书,我已经读完,有些地方还需要你讲一讲,才能完全懂得。”
牛金星恭敬地回答说:“《通鉴》自然要继续讲下去。将来大元帅建立江山,经邦治国,这里边有取不尽的经验。《贞观政要》既然已经读完,有些重要地方可以再讨论讨论。我想如今天气太热,大元帅也不必过于劳累。像大元帅这样于军旅繁忙之中还能勤学好问,真是千古难得!”
李自成近来已经听惯了这样颂扬的话,不再表示谦逊,随即转向李岩说:“林泉,你稍留一步,我有话跟你谈谈。”
大家走后,李自成拉着李岩的手,步出帐外,站在一棵大树底下。树梢上传来知了的叫声,叫叫停停。附近有战马在吃野草,偶尔还听到它们用蹄子刨土地的声音。天上满布星辰,一道银河横斜,织女星和牛郎星隔银河默默相望。旷野上,很多很多军营,到处有火光闪灼,分明是有的将士还没有睡觉。在李自成和李岩站立的地方,树枝上有一只喜鹊,在梦中被火光惊醒,从枝上飞起来,但忽然明白几天来都是如此,随即又落下来,换了一个树枝,重新安心地闭起眼睛,进入梦乡。
闯王说道:“帐中闷热,站在这里倒觉得十分清爽。林泉,河南是你的家乡,人地熟悉,刚才议事,你怎么很少做声?莫非另有深谋远虑,不肯当众说出?”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对否。因为尚未思虑成熟,所以不敢说出。”
“大家议事,不一定思虑的都完全周到,你说出来何妨?好吧,现在没有别人,你不妨对我说说。”
“大元帅,我有一个愚见,不知妥否。请大元帅速命一大将率领三万人马去追左良玉,乘其在襄阳立足未稳,元气未复,攻占襄阳。将南阳与襄阳连在一起,随后再经营郧阳,可称为‘三阳开泰’之计。如此,则我军进可攻,退可守,将立于不败之地。自古以来,襄阳十分重要,为南北交通要道,又在汉江上游。将来从襄阳出兵,可以东出随、枣,南取荆州。总之,占了襄阳,今后进湖广,人四川,下江南,都很方便。”
李自成用心听着,不置可否。李岩接着说道:
“对曹操只说追左良玉,不必说占领襄阳、南阳。等占领之后,大力经营,那时曹操即使心里不乐意,也莫可如何。”
李自成微微点头,又沉默半晌,方才小声说道:“林泉,我们今天虽说有四十万人,可是能战的精兵不多,这你是知道的。此次朱仙镇之战,我们是全力以赴,所以不惜将阎李寨的很多粮食丢掉。今后既要攻开封,又要防朝廷,还要防曹操,兵力便很不足。要围攻开封,就不能分散兵力。还有一层,倘若我们的力量一弱,曹操对我们也就不再重视;纵然他没有别的想法,他的部下也很不可靠。所以你的想法虽然很好,也只能等攻破开封以后,再作计议。”
李岩不敢勉强,说:“大元帅从全局着眼,以破开封为当务之急,又得防曹营怀有二心,所以将兵力集中在手,以策万全。老谋深算,胜于岩之管见远矣。”
李自成想了想,问道:“林泉,从明日起,我们就专心围攻开封。你今晚很少对围困开封的事说话,不知你尚有什么妙策不肯当众言明?”
“围困开封,众位文武讨论甚详,我没有别的妙策可说。今后倘有一得之见,定当随时献曝①。只有一件事情,刚才议事的时候大家都一时忘了。”
①献曝——古人的谦词,意思是贡献很不重要的意见或礼物
“什么事儿?”
“明日大军重围开封,应该向开封城内射进告示,劝谕城中官绅军民及早投降,免遭屠戮。就说大元帅体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动用武力,暂时围而不攻,以待开门投降,文武官员一律重用,市廛不惊,秋毫无犯。如敢顽抗,破城之后,寸草不留。”
“好,好。我因为事情多,忘了让献策和启东他们草拟一个告示了。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你回去休息一晚,明天早晨把告示拟好,带到阎李寨交我。”
李岩辞别大元帅,跳上战马,向朱仙镇附近的驻地奔去。
同日下午,约摸申时光景。
在开封城内,靠近南土街的酉边,有一条东西胡同。在这条胡同的西头,有一个坐北向南的小小的两进院落。破旧的黑漆大门经常关着,一则为防备小偷和叫化子走进大门,二则为前院三间西房设有私塾,需要院里清静。倘若有生人推开大门,总会惊动一条看家的老黄狗,立刻“汪汪”地狂叫着,奔上来拦着生人不许走进,直到主人出来吆喝几声才止。那大门的门心和门框上,在今年春节时曾经贴过红纸春联。当时开封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攻防战,家家户户都不知这城是否能够保住,也没有心思过年。可是贴春联是两百多年来一代代传下的老规矩,又都不能不贴。现在这春联已被顽童们撕去大半,剩下的红纸也褪了颜色。只有门头上的横幅,红纸颜色还比较新鲜,上写着“国泰民安”四个字。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这四个字看起来都十分滑稽。
如今虽然天气很热,却仍旧从院中传出一片学童的读书声。有的孩子读“四书”,有的读《千字文》,有的读《百家姓》,还有的在读《诗经》,不过那是个别人罢了。这些学生,有的用功,有的淘气,而且各人的天赋、记性都不一样。有一个孩子,显然是在背书,非常吃力,只听他扯着喉咙背着“子日,呀呀呀,呀呀呀”,“呀”了好久,接不上别的字句。夹在这些学童的声音中间,有一个中年人的声音,也在朗读文章,音节很讲究抑扬顿挫。那文章听起来好像是一段跟一段互相对称的,懂得的人会听出来他是在读八股文,也许他面前的书就叫做《时文①选萃》,或《闱墨②评选》,总之,这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中举人、进士所必修的课程。这个中年人的琅琅书声一直传到大门以外,传到小胡同中。
①时文——明朝人将八股文称为“时文”.以别于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
②闱墨——评选出来乡试或会试考中的试卷,称做闱墨。“闱”指试院。
这时在胡同的西头,有一位少妇牵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向东走来。她分明听见了读书的声音,特别是辨出了那个中年人读八股文的声音,忧郁的脸孔上不觉露出来一点若有若无的笑,也许是一丝苦笑。她低下头去望着那个小男孩,轻轻问道:
“你听,那是谁读书?”
小男孩并没有理会这读书的声音,用一只手牵着妈妈,用一只手背擦自己脸上的汗。遇着一块小砖头、一块瓦片,他总要用他的破鞋子踢开。由于天气太热,他的上身没有穿衣服,只带了一个花兜兜;裤子是开裆裤,用襻带系在肩上。他长得胖乎乎的,大眼睛,浓眉毛,五官端正,一脸聪明灵秀之气。
那少妇大约有二十八岁的样子,平民衣饰,梳着当时在省城流行的苏州发髻,脸上薄施脂粉,穿的是一件藕荷色汴绸褂子,四周带着镶边,一条素色带花的长裙,已经半旧了。她的相貌端正,明眸皓齿,弯弯的眉毛又细又长,虽然算不得很有姿色,但在年轻妇女中也算是很好看的了。她正像当时一般少妇那样,走路低着头,目不旁视。与往常不同,今天她脸上带有忧郁的神色,好像有什么沉重的心事压在眉头。
这小胡同里行人不多,偶尔有人从对面走来,她就往胡同北边躲一躲,仍然低头走她的路,不敢抬起头来看人,但也不由得看看别人的脚。刚才她是去胡同转角处的铁匠铺,找铁匠孙师傅间几句话,问过以后,就很快转回家来。
她的婆家姓张,丈夫是一个资门秀才,原籍中牟县,是当时有名的河南名士张民表的远房侄儿,名叫张德厚,字成仁。她的娘家姓李,住在开封城内北土街附近。她小时候本来也有名字,叫做香兰,但当时一般妇女的名字不许让外人知道,只有娘家父母和家族长辈呼唤她的小名。一到婆家,按照河南习俗,婆家的长辈都称她李姑娘,晚辈称她大嫂或大婶,也有邻居称呼她秀才娘子。但由于省会是一个大地方,秀才并不稀罕,称呼她秀才娘子的人毕竟不多。自从开封第一次被围以来,家家门头上都挂着门牌,编为保甲,门牌上只写她张李氏,没有名字。
她推开大门,惊醒了正在地上睡觉的老黄狗,刚要狂吠,闻到了主人的气味,又抬头一望,见是女主人回来,立刻跳起来迎接她,摇着尾巴,十分亲昵。它身边有条小狗,已经两三个月了,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也摇着小尾巴,随着老黄狗一起迎接主人。香兰回头把门掩上,忍不住隔门缝偷着朝外望望,恰好有个男人走过,她赶快把门关严,还上了一道栓。黄狗和小狗仍然摇着尾巴,同她亲昵。小男孩蹲了下去,不断地摸着小狗,拍它的头。那小狗受到抚爱,也对小男孩表示亲昵。但香兰心中有事,拉着孩子离开小狗,走进院中,来到学屋前。由于天热,学屋的两扇门大开着,窗子的上半截也都撑开。香兰有话急着要对丈夫说,但她不愿走到门口,让自己全身被学生看见。尽管这是蒙学,但内中还是有一二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为了回避学生们调皮的眼光,她默默地站在窗外,听她的丈夫读书,并从一个窗纸洞里张望她丈夫读书时那种专心致志、摇头晃脑的模样。望着望着,她感到心中不是滋味。自从丈夫中了秀才之后,三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举人,如今还是拼命用功。可是大局这样不好,谁知今年能不能举行考试呢?她为她丈夫的命运,也为她自己和一家人的命运感到焦心。等张成仁读完一篇文章,放下书本,正要提起红笔为学生判仿时,她轻声叫道:
“孩儿他爹!你出来一下。他爹!”
香兰正像许多“书香人家”的少妇一样,温柔沉静,从来不大声说话。今天虽然心绪很乱,仍没有改变说话小声细气的习惯。张成仁于满屋蒙童的读书聒噪声中听见妻子的声音,知道她已上铁匠铺去过,便放下红笔,走出学屋来。他摸摸小孩的头顶,问道:
“回来了么?外面有什么消息?”
香兰忧郁地摇摇头,说:“二弟还没有回来。有些人已经口来了,说是在阎辛寨那边,又有了闯贼的骑兵,不许再运粮食。可她叔叔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知会不会出了事情,孙师傅也很操心。外面谣言很多,怎么好啊!”
张成仁口头望了一眼,发现有几个大胆的学生正在门口张望,见他回头,都赶紧缩了回去。他便对香兰使了个眼色,说:
“我们到后边去说吧。”
说罢,他牵着小男孩一直走进二门。二门里边是个天井院,几只鸡子正在觅食。忽然一只母鸡从东边的鸡窝内跳出,拍着翅膀,发出连续的喜悦的叫声。小男孩笑着说:
“妈!鸡子嬎蛋①了。”
①嬎蛋——嬎,音tá。河南话将鸡鸭下蛋叫做嬎蛋。
妈妈没有理他,嚷着眉头,跟在丈夫的身后进了上房。上房又叫做堂屋,是朝南三间:东头一间住着父母,西头一间住着成仁的妹妹德秀,当中一间是客堂。张成仁夫妻住在西厢房。他们除有小男孩外,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如今这小女儿也在堂屋里随着祖母学做针线。祖父有病,正靠在床上。
他们一进上房,不等坐下,成仁的母亲就愁闷地向媳妇问道:
“你去铁匠铺打听到什么消息?德耀回来了么?”
母亲问到的德耀是张成仁的叔伯弟弟,他的父亲同成仁的父亲早已分家,住在中牟城内,因受人欺侮,被迫同大户打官司,纠缠数年,吃了败诉,微薄的家产也都荡尽。父亲一气病故,母亲也跟着死去。那时德耀只有五岁,被成仁的父亲接来开封,抚养到十二岁,送到孙铁匠的铺子里学手艺,现在早已出师了。因为德耀别无亲人,而成仁家也人丁单薄,南屋尚有一间空房,就叫德耀住在家中,像成仁的亲弟弟一般看待。自从李自成的义军撤离阎李寨后,开封城内天天派了壮去那里运粮。今天早晨恰好轮到德耀和一批丁壮前去。可是丁壮们刚到阎李寨就碰见李自成的骑兵又回来了,大家赶紧往回逃。有些人还未走到阎李寨,也跑回来了。德耀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香兰怕她公婆操心,不敢把听到的话全部说出来,只说外边有谣言,好像官军没有把贼兵打败。
公公一听说消息不好,就从床上挣扎着要下来。成仁赶紧上前搀扶。老头子颤巍巍地说:
“这样世道,怎么活下去啊!昨日一天没有听见远处炮声,原以为流贼已经退走,官军打胜了。没想到事情变化得这么大,竟是官军打败了。德厚啊,你只会教书读书,天塌啦都不关心,也该出去打听打听才是!”
张成仁安慰父亲道:“爹,你放心,像开封这样大城,又有周王殿下封在这里,朝廷不能不救。纵然朱仙镇官军一时受挫,朝廷也会另外派兵来救的。”
“你不能光指望朝廷来救兵,还是赶快出去打听一下吧!你不要只管教书,只管自己用功,准备乡试。虽然是天塌压大家,可是咱家无多存粮,又无多钱,经受不住围困。外边的情形一点也不清楚,怎么行呀?”
张成仁斯斯文文地说:“我今天也觉得有点不对头。前些日子因为贼人来到城外,人心惊慌,只好放学。这几天开封城外已经没有喊人,学又开了,学生们来得也还不少。可是今日午后,忽然有些学生不来了,我就心中纳闷:莫非又有什么坏的消息?现在果然又有了坏消息!不过,我想,胜败乃兵家常事,开封决不要紧,请你老人家放心。”
老头子因为香兰说的消息太简单,一心想要儿子出去打听,便又感慨地说:
“要是战事旷日持久,这八月间的乡试恐怕不能举行了。”
张成仁一听这话,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最怕的就是今年的乡试不再举行,一耽误又是三年。他至今没有考中举人,照他看来,不完全是他的八股文写得不好,好像命中注定他在科举的道路上要有些坎坷。上一次乡试,他的文章本来做得很好,但因为在考棚中过于紧张,不小心在卷子上落了一个墨点子,匆匆收走卷子后,他才想了起来,没有机会挖补。就因为多了这个墨点子,他竟然没有中举。这一次他抱着很大希望,想着一定能够考中,从此光耀门庭。可是现在看来又完了,他不觉叹了口气,说:
“唉,我的命真不好!前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原准备这次乡试能够金榜题名,不枉我十年寒窗,一家盼望。唉,谁晓得偏偏又遇着流贼攻城!”
母亲深知道儿子的心情,见他忧愁得这个样子,就劝说道:“开封府二州三十县,读书秀才四千五①,不光你一个人盼望着金榜题名。要是今年不举行乡试,只要明年天下太平,说不定皇恩浩荡,会补行一次考试。”
①四千五——意思是很多,一般指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