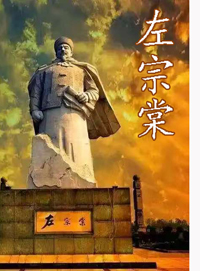她赶快垂下眼睛,免得他忽然抬起头来看见她脸上的表情。她知道她浑身洋溢的那股胜利之情必然明显地表现在她的眼睛里。他立刻就要向她求婚了——或者至少会说他爱她,然后……正当她透过眼睑观察他时,他把她的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准备也要吻它,可是他突然紧张地吸了一口气。她也低下头去看自己的手心,仿佛一年中真的头一次看它似的,这时她吓得浑身都凉了。这是一个陌生人的手心,而绝不是思嘉·奥哈拉那柔软、白皙、带有小涡和柔弱无力的纤手。这只手由于劳动和日晒已变得粗糙发黑了,并且布满了斑点。指甲已经损坏和变形,手心里结了厚厚的茧子,拇指上的血泡还没有完全好呢。上个月因溅上滚油而留下的那个微红的伤疤是多么丑陋刺眼啊!她怀着恐怖的心情看着它,随即不加思索地赶快把手握紧了。
这时他仍然没有抬起头来。她仍然看不见他的脸。他毫不容情地把她的拳头掰开,凝视着它,然后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拿起来,把双手合在一起,默默地捧着,俯视着。
“看着我,”他最后抬起头来说,但声音显得十分冷静,“放下那副假装正经的样子吧。”
她很不情愿地看着他的眼睛,满脸反抗和烦乱的神色。他的黑眉毛扬起来,眼里闪着奕奕的光辉。
“你就这样在塔拉一直过得很好,是吗?种棉花赚了那么多钱,能够出外旅行来了。你用自己的双手在干什么——耕地?”
她试着把手挣脱出来,可是他拉住不放,一面用拇指抚摩着那些茧子。
“这不是一位太太的手呀!”他说罢就把她的双手放到她的膝上。
“啊,住嘴!”她高声喊道,觉得顿时得到解脱,可以发泄自己的感情了,“我用自己的双手在干什么,谁管得着!”
“瞧我多么傻呀,”她恼火地想,“我应当把皮蒂姑妈的手套借来或者偷到手呀!可是我没发现自己的手那么难看。当然,他是会注意的。现在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看来一切都完了。啊,怎么恰好在他马上就要表白的时刻偏偏发生这种事呀!”
“你的手我当然管不着。”瑞德冷冷地说,一面将身子挪回来,懒懒地靠到椅背上,他的脸上似乎毫无表情。
看来他要变得不好对付了。那么,如果还想从这一挫折中夺回胜利,即使她很不乐意,也得乖乖地忍受些许,只要她甜言蜜语地说说他——
“我看你也太鲁莽了,把我这双手肆意说成那样。只不过上星期我没戴手套骑马,把手弄——”
“骑马,见鬼去吧!”他以同样平板的语调说,“你明明是用这双手在劳动,像个黑鬼一样在劳动。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什么要骗我说在塔拉一切都好呢?”
“现在,瑞德——”
“我看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这次来究竟要干什么?我几乎被你虚情假意的媚态迷住了,还以为你真的关心我,替我着急呢。”
“啊,我就是为你着急呀!真的!”
“不,你没有。即使他们把我吊得比海曼还高,你也不会在乎的。这明明写在你的脸上,就像艰苦的劳动写在你手上一样。你是对我有所求,而且这需求非常急迫,才不得不装出这副样子。你干吗不开门见山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呢?那样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满足,因为,如果说女人有什么品性让我赞赏的话,那就是坦率了。可是不,你到这里来,却像个妓女晃荡着丁丁响的耳坠子,撅着嘴,嬉笑着讨好一位嫖客似的。”
他讲最后几句话时并没有提高嗓门或用别的方式加重他的语气,可是这些话对于思嘉仍然像鞭子一样噼啪作响,这使她伤心地看到她引诱他向她求婚的愿望破灭了。要是他大发脾气,伤害她的虚荣心,或者斥责她,像别的男人那样,她还能够对付。然而他可怕的平静声调却把她吓蒙了,使她根本无从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尽管他是个犯人,北方佬就在隔壁,可她突然觉得巴特勒是个危险人物,谁也休想去冲撞他。
“我看我的记忆力出毛病了。我本来应当记得你这个人跟我一样,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没有一个隐秘的动机。现在让我猜猜,你究竟打的什么主意,汉密尔顿太太?你不会糊涂到认为我会向你求婚吧?”
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可是她没有回答。
“不过你不该忘记我经常讲的那句话,就是说,我是不准备结婚的。”
她还是一言不发,这时他忽然粗暴地问:
“你没有忘记吧?回答我。”
“没有忘记。”她无可奈何地答道。
“思嘉,你可真是个赌徒!”他讥讪地说,“你想碰碰运气,以为我蹲在监狱里,不能同女人亲近了,便会像鳟鱼咬饵似的把你一手抓过来啦。”
“可你正是这样做的呀,”思嘉愤愤地想道,“要不是因为我的这两只手——”
“好,现在我们已经大体上谈清楚了,除了你的理由以外一切都明白了。就看你敢不敢老实对我说究竟为什么要引诱我结婚。”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温和的、甚至是挑逗人的语调,这使她又有了勇气。也许到头来并没有全完蛋呢?当然,她已经把结婚的希望给毁了,不过,即使在绝望中她也不无高兴之处。这个木然不动的男人身上有些叫她恐惧的地方,因此她现在觉得那种同他做夫妻的念头是可怕的。可是,如果她能机灵些并利用他的同情心和记忆,她也许还能得到一笔借款。于是她装出一副稚气的想要和解的样子来。
“唔,瑞德,你能给我很大的帮助——只要你为人温和一点就好了。”
“为人温和——这是我最乐意不过的了。”
“瑞德,讲点老交情,我要你帮个忙。”
“看来这位磨硬了手心的太太终于要谈谈自己的使命了。我担心你扮演的真正角色并不是‘探监’。你到底要什么呢,钱吗?”
他问得这么直截了当,使她原先设想用委婉动情的迂回手法来诱导的计划一笔勾销了。
“别那么小气吧,瑞德,”她娇声娇气说,“我的确需要一笔钱。我要你借给我三百美元。”
“到底说真话了。讲的是爱情,要的是金钱。多么地地道道的女性呀!这钱要得很急吗?”
“唔,是——嗯,也不那么急,不过我要用。”
“三百美元。这是一大笔钱呢。你拿它干什么?”
“交塔拉的税金。”
“你原来是要借钱。好吧,既然你跟我讲生意经,我也就跟你讲生意经了。你给我什么作抵押呢?”
“什么——什么?”
“抵押。作为我的投资担保。我当然不想把这笔钱白白丢掉。”他的口气很圆滑,甚至有讨好的意思,可是她没在意。也许到头来一切都蛮不错呢。
“拿我的耳环。”
“我可不喜欢耳环。”
“我愿意用塔拉作抵押。”
“这时候我要个农场干什么?”
“喏,你可以——你可以——那是个上好的种植园呢。你决不会吃亏的。我一定拿明年的棉花来偿还你。”
“我倒觉得不怎么可靠。”他往椅背上一靠,把两只手插进衣袋里,“棉花价格正在一天天下跌呢。时世那么艰难,钱又那么紧。”
“啊,瑞德,你这不是逗我玩吗!你明明有几百万的家当嘛。”
他打量着她,眼里流露出一丝温暖而捉摸不定的恶意。
“看来一切都满顺利,你并不十分需要那笔钱喽。那好,我听了心里也很高兴。我总是盼望老朋友们万事如意。”
“啊,瑞德,看在上帝的面上……”她开始着急起来,勇气和自制都失灵了。
“请你把声音放低些。我想你不至于要让北方佬听到你的话吧。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像只猫——黑暗中的猫——,眼睛尖得很呢!”
“瑞德,别这么说!我愿意把一切都告诉你。这笔钱我的确要得很急。我——我说一切顺利,这是在撒谎。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我爸已经——已经——精神恍惚了。从我妈死后,他就变得古怪起来,对我没有任何帮助。他完全像个孩子了。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会干田间活的人去种棉花,可需要养活的人却很多,一共十三个。何况税金——高得很呢。瑞德,我把什么都告诉你。过去一年多,我们差点儿没饿死呢。啊,你不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呀!我们一直不够吃,白天黑夜的挨饿,那滋味真可怕啊!而且我们没有什么暖和的衣裳,孩子们经常挨冻,生病,还有——”
“那你这身漂亮衣着又是从哪里弄到的?”
“这是用母亲的窗帘改做的,”她答道,因为心里着急,编不出谎话来掩盖这桩有失体面的事了,“挨饿受冻我能忍受得住,可如今——如今那些提包党人把我们的税金提高了,而且必须立即交钱。但是除了一个五美元的金币,我什么钱也没有。我非得有钱来交那些税款不行了。难道你还不明白?要是我交不出,我就会——我们就会失掉塔拉,而我们是万万不能失掉它的!我决不放走它!”
“你干吗不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些情况,却来折磨我这颗敏感的心——常常一碰到漂亮女人就要发软的心呢?不,思嘉,不要哭。你除了这一着外什么手段都采用过了,可这一着我恐怕是经受不住的。当我发现原来你所需要的是我的钱而不是我这个有魅力的人时,失望和痛苦便把我的感情撕碎了。”
她记起,每当他嘲讽别人时,总是说一些有关自己的大实话,于是她便赶快抬起头来看着他。难道他的感情真正被伤害了?他真的有意于她吗?当他看她的手时,他是预备提出结婚的要求了吗?或者他那时仅仅准备像以前两次一样提出那种可厌的要求来呢?要是他真正有意于她,或许她还能使他温驯下来。然而他的黑眼睛紧盯她时不是用一种爱人般的神态,而是在轻轻地嬉笑呢。
“我不稀罕你的抵押品。我不是什么种植园主。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拿得出来吗?”
好,他终于谈到正题上来了。该摊牌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勇敢地面对着他的目光。她既然敢于冲出去抓那件她最害怕的东西,一切的风情媚态便都不复存在了。
“我——我还有我自己。”
“是吗?”
她的下颚紧张得成了方形,她的眼睛变成翡翠的颜色。
“你还记得围城期间在皮蒂姑妈家走廊上的那个夜晚,你说过——那时你说过你是要我的。”
他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向后一靠,注视着她那紧张的脸,同时他自己的棕色脸庞上露出一种莫测高深的表情。仿佛有什么在他眼睛后面闪烁,可是他一声不响。
“你说过——你说你从来没有像现在想要我这样想要过任何一个女人。如果你还想要我,你就能得到我了。瑞德,干什么我都行,你说好了。不过看在上帝面上,你得给我开张支票!我说话算数。我发誓决不食言。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立个字据。”
他古怪地看着她,仍然难以捉摸,因此当她迫不及待地接着说下去时也弄不清他究竟是高兴还是在无可奈何地听着。她巴不得他能说点什么,无论说什么都好啊!她觉得自己脸上发烧了。
“我得马上要这笔钱呢,瑞德。他们会把我们赶出门去,然后我爸的那个天杀的监工就会来占领,并且——”
“别急嘛。你怎么会认为我还要你呢?你怎么会认为你值三百美元呢?大部分女人都不会要价那么高呀。”
她的脸顿时通红,心里感到莫大的侮辱。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为什么不放弃那个农场,住到皮蒂帕特小姐家去呢?那幢房子你有一半嘛。”
“天哪!”她叫道,“难道你是傻瓜?我不能放弃塔拉,它是我们的家嘛。我决不放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
“爱尔兰人真是最不好对付的民族,”他说着,一面向后靠在椅子上躺平,把两只手从衣袋里抽出来,“他们对许多没意思的东西,譬如,土地,看得那么重。其实这块地和那块地完全一样嘛。现在,思嘉,让我把这件事说个明白吧。你是到这里来做交易的了。我愿意给你三百美元,你呢,做我的情妇。”
“好。”
这个讨厌的字眼一经说出,她便觉得轻松多了,同时希望也在她心中重新升起。他说了“我愿意给你”呢。那时他眼里闪耀着一丝残忍的光辉,仿佛有什么叫他大为高兴似的。
“不过,我以前厚着脸皮向你提出同样一个要求时,你却把我拒之于门外。而且还用许多十分恶毒的话骂我,并捎带声明你不愿意养‘一窝小崽子’。不,亲爱的,我不是在揭疮疤。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古怪心理。你不愿意为自己享乐做这种事,但为了不饿肚子却愿意做了。这就证明了我的观点,即一切所谓的品德都只不过是个代价问题罢了。”
“唔,瑞德,看你说的!要是你想侮辱我,你就继续说下去吧,不过得把钱给我。”
现在她平静了一些。出于本性,瑞德自然要尽可能折磨她,侮辱她,对她以往的轻视和最近蓄意耍的手腕进行报复。好吧,她能够忍受,什么都能忍受。为了塔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一会儿,她想象着在仲夏天气,午后的天空蓝湛湛的,她昏昏欲睡地躺在塔拉草地上浓密的苜蓿里,仰望飘浮的朵朵白云,吸着白色花丛中的缕缕清香,静听着蜜蜂愉快而忙碌地在耳旁嗡嗡不已。午后的寂静和远处那些从红土地里归来的大车的声音,更使人悠然神往。这一切完全值得你付出代价,还不止值得呢!
她抬起头来。
“你准备把钱给我吗?”
他那模样仿佛正自得其乐似的,但他说起话来语气中却带着残忍的意味。
“不,我不准备给。”
这句话出人意料,一时间她的心情又被搅乱了。
“我不能把钱给你,即使我想给也不行。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在亚特兰大一个美元也没有。是的,我有些钱,但不在这里。我也不准备告诉你钱有多少,在什么地方。可是如果我想开张支票,北方佬就会盯住我,像只鸭子盯住一只无花果虫那样,那时我们谁也休想拿到它了。你说呢?”
她的脸色很难看,都发青了,那些斑点突然在她的鼻子两边显露出来,而那张扭歪的嘴和杰拉尔德激怒得要杀人时一模一样。她忽地站起来,怪叫了一声,这使得隔壁房间里的嗡嗡声都突然停止了。瑞德也迅猛得像头豹子,一下跳到她身边,用一只手狠狠捂住她的嘴,另一只紧抱住她的腰。她拼命挣扎着反抗他,想咬他的手,踢他的脚,尖叫着借以发泄她的愤怒、绝望和那被伤害了的自尊心。她弓着身子左右前后地扭动,想挣脱他那只铁一般的胳臂,她的心就要爆炸了,她那紧箍着的胸衣勒得她快要断气了。他那么紧、那么粗暴地将她抱住,使她疼痛不堪,而那只捂在她嘴上的手已残忍地卡进了她的两颚之间。这时他那棕黑的脸已紧张得发白了,他的眼光严峻而炙热,他把她完全举了起来,将她高高地紧压在他的胸脯上,抱着她在椅子上坐下,任凭她继续挣扎。
“乖乖,看在上帝面上,别再做声,别嚷嚷了!再嚷,他们马上就会进来。快静一静。难道你要北方佬看见你这副模样吗?”
她已顾不得谁看见她怎样了,什么都不顾了,只是火烧火燎,一心要杀死他,不过这时她浑身感到一阵晕眩。他把她的嘴捂住,她都不能呼吸了;她的胸衣像一根迅速缩紧的铁带;两只胳臂抱着她使她怀着无可奈何的仇恨和愤怒在浑身颤抖。随后他的声音渐渐减弱了,模糊了,他那张俯视着她的脸在一片令人作呕的迷雾中旋转起来,这片迷雾愈来愈浓,直到她再也看不见他——也看不见任何别的东西了。
当她轻轻扭动身子,渐渐恢复知觉时,她感到浑身彻骨地疲倦、虚弱和迷惑不解。如今她是躺在椅子上,帽子脱了,瑞德正在拍打她的手腕,一双黑亮的眼睛焦急地察看着她的脸色。那个好心的年轻队长正动手将一杯白兰地灌进她嘴里,可是酒洒出来,流到脖子上去了。其他军官不知所措地在旁边走来走去,摆着手悄悄地议论。
“我想——我准是晕过去了。”她说完觉得自己的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便不由得害怕了。
“把这杯酒喝下去吧。”瑞德说,端过酒杯送到她嘴边。这时她想起来了,但只能无力地狞视着他,因为她已疲乏得连发火的力气也没有了。
“请看在我的面上,喝吧。”
她喝了一口便呛得咳嗽起来,可是瑞德又把杯子送到她嘴边。这样她便喝了一大口,那烈性液体立即从喉管里火辣辣地冲下去了。
“我看她已经好些了,先生们,我十分感谢你们,”瑞德说,“她一明白我将要被处决,就受不了啦。”
穿蓝制服的军官们在地上擦着脚,显得很尴尬。他们干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便出去了。只有那个年轻队长还待在门口。
“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
“没有了,谢谢你。”
他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
“再喝一点。”瑞德说。
“不了。”
“喝了吧。”
她又喝了一大口,热流开始向全身灌注,力气也缓缓地回到两只颤抖的大腿上。她推开酒杯,想站起来,可是他又把她按了回去。
“放开我吧,我要走了。”
“现在还不行。再过一会儿。你还会晕倒的。”
“我宁愿晕倒在路上也不要跟你待在这里。”
“反正都一样,我总不能让你晕倒在路上呀。”
“让我走。我恨你。”
听她这么一说,他脸上又露出一丝笑意。
“这话才像你说的。你一定感觉好些了。”
她轻松地躺了一会,想凭怒气来支撑自己,同时汲取一点力量。可是她太疲乏了。她已经疲乏得不想去恨谁,以致对一切都不怎么在乎了。失败像铅块一般压抑着她的精神。她孤注一掷,结果输个精光!连自尊心也没有了。这是她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这是塔拉的下场,是他们全体的下场。她仰靠在椅背上躺了好一会,闭着眼睛,静听着身边瑞德沉重的呼吸,这时白兰地的热劲已逐渐渗透全身,带给她以温暖和一种虚假的力量。末了她睁开眼睛,凝望着他的面孔,怒气又油然而生。当她那双高挑的眉毛向下一落显出一副蹙额不悦的神气时,瑞德原先那种微笑又重新出现了。
“现在你好些了。从你这眉头一皱的神态就看得出来。”
“当然,我完全好了。瑞德·巴特勒,你这人真可恨,如果说我见过流氓的话,你就是个流氓,我一开口你就明明知道我要说什么,同时也打定主意不给我那笔钱。可是你还让我一直说下去。你本来可以不要我说了——”
“不要你说,白白放弃机会不听你说的整个故事吗?不大可能。我在这里太缺少可供消遣的玩意了。我还真的从没听过这么令人满意的故事呢!”他忽然又像往常那样嘲讽地大笑起来。她一听这笑声便跳起来,抓起她的帽子。
他猛地抓住她的肩膀。
“现在还不行。你觉得完全好了可以谈正经话了吗?”
“让我走!”
“我看你是完全好了。那么,请你告诉我,我是你火中惟一的一块铁吗?”他的眼光犀利而警觉,审视着她脸上的每一丝变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不是你要玩弄这把戏的惟一对象?”
“这同你有什么关系呢?”
“比你所意识到的关系要大得多。你的钓丝上还有没有别的男人?告诉我!”
“没有。”
“这不可信。我不能想象你就没有五六个后备对象保留在那里。一定有人会站出来接受你这个有趣的提议。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因此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忠告。”
“我不需要你的忠告。”
“可我还是要给你。目前我能给你的大概也只有忠告了。听着,因为这是个好的忠告。当你想从一个男人身上取得什么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像对我这样直通通地说出来。要装得巧妙一些,更带诱惑性一些,那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你自己是懂得这一着的,而且很精通,可就在刚才,当你把你的——你借钱的——抵——押——品提供给我时,你却显得像铁钉一样生硬。我曾经在距我二十步远的决斗手枪上方看见过像你这样的眼睛,那可不是令人舒服的景象。它激不起男人胸中的热情。这玩意不能用来操纵男人,亲爱的。看来你快要把早年受的训练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的行为用不着你来教训。”她说,一面疲惫地戴上帽子。她不明白他怎能在自己脖子上套着绞索和面对她的可怜处境时还这么开心地说笑。她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两手捏着拳头插在衣袋里,似乎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在竭力挣扎。
“振作起来吧,”他说,一面看着她把帽带系好,“你可以来观看我的绞刑,这会使你舒坦多了。那样一来,我们之间的旧账——包括这一次在内,就一笔勾销了。我还准备在遗嘱里提到你呢。”
“谢谢你,不过他们也许迟迟不给你行刑,到时候再交纳税金也就晚了。”她说这话时突然发出一声与他针锋相对的狞笑,她的话的确也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