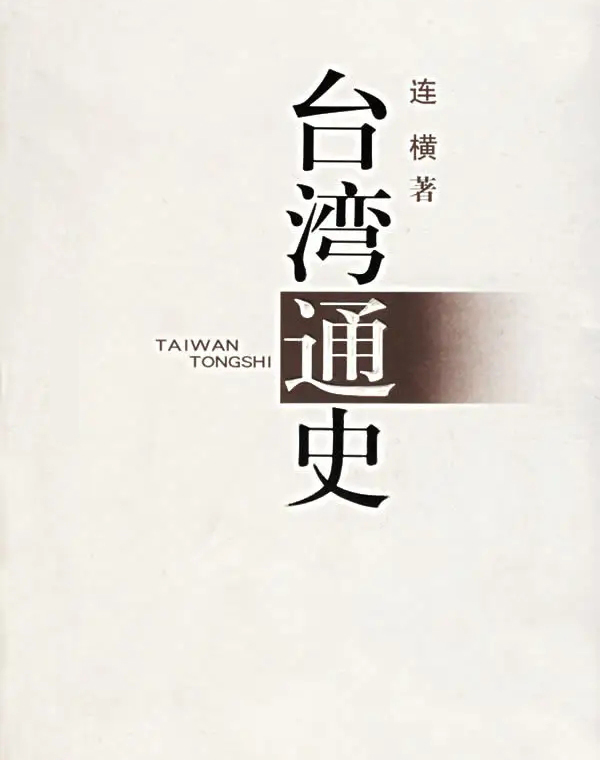第三十五章
她从消防站走出来时正在下雨,天空是阴沉沉的一片浅灰色。广场上的士兵们都到棚屋里躲雨去了,大街上也很少有行人。她看不见哪里有什么车辆,便明白自己只能一路步行回家,可路还远着呢。
她一路艰难地走着,白兰地的热劲渐渐消退了。寒风吹得她瑟瑟发抖,冷如针刺的雨点迎面向她打来。雨水很快淋透了皮蒂姑妈那件薄薄的外套,弄得它黏糊糊地贴着她的身子。她知道那件天鹅绒新衣也快糟蹋完了,至于帽子上的羽毛已水淋淋地耷拉下来,就像它们原先的主人雨天戴着它们在塔拉后仓场院里走动时那样。人行道上的砖块多已损坏,而且大段大段的路面上已完全没有砖了。这些地方泥泞已经齐脚踝深,她的便鞋陷在里面像被胶粘住似的,有时一拔脚鞋就掉了。每回她弯下腰去用手提鞋时,衣服的前襟便落在泥里。她甚至懒得绕过泥坑,而随意踏到里面,撩着沉重的衣裾径直走过去。她能感觉到那湿透了的裙子和裤腿边缘冰冷地纠缠在脚踝上,可是她已不再去关心这套衣裳的命运了,尽管在它身上她曾经押了那么大一笔赌注。她只觉得凄冷、沮丧和绝望。
她怎么好在说过那些大话之后就这样回到塔拉去见大伙呢?她怎能告诉他们,说他们都得流落到别处去呢?她怎能丢下那一切,丢下那些红色的田地、高大的松树、褐黑色的沼泽腹地、寂静的坟地呢?那坟地上的柏林深处还躺着她的母亲爱伦呀!
她在溜滑的道路上吃力地走着,心中又燃起了对瑞德的仇恨之火。这人简直是个无赖!她巴不得他们把他绞死,免得她日后再要同这个对她的丑事和受的屈辱了如指掌的人见面。当然,要是他愿意,他是完全可以替她弄到那笔钱的。啊,绞刑还太便宜了他呢!感谢上帝,他现在已经看不见她,看不见她浑身湿透、披头散发、牙关打颤的模样!她一定显得十分难看,而他见了准会哈哈大笑的!
她一路上遇到的一些黑人都对她露齿而笑,他们还相互嬉笑着看她在泥泞中连行带滑地匆匆走过,有时停下来喘着气换鞋,显得非常狼狈。他们竟敢笑话她,这些黑猴儿!他们竟敢对她这位塔拉农场的思嘉·奥哈拉小姐龇牙咧嘴!她恨不得把他们全都痛打一顿,打得他们的脊背鲜血淋漓。那些把他们解放、让他们来嘲笑白人的北方佬,真该死啊!
她沿着华盛顿大街走去,这时周围的景色同她自己的心情一样阴沉。这里一点也没有她在桃树街见到的那种喧闹和欢乐气氛。这里曾经有过许多漂亮的民房,但如今很少有重建起来的。那些经过烟熏火燎的房基和黑乎乎的烟囱(如今叫做谢尔曼的哨兵)令人沮丧地不断出现。杂草丛生的小径所到之处,往往是原来有房子的地方,或者是早已荒废的旧草地,标着她所熟悉的名字的停车间,以及再也不知缰绳为何物的拴马桩,等等。眼前只有寒风冷雨、泥泞和光秃秃的树,寂静与荒凉。她的双脚多么湿冷,回家的路又是多么长啊!
她听到背后马蹄蹚水的声音,便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更往里靠一点,免得让更多的污泥溅上皮蒂姑妈的那件外套。一辆四轮马车在街上缓缓地驶着,她回过头去观看,要是赶车的是个白人便决定求他带上一程。当马车来到近旁时,她在雨雾中虽然看得不怎么清楚,但看得见驾车的人从高高的防雨布后面探出头来,他的面貌似曾相识。她走上街道去仔细一看,那人不好意思地轻轻咳了一声,随即用一种熟悉的声音惊喜地喊道:“怎么,那不会是思嘉小姐吧?”
“啊,肯尼迪先生!”她喊着,蹚过街道,俯身靠在泥泞的车轮上,也不管那件外套会不会弄得更脏了,“我遇见谁也没像现在这样高兴过呢!”
他一听她说得这么亲热就高兴得脸都红了。随即从马车对面吐出一大口烟叶汁,然后轻快地跳下来。他热情地同她握了握手,掀起那块防雨布,扶她爬上车去。
“思嘉小姐,你一个人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你不知道近来这里很危险吗?而且你浑身湿透了。赶快拿这条毯子把脚裹起来。”
当他像只咯咯叫的母鸡忙着照料她时,她一动不动,乐得享受他的殷勤好意。有这么一个男人,即使是弗兰克·肯尼迪这么个婆婆妈妈的男人也好,在身边忙活,咯咯地叫,疼爱地责怪她,那有多美呀!在刚刚受过瑞德的冷遇之后,便尤其感到惬意了。还有,在她远离家乡时看到一张同乡人的面孔,更是多么可喜的事呀!她注意到他穿得很好,马车也是新的。那匹马显得年轻膘壮,可是弗兰克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多了,比他和他的那伙人到塔拉时那个圣诞之夜又苍老了些。他很瘦,脸色憔悴,一双发黄多泪的眼睛深陷在面部松弛的皱褶里。他那把姜黄色的胡子显得比以前少了,上面沾着烟叶汁,而且有点蓬乱,仿佛他在不断地搔它似的。然而,在思嘉到处碰到的那些愁苦、忧虑而疲惫的面孔对比下,他看来还算是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的呢。
“看到你很高兴,”弗兰克热情地说,“我不知道你到城里来了。上星期我还见到皮蒂帕特小姐,可她没有说起你要到这里来。有没有——嗯——有没有别人从塔拉跟你一道来?”
他在想苏伦呢,这可笑的老傻瓜!
“没有,”她说,一面用那条暖和的旧毛毯把身子裹好,并试着将它拉上来围住脖子,“我一个人来的,事先也没有通知皮蒂姑妈。”
他对马吆喝了一声,车轮便开始转动,谨慎地在泥滑的街道上行驶起来。
“塔拉的人都好吧?”
“唔,是的,都还可以。”
她必须想出点事情来说说才好,可是要谈起来也真不容易。她的心情沮丧得像铅一般沉重,因此她只想裹着暖和的毯子,仰靠着独自思量:“现在我不想塔拉的事,以后再去想吧,那时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了。”要是她能引这老头谈一个可以一路谈下去的话题就好了,那时她就用不着说什么话,只需间或说一声“真好”或“你真能干”就行了。
“肯尼迪先生,我真没想到会遇见你呢!我明白自己太不应该了,没有同老朋友们保持联系,不过我并不知道你到了亚特兰大。仿佛有人跟我说过你是在马里塔嘛。”
“我在马里塔做买卖,做过不少买卖呢,”他说,“苏伦小姐没有告诉你我已经在亚特兰大落脚了吗?她没有对你说起过我开店的事?”
她模糊地记得苏伦唠叨过弗兰克和他的铺子,可是她从来就不注意苏伦口里的话。她只要知道弗兰克还活着和他总有一天会把苏伦从她手里领走就足够了。
“不,她一句也没说,”她撒了个谎,“你开了个铺子?看你多能干呀!”
他听说苏伦竟没说关于他的消息,心里颇为难过,可是随即思嘉的一句恭维话又使他乐开了。
“是的,我开了个铺子,并且我觉得还是个满不错的铺子。人们说我是个天生的买卖人呢。”他开心地笑着,他那似乎忍不住的咯咯笑声,思嘉一听就觉得讨厌。
她心想:看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傻瓜!
“唔,你无论干什么都一定会成功的,肯尼迪先生。不过你怎么居然会开起店来了呢?记得前年圣诞节你说过你手里一分钱也没有嘛。”
他刺耳地假咳了几声,又搔了搔胡子,流露出一丝羞涩不安的微笑。
“唔,说来话长,思嘉小姐。”
真是谢天谢地!她心想。也许这可以让他唠叨下去,不到家不罢休了。于是她高声嚷道:“你就说吧!”
“你记得我们上次到塔拉搜集军需品的时候吧?对了,就在那以后不久,我便积极行动起来。我的意思是投身于真正的战争。因为我已经没有别的差使好干了。那时候也不怎么需要原来这种差使,因为,思嘉小姐,我们已经很难给军队做什么事了;所以我想对于一个身体还不错的人来说最好是去参战。于是我便跟着骑兵打了一阵子,直到肩膀上挨了一颗小小的子弹。”
他显得很骄傲,这时思嘉说:“多可怕呀!”
“唔,那也没有什么,只不过皮肉受了点伤罢了,”他似乎不大赞成思嘉这么大惊小怪,“后来我被送进南边一家医院,等到我快要好起来时,不料北方佬的突击队冲过来了。乖乖,乖乖,那可真叫紧张啊!我们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突然消息传来,凡是能够行走的人都得帮助把军备物资和医院设备搬到铁路上去启运。我们刚要装完一列货车时,北方佬冲进了城镇的一端,于是我们只好尽快从另一端撤出去。乖乖,乖乖,多么凄惨的一幅景象呀,你坐在列车顶上眼看着北方佬焚烧那些我们不得不丢在站台上的军需品。思嘉小姐,他们把我们堆置在铁路旁边长达半英里的物资全都烧掉了。我们仅仅让自己空着手逃出来了。”
“多可怕呀!”
“是的,就是这样。可怕呀。那时我们的人已回到亚特兰大,我们的火车也就开到了这里。你看,思嘉小姐,那已经是战争结束前不久的事,因此——好了,有许多的瓷器、帆布床、床垫、毯子等等没有人来认领。我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北方佬的东西。我想这些就是我们投降的条件吧,难道不是吗?”
“唔。”思嘉心不在焉地应着。她现在已渐渐暖和过来,有点瞌睡了。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到底做得对不对,”他带点发牢骚的口气说。“不过据我看来,这批物资对北方佬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很可能会把它烧了。而我们的人却为它付出了硬邦邦的现款,因此我觉得它应当仍属于联盟政府或属于联盟政府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唔。”
“我很高兴你同意我的看法,思嘉小姐。不知怎的,我良心上总有点过意不去。有不少人对我说:‘哎,忘了它吧,弗兰克,’可我就是忘不了。只要我做了点什么亏心事,我就抬不起头来。你认为我做得对吗?”
“当然对。”她说,但不明白究竟这个老傻瓜刚才都说了些什么。似乎,是良心上有点不自在。一个人到了弗兰克这个年纪,应当早就学会不去介意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了。可他却总是这样胆小怕事,小题大作,像个老处女似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高兴了。宣布投降以后,我有大约十块银元,别的一无所有。你知道他们对琼斯博罗和我在那里的房子和店铺都干了些什么。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可是我用这十块钱在五点镇旁边一家旧铺子上盖了个屋顶,然后将那些医院设备搬进去并做起买卖来。谁都需要床、瓷器和床垫的,我便把它们卖便宜一点,因为我琢磨着这些现在归我所有的东西本来也可能属于别人的嘛。不过我用卖得的钱又买来更多的东西。这样一来,生意就满不错了。我想只要继续兴旺下去,我是会从中赚到许多钱的。”
一谈到“钱”这个字,她的心思一清二楚地回到他身上来了。
“你说你赚了钱是吗?”
他发现她有兴趣,显然更加起劲了。除苏伦之外,还很少有女人向他表示过超乎敷衍的殷勤呢。如今得到像思嘉这样一位他曾经倾慕过的美人来倾听他的话,真是莫大的荣幸了。他让马走慢一点,好叫他们在他的故事结束之前不会到家。
“我还不是百万富翁呢,思嘉小姐;而且想到我从前有过那么多的钱,目前所有的就显得少了。不过我今年赚了一千美元。当然,其中的五百美元已用在进新货、修理店铺和交纳税金上。我只是净挣了五百美元,并且从眼前必然兴旺的趋势看,明年我应当能净赚两千美元。这笔钱我也完全用得着的,因为,思嘉小姐,我手头还有一桩活儿准备干呢。”
思嘉一谈起钱就兴致勃勃了。她垂下那两扇浓密而不怎么驯顺的眼睫毛微微地觑着他,同时挪动身子向他靠近了一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肯尼迪先生?”
他笑笑,将手中的缰绳在马背上抖了抖。
“我想,尽谈这些生意经会叫你厌烦的,思嘉小姐。像你这样一位美人儿,是用不着懂生意上的事的。”
看这老傻瓜。
“唔,我知道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可是我非常感兴趣呀!请你只管讲下去吧,我不懂的地方你可以解释嘛!”
“好吧,告诉你,我另一桩要办的事是个锯木厂。”
“什么?”
“一个锯木料和刨木板的厂子。我还没有把它买到手,可是正准备买。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有这么个厂子,在桃树街那头,他急于要卖掉它。他眼下需要一笔现款,所以想卖给我,同时准备自己留下来替我经营,工资按周支付。这一带只剩下很少几家锯木厂,其余的都叫北方佬给毁了。现在谁要是有这么一家,谁就等于有了一个金矿,因为近来卖木材可以自己要价,要多少算多少呢。北方佬在这里烧掉了那么多的房子,如今人们住房不够,便发疯似的一个劲儿盖房。他们弄不到木料,或者缓不应急。人们还在大量拥进亚特兰大,他们全是从乡下来的,因为没有了黑人,已无法从事农业;还有就是那些北方佬和提包党人,他们也蜂拥而来,想把我们已经刮过的骨头刮得更干净一点。我告诉你,亚特兰大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大城市。人们需要木料盖房子,所以我想尽快买下这家锯木厂——尽快,只要收集到一部分赊欠户的账就动手买。到明年这时候,我手头便会松多了。我——我想你是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挣钱的,难道不是吗?”
他脸红了,又呵呵地笑起来。他在想苏伦呢,思嘉只觉得讨厌。
她考虑了一会,想问他借三百美元,但又觉得没意思,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会感到不好办的,他会支支吾吾,会找到借口,总之是不会借给她的。他辛辛苦苦挣了这点钱,到春天便可以同苏伦结婚了,可是如果拿钱作了旁的用途,他就不得不再推迟婚期。即使她设法博得他的同情和对未来家庭的责任感,让他答应借笔钱给她,她知道苏伦也绝不会允许的。苏伦愈来愈明白她事实上已成了个老姑娘,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容许任何人再来推迟她的婚期了。
这个成天唉声叹气的姑娘,她身上究竟有何妙处会使得这个老傻瓜急于要给她安排一个安乐窝呢?苏伦不配有这么个心爱的丈夫,也不配做一个商店和一家锯木厂的老板娘。一旦她手头稍稍有了点钱,她就会摆起令人作呕的架子而决不会为保存塔拉拿出一分钱来的。苏伦决不会的!她只会拿那笔钱图自己的舒服,也不管塔拉是否因交不起税金而丧失或者被烧得一干二净,只要她自己能穿上漂亮衣裳,同时拐得个“太太”的称号就行了。
思嘉想起苏伦安乐的未来和自己与塔拉岌岌可危的命运,不禁怒火中烧,觉得人生太不公平了。她连忙从马车里向泥泞的街道望去,生怕弗兰克发现她脸上的表情。她想她快要丧失所有的一切了,而苏伦呢——突然之间,她心上萌生了一个决心。
苏伦不应当享有弗兰克,以及他的商店和锯木厂!
苏伦不配享有它们。思嘉要把它们据为己有。她想起塔拉,也想起乔纳斯·威尔克森,他恶毒得像条响尾蛇,站在屋前台阶上,这时她抓住了命运之船沉没时上面飘浮着的最后一根稻草。瑞德叫她失望了,但上帝给她送来了弗兰克。
“可是,我能得到他吗?”她紧握十指,茫然地向雨中凝望,“我能够让他忘掉苏伦立即向我求婚吗?既然我能够让瑞德也几乎向我求婚了,我想我是准能得到弗兰克的!”她侧过脸来,朝他浑身上下迅速地瞟了一眼,“他的确不怎么漂亮,牙齿长得很难看,呼吸中有股臭味,而且老得可以当我父亲了——”她这样冷冷地思忖着,“此外,他还有些神经质,胆小怕事,婆婆妈妈,这些我看是一个男人所能有的最糟糕的品性了。不过他至少是个上等人,我想我可以凑合着同他生活,比同瑞德过得还好些。他当然更容易由我操纵。不管怎样,一个穷得像乞丐的人是没有权利挑选的。”
他是苏伦的未婚夫,这一点并没有在她身上引起良心的不安。要知道,正是道德上的彻底破产促使她到亚特兰大来找瑞德的,事到如今,把她妹妹的情人据为己有便显得只是小事一桩,不值得为它伤脑筋了。
既然有了新的希望,她的腰杆便硬起来,也忘记双脚又湿又冷的难受劲儿了。她眯着眼睛坚定地望着弗兰克,以致他颇觉惊恐,她也连忙把眼光移开,因为记得瑞德说过:“我在一支决斗的手枪上方看见过像你这样的眼睛……它们是不会激起男人胸中的热情的。”
“怎么了,思嘉小姐?你觉得冷吗?”
“是呀,”她无可奈何地答道,“你不会介意——”她胆怯地支吾着,“要是我把手放进你的外套口袋里,你不会介意吧?天这么冷,我的皮手筒又湿透了。”
“唔——唔——当然不会了!何况你连手套也没有戴!真是,真是,看我这老糊涂,一路上只顾这么慢吞吞地闲聊,聊得都昏头昏脑了!也没想到你在挨冻,需要马上烤烤火呢!快,萨利!顺便说说,思嘉小姐,我老是忙着谈自己的事,也没问问你在这鬼天气跑到这一带来干什么?”
“我刚才到北方佬总部去了。”她不加思索地答道。他听了大吃一惊,两道灰黄的眉毛直竖起来。
“可是,思嘉小姐!那些大兵——唔——”
“圣母马利亚,让我想出个上好的谎言来吧。”她急忙暗暗地祈祷。对于弗兰克来说,是万万不能让他疑心到她见过瑞德了。弗兰克认为瑞德是个最卑劣的无赖,一个规矩女人连跟他说话也是很不妥当的。
“我去那儿——我去那儿看看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军官要买我的针线活儿带回去送给他们的妻子。我的绣花手艺蛮不错呀。”
他惊慌得往座位上沉重地一靠,厌恶之情与惶惑的感觉在他脑子里揪斗起来。
“你到北方佬那里去——可是思嘉小姐!你不应当去的。你看——你看……肯定你父亲不知道!一定的,皮蒂帕特小姐——”
“啊,要是你告诉皮蒂姑妈我就完了!”她真的焦急得哭起来了。要哭是容易的,因为她身上又冷,心里又难受,可是哭的效果却惊人地显著。弗兰克感到很难为情又毫无办法,这样的困境即使是思嘉突然要把衣服脱下来也不过如此了。他的舌头好几次顶着牙齿发出啧啧的声音,叨念着“天啊,天啊!”同时做出无可奈何的手势。他心里忽然冒出个大胆的念头,想把她的头搂过来靠在自己肩上,抚慰她,拍拍她,可是他从来没有对任何女人这样做过,也不懂该怎样动手。思嘉·奥哈拉,一位漂亮得无以复加的年轻太太,正想把自己的针线活儿兜售给北方佬呢。他的心燃烧起来了。
她继续啜泣着,间或说一两句话,这便让弗兰克猜想塔拉的景况一定很不妙了。奥哈拉先生仍处于“精神严重失常”的状态,家中又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那许多人。所以她才跑到亚特兰大来想挣点钱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弗兰克嗫嚅了片刻,突然发觉她的头已经靠在他肩上了。他也不大明白它是怎样靠过来的。他确确实实没有挪动过她的头,但是她的头确实已经靠在他肩上,思嘉已经无力地靠在他的胸脯上嘤嘤地哭泣了,这对他来说可是一种又兴奋又新奇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拍着她的肩膀,起初还是怯生生的,后来发现她并不反抗才变得胆大起来,拍得也更起劲了。这是个多么可怜、可爱而又温柔的小家伙呀。她居然尝试着凭自己的针线活儿挣钱,又显得多么勇敢而幼稚可笑!不过,同北方佬打交道就太不应该了。
“我不会告诉皮蒂帕特小姐,可是你得答应我,思嘉小姐,你再也不做这种事了。只要想想你是你父亲的女儿——”
她那翠绿的眼睛无可奈何地搜寻他的目光。
“可是,肯尼迪先生,总得想办法呀。我得照顾我那可怜的孩子,可现在谁也不来管我们了。”
“你是一个勇敢可爱的女人,”他毫不含糊地说,“不过我不想让你做这样的事。要不你的家庭会羞死的!”
“那么我做什么好呢?”她那双泪盈盈的眼睛仰望着他,仿佛她认为他懂得一切,现在就等他的话来决定了。
“唔,眼下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我会想些办法的。”
“啊,我就知道你会的!你真能干——弗兰克。”
她以前从没称呼过他的名字,第一次这么叫他,他听得又高兴又惊讶。这可怜的姑娘大概是糊涂了,连自己说漏了嘴也没发觉。他对她感到十分亲切和满怀爱护。要是他能替苏伦的姐姐做点事情,他一定是乐意做的。他掏出一条红色大手帕递给她,她接过来擦了擦眼睛,然后对他嫣然一笑。
“你看我这个可笑的小笨蛋,”她用抱歉的口吻说,“请不要见怪才好。”
“你才不是小笨蛋呢。你是个十分勇敢可爱的女人,竟想把一副过分沉重的担子挑在自己肩上。我怕的是皮蒂帕特小姐对你不会有多少帮助。我听说她的大部分财产已经丧失,而亨利·汉密尔顿先生自己的景况也不好过。我但愿自己有个家可以接待你。不过,思嘉小姐,请你记住这句话,等到苏伦小姐和我结了婚,我们家里将经常为你保留一席之地,韦德也可以带来。”
现在是时候了!准是圣徒和天使们在守护她,终于给她带来了这么个天赐良机。她设法装成一副吃惊和难为情的样子,张开嘴像马上要说话似的,可是又吧嗒一声闭上了。
“到春天我就要当你妹夫了,别假装你还不知道似的。”他用一种神经质的快乐口吻说。接着,发现她眼里满含泪水,他又惊恐地问:“怎么了,苏伦小姐没有生病吧,难道她病了?”
“啊,没有!没有!”
“一定出什么事了。你得告诉我。”
“啊,我不能!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她一定写信告诉你了呢——啊,真丢人!”
“思嘉小姐,怎么回事呀!”
“唔,弗兰克,我这话本来不想说的,不过我以为,当然喽,你知道——我以为她写了信给你——”
“写信给我说什么?”他焦急得哆嗦起来。
“啊,对一个像你这样的好人做这种事!”
“她做了什么呀?”
“她真的没写信告诉你?唔,我猜想她是太不好意思了。她理应感到羞耻嘛!啊,我偏偏有这么一个丢人的妹妹!”
到这个时候,弗兰克连提问题的勇气也没有了。他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她,脸色发灰,手里的缰绳也放松了。
“她下个月就要同托尼·方丹结婚了。唔,我真抱歉呀,弗兰克。这件事要由我来告诉你,真不是滋味。她实在等得不耐烦了,生怕自己会当老姑娘呢。”
弗兰克搀扶思嘉下车时,嬷嬷正站在屋前走廊上。她显然在那里站了好一会了,因为她的破头巾已经淋湿,那件紧紧围在肩头的旧披肩上也有许多雨点。她那张皱巴巴的黑脸上流露着气恼和忧惧的神色,嘴唇撅得比以往思嘉见过的哪一次都高。她匆匆地瞥了弗兰克一眼,等到发现是谁时才变了脸色——变得又愉快又惶惑,同时掺杂着一丝歉疚的意思。她蹒跚着向弗兰克走来表示欢迎他,但当他要同她握手时,她却咧开嘴大笑着行起鞠躬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