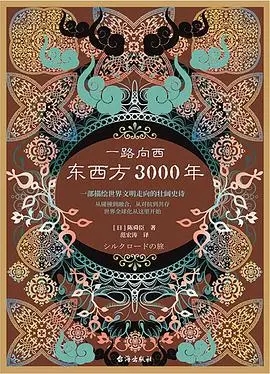思嘉连忙把战火引到敌人的领土上去。
“你为什么这么恨艾希礼?我想你准是妒忌他吧。”
她这话一说,恨不得把舌头咬掉,因为瑞德仰天大笑,弄得她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
“你不但不讲信用,而且还非常自负,”他说,“你以为你这全区的大美人儿可以没完没了地当下去,是不是?你老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小姑娘,男人见了没有不爱的。”
“不对!”她气呼呼地说,“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艾希礼。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个解释。”
“你再想想吧,小妖精,这个解释不对。至于我恨艾希礼——我既不喜欢他,也不恨他。实际上,我对他和他这一类的人只感到怜悯。”
“怜悯?”
“是的,还有一点鄙视。你现在可以像火鸡那样叫唤,你可以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流氓,一千个也顶不上他一个,怎么敢如此狂妄,竟然对他表示怜悯或鄙视呢。等你发完了火,我再向你说明我的意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唔,我没有兴趣。”
“我也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我不忍心让你继续作你的美梦,以为我妒忌他。我怜悯他,是因为他早就应该死了,但他没有死。我鄙视他,是因为他的世界已经完了,但他不知如何是好。”
思嘉觉得他这些话有点耳熟。她模模糊糊记得听到过类似的话,但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的了。她正在气头儿上,所以也没有多想。
“照你那样说,南方所有的正经人就都该死了!”
“要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办,我想艾希礼之类的人是宁可死了的。死了就可以在坟头上竖一块方方正正的碑,上面写着:‘联盟战士为南国而战死长眠于此’,或者写着:‘Dulce et decorum est——’[2]或者写着其他常见的碑文。”
“我看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要是不用一英尺高的字母写出来,放在你鼻子底下,你是什么也看不明白的,对不对?我是说,一了百了,他们死了就不必解决问题了,那些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此外,他们的家庭会世世代代为他们而感到自豪。我听说死人都是很幸福的。你觉得艾希礼·威尔克斯幸福吗?”
“那当然——”她没有说下去,因为她想起最近看到的艾希礼的眼神。
“难道他,还有休·埃尔辛,还有米德大夫,他们都幸福吗?他们比我父亲、比你父亲幸福吗?”
“唉,也许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因为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钱财。”
他笑了。
“不是因为失去了钱财,我的宝贝儿。我告诉你吧,是因为失去了他们的世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里面的那个世界。他们好像鱼离开了水,猫长了翅儿。他们受的教养要求他们成为某一种人,做某一种事,占有某一种地位。李将军一到阿波马托克斯,那种人、那种事、那种地位就都一扫而光了。思嘉呀,看你那副傻样子!你想,现在艾希礼的家没有了,农场也因交税的事而被没收了。至于文雅的绅士,现在一分钱能买二十个。在这种情况下,艾希礼·威尔克斯有什么可做的呢?他是能用脑子,还是能用手干活呢?我敢打赌,自从让他经管木材厂以来,你的钱是越赔越多了。”
“不对!”
“太好了!哪个星期天晚上你有空,让我看看你的账本好吗?”
“你见鬼去吧,而且用不着等你有空。你可以走了,随你的便吧。”
“我的宝贝儿,鬼我见过了,他是个非常无聊的家伙。我不想再去见他,就是你让我去,我也不去了……当初你急需用钱,我借给你,你也用了。我们当时有一个协议,规定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可你违反了这个协议。请你记住,可爱的小骗子,有朝一日你还要向我借钱的。你会让我资助你,利息低得难以想象,这样你就可以再买几家木材厂,再买几头骡子,再开几家酒馆。到那时候,你就别想弄到一个钱。”
“用钱的时候,我会到银行去借。谢谢你吧。”她冷淡地说,但胸口一起一伏,气得不得了。
“是吗?那你就试试看吧。我在银行里有很多的股份。”
“真的吗?”
“是啊,我对一些可靠的企业很感兴趣。”
“还有别的银行嘛——”
“银行倒是不少。不过我要是想点办法,你就别想从他们那里借到一分钱。你要是想用钱,去找北方来的放高利贷的吧。”
“我会很高兴去找他们的。”
“你可以去找他们,但是一听他们要的利息,你是不会高兴的。我的小宝贝儿,你要知道,生意人之间,搞鬼是要受罚的。你应该规规矩矩地跟我打交道。”
“你不是个好心人吗?又有钱,又有势,何必跟艾希礼和我这样有困难的人过不去呢?”
“不要把你自己和他扯在一起。你可算不上有困难。什么也难不住你。但是他有困难,而且解脱不了,除非他一辈子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支持他,引导他,保护他。我决不希望有人拿我的钱来帮助这样一个人。”
“你就曾帮过我的忙,当时我有困难,而且——”
“你是个冒险家,亲爱的,是个很有意思的冒险家。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依赖亲属中的男人,没有为怀念过去而流泪。你出来大干了一场,你的财产现在有了牢固的基础,不仅有从一位死者的钱包里偷来的钱,还有从联盟偷来的钱。你的成就包括杀人,抢别人的丈夫,有意乱搞,说谎骗人,坑人的交易,还有各种阴谋诡计,没有一项是经得起认真审查的。真是令人佩服。这说明你是一个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人,是一个很会赚钱的冒险家。能帮助那些自己肯干的人,是件很愉快的事。我宁愿借一万块钱给那位罗马式的老妇人梅里韦瑟太太,甚至可以不立字据。她是从一篮子馅饼起家的,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开了一家面包房,有五六个伙计,上了年纪的爷爷高高兴兴地送货,那个法国血统的不爱干活的年轻人雷内,现在也干得很起劲,而且喜欢这份工作……还有那可怜的托米·韦尔伯恩,他的身体相当于半个人,却干着两个人的活儿,而且干得很好——唉,我不说了,再说你就烦了。”
“我已经烦了,烦得要发疯了。”她冷冰冰地说了这么一句,故意让他生气,改变话题,不再谈这件涉及艾希礼的倒霉事。而他却只笑了笑,并不理会她的挑战。
“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值得帮助的。而艾希礼·威尔克斯——呸!在我们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里,他这样的人是无用的,是没有价值的。每逢这个世界底儿朝天的时候,首先消失的就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不会这样呢?他们没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他们不斗争——也不知道怎样斗争。天翻地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一旦发生天翻地覆的大事变,个人的一切全都失去,人人平等。然后白手起家,大家都重新开始。所谓白手起家,就是说除了脑子好使手有劲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有些人,比如艾希礼,脑子既不好使,手也没有劲,或者说,虽然脑子好使手有劲,却顾虑重重,不敢加以利用。就这样,他们沉了底,他们也应该沉底。这是自然规律。除掉这样的人,世界会更美好。但总有少数坚强的人能够挺过来,过些时候,他们就恢复到大事变之前的状况。”
“你也过过穷日子!你刚才还说你父亲把你赶出家门的时候,你身无分文,”思嘉气愤地说。“我觉得你该理解而且同情艾希礼才对呀!”
“我是理解他的,”瑞德说,“但如果说我同情他,那就见鬼了。南方投降以后,艾希礼的财产比我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多得多。他至少有些朋友肯收留他,而我是个被社会唾弃的人。但是艾希礼又为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你要是拿他和你自己相比,你这个高傲自负的家伙,那为什么——感谢上帝,他和你不一样。他不愿意像你那样把两手弄脏,和北方佬、冒险家和投靠北方的人一块儿去赚钱。他是一个谨慎、正直的人。”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谨慎、正直而不接受一个女人给他的帮助,给他的钱。”
“他不这样又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说呢?我只知道我自己,被赶出来的时候干了什么,现在干什么。我只知道另外有些男人干了什么。我们发现在旧文明的废墟上有机会可以利用,于是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有的光明磊落,有的见不得人,现在我们还在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艾希礼之流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同样的机会,却不加以利用。他们就是不会想办法,思嘉,而只有会想办法的人才有资格活下去。”
瑞德说了些什么,思嘉几乎没有听进去,因为瑞德开始讲话时她回想起来的一些模糊印象,现在清楚了。她记得那天冷风吹过塔拉的果园,艾希礼面对着她,站在一堆准备做栏杆用的木棍旁,两眼望着远处。他说——他说什么了?他提到一个很滑稽的外国名字,听起来像是异教徒的语言,他还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当时她不理解他的意思,现在她明白了,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有一种疲倦、不适的感觉。
“唉,艾希礼说过——”
“他说过什么?”
“在塔拉的时候,他有一天谈到——谈到诸神的末日,谈到世界的末日,以及诸如此类的傻话。”
“啊,Götterdämmerung!”瑞德的眼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还说什么了?”
“唉,记不清了。我当时也没注意听。噢,对了,他还说过什么强者通过,弱者被淘汰。”
“这么说,他是清楚的。这他就更难以忍受了。他们大部分人不清楚,也永远弄不清楚。他们一辈子都弄不明白,失去的幻影消失到哪里去了。他们只好默默地忍受着一切,既感到高傲,又感到无能为力。但艾希礼和他们不同,他是清楚的,他知道自己被淘汰了。”
“不对,他没有被淘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被淘汰。”
瑞德静静地看着思嘉,他那棕色的脸膛是舒展的。
“思嘉,你是怎么取得他的同意,到亚特兰大来为你经营这个木材厂的?他有没有极力推辞?”
思嘉马上想起父亲葬礼之后她和艾希礼谈话的情景,但随即置之脑后。
“当然没有,”她回答道,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我对他说我需要他帮忙,因为当时经管木材厂的那个家伙,我信不过他,弗兰克自己又忙得顾不上帮我,而且我也快要——快要生这个小爱拉了。他是很愿意来给我帮忙的。”
“拿做母亲当借口可真不错!原来你是这样说服他的。现在你把他放到你需要他的地方,这个可怜虫,你用他的责任心把他拴住,和用链子把你那些犯人拴住是一样的。我祝你们二人幸福。不过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了,今后不管你耍什么见不得人的鬼把戏,也别想再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女人。”
思嘉又生气,又失望,非常痛苦。她已经盘算了很久,想再向瑞德借钱在城里买一块地,再开一家木材厂。
“我用不着你的钱,”她说,“我靠约翰尼·加勒格尔那个厂赚钱,赚了很多钱,因为现在不用自由的黑人了。我还有作抵押的钱,而且我们的店做黑人生意,也很赚钱。”
“是啊,我听说了!你可真聪明,专门找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人,孤儿寡妇,愚昧无知的人,从他们身上捞钱。你要是非捞不可,思嘉,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非找这些软弱的穷人呢?自从罗宾汉到现在,劫富济贫才是最高尚的行为!”
“那是因为穷人的钱好捞得多,捞起来也安全得多——姑且就用你说的这个‘捞’字吧。”思嘉直截了当地说。
他悄悄地笑起来,连肩膀都抖动了。
“思嘉,你是一个很坦率的流氓!”
流氓!这话也能使她伤心,真有意思。她激动地对自己说,我可不是流氓啊。至少她并不想当流氓。她想当一个有地位的女人。她突然回想起多少年前的情况,仿佛看见母亲在走来走去,层层的裙子沙沙作响,随身的香囊散发着清香,两只小手不知疲倦地为别人操劳,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尊敬和怀念。想到这里,她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难受。
“你要是存心折磨我,那是白搭,”她说,脸上显得有些疲倦,“我知道我近来没有保持应有的——谨慎。也不像小时候的教育要求的那样宽厚、和气。可是,瑞德,我没有法子呀。的确是没法子。不这样又怎么办呢?那个北方佬闯进塔拉的时候,我要是手软一点,会怎么样呢?我和韦德,整个塔拉,我们所有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当时是应该——不过现在我连想也不愿意想了。还有乔纳斯·威尔克森来抢占房子的时候,我要是宽厚、谨慎,会怎么样呢?我们大家现在住到哪里去呢?还有我当时要是天真、顺从而没有盯着弗兰克去解决那倒霉的债务,我们就会——唉,不说了。也许我是个流氓,瑞德,但我不会永远当流氓的。可是这些年来,甚至现在,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我觉得仿佛是在风暴中划一只装得很满的船,勉强保持在水面上已经很不容易,我哪里还顾得上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那些弃之也并不可惜的东西,比如仪态端庄,以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非常害怕船会沉下去,就把看起来最不重要的东西扔掉了。”
“自尊心、体面、真诚、纯洁、宽厚,”他和颜悦色地一一列举,“思嘉,你做得对呀!船要沉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重要的。可是看一看你周围的朋友吧。他们或者把船安全地划到岸边,货物完好无损,或者宁愿仪容整齐地全船覆没。”
“他们是一群傻瓜,”她气冲冲地说,“一时有一时的情况嘛。等我有了很多钱,我也会像你说的那样好好地做人。我会做一个老实人。到那时候我就做得起老实人了。”
“现在你也做得起——但是你不愿意做。落水的货物是难以打捞上来的,即或打捞上来,也往往业已损坏,无法恢复原状了。恐怕等你有能力把你扔掉的体面、纯洁与宽厚打捞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已经在海里起了变化,但我想并没有变得充实,变得新奇……”
他突然站起来,拿起帽子。
“你要走吗?”
“是的。你不觉得松了一口气吗?你要是还有良心的话,我走以后,你就好好问问你的良心吧。”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低头看了看孩子,伸出一个手指让孩子来抓。
“我想弗兰克一定美得很吧?”
“当然,当然。”
“我想他一定为孩子作了很多安排?”
“哎呀,你还不知道男人对孩子总是胡思乱想。”
“那就告诉他,”瑞德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来,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告诉他如果他想实现他对孩子的那些安排,他就最好晚上多待在家里,而不要像现在这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告诉他待在家里。”
“你这个坏蛋!你怎么敢说可怜的弗兰克会——”
“哎呀,我的天哪!”瑞德放声大笑起来。“我不是说他去玩儿女人去了!弗兰克!啊,我的天哪!”
他一边笑,一边走下台阶。
[1]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29节。
[2] 拉丁语,意为:令人怀念和卓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