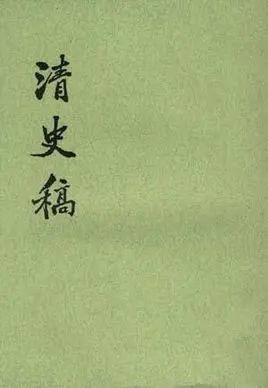债券成百万地发行,其中大部分是非法的,骗人的,但照发不误。州政府的财务局长是个共和党人,但为人诚实,他反对这种非法债券,拒不签字,可是他和另一些想阻止这种渎职行为的人,在那股泛滥的潮流面前也毫无办法。
州营铁路本来是州的一部分财产,可现在成了一种负担,它的债务已达到上百万的数额。这已经不再是铁路了。它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底食槽,猪猡们可以在里面肆意大喝大嚼,甚至打滚糟踏。许多主管人是凭政治关系委任的,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有经营铁路的知识,职工人数达到了所需名额的三倍,共和党人凭通行证免费乘车,大批大批的黑人也乐得免费到处游览,并在同一次选举中一再投票。
州营公路的管理不善尤其使纳税人气愤,因为免费学校的经费是要从公路赢利中拨给的。可是现在不但没有赢利,反而欠债,结果也就没有免费的学校了。由于有钱送孩子上学的人为数很少,因此出现了从小在无知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将在以后若干年中散播文盲的种子。
但是跟浪费、管理不善和贪污比起来,人们更加深恶痛绝的是州长在北方描述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错误观点。当佐治亚人民奋起反对腐败时,州长便急急忙忙跑到北方去,在国会控诉白人凌辱黑人,控诉佐治亚在准备搞另一次叛乱,并提议在那里进行严厉的军事管制。其实没有哪个佐治亚人要同黑人闹纠纷,而只是想避免这种纠纷。没有哪个佐治亚人想打第二次内战,也没有哪个佐治亚人要求和需要过刺刀下的管制生活。佐治亚惟一要求的是不受干扰,让它自己去休养生息。但是,在被州长称之为“诽谤制造厂”的摆弄下,北方政府所看到的佐治亚是一个叛乱的需要严厉管制的州,而且的确加强了对它的管制。
对于那帮掐着佐治亚脖子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喜事。于是产生了一股巧取豪夺的风气,高级官员也公开偷窃,而许多人对此采取冷漠的犬儒主义态度,这是令人想起来都不寒而栗的。事实上无论你抗议也罢,抵制也罢,都毫无用处,因为州政府是受合众国军事当局的鼓励和支持的啊。
亚特兰大人诅咒布洛克以及那帮拥护他的南方白人和共和党人,他们也憎恨那些同他们勾搭在一起的家伙。瑞德就是同他们有联系的。人人都说他跟他们很好,对他们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很熟悉。可是如今,他转过身来要抵制那股他不久以前还混在里面的潮流了,并且开始在奋力拼搏,逆潮流而上。
他缓缓地巧妙地进行他的活动,不让亚特兰大人发现他一夜之间判若两人而产生怀疑。他避免接触那些可疑的亲密伙伴,也不再同北方佬官员和拥护他们的南方白人以及共和党人在一起公开出现了。他出席民主党的集会,并且故意张扬地投民主党人的票。他戒掉了高赌注的牌戏,喝酒也比较有节制了。即使他有时还到贝尔·沃特琳那里去,也是在晚上偷偷去的,像本市一些较为体面的男人那样,而决不在下午去,把马拴在她的门前,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在里面。
他带着韦德上圣公会教堂做礼拜,但去得比较晚,当他踮着脚尖轻轻走进去时,几乎全场的人都惊讶得站起来了。他们不仅对瑞德而且对韦德的出现也大吃一惊,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是天主教徒呢。至少思嘉是天主教徒,或者大家认为她是。可是她多年没进教堂的门了,因为宗教也像爱伦的其他许多教导一样,早已被她抛弃得一干二净。大家都觉得她疏忽了对孩子的宗教教育,因此对于瑞德,由于他居然在设法纠正这一点,便比较有好感了,尽管他没有把孩子带到天主教堂去,而是带到圣公会教堂来了。
瑞德只要注意管住他的舌头,并且不让他那双黑眼睛恶意地嘲弄别人,他是能够显得又严肃又可爱的。他已经多年不注意这样做,可是现在却注意起来,装出严肃可爱的模样,甚至连背心也是穿颜色更加朴素的了。对于那些受过他救命之恩的人来说,瑞德要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要是瑞德的态度不使人觉得他们的感激无足轻重的话,他们早就向他表示谢意了。现在休·埃尔辛、雷内、西蒙斯兄弟、安迪·邦内尔和其他许多人都觉得他可亲而又谦虚,不愿意突出自己,而且当他们谈到他的恩惠时还显得很难为情呢。
“那不算什么,”他会表示不同的意见,“要是你们处在我的地位上,你们也都会这样做的。”
他向圣公会教堂修复基金会慷慨捐献,并且给了“阵亡将士公墓装修协会”一笔颇大而又大得适当的捐款。他请出埃尔辛太太来经办这一捐赠,并不好意思地请求她为这件事保密,虽然他明明知道这只会促使她到处传播这个消息的。埃尔辛太太不高兴接受这笔钱——“投机商的钱”——可是协会缺钱缺得厉害着呢!
“我倒有些不懂,怎么你也来捐钱哪。”她刻薄地说。
瑞德以适当冷静的态度告诉她,他是回想起以前在军队里的人,那些比他更勇敢可是不如他幸运的人,他们至今还躺在默默无闻的坟墓里,使他很受感动,因此才捐赠的。埃尔辛太太听得把胖胖的下颚张开了。梅里韦瑟太太曾告诉过她,思嘉说过巴特勒船长参加过军队,可是她当然不相信。实际上谁也没有相信过嘛。
“你参加过军队吗?你是哪个连——哪个团的?”
瑞德回答了。
“唔,炮兵队!我认识的人要么在骑兵队,要么是步兵。那么,这说明——”她突然打住了,不知怎么说好,只得准备看他那双眼睛恶意地眨巴了。但是他只垂下眼皮,玩弄他的那条表链。
“我本来想参加步兵,”他说,毫不理睬埃尔辛太太那讨好的语气,“可是他们发现我是西点军校出身的——尽管我没有毕业,埃尔辛太太,由于犯了孩子气的毛病——他们便把我编在炮兵队,正规的炮兵队,不是民兵里的。在那最后的战役中他们很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呢。你知道损失多重,死了多少炮兵队的人呀!在炮兵队是相当寂寞的。我在那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想在我整个的服役期间我没见过一个亚特兰大人。”
“嗯!”埃尔辛太太心里有点迷乱了。如果他真的参加过军队,那么她就错了。她曾经讲过他许多坏话,说他是胆小鬼,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内疚。“嗯!那你怎么从不对别人谈你这服役的事呢?你好像觉得进了军队很可耻似的。”
瑞德勇敢地直视着她的眼睛,他脸上显得毫无表情。
“埃尔辛太太,”他诚恳地说,“请你相信我,我对自己为南部联盟服务而感到的骄傲,胜过对于我以前所做和将来要做的一切呢。我觉得——我觉得——”
“好吧,可是你以前为什么要瞒着呀?”
“我不好意思说,想到——想到我过去的一些行为。”
埃尔辛太太把他的捐款和这次谈话详详细细地对梅里韦瑟太太说了。
“而且,多丽,我向你保证,他说到自己不好意思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呢!真的,眼泪!那时我自己也差一点哭了!”
“一派胡言!”梅里韦瑟太太根本不相信。“我既不相信他参加过军队,也不相信他会流眼泪。而且我很快就能查出来。如果他参加过炮兵部队,我能够了解到实际情况,因为当时指挥那个部队的卡尔顿上校是我姑婆的女婿,我可以写信去问他。”
她给卡尔顿上校去了信,结果叫她大为狼狈的是,回信中竟明确无误地称赞瑞德在那里服役的表现,说他是一个天生的炮兵,一个勇敢的军人,一位从不叫苦的上等人,他十分谦逊,连提供给他职位时也拒不接受。
“好啊!”梅里韦瑟太太说,一面把信交给埃尔辛太太看,“你就这样毫不费力地把我击倒了!也许我们不认为他当过兵是把这个流氓估计错了。也许我们应当相信思嘉和媚兰说的,他在这个城市陷落那天入伍了。不过,反正一样,他是个支持共和党的无赖,我就是不喜欢他!”
“不知为什么,”埃尔辛太太犹疑不定地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不一定那么坏。一个为南部联盟战斗过的人是不会坏到哪里去的。思嘉才坏呢。你知道吗,多丽,我真的相信,他——嗯,他为思嘉感到羞耻,不过作为一个上等人不太好意思说出口就是了。”
“羞耻!呸!他们两个完全是同样的货色。你怎么会有这种可笑的想法呢?”
“这并不可笑嘛,”埃尔辛太太生气地说,“昨天,在倾盆大雨中,他带着那三个孩子,请注意,连那个婴儿也在内,坐着他那辆马车出门,在桃树街上跑来跑去,还让我搭他的车回家了呢。那时我说:‘巴特勒船长,你在大雨天带着这三个孩子出门,不是发疯了吗?你干吗不赶快带他们回家呀?’他一言不发,只是显得很难为情似的。不过嬷嬷倒说话了:‘家里挤满了下流白人了。孩子们在雨里比在家里能呼吸更好的空气呢!’”
“他怎么说?”
“他还能怎么说呀?他只是对嬷嬷皱了皱眉头,就不再理会了。你知道思嘉昨天下午举办了一次桥牌会,所有那些下贱的女人全去了。我猜他是不让她们吻他的孩子呢。”
“好吧!”梅里韦瑟太太有点动摇,可仍然坚持不放。不过到了下一个星期,她就终于投降了。
瑞德如今在银行里有一张办公桌了。他究竟在那里干些什么,银行里那些莫名其妙的官员也不清楚,不过他持有那么多的股票,他们对此也不敢说什么话。过了一阵子,他们便忘记自己曾经对他产生过反感了,因为他又文静又和气,还真正懂得一些办银行和投资的事。不管怎样,他整天坐在办公桌前,装出很认真的模样,因为他希望同那些有工作而且勤奋工作的有声望的市民建立彼此平等的关系。
梅里韦瑟太太一心想扩充她的面包店,曾设法以她的房子作担保向银行借贷两千美元,可是银行拒绝借款,因为她的房子已经作了两处抵押了。这位壮实的老太太气冲冲地走出银行,这时瑞德把她拦住,向她问明了情由,然后抱歉地说:“这一定是发生了误会,梅里韦瑟太太。发生了某种严重的误会。怎么连你也得找担保了。要不,我借给你钱,只要你一句话就行!任何一位太太,只要她开办了像你开办起来的那种事业,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担保了。银行正是要借钱给你这样的人嘛。好,请就在我这椅子上坐坐,我立即给你去办。”
他回来时温和地微笑着,说事情就像他所想的那样,是发生了误会。那两千美元已经存在那里,任凭她什么时候支取都行。那么,关于她那所房子——是否就请她现在签个字好吗?
梅里韦瑟太太心里又是气恼又是羞辱,想不到居然要从一个她所厌恶和不信任的人手中接受恩惠呀!因此她尽管口头表示谢意,但实际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不过瑞德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把她送到门口,然后说:“梅里韦瑟太太,我一向非常钦佩你知识丰富,但不知你能不能传授我一点?”
她点点头,那帽子上的羽毛在一个劲儿颤动。
“你家梅贝尔小时候吮她的大拇指时,你是怎么对付的呢?”
“什么?”
“我家的邦妮吮大拇指,我怎么也制止不住她。”
“你应当制止她,”梅里韦瑟太太坚决地说,“那会弄坏她嘴巴的模样的。”
“我知道!我知道!她的嘴长得很美。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呀。”
“那,思嘉总该知道嘛,”梅里韦瑟太太直率地说。“她还养了两个孩子呢。”
瑞德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鞋,长叹了一声。
“我已经试过,在她的指甲底下放点肥皂,”他说,没有理会她对思嘉的指责。
“肥皂!哼!肥皂根本没用。我从前给梅贝尔在大拇指上放奎宁,我说,巴特勒船长,她很快就不再吮大拇指了。”
“奎宁!我可从没想过呢!感谢你不尽了,梅里韦瑟太太。这件事真叫我伤脑筋呀。”
他对她微微一笑,显得那么高兴,那么感激,这使得梅里韦瑟太太一时有点糊涂了。不过她向他告别时也笑了一笑。她不高兴向埃尔辛太太承认自己看错了这个人,但她还是老实地表示一个人只要是爱他的孩子便不会没有优点的。思嘉居然对邦妮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家伙不感兴趣,这多叫人伤心啊!一个男人得设法亲自抚育一个小女孩,这也够可怜的了!瑞德很清楚地知道这光景多么感人,至于是否会损坏思嘉的名声,他可不管了。
自从那孩子学会了走路以后,瑞德便经常将她带在身边到处走动,有时坐马车,有时骑马,把她放在马鞍前头。每天下午他从银行回到家里,便带她出去到桃树街散步,牵着她的手,自己放慢脚步让她蹒跚地行走,一路上耐心地回答她提出的无数问题。傍晚时候,人们常常站在自己的前院里或走廊上,看到邦妮这样一个满头黑色鬈发和眼睛蓝得发亮的小姑娘,都觉得她很好玩,总是忍不住要跟她说说话。瑞德从来不打搅这种谈话,只悄悄地站在一旁,流露出做父亲的骄傲和对人们这样夸奖他女儿的喜悦之情。
亚特兰大人的记性特好,他们对事物颇多疑忌,很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习惯和看法。现在时世艰难,人们对任何一个跟布洛克州长及其一伙有关系的人都抱着深深的敌意。可是邦妮身上综合了思嘉和瑞德两人各自最可爱的地方,因此瑞德就把她作为一个小小的楔子,用来打进亚特兰大人冷酷的墙壁中去了。
邦妮一天天迅速成长,她越发显出作为杰拉尔德·奥哈拉的外孙女的本色来了。她的两条腿又粗又短,一双大眼睛呈现出爱尔兰人特有的天蓝色,而那个小小的正方形下颚更说明她是坚决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她像杰拉尔德那样很容易发脾气,发作起来便突然大叫大嚷,可是一旦她的愿望得到满足就压根儿忘了。只要她父亲在身边,她的愿望总是很快就得到满足的。不管思嘉和嬷嬷怎样反对,他仍然姑息迁就她,因为她处处讨他喜欢,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她害怕黑暗。
她同韦德和爱拉一起睡在育儿室里,两周岁之前常常很快就能睡着。后来,也不知什么缘故,只要嬷嬷一拿着灯走出房间她就哭了。接着又发展到经常在深夜醒来,恐怖地尖声叫喊,这不但把别的两个孩子惊醒,而且闹得全家都惶惶不安起来。有一次不得不把米德大夫请来,他诊断说是做噩梦,瑞德听了还很不满意。无论谁问她,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词儿:“黑暗。”
思嘉给这孩子闹得不耐烦了,便主张打她一顿。她不想迁就她,在育儿室通宵点一盏灯,因为那会使得韦德和爱拉不能睡觉。瑞德也很苦恼,但仍然很耐心,希望从女儿嘴里掏出更多的解释来;他说如果要打一顿的话,那就由他自己动手,而且是打思嘉。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将邦妮从育儿室搬到瑞德现在一个人住的那间房里。她那张小床摆在瑞德的大床旁边,桌上有一盏带罩的灯,常常通宵点着,这件事一传出去,全城都窃窃私语起来。不管怎么样,一个女孩子睡在父亲房里,总是有点不怎么合适嘛,哪怕这姑娘还只有两岁呢。这种闲言使思嘉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压力。第一,它毋庸置疑地证实她跟丈夫是分房睡的,这本身就是骇人听闻的了。第二,人人都认为如果孩子不敢一个人单独睡,那就得跟她母亲在一起。而且思嘉觉得自己难以说明,她既不能点着灯睡觉,瑞德又不让孩子跟她在一起睡。
“你是只要她不大声喊叫就从不醒来的,而且醒来后可能还打她呢。”瑞德不满地说。
思嘉对于瑞德那么关心邦妮的夜哭症感到很恼火,但是她觉得她可能纠正这一局面,让邦妮再搬回育儿室去。所有的孩子都是害怕黑暗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决不迁就。瑞德正是在这一点上处理错了,结果反而让她这个当妈的显得很尴尬,这好像是由于她把他关在门外而给她的报复呢。
自从那天晚上她告诉他她不要再生孩子以来,他一直没有迈过她的门槛,甚至连门把手也没有扭过。从那以后,一直到他由于邦妮害怕而开始留在家里为止,他不在家吃晚饭比在家吃的次数还多。有时他整夜不归,使得思嘉锁着门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滴答的钟摆一直响到天明,也不知道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她记得他说过:“亲爱的,我还有别的床好去睡呢!”尽管她一想起这句话就心痛,可是也毫无办法。她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一说就会突然引起争吵,那时他准要指摘她锁门的事,有时还可能牵涉到艾希礼呢。是的,他让邦妮在房里——在他房里——点着灯睡觉这样的蠢事,只不过是一种报复她的卑劣手段罢了。
她不理解他对邦妮那种可笑癖好给予的重视,以及他对于这个孩子的全心全意的钟爱,直到一个可怕的夜晚出现为止。那个夜晚是全家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天白天,瑞德遇见一个过去跑封锁线的同行,他们彼此有谈不完的话。他们究竟到哪里叙谈和喝酒去了,思嘉并不清楚,不过当然她怀疑他们是在贝尔·沃特琳那里。下午他没有回来带邦妮出去散步,也没回来吃晚饭。邦妮整个下午都在窗口焦急地盼望着,渴望在父亲面前展览一大堆被弄死了的甲虫和蟑螂,可最后不得不连哭带骂地被卢儿抱上床去睡觉了。
不知是卢儿忘记点灯呢,还是灯自己熄了,反正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可是等到瑞德终于回来,尤其是喝了酒回来时,他还在马厩里便听见全家闹翻了天,邦妮的尖叫声显得特别刺耳。原来邦妮在黑暗中醒来了,她叫父亲,可是他不在,于是她想象中所有那些叫不出名来的妖魔鬼怪都一齐来把她抓住了。无论思嘉怎样抚慰,无论仆人们端来多亮的灯光,都无法让她安静,而瑞德三步并两步地奔上楼来时,也吓得像见了鬼了。
最后瑞德总算把她抱到了怀里,他问她怎么回事,她边喘,边抽泣着,从中只能听清楚“黑暗”这个词儿,于是他愤怒地回过头来向思嘉和几个黑人厉声质问。
“是谁把灯吹灭的?谁把她单独留在黑屋子里?普里茜,我要剥掉你的皮,你——”
“啊,上帝,瑞德先生!那不是俺呀!是卢儿呢!”
“天知道,瑞德先生,俺——”
“住嘴!你明明知道我的命令。上帝作证,我要——给我滚!别再回来了。思嘉,给她点钱,打发她走,在我下楼之前就走。现在,你们都给我出去,都出去!”
几个黑人都溜了,那个倒霉的卢儿还一路用围裙捂着脸伤心地哭泣。但思嘉留在那里。看到自己心爱的孩子在瑞德怀里渐渐安静下来,而刚才她抱着时却哭得那么可怜,这滋味是不好受的。同样,看到那两条小小的胳臂抱着他的脖子,听到那哽咽的声音在述说她是怎么受惊的,而她思嘉刚才从她嘴里却什么也没掏出来,这叫她多么尴尬呀!
“这么说,它是坐在你胸口上了,”瑞德温柔地说,“它是个很大的家伙吗?”
“啊,是的!大极了。还有爪子呢。”
“哎,还有爪子。现在好了。我一定整晚坐着,只要它回来就枪毙它。”瑞德的声音又认真又亲切,邦妮听着听着就不抽泣了。她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受压抑,现在开始用一种只有他懂得的语言在详细描述她的那个大怪物。瑞德跟她讨论着,仿佛那是真的似的,这使思嘉又烦躁起来了。
“看在老天面上,瑞德——”
但是他摆摆手叫她别做声。后来邦妮终于睡着了,他把她放在床上,盖好被子。
“我要去活剥那个黑鬼的皮,”他低声说,“这也是你的过错。你干吗不上来看看是不是点了灯呢?”
“别傻了,瑞德,”她悄悄地说,“她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因为你迁就她。有多少孩子害怕黑暗,可是他们慢慢就克服了。韦德本来也怕,但我没有姑息他。你只要让她哭一两个晚上——”
“让她哭!”顷刻间思嘉以为他要动手打她了,“你要么是个笨蛋,要么是个我从没见过的最没人性的女人。”
“我可不要她长大以后变得又神经质又胆小。”
“胆小?见鬼去吧!她身上连一点胆小的影子也没有。只不过你毫无想象力,因此才不能理解那些有想象力的人——尤其是一个孩子——的痛苦罢了。要是一个有爪子有角的东西来坐在你胸口上,你会叫它滚开去吧,是吗?你会拼命那样叫呢!你好不好回想一下,太太,我曾经听见你像只烫坏的猫似的狂叫着醒来,那仅仅因为你梦见在雾里奔跑而已。而且这种事不久以前还发生过呀!”
思嘉被堵回去了,因为她从来不喜欢去想起那个梦。而且叫她去回忆瑞德曾经以几乎像现在安慰邦妮这样的态度安慰过她,也是很难为情的。所以她便迅速改换了进攻的方式。
“你这样做正好是姑息她,而且——”
“而且我打算继续姑息下去。只要我这样做,她就会逐渐克服它,把它忘了。”
“那么,”思嘉刻薄地说,“你要是打算当保姆,你就得想办法改变一下习惯,晚上早点回家,也不要再喝酒了。”
“我一定早早回来,不过我高兴时还会喝得烂醉的。”
从那以后他的确回来得早了,常常在邦妮上床睡觉以前好久就到了家里。他坐在她身旁,拉着她的手,直到她瞌睡得渐渐把手放松了为止。那时他才踮着脚尖悄悄下楼,让灯光明亮地点在那里,门也半开着,好叫她一旦醒来害怕时他听得见。从此他再也不想让她在黑暗中受惊那样的事重新发生了。全家的人都经常当心让那盏灯亮着,思嘉、嬷嬷、普里茜和波克时常蹑手蹑脚上楼去看看,保证不出什么意外。
他每次回家都没有喝醉,不过这绝不是思嘉的功劳。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大量饮酒,尽管从没有真正醉过,而且有一天晚上他呼吸中的威士忌酒气还特别强烈。他把邦妮抱起来,把她一下扛在肩上,然后问她:“你要给你亲爱的爸爸一个吻吗?”
她耸起她那个翘翘的鼻子,扭摆着要下地来。
“不,”她坦率地说,“脏着呢。”
“我怎么了?”
“有股臭味。艾希礼叔叔没有臭味。”
“唔,那我该死,”他悔恨地说,一面把她放在地上,“我还从没想到居然我自己家里会有个提倡戒酒的人呢!”
不过从那以后,他就限制自己晚饭后只喝一杯葡萄酒了。邦妮是被允许喝他杯子里剩下的那一点的,她一点也不觉得葡萄酒有什么臭味。这样一来,他面颊上那两块开始隆起来的胖堆儿就渐渐消失,那双黑眼睛下面的两个圈圈也不再显得那么黯淡而深陷了。由于邦妮喜欢坐在他的马鞍前头外出,他现在骑马在外边游荡的时间也多了些,结果脸孔晒得黑黑的,肤色也比以前深了不少。他看来已更加健康,也更加快活,又像是战争早期激动过亚特兰大人的那个勇敢的年轻冒险家了。
每当他骑着马、鞍前带着那个小玩意从旁边走过时,那些原先厌恶他的人现在都开始露出了微笑。那些以前一直认为没有哪个女人跟他在一起不出乱子的妇女,如今也往往在大街上停下来跟他交谈,称赞邦妮几句。甚至有几位最古板的老太太都觉得,一个能像他这样细心地商讨孩子的毛病和问题的男人,是不可能坏到哪里去的。
[1]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9章第10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