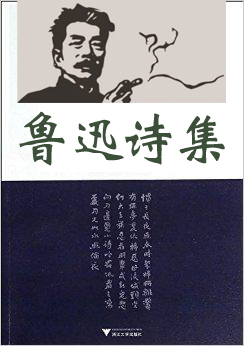“我并不觉得走投无路了,”她尖刻地说,“你永远也休想逼我就范,瑞德·巴特勒,或企图把我吓倒。你只不过是只喝醉了的野兽,跟一些坏女人鬼混得太久,便把谁都看成坏人,别的什么也不理解了。你既不了解艾希礼,也不了解我。你在污秽的地方待惯了,除了脏事什么也不懂。你是在妒忌某些你无法理解的东西。明天见。”
她从容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这时一阵大笑使她收住了脚步。她回头一看,只见他正摇摇晃晃向她走过来。天哪,但愿他不要那样可怕地大笑啊!这一切有什么好笑的呀?可是他一步步向她逼近,她一步步向门口后退,最后发现背靠着墙壁了。
“别笑了。”
“我这样笑是为你难过呢。”
“难过——为我?”
“是的,老天爷作证,我为你难过,亲爱的,我的漂亮的小傻瓜。你觉得受不了了,是不是?你既经不起笑又经不起怜悯,对吗?”
他止住笑声,将身子沉重地靠在她肩膀上,她感到肩都痛了。他的面容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凑得那么近,嘴里那股浓烈的威士忌味叫她不得不背过脸去。
“妒忌,我真的这样?”他说,“可怎么不呢?唔,是的,我妒忌艾希礼·威尔克斯。怎么不呢?唔,你不要说话,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在肉体上是对我忠实的。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哦,这一点我一直很清楚。这些年来一直是这样。我怎么知道的?哦,你看,我了解艾希礼的为人和他的教养。我知道他是正直的,是个上等人。而且,亲爱的,这一点我不仅可以替你说——或者替我说,为那件事情本身说。我们不是上等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尊敬的地方,不是吗?这就是我们能够像翠绿的月桂树一般茂盛的缘故呢。”
“让我走。我不要站在这里受人侮辱。”
“我不是在侮辱你。我是在赞扬你肉体上的贞操。它一点也没有愚弄过我。思嘉,你以为男人都那么傻吗?把你对手的力量和智慧估计得太低是绝不会有好处的。而我并不是个傻瓜。难道你不考虑我知道你是躺在我的怀里却把我当做是艾希礼·威尔克斯吗?”
她耷拉着下颚,脸上显然流露出恐惧和惊愕的神色。
“那是件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愉快。好像是三个人睡在本来只应该有两个人的床上。”他摇晃着她的肩膀,那么轻轻地,一面打着嗝儿,嘲弄地微笑着。
“唔,是的,你对我忠实,因为艾希礼不想要你。不过,该死的,我才不会妒忌艾希礼占有你的肉体呢。我知道肉体没多大意思——尤其是女人的肉体。但是,对于他占有你的感情和你那可爱的、冷酷的、不知廉耻的、顽固的心,我倒确实有些妒忌。他并不要你的心,那傻瓜,可我也不要你的肉体。我不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女人。不过,我的确想要你的情感和心,可是我却永远得不到它们,就像你永远得不到艾希礼的心一样。这就是我为你难过的地方。”
尽管她觉得害怕和迷惑不解,但他的讥诮仍刺痛了她。
“难过——为我?”
“是的,因为你真像个孩子,思嘉。一个孩子哭喊着要月亮。可是假如他果真有了月亮,他拿它来干什么用呢?同样,你拿艾希礼干什么用呢?是的,我为你难过——看到你用双手把幸福抛掉,同时又伸出手去追求某种永远也不会使你快乐的东西。我为你难过,因为你是这样一个傻瓜,竟不懂得除了彼此相似的配偶觉得高兴是永远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幸福了。如果我死了,如果媚兰死了,你得到了你那个宝贵的体面的情人,你以为你跟他在一起就会快乐了吗?呸,不会的!你会永远不了解他,永远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永远不懂得他的为人,犹如你不懂音乐、诗歌、书籍或除了金钱以外的任何东西一样。而我们呢,我亲爱的知心的妻子,我们却可能过得极其愉快,要是你给了我们半个机会的话,因为我们两人是十分相似的。我们俩都是无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们本来可以快快活活过日子,因为我爱你,也了解你,思嘉,彻头彻尾地了解,这绝不是艾希礼所能做到的。而他呢,如果他真正了解你,就会瞧不起你了……可是不,你却偏要一辈子痴心梦想地追求一个你不了解的男人。至于我,亲爱的,我会继续追求婊子。而且,我敢说,我们俩可以结成世界上少有的一对幸福配偶呢。”
他突然把她放开,然后歪歪倒倒地退回到桌旁去拿酒瓶。思嘉像生了根似的站了一会儿,种种纷乱的想法在她脑子里出出进进,可是她一个也没有抓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瑞德说过他爱她。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或者只是醉后之言?或者这又是一个可怕的玩笑?而艾希礼——那个月亮——哭着要那个月亮。她迅速跑进黑暗的门厅,仿佛在逃避背后的恶魔似的。唔,但愿她能够回到自己房里!这时她的脚脖子一扭,拖鞋都快掉了。她停下来想拼命把拖鞋甩掉,像个印第安人偷偷跟在后面的瑞德已来到她身旁。他那灼热的呼吸对着她的脸袭来,他的双手粗暴地伸进她的披肩底下,紧贴着赤裸的肌肤,把她抱住了。
“你把我撵到大街上,自己却跑去追求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行了,我床上只许有两个人。”
他猛地将她抱起来,随即上楼。她的头被紧紧地压在他胸脯上,听得见耳朵底下他心脏的怦怦急跳。她被他夹痛了,便大声喊叫,可声音仿佛给闷住了似的,显得十分惊恐。上楼梯时,周围是一片漆黑,他一步步走上去,她吓得快要疯了。他成了一个疯狂的陌生人,而这种情况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它比死亡还要可怕呢。他就像死亡一样,狠狠地抱着她,要把她带走。她发出尖叫,但声音被他的身子捂住了。这时他突然在楼梯顶停住脚,迅速将她翻过身来,然后低着头吻她,那么狂热、那么尽情地吻她,把她心上的一切都抹拭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那个使她不断往下沉的黑暗的深渊和压在她嘴唇上的那两片嘴唇。他在发抖,好像站在狂风中似的,而他的嘴唇在到处移动,从她的嘴上移到那披肩从她身上掉落下来的地方,在她柔润的肌肤上。他嘴里在喃喃自语,但她没有听见,因为他的嘴唇正在唤起她以前从没有过的感情。她陷入了一片迷惘,他也是一片迷惘,而在这以前什么也没有,只有迷惘和他那紧贴着她的嘴唇。她想说话,可是他的嘴又压下来了。突然她感到一阵从没有过的狂奋的刺激;这是喜悦和恐惧、疯狂和兴奋,是对一双过于强大的胳臂、两片过于粗暴的嘴唇以及来得过于迅速的命运的屈服。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了一个比她更强有力的人,一个她既不能给以威胁也不能压服的人,一个正在威胁她和压服她的人。不知怎的,她的两只胳臂已抱住他的脖子,她的嘴唇已在他的嘴唇下颤抖,他们又在向那片朦胧黑暗中上升,上升,那是一片柔软的、涡漩着的、包容一切的黑暗呢。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时,他已经走了,要不是她旁边那个揉皱的枕头,她还以为昨晚发生的一切全是个放荡而荒谬的梦呢。她回想起来不禁脸上热烘烘的,便把被头拉上来围着头颈,继续躺在床上让太阳晒着,一面清理脑子里那些紊乱的印象。
有两件事显得特别突出。一是好几年来她跟瑞德在一起生活,一起睡,一起吃,一起吵架,还给他生了个孩子——可是,她并不了解他。那个把她在黑暗中抱上楼来的人完全是陌生的,她做梦也没想过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而现在,即使她有意要去恨他,要生他的气,她也做不到了。他在一个狂乱的夜晚镇服了她,挫伤了她,虐待了她,而她对此却十分得意呢。
唔,她应当感到羞耻,应当一想起那个狂热的、漩涡般的销魂时刻就胆寒畏缩!一个上等女人,一个真正的上等女人,经历了这样一个夜晚以后便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可是,比羞耻心更强的是想起那种狂欢、那种令人销魂和为之屈服的陶醉的经验。她有生以来头一次感到自己有了活力,感到有像逃离亚特兰大那天晚上所经历的那种席卷一切和本能的恐惧感觉,也像她枪击那个北方佬时抱着的那种仇恨一样令人晕眩而喜悦的激情。
瑞德爱她!至少他说过他爱她,而现在她怎么还能怀疑这一点呢?他爱她,这个跟她那么冷淡地一起生活着的野蛮的陌生人居然爱她,这显得多么古怪,多么难以理解和不可置信啊!对于这一发现,她压根儿不清楚自己的感觉究竟怎样,不过有个念头一出现她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他爱她,于是她终于占有他了。她本来几乎忘记了,她早先就曾渴望着引诱他来爱她,以便举起鞭子把这个傲慢的家伙驯服下来。如今这个渴望又出现了,它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满足。就这么一个晚上,他把她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可这样一来她却找到了他身上的弱点。从今以后,只要她需要,她就可以拿住他。他的嘲弄长期以来把她折磨得够了,可现在她掌握了他,她手里拿着圈儿,高兴时就能叫他往里钻。
她想到还要在大白天面对面地同他相见,便陷入了一片神经紧张和局促不安之中,当然其中也有兴奋和喜悦的心情。
“我像个新娘一样紧张呢,”她想,“而且是关于瑞德的!”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愚蠢地笑了。
但是瑞德没有回家吃午饭,晚餐时仍不见他的影子。一夜过去了,那是一个漫长的夜,她睁着眼睛直躺到天明,两只耳朵也始终紧张地倾听着有没有他开门锁的声响。可是他没有来。第二天也过去了,他毫无消息,她又失望又担心,急得要发疯似的。她从银行经过,发现他不在那里。她到店里去,对每个人都很警觉,只要门一响,有个顾客进来,她都要惊讶地抬头一望,希望进来的人就是瑞德。她到木料场去,对休大声呵斥,吓得他只好躲在一堆木头后面。可是瑞德并没有到那里去找她。
她不好意思去问朋友们是否看见过他。她不能到仆人们中间去打听他的消息。不过她感觉到他们知道了一些她不知道的事。黑人往往是什么都知道的。这两天嬷嬷显得不寻常地沉默。她从眼角里观察思嘉,但什么也不说。到第二天晚上过后,思嘉才下决心去报警察。也许他出了意外,也许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躺在哪条沟里不能动弹了。也许——唔,多可怕的想法——也许他死了!
第二天早晨她吃完早点,正在自己房里戴帽子,她忽然听到楼梯上迅疾的脚步声。她略略欣慰地往床上一倒,瑞德就进来了。他新理了发,刮了脸,给人按摩过了,也没有喝醉,可他的眼睛是血红的,他的脸由于喝酒有一点浮肿。他神气十足地向她挥着手说:“唔,好啊。”
谁能一声不响地在外面过了两天之后,进门就这样“唔,好啊”呢?在他们度过的那么一个晚上还记忆犹新时,他怎么能这样若无其事呢?他不能这样,除非——除非——那个可怕的想法猛地在她心中出现。除非那样一个夜晚对他来说是很寻常的!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曾经打算在他面前表现的那些优美姿态和动人的微笑全都给忘了。他甚至没有走过来给她一个寻常而现成的吻,只是站在那里望着她,咧着嘴微微一笑,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雪茄。
“哪儿——你到哪儿去了?”
“别对我说你不知道!我相信全城的人现在都知道了。也许他们全知道,只有你例外。你知道有句古老的格言:丈夫都跑了,老婆最后才知道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前天晚上警察到贝尔那里去过以后——”
“贝尔那里——那个——那个女人!你一直跟她——”
“当然。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想你没有为我担心吧。”
“你离开我就去——”
“喂,喂,思嘉!别装糊涂说自己受骗了。你一定早就知道了贝尔的事。”
“你一离开我,就到她那里去,而且在那以后——在那以后——”
“唔,在那以后。”他做了一个毫不在意的手势,“我会忘记我的那些做法。我对上次我们相会时的行为表示抱歉。那时我喝得烂醉,你无疑也是知道的,同时又被你那迷人的魅力弄得神魂颠倒了——还要我一一细说吗?”
她突然想哭,想倒在床上痛哭一场。原来他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变,而她是上当了,像个愚蠢得可笑的异想天开的傻瓜,居然以为他真的爱她呢。原来整个这件事只不过是他醉后开的一个可恶的玩笑。他喝醉了酒便拿她来发泄一下,就像他在贝尔那里拿任何一个女人来发泄一样。现在他又回来侮辱她,嘲弄她,叫她无可奈何。她吞下眼泪,想重新振作起来。决不能让他知道她这几天的想法啊!她赶快抬起头来望着他,只见他眼里又流露出以前那种令人困惑的警觉神色——那么犀利,那么热切,仿佛在等待她的下一句话,希望——他希望什么呢?难道希望她犯傻上当,大叫大嚷,再给他一些嘲笑的资料?她可不干了!她那两道翘翘的眉毛猛地紧锁起来,显出一副冷冰冰的生气模样。
“我自然怀疑过你跟那个坏女人之间的关系了。”
“仅仅是怀疑?你干吗不问问我,好满足你的好奇心?我会告诉你的。自从你和艾希礼决定让我们俩分房睡以来,我就一直跟她同居着呢。”
“你居然还有胆量站在这里向你的妻子夸耀,说——”
“唔,请饶了我,别给我上这堂道德课了。你只要我付清那些账单,就无论我做什么都一概不管了。你也明白我近来不怎么规矩嘛。至于说你是我的妻子——那么,自从生下邦妮以后,你就不大像个妻子了,你说对吗?思嘉,你已经变成一个可怜的投资对象了,贝尔还好些呢。”
“投资对象?你的意思是你给她——”
“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事业上扶植她’。贝尔是个精干的女人。我希望她长进,而她惟一需要的是钱,用来开一家自己的妓院。你应当知道,一个女人手里有了钱会干出什么样的奇迹来。瞧瞧你自己吧。”
“你拿我去比——”
“好了,你们俩都是精明的女生意人,而且都干得很有成就。当然,贝尔还比你略胜一筹,因为她心地善良,品性也好——”
“你给我从这房里滚出去好吗?”
他懒洋洋地向门口挪动,一道横眉滑稽地竖了起来。他怎能这样侮辱她啊,她气愤而痛苦地想道。他是特意来伤害和贬损她的,因此她想起,当他在妓院里喝醉了酒跟警察吵架时她却一直盼着他回家来,这实在太令人痛心了。
“赶快给我滚出去,永远也不要进来了。以前我就这样说过,可是你没有一点上等人的骨气,根本不理会这些。从今以后我要把这门锁上了。”
“不用操心了。”
“我就是要锁。经过那天晚上你的那种行为——醉成那个模样,那么讨厌——”
“你看,亲爱的!并不那么讨厌嘛,真是!”
“滚出去!”
“别生气呀。我就走。我答应再也不来干扰你了。那是最后一次。而且我正想告诉你,要是我这种不名誉的行为实在使你忍受不了,我就让你去办离婚吧。只是邦妮要给我,别的我不争。”
“我可不想办离婚来玷辱家门呢。”
“要是媚兰死了,你很快就会玷辱的,你说不会吗?我一想到那时候你会多么急于离掉我,我的头就晕了。”
“你走不走?”
“好,我就走。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我要到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去,还有——唔,对,我要逛一大圈。我今天就走。”
“啊!”
“而且我要把邦妮带在身边。让那个傻女孩普里茜把她的小衣服收拾一下。我想把普里茜也带去。”
“你永远也休想把我的孩子带出这个家去。”
“也是我的孩子嘛,巴特勒太太。我想你不会反对让我带她到查尔斯顿去看看她的祖母吧?”
“她的祖母,去你的!你以为我会让你把孩子从这里带走,而你每晚都喝得烂醉,很可能还带她到像贝尔那里的地方去——”
他把手里的雪茄狠狠往地上一掷,雪茄在地毯上嗤嗤地冒起烟来,一股烧焦的羊毛味直冲鼻子。他不管这些,只立刻走过来站到思嘉跟前,气得脸都发青了。
“你如果是个男人,我就先把你的脖子拧断再说。现在我只警告你闭上你那张臭嘴。你以为我就不爱邦妮,就会把她带到——她是我的女儿!老天爷,看这个笨蛋!至于你,你把你做母亲假装虔诚的架势摆给你自己去看吧。不是吗,作为一个母亲,你还不如一只猫呢!你几时给孩子们做过些什么?韦德和爱拉看见你就吓得要死,要没有媚兰,他们连什么叫爱和亲密都不会知道呢。可是邦妮,我的邦妮!你以为我不能比你照料得好些吗?你以为我会让你去威胁她,损害她的心灵,像你对韦德和爱拉那样做吗?见鬼去吧,我决不会的!快替她收拾好,让我一个小时后便能起身,否则我警告你,那后果会比前两天那个晚上要严重得多。我常常觉得,用马鞭子结结实实抽你一顿,对你会大有好处呢。”
他没等她说话便转过身去,迅速走出了她的房间。她听见他经过穿堂向孩子们的游艺室走去,随即把那扇门推开了。那里传来一片热烈高兴的儿童尖叫声,她听出邦妮的声调比爱拉的还要高。
“爹爹,你上哪儿去了?”
“去找张兔子皮来包我的小邦妮。给你亲爹爹一个最甜的吻吧,邦妮——还有你,爱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