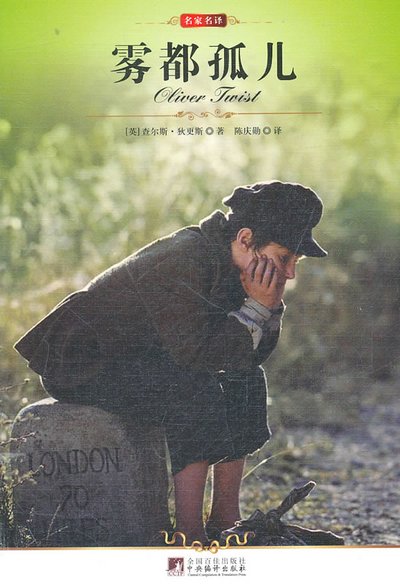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打麻将。这种简单的娱乐活动在金斯艾伯特很受欢迎。晚饭后,大家穿着胶鞋和雨衣先后到来,喝点咖啡,然后吃几块蛋糕和三明治,喝喝茶。
当晚和我们一起打牌的是甘尼特小姐和家住教堂附近的卡特上校。这样的晚间聚会是传播小道消息的好时机,有时聊得兴起,连正事都忘了。我们通常都打桥牌——边打边交头接耳,最后打得乱七八糟。我们发现麻将相对平和,不至于像打桥牌那样,因为搭档没打出某张牌就大为不满; 虽然我们仍然会直白地表达批评意见,但没那么有针对性。
“今晚真冷,是吧,谢泼德?”背靠壁炉的卡特上校说。卡洛琳把甘尼特小姐带进自己房间,正帮她脱下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外衣。“勾起了我对阿富汗的回忆。”
“是吗?”我礼貌地答道。
“可怜的艾克罗伊德,真是一场神秘的谋杀,”上校边接过咖啡边说,“背后大有玄机——我是这么看的。谢泼德,有句话我只对你说,我听说跟勒索有关呢!”
上校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毫无疑问,还牵涉到一个女人,”他说,“信不信由你,一定跟女人有关。”
这时卡洛琳和甘尼特小姐来了。甘尼特小姐喝着咖啡,卡洛琳则端出麻将盒,把牌倒在桌上。
“洗牌,”上校开着玩笑,“没错——洗牌,我们在上海的俱乐部里都是这么说的。”
卡洛琳和我都认为,卡特上校这辈子根本就没去过上海的俱乐部。大战期间他在印度做牛肉罐头、梅子酱和苹果酱生意,没去过印度再往东的地方。不过上校的军旅生涯是货真价实的,何况在金斯艾伯特,就算你再怎么吹嘘自己的离奇经历,大家也都买账。
“开始吗?”卡洛琳说。
我们围着桌子坐好,开头五分钟没人说话,彼此都暗暗较劲,看谁先把自己的城墙垒好。
“你先来,詹姆斯,”最后卡洛琳说,“你是东风。”
我打出一张牌。一两圈过后,沉闷的气氛渐渐被单调的喊声打破,“三条”“二筒”“碰”,甘尼特小姐时不时还喊“不碰”,因为她有个习惯,没看清牌就抢着“碰”,然后才发现碰不起。
“今天早上我看见弗洛拉·艾克罗伊德了,”甘尼特小姐说,“碰——不,不碰,我弄错了。”
“四筒,”卡洛琳说,“你在哪儿看到她的?”
“她可没看见我。”也只有在我们这种小地方,才能欣赏到甘尼特小姐那大惊小怪的模样。
“啊!”卡洛琳兴冲冲地说,“吃。”
“现在的正确说法是‘切’,”甘尼特小姐暂时分心了,“不是‘吃’。”
“胡说,”卡洛琳反驳,“我一直都说‘吃’。”
“在上海的俱乐部,他们都说‘吃’。”卡特上校说。
甘尼特小姐只好认输。
“你刚才说弗洛拉·艾克罗伊德什么来着?”卡洛琳专心地打了一两分钟,忽然问,“她和什么人在一起吗?”
“那还用说。”甘尼特小姐说。
两位女士四目相对,似乎在交换情报。
“真的?”卡洛琳来了兴致,“是真的?哈,果然不出所料。”
“都等你出牌呢,卡洛琳小姐。”上校说。他有时会摆出大男人的派头,看似专注于牌局,对小道消息漠不关心,但谁都不会上他的当。
“要我说啊,”甘尼特小姐说,“你刚才打的是条子吗,亲爱的?哦,不,我看见了——是筒子。要我说啊,弗洛拉真是走运,运气好得不能再好了。”
“这话怎么说,甘尼特小姐?”上校问,“那张发财我碰。你怎么看出弗洛拉小姐运气好?她确实是个漂亮姑娘。”
“犯罪这种事我或许不算太懂,”甘尼特小姐以一种万事通的口吻说,“但我可以告诉你,警察一开头总要问‘最后看见死者活着的人是谁?’而这个人总会成为怀疑对象。好了,弗洛拉·艾克罗伊德是最后看见她伯父还活着的人,这对她很不利——非常非常不利。依我看——管它三七二十一,拉尔夫·佩顿躲起来就是掩护她,分散她的嫌疑。”
“拜托,”我温和地反驳,“难道你真的以为弗洛拉·艾克罗伊德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会那么冷血,拿刀刺死亲伯父?”
“唔,很难说,”甘尼特小姐说,“这两天我从图书馆借了本书,里头说在巴黎下层社会,有些最凶残的罪犯就是漂亮的年轻姑娘。”
“那是在法国。”卡洛琳当即反对。
“行了行了,”上校连忙打圆场,“现在听我讲一件稀奇事——这故事在印度的集市上传得很凶……”
上校的故事极其冗长,没完没了,而且非常无聊。多年前发生在印度的事情,怎能与前天金斯艾伯特的爆炸性新闻相提并论。
卡洛琳幸运地和了一把,总算让上校的故事画上了句号。卡洛琳算番数时搞错了,被我纠正之后还有点不高兴。我们又开始新的一局。
“东风打完了,”卡洛琳说,“我对拉尔夫·佩顿自有看法。三万。可到现在为止还没跟别人提过。”
“真的吗,亲爱的?”甘尼特小姐说,“吃——我是说碰。”
“真的。”卡洛琳坚定地回答。
“靴子有问题吗?”甘尼特小姐问,“我是说,靴子是黑色的,有什么不对劲?”
“没什么不对劲。”卡洛琳说。
“依你看关键在哪里?”甘尼特小姐又问。
卡洛琳撅起嘴,摇着头,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势。
“碰,”甘尼特小姐说,“不对——不碰。谢泼德医生和波洛先生关系不错,应该会知道所有秘密吧?”
“没那回事。”我说。
“詹姆斯真谦虚,”卡洛琳说,“啊!暗杠。”
上校吹了声口哨,闲聊暂时中止了。
“你是庄家,”他说,“还碰了两次。大家当心,卡洛琳小姐要和一把大的。”
一连几分钟大家都埋头牌局,一句闲话也没说。
“说到这位波洛先生,”卡特上校问,“他真的是大侦探?”
“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侦探。”卡洛琳郑重其事地回答,“他隐姓埋名到这儿来,就是要避免和公众接触。”
“吃。”甘尼特小姐说,“我们这种小村子,难得来个大人物。对了,克拉拉——就是我那个女仆,你也认识——跟芬利庄园的女佣埃尔西关系很好,你们猜猜埃尔西告诉她什么来着?丢了一大笔钱。而且她认为——我是指埃尔西认为——那个客厅女仆手脚肯定不干净。她这个月就要卷铺盖走人了,天天半夜哭个没完。要我说,她很可能和什么犯罪团伙有关系。那姑娘的性子很古怪,在村里一个朋友也没有,每次轮休都单独出门——我看这就很不正常,非常可疑。有一次我邀请她来参加女孩子们的联谊晚会,被她拒绝了; 然后我又问她家住哪儿,家里都有谁,诸如此类; 我不得不说,她的态度特别傲慢。表面上礼数周全,但她居然当场拒绝了我的邀请,真是无礼到了极点。”
甘尼特小姐停下来喘口气,而上校对仆人的事不感兴趣,自顾自说着在上海的俱乐部,他们打麻将的速度向来都很快。
于是我们就加快速度打了一圈。
“那个拉塞尔小姐星期五早上来找詹姆斯,”卡洛琳说,“假装看病,依我看她其实是来打探毒药放在哪儿。五万。”
“吃。”甘尼特小姐说,“好惊人的想法!我觉得不会吧。”
“说到毒药,”上校说,“呃——什么?我还没出牌?哦,八条。”
“和了!”甘尼特小姐喊。
卡洛琳气不打一处来。
“如果再来一张红中,”她十分懊恼,“我就有三个对子了。”
“我一直压着两张红中。”我说。
“果然是你的风格,詹姆斯,”卡洛琳责备道,“你根本不懂得怎么打麻将。”
我却自认为打得相当聪明。如果卡洛琳和牌,我得输上一大笔; 而甘尼特小姐和的是最小的牌,连卡洛琳自己也没忘了指出这一点。
东风过了,大家默默开始新的一圈。
“其实刚才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另一件事。”卡洛琳说。
“什么?”甘尼特小姐撺掇她接着说。
“我想说说对拉尔夫·佩顿的看法。”
“说吧,亲爱的,”甘尼特小姐越发起劲,“吃!”
“这么早就‘吃’太亏了,”卡洛琳一本正经地指点,“你应该做大牌才对。”
“我知道,”甘尼特小姐说,“你刚才说——拉尔夫·佩顿,是不是?”
“对。嗯,关于他的去向,我有个绝妙的想法。”
我们都停手盯着她。
“有意思,卡洛琳小姐,”卡特上校说,“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唔,也不全是。听我慢慢说。你们都知道我们家大厅里有张全郡的大地图吧?”
我们都回答知道。
“那天波洛先生从里屋走出来时,在地图前停步,看了好久,还说了好多话——原话我记不清了,好像是说这附近唯一的大镇子是克兰切斯特——那当然是明摆着的。他一走,我突然就想到了。”
“想到什么?”
“他的言下之意,拉尔夫当然就在克兰切斯特。”
就在这时我碰倒了搁麻将牌的架子,姐姐立刻指责我笨手笨脚,但她的心思基本都沉浸在那番高论里。
“他在克兰切斯特,卡洛琳小姐?”卡特上校说,“不可能!那地方离这儿也太近了。”
“绝对错不了,”卡洛琳得意扬扬地喊道,“现在看来就很明显了,他并没有乘火车逃走,而是步行去了克兰切斯特。而且我相信他还在那里。大家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就藏在这么近的地方。”
我指出她的理论有几处难以自圆其说,可是一旦某种观念在卡洛琳的脑子里生根发芽,那别人无论如何都拔不起来。
“而且你觉得波洛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甘尼特小姐若有所思,“一定是离奇的巧合,不过我今天下午在克兰切斯特的马路边散步时,看见他乘车驶过我身旁。”
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
“哎呀,我的天!”甘尼特小姐突然喊道,“我都和牌半天了,一直没注意。”
卡洛琳这才从幻想中回到牌桌上。她向甘尼特小姐指出,这是一副混一色的牌,可以吃很多张,不做大牌直接平和非常不划算。甘尼特小姐一边沉住气听着,一边收着筹码。
“是啊,亲爱的,我懂你的意思,”她说,“可这总要看你一上手拿的牌好不好,对不对?”
“你如果不做牌,就永远和不了大牌。”卡洛琳固执己见。
“哎,大家各有各的打法,不是吗?”甘尼特小姐低头瞧了瞧面前的筹码,“不管怎么说,现在是我赢得多。”
卡洛琳沮丧不已,没吭声。
东风打完了,我们继续洗牌开局。安妮端上茶点。卡洛琳和甘尼特小姐之间有些不愉快,在晚间娱乐中,这种场面司空见惯。
“拜托你稍微打快点儿,亲爱的,”每当甘尼特小姐出牌犹豫时,卡洛琳就催促,“中国人打牌时动作很快,就像唧唧喳喳的小鸟。”
五分钟过后,我们也仿效中国人,打得飞快。
“你还没和我们分享情报呢,谢泼德,”卡特上校快活地说,“真是只老狐狸。你和大侦探一起查案,却一点风声都不透露。”
“詹姆斯这个人很特别,”卡洛琳说,“嘴缝得非常严。”
她冷冷地白了我一眼。
“我发誓,”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波洛的保密工作做得好。”
“他真聪明,”上校咯咯笑道,“不肯走漏消息。不过这些外国侦探都很有本事,我觉得他们个个诡计多端。”
“碰,”甘尼特小姐平静的口吻中带着几分得意,“和了。”
形势更加紧张。甘尼特小姐连和三把,令卡洛琳恼怒不已。码牌时她教训我: “你真烦人,詹姆斯。像个木头人一样傻坐着,什么也不说!”
“可是,亲爱的,”我反驳道,“对于你想听的那些事情,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胡扯,”卡洛琳一边码牌一边斥责我,“你肯定知道一些有趣的内幕。”
我一时没吭声。此刻我兴奋极了。以前我也听说过天和——刚上手的一副牌就是和牌,但从没指望过自己也能拿到。
我抑制住狂喜之情,将牌推倒在桌面上。
“在上海的俱乐部里——”我宣布,“他们管这叫做天和——完胜!”
上校的眼珠子都快迸出来了。
“太不可思议了,”他惊呼,“我发誓,从没见过这种牌!”
受到卡洛琳之前冷嘲热讽的刺激,加上一时得意忘形,我没管住自己的嘴巴。
“至于有趣的内幕嘛,”我说,“一只内侧刻着‘R赠’的结婚金戒指怎么样?”
在他们的逼迫下,我虽省略了前因后果,但还是不得不供出发现那宝贝的确切地点,以及戒指上所刻的日期。
“三月十三日,”卡洛琳说,“刚好六个月前。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地做出各种推测,最后可归结为三种观点:
一、卡特上校认为: 拉尔夫和弗洛拉已经秘密结婚,这种解释最简单。
二、甘尼特小姐认为: 罗杰·艾克罗伊德已经和弗拉尔斯太太秘密结婚。
三、我姐姐认为: 罗杰·艾克罗伊德和女管家拉塞尔小姐秘密结婚了。
后来,准备睡觉前,卡洛琳又提出来了第四种高论。
“记住我的话吧,”她突然说,“就算杰弗里·雷蒙德和弗洛拉已经结婚了,我也一点都不意外。”
“如果他们结婚,戒指上应该刻‘G赠’而不是‘R赠’。”我提出异议。
“你哪里知道,有些姑娘喜欢用姓氏称呼男人。而且今天晚上甘尼特小姐不是说了吗——弗洛拉举止轻率。”
严格说来,我根本没听到甘尼特小姐说过这句话,但我很佩服卡洛琳含沙射影的功力。
“会不会是赫克托·布兰特?”我暗示道,“如果有谁——”
“瞎说,”卡洛琳说,“我敢说布兰特十分仰慕她——甚至可能已经爱上她了。但她这种年轻姑娘,身边有位英俊的秘书,怎么可能看得上年龄足够当她父亲的人?但她有可能鼓励布兰特对她献殷勤,姑娘们都是很狡猾的。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詹姆斯·谢泼德: 弗洛拉·艾克罗伊德一点儿也不在乎拉尔夫·佩顿,而且从来都看不上他。这一点你完全可以相信我。”
我乖乖地接受了她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