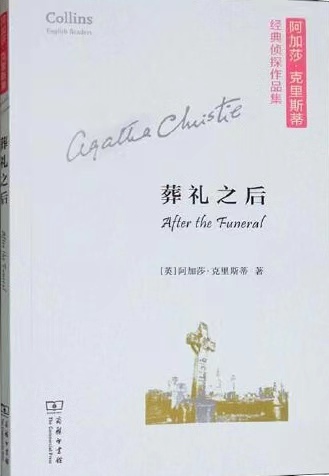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给他的出生地湖南涂上了一层永生的色彩。娥皇和女英身着万朵红霞裁成的百迭彩衣走向人间,洞庭湖的波涛似乎在拍打着天堂的大门。1921年,毛泽东曾和萧瑜横渡这湖水,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他年轻时漫步过的长岛是如此地震颤,仿佛它对地球的依附已不复存在。在毗邻的生死线上,毛泽东梦想着再生。到那时会摆脱这种羁绊吗?
《咏梅》是他1961年来所赋诗词中的佳品。毛泽东说,他读了12世纪词人陆游的《咏梅》词,便和了一首,但“反其意而用之”。
面对正在出现的中苏之争,这首词旨在振奋军心,当然毛泽东自己也寓意于中: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卜算子·咏梅》手迹。
陆游原词: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香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春天被冷峭的气氛所包围,毛泽东认为一切好的事物都是如此。梅花——中国传统中正直高洁的象征——勇敢地屹立在冰山峭崖之上。毛泽东在慨叹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孤立,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如果说陆游看到梅花时只想到令人伤感的一面,那么毛泽东却看到了梅花壮丽的归宿,尽管它孤芳自赏;因为高贵的梅花已抛弃了私欲(“俏也不争春”),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确实,最后一行的“笑”预示它的永生。
和陆游词描绘的那样,梅花确也孤寂。然而,陆游仅仅为之伤感,而毛泽东却能体味出孤独中的欢悦。
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和想像之中。
当“大跃进”开始遭受挫折时,毛泽东指出:“自己作个菩萨自己拜,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偶像。”在彭元帅被罢免后写的一份“检讨”书上,他批写道:“如果他彻底转变了,就会立地成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敦促干部走出城市,放下架子,到农民中去,毛泽东对他们讲“应该每年离开北京四个月,到劳动人民那里去取经”。
他的这种想法源于《西游记》,这部小说中的猴王就是离开宝座出外寻找佛经的。
毛泽东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问:“和尚念经为什么要敲木鱼呢?”当时他正在重读《西游记》。原来,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被黑鱼精吞掉了。敲一下,它才肯吐一字。“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毛泽东这是利用佛教的传说来阐述党的领导者说话时不应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
他开始赞赏宗教君主制。难道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不比由总统领导的南越傀儡强吗?友善的睦邻尼泊尔王国不是比议会制的印度更好吗?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的王海容是一位拘谨严肃的姑娘,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毛泽民的女儿。1964年王海容来看望毛泽东。她感到不解的是,毛泽东竟主张她去读读圣经和佛经。
毛泽东在同彭德怀冲突之后开始谈论佛教绝非巧合。既然他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就会返回到中国传统,对宗教表现出一种新的宽容态度。他日渐发现中国所有的好经验都是有先例的,因而日渐把历史看作一连串道德故事,历史不仅只是精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翻版,而是不断发生的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永恒斗争。
有一次,王海容向毛泽东偶然提到她的一个同学只顾读《红楼梦》,而不学英语语法。毛泽东听了后显得很严肃。“你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年轻女子说她读过。毛泽东问道,“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王海容说她谁也不喜欢。毛泽东继续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事实上,他推荐的小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三大贡献之一。当王海容正忙于学习以图成为一个四海为家的现代女性时,毛泽东却在第五次通读《红楼梦》。
毛泽东又问她是否读过唐代诗人杜甫的《北征》,王海容的回答是标准的学生式的:“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毛泽东站起来走到放诗册的书架前,找到那首《北征》,递给王海容,并嘱咐她要多读几遍。
王海容问道:“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泽东有点恼火:“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为什么要打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
6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一眼就看出他的侄女太死板(他鼓励她在学校里要敢于反抗),同时又太左(他要她多了解中国的过去)。
60年代,是毛泽东自1918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读史最多的时期。他在历史中找到了慰藉。
孙子不被膑脚,能修列兵法?他向一位听众问道。韩非不囚秦,能写出他的《孤愤》?诗三百篇,不多是贤圣发愤之所作么?
毛泽东把他取得控制权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成五个“朝代”。陈独秀等人都是失败的昏庸之主,因此自然而然地他把自己比作是成功的贤明君主。
毛泽东的令人惊叹的词《沁园春·雪》*写于长征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发表,毛泽东在词的最后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似乎把对过去的羡慕和对现实的把握联系在一起。*(见《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在毛泽东的意识中,自己同命运的主宰不可避免的会面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有时称这位命运的主宰为“上帝”,有时则称之为“马克思”。
毛泽东在1964年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
但是,毛泽东在内心里却不乐观。“不过,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
几星期后,四位副总理来和毛泽东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
“制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而在1958年毛泽东不相信这一点。
他继续说,“我已经七十多了,但我们不能把‘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制订计划的基础。”
毛泽东对一些军队干部讲:“如果原子弹投下来,只有去见马克思一条路了。不过,年纪大了,终究要死的。”毛泽东还曾伤感地说:“负担太重时,死是很好的解脱方法。”
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共进晚餐,问毛泽东是否可以拍一部电视片来重现当晚的情景。斯诺说:“有谣言说您病得很重,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幕公之于世,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毛泽东苦笑了一下,好像是信心不足。事实上,他认为自己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毛泽东确实看到自己生命将尽并坦然以对。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人说:“谁都难免一死,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从毛泽东和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心中把中国的垮掉和自己的垮掉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已很难把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分割开来。他已接受作为人的毛泽东将会死去这一事实,但他不能接受中国在他死后偏离毛泽东主义的道路。
他对几个军队的领导人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
和邓小平相反,毛泽东的面部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越发容光焕发,他已是面如满月,少有皱纹,表情已不那么丰富,双眼更加深不可测,发型则依然如故。
1964-1965年间,毛泽东与客人交谈时护士不离左右。帕金森氏综合症引起的震颤、僵硬和动作不协调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并不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嗜烟,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的“中华”牌香烟。与斯诺在一起一个晚上就抽了12支。他很少洗澡——卫士用湿毛巾为他擦身——从不刷牙。
他同李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
由于轻视一切专家,毛泽东把自己的医生看成是清洁女工。
他曾说:“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另一半他要听我的。”
现在,毛泽东的多数时光不是在菊香书屋度过的,而是在近处的室内游泳池,那儿有接待室,书房,卧室,这些都为他增添了方便。
毛泽东还和以前差不多,在豪华的地方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他从不将茶叶泼掉或留在茶杯里,而是用手指夹着将其放进嘴里,咀嚼过后咽下去。当他在湖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处置这些茶叶。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摆设鲜花或其他装饰品。他总是吃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无论是和江青一起吃饭,还是跟外国首脑共进晚餐,美餐之后他都要咕噜咕噜地喝汤,还会打着饱隔,且毫不在意。
毛泽东在60年代的工资是每月430元,只是工厂里高级技术人员工资的两倍。毛泽东不喜欢购置贵重物品,不过,他真的需要什么,党都会使其满足。因而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他在1964年说的一句牢骚话:“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雇不起。”
尽管毛泽东的地位看上去已脱离了人世间的任何官职,但人们仍称他“毛主席”。这与“周总理”和“林国防部长”的称谓含义不同。
确实,红色中国不知该怎样加衔于毛泽东,但它知道不能给他加上什么。毛泽东是一位将军,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他不喜欢俗气的军衔。他变得越来越像帝王,但又不便公然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与帝王类似的身份。
因之,“主席”的头衔便意味着,毛泽东头顶不乏城市会议严肃性的民主桂冠,占据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历来由上天指定凡世统治者人选的职位,恰似一位半人半神的被崇敬者不伦不类。
‘主席”一词的频繁使用,使刘少奇大为不满。这位一国首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被称作‘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你听见谁叫过‘列宁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