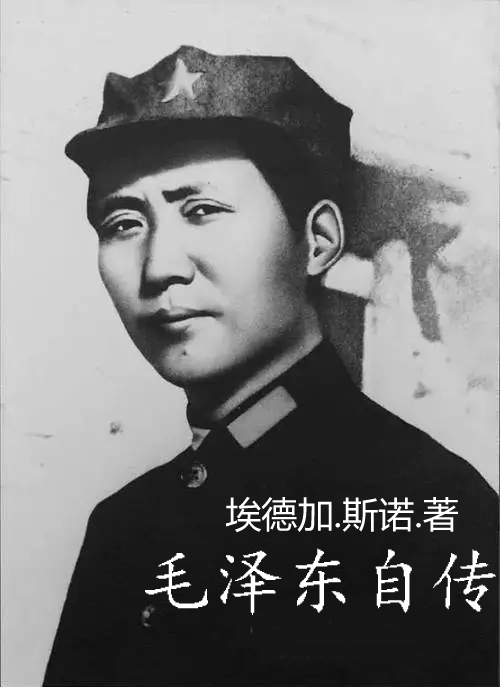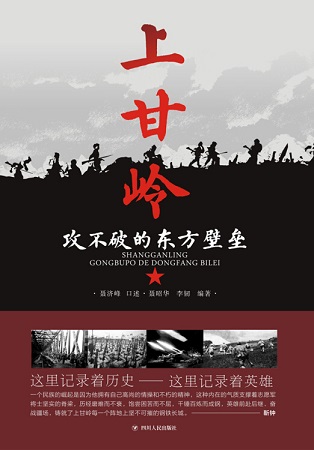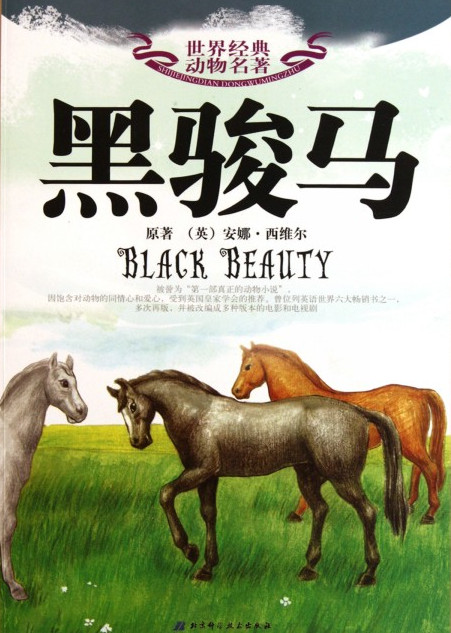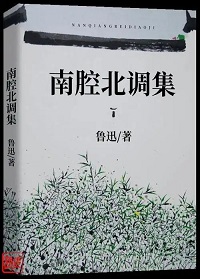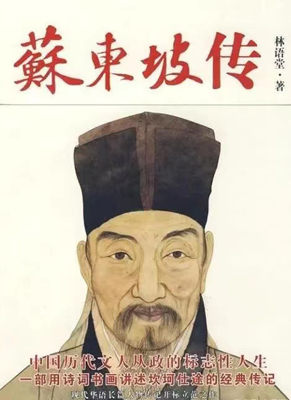4.神圣化
美国人倾向于非神秘化,但他们也最倾向于神圣化。神圣化依然不是神化,因为它牵涉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很少把什么东西神化。在有些社会中,一种事物达到了超出普通人能力时,往往会被神化。如《众神之车》的作者所描绘的种种现象。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人把二次大战时美军飞机的偶然降落神化,用木头做了一个逼真的飞机加以崇拜。在不少社会中,巫医具有神秘的感觉。美国社会没有这样的文化,虽然有人民圣殿教这样几百人集体自杀的案例,但这是罕见的。美国民族不倾向于神秘化和神化,但这个民族有一种特殊的天性,我称之为“神圣化”。
何为“神圣化”?神圣化首先是一个世俗领域。它带有某种崇拜的性质,但不是宗教崇拜。神圣化的过程,是将某一人间现象推到极高的地位。这个过程并非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组织发动的,而是社会化的过程。我们先来看我所谓的神圣化的具体实例,再来分析这种现象的社会功能。
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很容易感情冲动的种族,也是一个很容易接受外部事物的民族。神圣化可以在政治领域中看到。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便是这种神圣化的典型表现。会场上的人们如痴如狂,那种热烈,那种激动,那种真情,都是一种少有的情感上的共鸣。两党各自的候选人,都会在这个会场上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出场时,人们可以欢呼十分钟之久。他们的讲话,不断地被鼓掌声和欢呼声打断。整个竞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这样的欢迎。照理这样一个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文化中,一个个人很难受到这样的崇拜。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被神圣化了,他们只是一个象征,一种文化或大家追求的目标的象征。人们更多地是在追求一种神圣化了的精神。
美国人对个人也极容易走到这一步。不论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取得了成就,往往容易成为神圣化的对象。上至总统,可以说华盛顿和建国之父、林肯、罗斯福、肯尼迪等是被神圣化了的。美国人在赞美他们的同时,也在赞美一种精神。个人的神圣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中,在体育界,很多著名的球星或其他运动员都被纳入神圣化的过程,如田径运动员刘易斯、跳水运动员洛加尼斯等。在经济界,被神圣化的可能性更大,艾柯卡一度是这种神圣化的热点,艾柯卡在福特汽车公司取得了光辉的业绩,被赶出福特公司后,加盟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又引人注目,他的书成为畅销书。电影明星自然在神圣化之列,著名导演、艺术家也不例外。尤伯罗斯因组织第 23 届奥运会而名声大震,也被神圣化。最近在伊朗门事件中受牵连的诺思中校,居然也成为神圣化的对象,因为许多人觉得他忠于职守,是美国精神。不过,好象很少有哪位教授成为神圣化的对象。歌星自然非君莫属,玛多纳红极一时,杰克逊更是红得发紫,连里根总统都授予他一个什么奖章。他的演出达到的效果,令人惊奇,听众们的崇拜劲头,恨不得死了去。科技界的人士,也极容易成为神圣化的对象,如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王安电脑公司的王安等。这个神圣化的过程,充分开放,不是由一个中心决定谁可以成为神圣化的对象,而是由社会大众加以选择的。
这种神圣化,自然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如橄榄球比赛,实际上也被神圣化了。人们不是在那里看球,而是看各自所信奉和拥戴的东西。比赛的整个进程,从奏国歌、仪仗、出场、比赛、球场休息时的演出,都超出了球赛本身的意义。如庆祝建国二百周年在自由女神像下搞的活动,热闹、场面大,其性质也非一般的庆祝,带有某种神圣化的味道。这是政府所为。政府常常成为神圣化的推动者,如军队,军队的神圣化很明显。尤其表现在美国人对军事胜利的态度和对在战场上阵亡的人身上。华盛顿有一座奇特的越南战争纪念碑,每一个阵亡的人都留下了名字。对于阵亡者,官方要举行隆重的葬礼。政府对航天飞机的态度,也是一个极好的实例。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后,政府给予遇难的宇航员极高的评价和荣誉,把他们视为开拓美国精神的献身者。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成功,政府视为美国精神的胜利,意义已在宇航技术突破之外了。
神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将各种人们信奉和选择的现象上升为美国精神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接受美国精神的过程。社会培养了这种机制,人们有牢固的英雄崇拜、成就崇拜的心理沉淀。西部片中描绘的基本精神,就是英雄崇拜和成就崇拜。《星球大战》在另一个角度体现这种精神。今天的英雄已非昔日的牛仔形象,今天的成就概念也在变化。然而,美国人内心中英雄崇拜和成就崇拜的性格依然存在。美国民族缺乏鬼神崇拜,取而代之的是前两种崇拜。
这两种崇拜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在得到强而有力的呼唤时会显现出来,当代美国文化中平均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生长,使这种性格受到很深的压抑。在一般条件下,很难想象美国人会有这样强烈的崇拜情感。神圣化过程,一方面是一个社会感应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自我释放的过程。看一下球扬、会场和演唱会上观众疯狂的情感,就会明白它们如何满足了人的上述两种基本需要:崇拜感和个人释放感。
这种世俗崇拜,不同于神化崇拜。神化崇拜是崇拜超人和超自然的力量,如神、仙、鬼、图腾等。对上帝的情感,在美国人是一种信仰、一种情感、一种信念,而更多地不是一种崇拜。美利坚民族非神秘化的倾向,使他们很难产生神化崇拜,人的崇拜需要便转向世俗。人们在自己的周围寻找崇拜的寄托。美国人是个实用主义的民族,他们难以崇拜抽象的、传说中的、看不见的对象,但对自己周围的成功、勇敢、冒险、智慧,他们可以崇拜。这种崇拜夹带着复杂的因素,理性的,非理性的,情感的,非情感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神圣化过程,实际上不是神圣化个人,而是神圣化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已构成文化的传统,成为其中的基因。社会的神圣化过程又不断地巩固它。这是一种什么精神,难以名状。抽象地讲,存在。有关这点,可见康马杰所写的《美国精神》一书。
神圣化的过程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功能,这就是维持和传播社会的核心价值。社会的神圣化过程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它一方面将其精神传播给社会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又吸引人们加入神圣化的过程。人们的情感、思想、信念、追求在这里达成某种一致。我想起卢梭说社会必须有公民宗教的论点,觉得社会神圣化的过程,十分象制造和传播公民宗教的过程。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的社会中,神圣化是最好的传播核心价值的机制。
一个社会没有核心价值就不能均衡发展。问题是核心价值从哪里来,又怎么样来维持。如果是来自对人们周围事物的提取,由人们自己来传播和维持,则可能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机制。
5.航天飞机的误导
“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成功,飞黄腾达,直奔蓝天。各电视网都播发了现场镜头。这次发射成功,对美国人来说非同凡响。1986 年 1 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美国没有发射过航天飞机。那一年,“挑战者号”爆炸,宇航员不幸遇难,曾震动世界。两年半之后,“发现号”发射成功,不能不说实现了许多人的梦想。
航天飞机的计划最好地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精神,也就是康马杰所云:美国人的信念是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除非得到全胜就绝不罢休。对太空的探索恰恰体现了这种信念。航天飞机的制造、发射和控制过程异常复杂。只要看一下控制中心令人眼花缭乱的成百台电脑,就可以想象这里面需要的科技能力。自从“挑战者号”出事之后,美国航天部门,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来改进计划,共作了四百多项技术改进。美国人的信念是如上所说,所以他们坚信能找到办法,坚持不懈。这种精神促使他们进行许多极为大胆的想象,如星球大战计划、航天飞机等,也促使他们接受许多不起眼的小发明,如开信封的机器,开罐头的机器,电动削铅笔刀等。应当说,这种信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
不过,这种信念也会异化。这种信念促使美国人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面临的问题,结果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之后,人们又往往产生错觉,似乎最终解决难题的不是人,而是科学技术成为最终的力量,人成了它的奴仆。
一位教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也有同感。这种错觉主导着很大一部分社会。在一些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面前,美国人往往会认为是科学技术问题。或者是钱的问题(这是商业主义精神的结果),而不是人的问题,主观性的问题。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对待苏联实力增长的态度是拼命发展优于苏联武器系统的装备,包括最终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对待恐怖主义的方法,就是用先进的攻击力量打击对方。对待国际海域的威胁,就是强大的设备精良的舰队。对待不喜欢的政权,就是向反对派提供大量先进的武器。最典型的说明就是残疾人得到的装备,自动导向的轮掎,可以听从命令的床边服务设备,可以导向的眼镜。残疾人可以自由行动。但作为人,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在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也如此。
一方面人们过分信仰技术,另一方面技术也成为政治。“发现号”发射成功后,肯尼迪航天中心主任佛莱斯特·麦克卡尼(Forrest McCartney)说:“今天每个美国人都肯定扬眉吐气。”总统里根在华盛顿看了电视,并发表演说:“美国重新回到了空间。”其实,航天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砝码。六十年代,苏联登月成功,美国人大为恼怒,肯尼迪总统下令全力发展航天计划,后阿波罗登月,压倒苏联一筹。技术竞争背后存在着政治竞争,政治竞争需要技术竞争、技术竞争支持政治竞争。
二十世纪人类的一个重要走向,就是政治与技术的高度一体化,没有技术的政治无法成为强大的政治,当然,没有政治的技术也成不了强大的技术。
由于技术与政治的这种结合,技术本身异化了。这一现象在美国尤为鲜明。有时候,不是人掌握技术,而是技术掌握人。如果要压倒美国人,必须做一件事情:在科学技术上超越他们。对很多民族却不一样,有技术不行,还必须有文化的、心理的和社会学的条件。
美国人长期处在优越的地位,差不多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优越地位就形成了。七十年时间里,美国有过几代人,二次大战之后出生的人目前也已是四十多岁。这一代美国人更是处在“美国第一”的氛围之中,心理上形成一种定势。因而,美国也是输不起的民族。技术优越感已渐渐发展成民族优越感,他们不能想象有什么民族可以超越他们。日本在战后几十年中迅速崛起,在高科技领域中发展异常快速,在有些方面已超越美国,如电子产品、汽车等。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日本资金也大量涌入美国。有人说夏威夷的地产不少落入日本人手中,由于日本人纷纷来买房子,弄得地价飞涨。美国人对此是不服气的,对日本人往往不屑一顾,谈起来总带有轻蔑的神态。美国人在很长时间里不愿承认日本的成功。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为使美国人明白这一点,花了不少气力。他的《日本名列第一》令美国人如梦初醒。类似的状况,我想美国人还会遇到。
政治和技术的这种奇妙的交合,也涉及航天飞机。而且这种高科技更是这种关系的集中反映。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批评这种“异化”。有一位叫阿伦(Allen)的物理学教授就认为,在“挑战者号”发射失败之后,为了挽回面子和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宇航局把发射成功放在首位。我说航天飞机的误导,只是个比喻,实际上指科学技术的误导。美国人可能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这种“误导”。
6.工作伦理
美国人对待工作的态度,自然不能说是清一色的,有很大差别。如果言整个社会的劳动力,那差别极大,很多人宁可领政府发的救济金,也不肯去找工作,有工作也不做。这构成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很多纳税人牢骚满腹:为什么政府要把我们口袋里的钱拿去给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此忿忿不平。
如果说在工作的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大多数工作的人,都工作得努力、勤奋、积极。对此,可以作多种解释。工作态度是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人们的工作态度认真、勤勉,社会就获得了这笔财富。反之,社会就会丧失这笔财富。日本、新加被、香港、南朝鲜的经济起飞、与人们的工作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自然,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促进工作态度。如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香港这样的东方文化中,严格的管理制度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个人主义占主导堆位,什么东西促进着人们的工作态度,很值得分析。无论如何,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激发出来的良好的工作态度。均是一个社会的第一财富。
美国人的工作态度,可以说是认真的,勤勉的,而且有些人的工作态度使人觉得不易做到。
在所有的政府机关、公共场所、商店、机场、车站、饭店等地方,大部分人都有较好的工作态度。他们认真、热情、主动、熟习业务。我去过许多公共的或私人的部门,有的去做调查,有的是去办事,那儿大部分人都可以称得上工作称职。他们工作主动。我在国会议员内格尔(Negel)的联络处做调查时,那里的两个办事人员一件一件地认真解释,还翻箱倒柜地找参考资料。我在的政治学系的三位秘书,每天坐在那里,三个人很少讲话,自己忙自己的事情。大部分工作场合的人,都是忙忙碌碌的,闲着的人几乎没有。
如果到第三产业的部门去,服务态度均不错。饭店里的招待,热情主动;商店里的营业员,也一样,有问必答,常常主动问,要什么帮助。公共汽车的驾驶员,处处为乘客着想。我乘坐的一班车,由于时间长了。驾驶员知道我住在哪里,就在那个路口主动停车。乘坐飞机,如果有什么问题,航空公司会全程安排。我的一位朋友的父母来美国,老人不会讲英语,又遇上飞机误点。航空公司全部负责安排,包括误点安排旅馆、接送。如果坐在家里想吃 pizza,打一个电话去,有关公司就会送货上门。整个服务业,十分方便,令人感到不陌生。
讲到工作态度,许多美国人也是极其勤奋的。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助教,几乎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要来办公室工作。他正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大部分教师每天都来系里办公,坐在计算机前著书立说。据说一些人达到正教授的位置后,就不那么勤勉。一位教授的夫人,是搞激光的,那个工作劲头令人吃惊。几乎每个晩上和星期天都在实验室工作。可能日本人的工作态度还要厉害。日本人每天工作到深夜是很正常的。日本人有过一句名言,叫“工作到小便发红”。美国很多人也工作勤奋,但他们与日本人还是有区别。美国人有一个专门的字眼描绘这种人,叫 Workaholics,直译叫“酗工作者”,由“工作”和“酗酒”两个字眼组成。
问题是什么东西促使美国人这样工作?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促使他们这样做?如果工作态度需要庞大的机构来促进的话,那这对社会的经济管理来说,将是不堪忍受的负担。
解释有多种、其一就是工作伦理(Work ethic)。工作态度受工作伦理的影响。工作伦理,也成为清教伦理,新教伦理。有的认为它们鼓动人们勤奋工作。这种精神由早期殖民者从欧洲带到美国,其基本精神是:物质上的成功是上帝恩赐的信号,实现了这些成功的将是上帝的选民,将会进入天堂。韦伯曾写过一本书来分析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关系,算是这派的著名理论家。如今,这种宗教色彩早已大大淡化,但这种精神在小范围内还存在。大部分人已不能说受这种宗教精神的影响。文化的发展,早就把这种宗教精神排挤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如果说上了年纪的人还有这种观念,年轻一代就不知这种宗教信仰为何物了。所以,显然不能用宗教的感情来解释。宗教情感,对新一代人来说,已是十分遥远的故事了。
另一种解释就是美国之梦(American Dream)驱使人们勤奋工作,看过电视连续剧《埃利斯岛》的人,不难明白什么是典型的美国之梦:这就是发财致富。勤奋工作可以得到报酬,可以拥有财富,提髙社会地位。移民到美国来,结果“发”了,成为巨富这种解释,至今还能成立,大部分工作着的美国人出于几种交汇的动机,其中获得金钱是很基本的动机。但是否每个人都想腰缠万贯,难说。不少美国人已没有这样的兴致,只要能生活得舒适就行了。
还有一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这种解释相信工作可以使人产生满足感,如马斯洛就有系统的理论分析。事实上,的确有不少美国人在工作中追求心理上的满足。这种现象可以从大量的自愿工作者的现象中得到证明。自愿工作者没有报酬,完全是义务的,但他们由工作可以摆脱个人的孤独感,得到社会的承认,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但从纯粹心理学考虑问题的人毕竟不多。
应该还存在别的什么机制,促使人们认真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们追求生活的愿望只有在勤奋工作时才能得到满足。产生这种机制的主要原则有两个:一是生活水准的提高与否主要决定于收入的多少,金钱的多少,金钱成为维持和改善生活之必需;二是大部分工作职位由私营的部门提供,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有充分的用人权,没有终身雇佣制。一方面是人们为了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必须工作,另一方面如果要继续工作下去或得到更好的报酬,必须勤奋工作,不然就可能失去工作。这两种原则,是当今促使大部分美国人勤奋工作的主要动力。
当然,这两种原则要能发挥作用,还需要其他条件。从经济上来说,商品的充分涌流是一大条件。商品充分涌流使每一个有钱的人可以购买任何出售的东西,地位、权势、家族不再成为限制,这样大家就会去追求金钱,而非其他。从文化上来说,由于金钱在任何一件工作面前都是平等的,各行各业的髙低之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拿这些钱一样可以达到一个人所追求的目标。搞环境卫生的人挣的钱并没有臭味,在社会上一样流通。当人们的消费欲望被充分刺激出来后,只要有钱便可以,而工作性质的差别是第二层次的东西。
可以说,这套机制具有强制性,它们把所有的人都纳入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之中,并且强迫进入这个机制的每一个人服从它们的规则,也可以说送是私有制的强制。它们可以把任何不愿服从这个机制的人驱逐出去。人们在这里得到金钱,资本也在这里得到利润。这套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转的基本机制。同时,这套机制又在政治系统之外,人们的工作态度由这套机制来保证,而非由政治系统来保证。政治系统显得轻松多了。
以上说是概而论之的,社会存在反社会和反这套制度的力量。许多人宁愿游离于这套制度之外。
美国人工作勤勉,但也最善于放松。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 to work hard and play hard,玩命地工作,玩命地玩。这一点和日本人不同,日本人大概只有前一半,玩命地工作。日本人最近纷纷议论一种病,叫“过劳死”,即[1]美国人在周末或在假日里,具有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大笔大笔地花钱。学生在周末也最疯狂。也许是在工作中受的强制和压抑太多,要发泄一下。
任何社会要使人们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都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很简单:就是想办法使每一个人部感到是在为自己工作,而非为别人工作。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重要的。怎样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方法可以不同。这种感觉,仅在经济领域并不一定能产生,还需要政治、文化等其他条件。其实社会组织,无论何种方式,很少允许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这样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关键的是要使人们有这种感觉,这种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