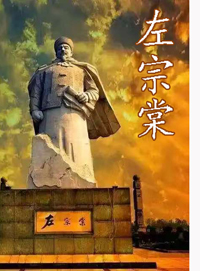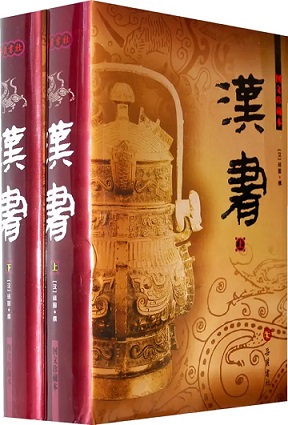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天,又是海棠如雪、红榴似火的时候,韩子奇一家在沉闷惶恐的气氛中庆祝爱子天垦的周岁生日。没有邀请任何客人,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让姑妈做了打卤面,一家人默默地吃,祝愿这个生在多事之秋的孩子健康成长,长命百岁。去年的“览玉盛会”,像一个美好的梦,韩子奇不知道这个梦还能持续多久,他辛辛苦苦创下来的家业,还能够完好无损地传给儿子吗?
一辆洋车停在门口,沙蒙。亨特出人意料地来了。
“亨特先生,今天是犬子周岁生日,谢谢您的光临。”韩子奇把沙蒙。亨特迎进客厅,“您吃一点儿面怎么样?庆祝生日的长寿面!”
“噢,很好!”沙蒙。亨特歉意地说,“很抱歉,我没有给令郎带来任何生日礼物!”
韩子奇笑了笑:“今年不敢像去年那么张扬了,朋友们都没告诉,您也不必客气。何况,我们十多年的友谊,比什么礼物都珍贵啊!”
这话是十分真诚的,他们两人都心里清楚其中包含的内容。十一年前,如果没有沙蒙。亨特的鼓动,韩子奇还不敢那么贸然地脱离汇远斋;而如果没有沙蒙。亨特预付了一大笔货款,他也决没有能力那么快地重振奇珍斋,公开亮出金字招牌。创店之初,他仍然自己琢玉,自产自销,积累了资本之后,便将作坊撤销,成为以做“洋庄”买卖为主的、敢于与汇远斋争雄的玉器店。为了信守当初的协定,他把沙蒙。亨特的玉玦依照原样仿制了三块,做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满足了沙蒙。亨特“古物复原”的心愿,而韩子奇则要求沙蒙。亨特将玉块的原件转让给他:“亨特先生,我可以为您做十件、百件仿制品,但希望这件国宝能留下来!您知道,我要做的事是无论如何也要做到的,为此,不惜任何代价!不然的话,我总觉得对不起这旧宅的主人。他一生的收藏,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流散,我要尽我所能,把它们都收回来!”一片痴情,感动了沙蒙。亨特,韩子奇和那个毁宝、卖宝的蒲缓昌多么不同啊!一言为定,他把五块转让给了韩子奇,为了友谊,韩子奇给了他高出当初买价的价格。十年之后,刮目相看,韩子奇终于以其收藏的富有、鉴赏力的高超,成为北平的“玉王”,这当中不能不说包含着沙蒙。亨特的一份力量!
姑妈送上来一小碗打卤面,沙蒙。亨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说:“这长寿面简直太好了!可惜呀,韩先生,明年的今天,我就吃不到了!”
“这......什么意思?”韩子奇一愣。
“我要回去了,”沙蒙。亨特放下了筷子,“中国的局势令人不安!有消息说,贵国政府向东京表示,愿意和日本签订友好条约,并且答应迫使所有的西方利益集团离开中国,把西方的商业权利和租界地转让给日本。日本的外务当局倒是欣然同意,但是遭到日本‘皇军’的拒绝,他们的胃口是以武力征服整个中国!现在,就连那些宁愿忍受独裁统治的中国人,也感到恐慌了!”
韩子奇默默无语。沙蒙。亨特说的这一切,正好切中他的心事,他这个向来不问政治的人,却无法摆脱政治的困扰,近几个月来,越来越不能安宁地潜心于他的买卖和收藏了。
“现在,许多西方人士都打算撤离这个是非之地。”沙蒙。亨特继续说,“我这次回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了,也许我们之间的贸易很难继续了呢,韩先生!”
韩子奇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不是您、我所能够掌握的,只好听之任之。我们的命运掌握在......”
“不,韩先生,”沙蒙。亨特说,“您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呢?”
“这......怎么可能?”韩子奇轻轻地摇了摇头。他本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十几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命运搏斗,忍受了艰难困苦,终于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得到了他所想要得到的一切,自己主宰了自己。但是,他现在面临的威胁不是一个小小的蒲缓昌,而是整个北平、整个中国发发可危,在“莫谈国事”的年代,他作为商人、匹夫,又有什么能力和命运抗争呢?
“韩先生没有想到《孙子兵法》上说的‘三十六计,走为上’吗?”沙蒙。亨特眨着蓝眼睛。这个精明的英国人引证起中国的经典,简直如数家珍。
“走?我不能像您那样一走了之!我是中国人,往哪儿走?”韩子奇眼前一片茫然。
“和我一起到英国去,继续您的事业!”沙蒙。亨特伸开两手比划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又......”他一时忘记了下面的词儿该怎么说。
“又一村!”韩子奇苦笑着说,“这‘又一村’恐怕我去不得!我这儿有商店,有家,有老婆孩子......”
沙蒙。亨特不以为然:“不,对一个商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资本!只要有资本,一切都会有的!您可以把夫人和令郎带走,把家搬走嘛,英伦三岛的二十四点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难道没有您立足的地方?”
“哦,我从来......没这么想过,”韩子奇觉得沙蒙。亨特向他描述的景象只不过是海外奇谈,根本不可行,“我离不开这块地方,您知道,奇珍斋能有今天,是多么不容易,这里面有我们两代人的心血——也是祖辈的心愿!刚刚有了点儿起色,我怎么能毁了它?还有这所宅子,我对它的感情,别人也许无法理解,我离不开它!”
沙蒙。亨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太重了,太恋家了!岂不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贵国政府面对日本的蚕食,步步退让,今天的东三省和察哈尔、河北,恐怕就是明天的北平!请问:又有谁会想到北平有一个奇珍斋和‘博雅’宅面手下留情呢?一旦战火烧到北平,您的心血结晶也就难免玉石俱焚!”
韩子奇打了个寒战,痛苦地闭上眼睛,手指掐着眉心,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不可避免的凄惨景象!
“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沙蒙。亨特低声说,“故宫博物院的珍宝,已经秘密地运走了二十四万件,整整装了六列火车!”
“唔?运到哪儿去?”
“上海。为防不测,现在存在英、法租界里,这是我的朋友透露的可靠消息!根据战局的发展,这批东西可能还要转移。看来,贵国政府已经对北平不抱希望了,那么,您呢?韩先生,现在看来,您去年的‘览玉盛会’很不是时机啊!您把自己的收藏公之于众,已经尽人皆知,一旦局势有变,您连转移都来不及,恐怕就难以保住了!”
韩子奇愣住了。赏玉的内行,政治的外行,他办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去年踌躇满志的“览王盛会”,赢得了“玉王”的美称,却把自己推向了绝境!“亨特先生,我该怎么办呢?”
“防患于未然,转移!”沙蒙。亨特说,“如果您信得过我,我愿意为朋友效劳!北京饭店就有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的办事机构,车票、船票、客运、货运都可以委托他们办理,您和我一起走,会方便得多!您要是觉得合适,我就等一等您......”
“唔......”韩子奇动心了,“谢谢您的友谊,亨特先生,请让我再想一想,对我来说,这件事毕竟太大了。”
沙蒙。亨特起身告辞,又叮嘱说:“我不能等您太久,要早下决心啊,老朋友!不要忘了鸿门宴上项羽的教训,我现在扮演的是范增的角色,您要‘决’啊!”他抬起右手,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仿佛是捏着一块玉玦.送走了沙蒙。亨特,韩子奇默默地走回来,在院子里那棵海棠树下站了半天。海棠的繁茂花期已是尾声,微风吹来,落英缤纷,天井中撒得满地,像铺了薄薄的一层雪。韩子奇踏着落花,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伤感:万物都有代谢,花开之后便是花落!不知明年花开之日,“博雅”宅主身在何方?
韩太太见他那闷闷不乐的样子,就问:“孩子的生日,一整天都耷拉着脸,这是怎么了?那个洋人来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韩子奇一言不发,只是连连叹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把心里想的事儿向妻子说清楚!
天快黑的时候,玉儿突然回来了。她好像在路上赶得很急,脸上冒着汗珠儿,毛背心脱下来拿在手里,身上只穿着那件月白色旗袍,还不停地把毛背心当扇子扇。
“今儿又不是礼拜六,你怎么回来了?”韩太太看她那气喘吁吁的样子,以为一定有什么急事儿。
“咦,不是天星要过生日吗?我特意赶回来的!明天没什么重要的课,不碍事的!”
“哟,还是小姨疼我们天星!”韩太太笑着说,“姑妈,您快着把小‘寿星老儿’抱过来呀!”
“哎!”姑妈答应着,从东厢房里抱着天星到上房里来,刚刚满周岁的天星,长得虎头虎脑,个头儿像个两三岁的孩子,挣扎着要下地。姑妈扶着他的腰,他伸着胖胖的小手向玉儿跑去,嘴里亲切地叫着:“姨,姨......”
“哎,好天星,乖天星,小姨想你都快想疯了!”玉儿伸手把他抱起来,在那粉红色的圆脸上亲个没够,“天星,小姨还给你带来了生日礼物呢!”
玉儿从衣兜儿里掏出一个精巧的小锦盒,取出一只碧绿的如意,给天星挂在脖子上。
“好看,好看!这一打扮,我们天星就更俊了!”姑妈喜得合不拢嘴。
韩太太撩起那只如意看了看:“翠的?你呀,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
“这不是买的,就是我考上燕大的时候,奇哥哥送给我的那块!给天星吧,他是我们奇珍斋的小主人,一切都是该属于他的!”玉儿又亲着天星,“绿色象征和平、生命,小姨祝你幸福成长、万事如意!”说着,她那双大眼睛突然潮湿了,涌出了泪珠。
韩太太伸手把天星接过来,嗔笑着说:“你看,你看,疯子似的,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玉儿却忍不住泪,掏出手绢儿来擦,眼睛红红的。
韩子奇疑惑地看着她:“你今天是怎么了?”
玉儿强做笑容说:“没什么......就是心里憋得慌,看见天星,就好多了。就盼着下一代能幸福,别再像我们......”
“你们学校出了什么事儿吗?”韩子奇发觉她好像有些不正常。
玉儿抬起泪汪汪的眼睛说:“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失踪了......”
“噢!是投河了?还是上吊了?”姑妈插嘴问。
韩太太挺各漾地瞅了她一眼。在儿子的生日,谈论这种不吉利的话题,是令人不愉快的。
“都不是。让警察抓走了!”玉儿说。
“因为什么?”姑妈又问。
“因为他宣传抗日......”
“这帮子挨刀儿的!”姑妈愤愤地骂道,“胳膊肘儿朝外拐,向着日本人!我也骂过日本人,叫他们来抓我吧!”
“得了,别这儿裹乱了,”韩太太心烦地说,“您还不张罗做饭去?到这会儿了,大伙儿都还饿着呢!”
姑妈嘟嘟囔囔地走了,韩大太沉着脸问玉儿:“你说的那个人,是男的?是女的?”
“男的,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同学。”玉儿擦着泪说。
韩太太心一动:“跟你没有什么连扯吧?”
“什么连扯?都是中国人!”
“我是说......”
“你说什么?你什么也不懂,尽瞎猜!人家是个正派的人,同学们都敬重他!就因为他散发过传单,就被抓走了!”
“没你的事儿,就好。”韩太大放心地说,“一个大姑娘家,在外头可别惹事儿,踏踏实实地念你的书......”
“念书?”玉儿鼻子里哼了一声,“人心乱成这样儿,还怎么念书啊?真像去年冬天上街游行的同学说的那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那你想怎么着?”韩太太不高兴地瞪了她一眼,“家里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倒身在福中不知福!要不,就甭念了,回家来帮帮我,也省得......”她本来想说:就是因为你帮不了我,才收留了姑妈,养着个外人。可是,话到舌尖儿又咽住了,姑妈是个苦命人,这一年来给她带孩子、做饭、洗衣裳,什么活儿都干了,却没要过一个子儿的钱,把这儿当成自个儿的家了,她不忍再说什么,让姑妈听见,准得难受。
玉儿却冷笑着说:“燕大的大笼子还不够我受的?你还要把我关到家庭的小笼子里?够了!”
“说什么疯话呢?”韩大大听她说话没谱儿,心里就有气,“家是笼子?赶明儿我给你找个好‘笼子’!请‘古瓦西’给你打听个人家儿,早早儿地把你聘出去,省得你这么没事儿找事儿!”
“算了吧你,我才不会像你似的当管家婆呢!我这辈子决不会嫁人,当做饭、生孩子的机器,我谁也不爱!谁也不爱!”玉儿像是和姐姐赌气,又像是在借题发挥地倾吐她胸中的怨气,说着说着,眼泪又像断线的珠子似的滚下来,“不用你赶我,我走!”
韩太太脸一沉:“越说越邪乎,你上哪儿去?”
玉儿擦着泪说:“你甭管!这里的空气太沉闷了,要憋死人,我要离开这个世界,躲到世外桃源去!”
韩子奇一直插不上嘴,玉儿的话,他听得似懂非懂。近一年来的局势变化,使他也感到沉闷和压抑,但是,玉儿的情绪反常似乎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会不会和那个男同学的“失踪”有什么关系?玉儿不是小孩子了,她是个大姑娘了,在大学里,男女生相处在一起,会不会她和那个同学有了某种情感,这个突然变故刺激了她?如果是这样,那将是很麻烦的事儿,这不但会影响她的学业,甚至会给她今后的人生道路罩上阴影。他作为兄长,该怎么帮助她呢?想到这里,就说:“傻妹妹,你太爱幻想了,世界上没有世外桃源,人,都得在现实中挣扎!今天中午,亨特先生还劝我到英国去呢......”
“英国?”玉儿突然不哭了,睁大了眼睛看着他,“英国没有日本人吧?没有抓学生的警察吧?去,咱们去!你和亨特说定了吗?”
“还没有,”韩子奇没想到她会对此感到这么大的兴趣,“我还没跟你姐商量呢,我觉得......”
不等他说完,韩太太就打断了他的话:“什么,什么?这一个还没哄好呢,你又出来了新鲜的?我说那个洋人大中午地跟你嘀咕个什么呢,闹半天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英国?我们在中国好好儿地待着,干吗上英国?”
“还‘好好儿地’呢?也许到了明年,你就连炸酱面都吃不上了!愚昧呀,北平眼看就是日本人的了!”玉儿为姐姐的目光短浅而叹息。
韩太太不知道“愚昧”是什么意思,只当她是着急,就说:“我就不信,中国养着那么多的兵,能让日本人打过来?不会跟他们打吗?”
“听你的?”玉儿鄙夷地说,“连个抗日传单都不许发,还打呢?我们的军队要是真打,大姐的丈夫和孩子也就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