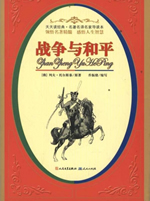现在,天星睡了,侯家的三个淘小子、两个愣丫头也在南房里打上呼了。院子里黑灯瞎火,上房的客厅里却亮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黑布窗帘,这是战时的特产,连一星亮光也被遮挡得严严实实。侯嫂给韩太太沏上盖碗配茶,凑在灯下做针线。韩太太半闭着眼睛坐在八仙桌旁,听老侯向她报账。
老侯拨了一阵算盘珠子,说:“太太,这个月进项寥寥,创去伙计们的工钱、饭钱、电灯钱、水钱、房产税、地皮税、营业税,一个子儿也入不了柜,还得往外赔法币一千二百六十七元五角!”
“啧,”韩太太不耐烦地睁开了眼,“我不懂得这个税那个税的,简断捷说,月月都得干赔?我不是让你在账上想想法子嘛!”
“这不用您吩咐啊,太太,”老侯赔着笑说:“先生在家的时候,我们也是两本账:一本是实打实的,自个儿存底儿;一本是给税务局打马虎眼的。这已经是打了一半儿的虚头了,要是实报,赔的就不止这个数了!”
“唉!”韩太太叹了口气,拈起一根牙签剔着牙,“你这还光说的是柜上呢,还没算上家里的开销,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姑妈就只知道朝我伸手,这花销也见风儿长......”
“那可不!”侯嫂插嘴说,“别瞅着吃不上喝不上,东西倒是赛着地贵!肉也吃不着,卖菜的也不敢进城了,混合面儿吃得孩子们拉不出屎来,倒比白面还值钱!洗衣裳没有胰子,买盒取灯儿都得......”
老侯打断她的话说:“你跟着瞎叨叨什么?太太跟我说正经事儿呢!”
韩太太端起茶碗,“她说得一点儿不错,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家里的日子可都指着柜上呢,老侯,咱老是这么样儿光出不进算什么事儿?”
“太太,这可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儿!自打日本人一来,什么买卖不这样?东来顺饭庄、天义顺酱园、月盛斋马家老铺、全聚德烤鸭店、同仁堂药铺......连王麻子刀剪铺,都一天不如一天,眼瞅着要玩儿完,”老侯阖上账本,扳着指头,一一历数,“再说咱们玉器行吧,宝珍斋、德宝斋、富润斋、魁星斋、荣兴斋......也衰败萧条了,有的铺子都想关门不干了。日本人什么都‘封锁’,玉料没法儿进了,坐吃山空能糊弄几时?欧美的洋人都跑了,‘洋庄’的买卖哪儿还有主顾?中国人连命都怕保不住,谁还有闲心玩儿珠宝玉器?唉,我瞅着这一行要完啊!......”
“完不了,完不了!”韩太太最怕这种让人听了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话,把茶碗往桌上一搁,老侯就不言语了。韩太太懒懒地站起身,打了个哈欠,想去睡觉,不再想这些烦心的事儿,又怕躺下反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烦,就顺手从条案上取下那一盒象牙麻将,哗地倒在桌上,“来,来,来,试试运气!”
老侯笑笑说:“太太,您这可真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韩太太重又坐下来,“自个儿逗自个儿吧,要不,光听你报账,能把人烦死!侯嫂,把姑妈也叫过来,谁‘和’(音hu)了谁请客!”
“哟,我们可是输不起也赢不起!”侯嫂说着,伸嘴咬断了手上的线头,起身走到廊子底下,冲着东厢房喊:“姑妈,快来,赢太太一把!三缺一,就等您了!”
姑妈压根儿就没睡,揉着眼皮走进上房,叨叨着说:“咳!我说话总是没人听,咱回回不兴赌博!”
“赌什么博啊?”韩太太苦笑着说,“拿这占着手熬夜吧,省得做噩梦!”
把麻将搓得稀里哗啦响,颠三倒四地撒了一桌面儿,于是,四个人各安其位。码齐了,让韩太太掷骰子。
“五!我坐桩!”韩太太倒是一出手就是主将的地位。
“红中!”
“六饼!”
“两万!”
开始勾心斗角地较量,各人审视着自己的实力,互相保守着秘密,拼凑班底,组织武力,以击败他人为目标。牌桌上是一场没有枪声炮声刀光剑影的争夺战。姑妈纯粹是凑数,她不精于此道,老是探头去看人家的牌,侯嫂拦着她说:“哎,哎,您这叫怎么回事儿?各人撞各人的运气,不兴摸旁人的底!”姑妈就一次次地缩回去,正襟危坐。老侯为了给韩太太解闷儿,玩儿得挺认真,颇费心机地盘算着战局,欲知天下纷争,鹿死谁手。
其实韩太太的心思很难集中到牌桌上,她还是惦念着买卖的事儿,“老侯,你才刚说,谁的铺子关了?”
“噢,是抱玉轩,”老侯捏着一个“六万”说,“他们老板病得不行了,等着料理后事,得用钱,柜上又没什么买卖,老板娘就把店整个儿‘倒’出去了。”
“这个娘们儿,是个败家的货!”韩太太感叹道,又问,“‘倒’给谁了?”
“汇远斋啊!”
“蒲绶昌?”提起这个人,韩太太就恨得牙根疼,“他是专干这种趁火打劫的缺德事儿!哎,他‘倒’到手里不也是个包袱吗?别人的买卖玩儿不转,他能有什么咒儿?”
“他跟别人不同啊,”老侯说,“西洋路子一断,他就走东洋路子了,跟一个翻译官认了干亲家,如今一个什么‘株式会社’包销他的东西,往南发货,香港、新加坡、婆罗洲!他买了抱玉轩,东西都挪到汇远斋去了,这边儿把‘抱玉轩’的字号一摘,卖上日本的白面儿了!”
“啧啧,什么东西!好好儿的一个抱玉轩,叫他给灭了!”
“唉,这有什么法儿?如今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谁也不知道走到哪一步!”老侯看着姑妈扔出来一个“五饼”,摇摇头,“咱们奇珍斋要是这么下去,也够戗!”
“够戗怎么着?”韩太太翻眼看看他,“你也想把它‘倒’出去?”
“哪儿能够啊?太太!”老侯赶紧说,“我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主事,全凭太太的吩咐,能维持多久,我就尽力儿维持!”
姑妈又在偷看人家的牌:“哎,你这......”
跟她“对戳”的侯嫂伸手护着丈夫这边儿,“别让她瞅见呀!哟,”她自己倒去检阅老侯的阵容,不觉兴奋地叫起来,“光顾着说话儿,你怎么连自个儿‘和’了都不知道?”
“噢,我‘和’了!”老侯这才发觉自己的牌果然都凑齐了,刚才他嘴里说着买卖的事儿,手里瞎打一气,不料瞎猫撞上了死耗子!
侯嫂像赢了天下似的,“轮流坐庄,该你了!”
韩太太心烦意乱地把面前的麻将一呼噜都推倒,说:“老侯,先生临走的时候,交给你手里的可是整个家当,你可别让他回来一瞅,奇珍斋改了姓!”
“太太!”老侯听出了这话的分量,打麻将的闲心全没了,“您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老侯活着是奇珍斋的人,死了是奇珍斋的鬼!”
“得了,红口白牙的,赌咒发誓地干什么?”韩太太又把话往回说,“接着来,再打一圈!该谁了?噢,该你了,给你给你!”
于是又周而复始,直到都困得认不清麻将几是几。
第二天老侯还得到柜上去“维持”,姑妈和侯嫂陪着韩太太在家里“维持”,混合面儿的卷子掏上花椒大料芝麻盐儿,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味儿。老侯晚上回来就带回一大堆和玉器买卖无关的新闻:老二西堂存的过去给皇上印家谱用的御制“榜纸”,让日本人讹走了好几刀,那纸每一张都合四块银元呢,这一家伙老二酉堂亏大发了;内一区警署的一个署员上东来顺吃饭,没伺候好,经理被警察抓去打了一顿旧本宪兵队到宝文堂搜查抗日的书画,把掌柜的给押起来了......这些事儿,让人越听就心里越烦,无处排遣,就搓麻将。人需要自己麻醉自己。
后来麻将从家里挪到了柜上。韩太太不放心柜上的买卖,隔三岔五地到柜上去瞅瞅,奇珍斋门可罗雀、架上生尘,伙计们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儿讨老板娘的笑脸儿,就陪她打麻将。姑妈和侯嫂自然都不去的,韩太太跟那些小子们又没话说,就邀了张家的太太、李家的姑娘、刘家的姨太太,闲着没事儿在账房喝茶嗑瓜子儿打麻将。这都是些闲人,爷们或是有公务在身,或是出去张罗买卖,娇妻贵妾们百无聊赖,又没个地方花钱去,乐得陪韩太太吆五喝六,听她讲讲韩先生怎么从侦缉队长手里买了那所尊贵的宅子,怎么瞅见半夜里从天上掉下来一颗夜明珠,真吧假吧,好似听戏一般,也怪有意思。一边儿聊,一边儿打麻将,开头只是解闷儿,不论输赢。后来就有嫌不过瘾的,要下注。这注开头也寥寥,后来就渐渐增加,几十几百都打不住。来的都是趁钱的主儿,输了赢了都是现钱,硬哗哗的票子摆在桌子上。韩太太又有了主意,不让她们揣着票子走,“您这副银镯子太单薄了点儿,还是翠的是作儿!”“您这串珠子是哪儿买的?瞧这成色,摆在我们柜上都觉得寒碜!”这些贵妇人于是就感叹韩太太的眼界宽、见识广,洗耳恭听她的忠告,该戴什么、插什么、挂什么、别什么,听得心里痒痒的,而这些东西又一定是奇珍斋都有的,于是精挑细选各人都有了称心如意的首饰,对韩太太千恩万谢,约好了明儿再来,或者还要邀来七大姑八大姨。牌局一散,老侯就露出了笑容。韩太太疲惫地长出一口气,数落着老侯和伙计们:“你们呀,怎么学的买卖?还不如我一个妇道人家呢!其实这点儿眼眉前儿的本事不算什么,买卖常是在饭桌牌桌上做成的!”
奇珍斋的买卖本来已经微弱得像个眼看要熄灭的蜡烛头,韩太太竟然能使这火苗儿又闪了几闪,兴许能起死回生也说不定。
太阳懒懒地爬上半空,掩在灰??鞯谋≡坪竺妫野兹缭铝痢S氨谂员叩奶俾芗埽兑崖渚。皇?萏俸崽墒裕褚晃讯辰┑纳摺?
垂华门里出来一群小将,为首的是侯家十二岁的大小子,躬着腰,手脚着地往前爬,天星骑在他身上,“嘚儿,驾!”原来是把他当马骑,二小子和愣丫头还有两个小的跟在后头乐。耳鬓厮磨的孩子们分不清高低贵贱,骑马的和被骑的都充满了兴致,大小子一边学着马跑,还一边摇头晃脑地唱着《颠倒歌》,那词儿好古怪,没有一句是真的:
东西街,南北走,忽听门外人咬狗。
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又被砖头咬了手!
天星听得十分开心,格格地乐:“你瞎说,砖头还能咬手?”
大小子又唱:
骑了轿子抬了马,吹了鼓,打喇叭......
“博雅”宅的大门突然被擂鼓似地敲响了,这边正玩得高兴,没人答理。那门接着响,天星吼道:“干吗干吗!”
外边嚷上了:“是我,快开门哪!”
大小子住口不唱了:“噢,是我爸!”
二小子上前拉开了门闩,老侯风风火火地闯进来。趴在地上的大小子抬起头来,呼哧带喘地问:“爸,您怎么刚走不大会儿就回来了?”
“哼,作死吧你!”老侯瞟了一眼满脸泥汗的儿子,就急急地往里走,“太太,太太!”
韩太太正在上房里喝茶,听得声音不对头:“什么事儿?”
老侯气喘吁吁地跑上台阶,直奔上房:“太太,柜上出事儿了!”
“到底什么事儿?”韩太太手一哆嗦,茶碗摔成了两半儿!
“东西......丢了!”
“什么东西?”
“是......是那只镶着三克拉蓝宝石的戒指儿!”
“啊?!”韩太太大吃一惊,她记得,柜上的戒指虽然不少,但镶着蓝宝石的只有这么一只!“什么时候丢的?”
“不......不知道,”老侯哆哆嗦嗦地说,“今儿早上发现的,原来搁在尽西头的柜子里的,旁边挨着一副碧玺镯子,一只玛瑙鸣心项链坠儿,现在别的东西都在,就是那只蓝宝石戒指没有了!”
“你查了账了吗?”
“查了,存货清册上记着呢,可是门市流水账上没有,卖是肯定没卖出去,我记得清清楚楚......”
“亏你记得清清楚楚!你倒是说呀,东西哪儿去了?”
上房里这么一嚷嚷,院子里的孩子们就都不敢言声儿了,正忙乎着拆洗棉衣裳的姑妈和侯嫂都惶惶地跑过来,听了这话,脸惊得发青!
“那什么......”侯嫂从后头扯着她男人的衣裳襟儿,“别这么毛毛糙糙的,那些伙汁,你都问过了吗?”
“问了,问了!”老侯不耐烦地甩开老婆,“都说不知道,要不,我能跑回来问太太吗?”
“问我?”韩太太把脸一沉,“我还得问你呢,你是干吗吃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从眼皮子底下飞了,你是聋子、瞎子、傻子?”
“是啊,是啊,”老侯气急败坏地拍着自己的脑袋,“我糊涂了,疏忽了,这叫怎么个话儿说的......哎,好像昨儿早起来我扫了一眼,那戒指儿还在呢,晌午......晌午前儿您不是在那儿打麻将呢嘛......”
“打麻将怎么着?我还在那儿做买卖了呢!卖的东西,你不是都有账吗?”
“那倒是,我查了,昨儿那几位太太买了一只玉香炉、一副碧玉镯子、一挂欧泊珠子......可就怕保不齐......”
“什么‘保不齐’?人家都是有身份的人,冲我的面子才来的,凭你?连请都请不动!人家会借这机会偷东西?你一个爷们家嚼这样的老婆舌,屈赖好人,人家知道了能告你!”
“我......我没这么说呀!”老侯急得昏了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是怕人多手杂......”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韩太太火了,“我一去就人多手杂了?闹了半天你是多嫌我呀?”
姑妈急急白白地抢上前劝她:“天星他妈,甭这么咋咋唬唬地,老侯他不能够......”
“他不敢!太太,他不敢!”侯嫂吓得腿肚子转筋,两手拉着韩太太,“他决不敢......”
“他怎么不敢啊?这不是指着鼻子说我呢吗?合算这东西是我偷的!”韩太太嘴唇发白,手脚都在哆嗦,“闹了半天你是上家来抓贼追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