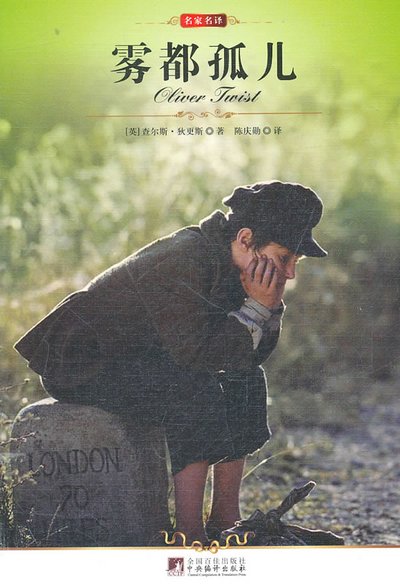先说三则故事。
一
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向他的侄子汉成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希望皇帝可以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之书与太史公所写《史记》赐一份给自己,让自己带回封地慢慢研读。
汉成帝找来舅舅王凤商议此事。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1)意思是,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褒奖的圣人行迹是唱反调的,《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家权谋,披露了本朝开国的秘事,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
汉成帝采纳了舅舅的意见。他告诉叔父,“‘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好好读朝廷推荐的“五经”就行了,那里面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王凤所谓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直白点说就是“刘氏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无法拿上台面。只有“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样的虚无故事与“四方归心”(2)之类的空洞言说,才可以写进官修史书。
东平王刘宇对诸子百家之书与《史记》的兴趣,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的更严密监视。
二
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闰九月,检校纳言魏玄同被酷吏周兴诬陷。武则天勒令他在家中自尽,由监刑御史房济现场监督执行。
闰九月十五日,魏玄同奉武后之命即将自裁。房济素来钦佩他的德行,忍不住劝他:“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意即,您可以说有事要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召见(武则天几乎会召见所有告密大臣),如此就可以得到当面辩解、自证清白的机会。
魏玄同拒绝了房济的好意。他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3)被人杀死,被岁月杀死,没什么区别。我魏玄同岂能做一个告密之人?
武后时期,构陷与杀戮当道,坚持不做告密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暗无天日的时代始于五年之前,也就是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那年春天,“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发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并无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年初,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废黜帝位)。其中一人当即离座,去洛阳宫告密。酒未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发牢骚者被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遭绞杀,举报者赐官五品。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说,武后时期的告密之风“自此兴矣”。
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比如,不许任何官员盘问告密者。地方官府须给告密者准备马匹,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到女皇跟前,途中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告密的内容若合武则天心意,告密者可以越级升官;若有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4)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令人战栗的素材,让天下人胆战心惊,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所以,武则天重用的酷吏侯思止、来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贫,懒不治业”,沦落到给人做家奴,告密时代一开始,就飞奔入京诬告本州刺史谋反。来俊臣的亲爹与养父都是赌徒,他成年后终日游手好闲、为非作歹,是告密之风将他从牢狱中“解救”了出来,他在狱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无人敢阻拦。
风潮所及,许多人的行为出现了扭曲。鱼保家本是一名发明家,却在告密时代的第三年选择了职业转型,决定将自己的发明天赋用在更有“前途”的告密事业上。鱼保家设计了一种叫作“铜匦”的工具,献给未来的女皇。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为东、南、西、北四格:东面的青色格子写着“延恩”,供人为女皇歌功颂德,求取功名,也可提出促进农业和人民福利的设想和计划;南面的红色格子写着“招谏”,供人对朝政提出批评;西面的白色格子写着“伸冤”,供有冤情者诉说冤屈,要求公正;北面的黑色格子写着“通玄”,供人报告自然灾害的消息和机密。简言之,它是一个意见箱,也是一件鼓励告密的利器。
未来的女皇武则天很满意这件作品,下令将它安放在朝堂之上。她要的是众人面对铜匦时的战战兢兢。
但鱼保家并没有迎来他预期中的光明前途。铜匦中很快就出现了一封针对他的告密信,信中说鱼保家给李敬业的叛军制造过兵器。不需要查证,也不需要审判,鱼保家被直接交给了酷吏索元礼。索元礼是一个胡人,在大唐全无根基,他的荣华富贵全系于武则天一身。为了配合告密时代,索元礼兢兢业业发明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刑具,有“凤凰展翅”“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多种名号。其中有一种铁圈,先套在头颅之上,再往圈中打入木橛,可致“脑裂髓出”。索元礼刚拿出他的刑具,鱼保家就招了供,认了罪,只求速死。
发明断头台的人死于自己的断头台,发明铜匦的鱼保家也死于自己的铜匦。对武则天而言,铜匦是有用的,鱼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们能带来恐惧,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但活着的鱼保家没什么用。这是鱼保家想要加入告密者的队伍,求取功名利禄,却被告密时代吞噬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永昌元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则天一手构筑的黑暗时代。他以一句“岂能做告密人邪”,让那个时代仍存留着最后的道德底线,而没有堕落成百分之百的人间地狱。
三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赵佶在位,权臣蔡京当道。在赵佶的授意下,蔡京亲笔书写,将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三百余人列入了“奸党”名单。这么做的原因是这些人反对“新法”,批评朝廷以搜刮民财为要务。宋徽宗与蔡京“敕令诸州据以刊石”,命各州县根据名单刻成“元祐党籍碑”,即“奸党碑”,立遍全国。
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
长安有一位石匠叫作常安民。朝廷让他刻碑,他接到任务后,跑去见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常安民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5)意思是,我常安民是个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马光这样的大人,大家都称赞他正直,如今朝廷却说他们是奸邪,我不忍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地方官闻言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于是说:“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他的意思是,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敢推辞朝廷的任务,但是请求朝廷不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告诉后世“奸党碑”是自己刻的。
常安民的故事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录》,这本书的作者邵伯温生活在两宋之际。邵伯温在他的书中说,他愿意把这个庶民的故事写下来,是因为“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意思是,石匠尚且知道是非和善恶,比许多士大夫强多了。
常安民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迄今仍有史料可查、署名由常安民镌刻的石碑尚有六七块之多,如《奉天县新修浑武忠公祠堂记》《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游师雄墓志铭》《孙昭谏墓志》等。(6)
常安民不是唯一不愿助纣为虐的石匠。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宁开了一间“琢玉坊”,崇宁二年,九江的地方官让他去刻“元祐党籍碑”。李仲宁委婉地拒绝了官府的征召:“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7)意思是,他告诉地方官,自己以前很穷,谋了份石匠的营生,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强得以温饱。今日朝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想到自己从前的工作,实在下不了手。
1970年出土的《中书舍人曾巩墓志铭》与1972年出土的《刘元周妻易氏墓志铭》证明了李仲宁确有其人。他的故事出自《挥麈录》,这本书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王明清说,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宁,满足了他的愿望,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宁,所以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
四
讲以上三则故事,是因为本书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对这三则故事的一种回应。
今人常引用一句俗语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这话其实错得离谱。普通人见不到“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依赖不完整乃至错误的信息加工出来的往往会是“假的历史教训”。拿了“假的历史教训”去比对前人的言行,自然会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感慨。而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遗憾的是,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所以,站在文明史的角度,魏玄同、常安民与李仲宁等人物其实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为重要。美国历史学家海斯有一段论述:“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8)苏联教育家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也有类似的感慨:“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9)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最后,感谢为此书从酝酿到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所有人。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感谢我可爱的女儿谌大猫,她是我努力想要写一点有价值的文字的动力。
(1) 班固:《汉书·宣元六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24—3325页。
(2) 班固:《汉书·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页。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0—6461页。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39页。
(5)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6) 罗昌繁:《大历史与小人物: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7) [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8) [美]海斯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新月书店1930年版,第322页。
(9) [苏]B.A.苏霍姆林斯基著,赵玮、王义亮、蔡兴文、纪强译:《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