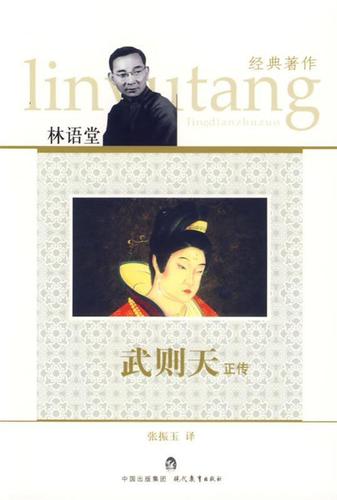自秦汉至于明清,是为中国的“秦制时代”,或谓“秦政时代”。
“秦制”“秦政”皆是由来已久的词语。宋人欧阳修曾言:“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1)至近代,则有谭嗣同在《仁学》中畅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2)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秦制的萌芽、成型与西周分封制的衰落、崩溃大致同步。秦制的基本观点至迟可以追溯到《管子》。《管子》中记载了管仲的这样一种政治思想: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3)
这段话的大意是:财富的流出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也就是“利出一孔”,不能让百姓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发财的渠道。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君王决定,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不过,作为齐国“稷下之学”的产物,《管子》一书带有强烈的杂烩气息。比如,它提出了“利出一孔”这样典型的秦制理念,但也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4)。提倡“利出一孔”,显然不能说是“顺民心”;提倡“顺民心”,就应该反对“利出一孔”。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与韩非子完成的。
一、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的记载不够详尽,大略可以知道的是:商鞅姓姬,公孙氏,原是卫国贵族的远支,成年后投到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世称公孙鞅、卫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受封于商后才有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商鞅,让他接替自己做相国。且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杀之。这大约不是史实,更像是商鞅入秦之后,为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同时,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了招贤公告:“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5)商鞅遂决意西行,去碰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两年时间毫无进展,直到通过贿赂秦王的宠臣景监,才见到了秦孝公。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分别谈了帝道、王道与霸道,秦孝公的选择是霸道。对于秦孝公的选择,《史记》保留了一段商鞅的“自述”: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6)
大意是:我先拿出来献给秦君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但秦君追求生前“显名天下”,不愿等待“数十百年”,于是我换了一套“强国之术”,获得秦君青睐。秦君的选择虽佳,却也将导致其国之“德”难以与尊奉“帝王之道”的殷周相提并论。这段“自述”的来历相当可疑。“帝王之道”与“强国之术”的分野是汉儒喜欢讨论的话题,“难以比德于殷周”的感慨更像是事后诸葛亮刻意将自己的观点挂靠在了商鞅身上。
其实,商鞅是一个所学庞杂、并无固定思想体系之人。君王喜好“帝王之道”,他就献上“帝王之道”;君王喜好“强国之术”,他就提供“强国之术”。他可以在道、术之间自由切换,毫无思想压力。秦王选择霸道,于是就有了商鞅变法。
严格来说,商鞅变法其实有先后两次。第一次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见到秦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左庶长,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中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50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行变法。
前后两次变法,主旨上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之法。具体的办法是“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即不举报奸人者腰斩,举报奸人者获赏等同于斩敌首,藏匿奸人者受罚等同于投敌。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
3.鼓励公斗,按军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斗,按情节轻重量刑。努力耕种、纺织之人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因懒惰而贫困者没为奴隶。
4.宗室也得靠军功来谋取富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制定明确的爵位和俸禄制度,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有军功才有社会地位,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也无法提高政治身份。
有说法认为,商鞅的变法措施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这样的效果或许确实是有一些,但商鞅的本意并不在此。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什伍、连坐与告奸),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这一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
秦国致力于消灭国内的贵族。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给国家添砖加瓦。按《商君书》(该书虽未必是商鞅亲笔所写,却属于商鞅思想、言论的汇编无疑)的说法,要让百姓更好地为国家添砖加瓦,首要之务是消灭“六虱”。
“六虱”的概念见于《商君书·靳令》,具体是指六种危害国家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威胁。商鞅另有一套强国的逻辑: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7)
大意是:国家贫穷,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的,既可以损害敌国的利益,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虱”,国家必强;反之,国家富足,却不对外扩张,百姓生活安逸了,就会追求诗书礼乐,就会讲究孝悌、诚信,就会倡导仁义,反对战争,“六虱”全跑了出来,国家必弱。
《商君书》还解释了国家为什么应该制定告密制度,让百姓互相监视: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8)
大意是:罪行发生后,再对犯罪者实施刑罚,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义举发生后,再来奖赏当事人,也起不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国家就会乱。所以,统治者必须在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实施刑罚,如此才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赏赐告密的百姓,如此才不会忽略“细过”。统治百姓,能够做到“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国家就会强盛。
针对上述思想,商鞅有一句简练的总结:“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9)——仁义只会抵达“暴”,杀戮反而会归于“德”。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将“事前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变法。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与秦国的兴亡相始终,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10)
汉文帝与众臣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才使得“告讦之俗易”,社会上的告密风气得到纠正。事前惩罚制度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罪疑者予民”(近似于疑罪从无)。
商鞅的变法思想里还有一条叫作“国富而贫治”,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11)
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放纵、贪图安逸(淫),然后国家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拿出粮食来顶替外出服役。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六虱”就不会产生。所以,让国家富有,使百姓保持贫穷的政策,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百姓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上面这段话里的“虱”,前文已经说过,指的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六种危害国家的弊端。至于“淫”,《商君书》中有一段解释:
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12)
“淫”即淫逸。按商鞅的理解,“淫道”包括了靠能言善道得到富贵,靠游散求官进入体制,靠著书立说获取名声。也就是说,只有靠军功和耕作来获取社会地位才是正道,其他靠智慧、人脉资源、学识来提升阶层的做法都属于邪道,都对国家有害——尽管商鞅自己正是依靠着辩智和游宦而得到秦君的重用。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对此,《商君书》中有大量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制其民者也。”(13)过去能够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境外强敌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14)“朴”是“淫”的反义,意思是没有知识、人脉、温饱之外的追求。这句话的意思是:百姓甘于“朴”国家就强,追求“淫”国家就弱。百姓弱,就安分守己;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朝廷(越志)。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15)如何引导百姓不去追求知识,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在战功与农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16)国家不许大臣与士大夫去做任何展示其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寄居他乡。这样的话,农民就没有机会听见“变”(通“辩”,论辩)与“方”(学问、道理)。“知农”(聪明的农民)没有机会结识大臣、士大夫,也就没有机会放弃农业生产;“愚农”无知,不喜欢学问,也就会积极务农。
为了彻底贯彻“民愚则易治”的理念,商鞅在变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相当极端。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17)
百姓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百姓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百姓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百姓只需要遵守变法推行的政策,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对此,商鞅本人是有预感的。他的变法帮助秦孝公极大地提升了秦国的资源(人力与物力)汲取能力,但这种提升是以打压秦国的封建贵族为前提的——秦孝公想要掌控更多的人力、物力,就需要秦国的封建贵族吐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如今,新君即位,首要之务不在汲取资源,而在君位的巩固。君位的巩固需要获得国内政治力量足够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势力仍盛的封建贵族。而取悦封建贵族、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鞅。
为了保全性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自请隐退,回归封地,希望利用封地的武装保护自己(削弱贵族力量恰恰是商鞅变法的核心诉求),并联络魏国权臣,欲以秦国的利益为筹码换取魏国的帮助(但魏国无意为了商鞅与秦国开战)。最终,秦军攻入商地,“灭商君之家”,商鞅被杀,他的尸体被带回秦都咸阳,公开车裂。
商鞅虽死,但他的强国之道保存了下来,被历代秦君奉为治国的圭臬。
二、韩非子的“理想民”:五蠹与六反
商鞅之后,将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使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人是韩非子。
与商鞅一样,韩非子也是反民智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浸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18)
韩非子说:民众的认识跟婴儿的心智一样靠不住。给婴儿剃头、剖疮,因为慈母抱在怀里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受的一点小苦将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啼哭不休。如今国君勒令百姓去垦荒,他们认为太残酷;制定严刑峻法,他们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去服兵役,他们觉得太暴虐。其实,这些政策都是为百姓好,但百姓不领情、不高兴。以前的大禹、子产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民智是靠不住的。
在《忠孝》篇里,韩非子还发过这样一番感慨: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19)
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随便鼓动几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百姓有了智慧,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肯听从君主的命令。
那怎么办呢?
韩非子说,常规的办法是“劝之以赏”,即用利益来诱惑百姓;“畏之以罚”,即用刑罚来恐吓百姓。但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在《五蠹》《六反》等篇章里,韩非子建议,应该对百姓实施改造。具体的改造方法如下:
首先,需要清除五种人。
这五种人是:学者(相当于战国末期的儒家)、言谈者(相当于纵横家)、带剑者(相当于游侠)、工商之民(商人和拥有各种技艺的人)和患御者(害怕承担耕役而去充当贵族的门客或权力掮客的人)。(20)
这些人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四方,他们有知识,也有资源,还懂得社会体制的运作规则,对国家是有害的。韩非子把他们合称“五蠹”,即五种会蛀蚀树心的虫子。
其次,有六种人需要被教育。
这六种人是: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21)
若仅从“畏死远难”等词语来看,上述六种人似乎算不得好人。但要注意的是,“畏死远难”等字眼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为了让统治者更方便地分辨出这六种人,韩非子在文章中还写下了普通百姓对这六种人的看法。在百姓的眼中,他们依次是:贵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文学之士(追求学问的人)、有能之士(相当于能出门远游、在外谋生的人)、辩智之士(相当于能用智力、口才谋生的人)、磏勇之士(相当于能提剑杀人的人)、任誉之士(敢违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的人)。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韩非子的逻辑了: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追求最大限度汲取人力、物力的秦制政权而言是有害的。
最后,有六种人必须得到奖赏、表彰,要树为模范。
这六种人是:赴险殉诚之人、寡闻从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纯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贼遏奸之人。(22)
若仅从“赴险殉诚”等词语来看,上述六种人似乎都是极好的人。但要注意的是,“赴险殉诚”等字眼也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根据韩非子的记载,普通百姓对这六种人的看法依次是:失计之民(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朴陋之民(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寡能之民(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的人)、愚戆之民(没有智慧,逆来顺受的人)、怯慑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的人)、谄谗之民(给官府充当耳目的人)。
这六种人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被汲取疼了也不会叫唤,是韩非子心目中最理想的国民。
韩非子对百姓的筛选与改造,与商鞅的理念高度吻合。在商鞅看来,合格的秦民不应该具有思考的能力。所以,他先是杀了一堆反对变法者,后又流放了一批“有来言令便者”(跑来赞颂新法好的人),造成了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从此再没人敢议论新法的好坏。反对者被杀,歌颂者被流放,看似矛盾的做法实质上正是不让百姓思考变法推行的政策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同样需要动脑子。百姓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但百姓毕竟不是工蚁。正常情况下,正常智力的百姓绝不会主动愿意去做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与谄谗之民。那又该怎么办呢?
在《韩非子·说疑》篇里,韩非子提供了一套办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23)禁事、禁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具体说来就是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二者结合可以做到无往不利。比如,东汉时期用五斗米道统治汉中的张鲁就深谙韩非子所述的“远仁义,去智能”的手段。五斗米道发展信徒的办法是让信徒“有病自首其过”(24),但张鲁不会告诉信徒有些病是可以自愈的——这就是在控制资讯。只要有人在自我反省后病愈,单纯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张鲁渲染成因果关系。病好了是五斗米道的神力,病没好是自己反省不够,这就是在灌输错误的逻辑。
按《史记》的说法,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与《五蠹》后,曾长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25)《三国志》也记载,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太子刘禅,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多向丞相请教《申子》《韩非子》《管子》中的道理。(26)及至北魏,又有博士公孙表,因向道武帝进呈《韩非子》而获赏。(27)再往后,则如明朝学者赵用贤所云:“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28)
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1) 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三册,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78页。
(2)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8页。
(3) 管仲:《管子·国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页。
(4) 管仲:《管子·牧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5)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6)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28页。
(7) 商鞅:《商君书·靳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页。
(8) 商鞅:《商君书·开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33页。
(9) 商鞅:《商君书·开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页。
(10) 班固:《汉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97页。
(11) 商鞅:《商君书·弱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页。
(12) 商鞅:《商君书·外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1页。
(13) 商鞅:《商君书·画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58页。
(14) 商鞅:《商君书·弱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页。
(15) 商鞅:《商君书·垦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页。
(16) 商鞅:《商君书·垦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
(17)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1页。
(18) 韩非:《韩非子·显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1—562页。
(19) 韩非:《韩非子·忠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7页。
(20) 韩非:《韩非子·五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2页。
(21) 韩非:《韩非子·六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03页。
(22) 韩非:《韩非子·六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03页。
(23) 韩非:《韩非子·说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5页。
(24) 陈寿:《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3页。
(25)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55页。
(26) 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1页。
(27) 魏收:《魏书·公孙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2页。
(28) 《管韩合刻四十四卷·韩非子书序》,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附录》,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