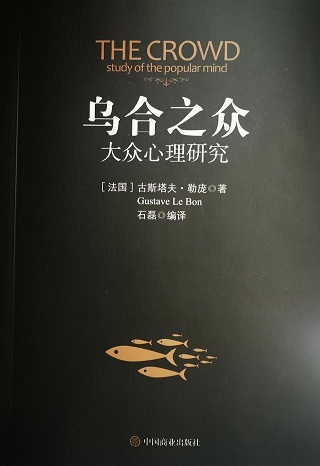1
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稻草堆上。背上是松散而没有弹性的稻草,肩膀窸窸窣窣作响。空气中弥漫着纤维质受潮的味道。
奇怪的是我全身僵硬。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没有天花板的屋横梁。这些横的竖的梁与栋似乎随时有塌下来的可能。屋檐是老旧的暗褐色木板。透过间隙泻下来的阳光中,可以看见房里飘浮着的尘埃。
——这里究竟是哪里?
我全然没有印象。
还是一迳呆望着屋顶0
努力在记忆中搜索蛛丝马迹。躺在这里之前——对了!我本来是打算去便利商店买便当的。
因为写长篇小说写不下去,延误了晚餐,想藉着散步舒松一下心情,便步行到脚程十分钟的便利商店去。夜凉如水,脑筋想必会因而灵感泉涌才是。
离家时……记得是深夜一点左右。
星星很美。黑夜将大阪脏污的天空掩藏得极好。偶尔洁白的月光也会投射在身后。
很有那么一点诗意——
我还记得,在一处贴有高利贷广告的电线杆转了个弯。穿过这条公寓夹道的小暗巷就可以到达国道边的便利商店了。
然后呢?想不起来……
此刻是白天吧,有阳光。我抬起腕看看表。
十一点二十六分,日期是八月九日,已经过了一晚了,正确说来是过了十个小时又多一点。这段时间内,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全无记忆。
我努力地回想,却仍是徒然。什么也记不得。好像走在路上身体突然感到一阵麻痹,同时还有寒气逼人。恐怖?
两肘用力想撑起身子,可是后脑勺传来一阵阵痛楚。小心翼翼地摸摸看,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肿包。
我这下才明白果然曾经发生事情。可能是在暗巷内遭人偷袭,再被运到这儿来的。然后就被丢弃在这里了。
可是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这呢?还有,这是哪里?我被人强拉来此的吗?
绑架?可是,谁付赎金呢?乡下虽有双亲在,但他们并不富有。难道有人想绑架一个年近三十的男人谋利?
那、到底是什么阴谋呢?抓错人了?
越想越多可能性。平常我只是坐在文字处理机前思考的。可是现在,心里却完全没有谱。
我只知道自己被人打昏后带到这儿来。
我缓缓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口。大门和屋顶一样,似乎一踢就会倒下来,而且没有上锁。想来也没有装锁的必要,不过是一间堆置杂物的破屋子罢了。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不安地窥伺外头。陌生的世界在眼前展开。眼前是一大片森林。绿,满眼的绿。
好像是在哪座山里。空气比平地要凉。昨天之前还是若不开冷气几乎可以熏制东西的溽暑。居家附近似乎没有这样的一座山。
小屋前面有一条一辆车可以勉强通行的小路,路上有比较新的轮胎痕迹。大概是用车运我过来的吧。
附近没有人迹,只见一大堆树木。
我好像被单独留置深山里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筹莫展,我靠在小屋的壁板上,两脚不停发抖。
烟、香烟……一定要先镇定下来,我急急搜寻夏用夹克的内袋,摸到里头有个朋友送的香烟盒。
这是三天前浦泽大黑送我的。
浦泽大黑是我大学时代的朋友,两人都是修本国史的。他虽然情绪起伏很快,但却是个表里一致的人。加上他的名字极少见,大伙儿都直接叫他大黑。他自己也颇满意,除了正式文件之外,一律署名大黑,很多人以为那是他的姓氏。
他原先志在学画,想入美术大学,却因父亲反对而选择文学院。不知是因为如此,或他本性使然,他很少来上课,反而经常过了中午才见他在福利社餐厅内一边用餐一边瞑想以打发时间。中午之前是他的睡眠时间,下午到早上他则待在便利商店打工。
“我自己存钱读美术大学,不要靠我父亲。”
这是他的口头禅。
我喜欢推理、侦探小说,又爱写东西,我们唯一相同的一点就是:同为历史系学生却对历史毫无兴趣。不过他曾经有一回请我当他的模特儿。我原先以为他擅绘风景,这可令我大吃一惊。不过听他说可以画得不错,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
他给我看作品,只见画中的校园有夏威夷的威基基海滩和摩天大楼交错其间,妙不可言。但是却不见我在画中。我质问是否恶意开我玩笑,他只是一脸认真地说:“看起来是如此呀!”
事后再问其他人才知道很多人也上过当。有人被画成月球表面上三部汽车追撞;也有人被画成缅甸的古迹上倒插着滑梯,还有泳池。
倒是受害人对不知情者皆保持缄默,直到那个人也成为受害人为止。然后大家再一同来猜测何以自己在他眼中竟成如此景象。当时众人对于我上当一事也是报以沉默与微笑。关于这点,据一位毒舌派的朋友解释说他是个厌世悲观论者。
总之我与大黑因此成了好友。但三年后他辍学,并如愿地进了他梦寐以求的美术大学,我们便几乎没有机会见面了。听说为了他重考之事又与他父亲相持不下。
这三年来我们连贺年片也不曾互寄,各自忙着自己的生活,之间的情谊自然转淡。也曾听说他依父亲意思经营民宿——结果还是听了父亲的话,但不管如何,对目前的我而言,大黑已是记忆中的人物了。
三天前大黑忽然寄来一个包裹。
“亲爱的美袋,请代我保管这个东西,不要问我为什么。并且请尽可能随身携带。”
包裹内附,的纸条如此写道。简单明了,但却不似他往日的作风,反而令人有压迫感。他向来是宁死也不用“亲爱的”这三个字的人。
我匆忙打开,里面赫然是一个香烟盒。中间有金属装饰的“大黑”字样。一眼就看出是他的东西。那是他在福冈的土产店里发现的,因为喜欢,就一直用到后来。这种一看就像用来欺骗乡巴佬、观光客的东西,谈不上有何品味,而且很便宜,他却视如珍宝。我便戏称它为“大黑牌香烟盒”。
现在香烟盒在我眼前。
大黑是不是出事了?或者他想做什么?心中掠过一丝不安。
不过,从此之后,即使去便利商店我也随身带着。
难道自己是因为这个香烟盒而遭到袭击的?若是如此,大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究竟有何秘密——
我仔细地看着大黑的香烟盒,可是上面除了锦蛇一般附在其上的饰金大黑字样外,看不出有什么像是秘密的东西。
我真是不明白。
不管如何,先下山吧!下山求救。有命才有然后——
将香烟盒放入上衣内袋,我开始沿路奔跑下山。
太阳已西沉,我仍在山中徘徊。不要说住家,连个人影也没遇见。路只有一条,不可能迷路。可能运我上山的车轮痕迹还蜿蜒在山路上,但路边景色除了浓密的树之外还是浓密的树。当初以为单纯下坡的路不但弯来拐去,而且时而上坡时而下坡。
真的下得了山吗?不安的情绪沁入骨里。
还有,肚子也饿了,脚也酸了。绝望地仰望天空。原以为有救的……
星星像一颗颗晶莹的小天体,可是今晚我无论如何也诗意不起来。
我会不会是昏倒被人发现而送到山中小屋来的?若是如此,我不假思索地走上山路或许太轻率了。我明知故犯中了对方的圈套……空气渐冷,后悔在我T恤底下的胸中騒动。肩膀感到沉重异常。
不久太阳完全西下,四周渐次笼罩黑暗。听得见夜行鸟鬼鬼祟祟的啁啾与振翅之声。
前面还有路,不知道已经走多久了。
两根大拇指走得起水泡而且磨破了。现在两条腿像枯木一般失去弹力,与其说走路,不如说是拖着。
感觉口干舌燥,别说食物了,连一滴水也没沾口,有的只是香烟盒。没有任何帮助。
救命呀——我想叫喊却没有声音。一切早已超过我的能耐。
接着一个缓降坡,然后又是上坡,这时我终于跌坐在路边的树丛。
……不,我再也走不动了。
再往前走一点,一定有人家。再十分、再五分,刚才我一直如此激励自己。但是现在心里只有绝望。
我会就此横尸荒野吗?谁来救救我呀……为什么一个路人也没有呢?
眼前浮现自己在房里吃着便利商店买来的便当的景象。本来应该边看电视边享受的才是。好想洗个痛快的澡。好想喝冰块沉浮其间的冰咖啡。哦,茶也可以、青草汁也行。我好想喝东西。
可是,为什么我会碰上这种事呢……太惨了——该如何形容呢?
就在这时候——
黑暗中变得黑黑的树与树的间隙中有人工的黄色光线。虽然只闪了这么一下子。
光?我再三揉了揉眼睛,凝视那个方向。
人家?
天助我也!虽然我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此时也不由得如此感叹,神还没有放弃我。
得救了——我卯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拖着疲惫酸软的双脚向着亮光处前进。
这是与其是民家,毋宁说是一栋木造洋房。大门上写着“马哈·卡拉”。或许房屋维修得好,横木做的墙依旧散发木头的光泽。先前的孤独感一扫而空。窗内泄出光亮,就想我这流浪者的灯塔指引着前路。
来到门前按了门铃。门里传出脚步声。
得救了……一股暖流在体内窜流。这次肯定有救了。这种放心松弛了我的神经,分不清是梦境或现实。
我,昏倒了。
醒来时我睡在洁白的棉被里。
柔软的棉布被,让全身感受到温软的质地。
眩目的日光灯——方才渴求的光,而今就在我头上。
我得救了,我终于得救了……我再次真实体验到那种感觉。
忽地,见一青年坐在椅子上,一脸担心地看着我。他也注意到我。
“你醒了?”沉稳的声音对我说。
“你救了我……?”
“是的。”
他看起来大概二十五岁左右,脸庞略瘦,脸色显右。看似生活无忧的青年不好意思地伸手摸着脑勺回答。
“谢谢你。”
口干舌燥之余,我喝了一口摆在床边的水润润喉。
“你发生什么事了,我看到你时,你好像在山里走了很久。”
“哦,是的。对了,这是哪里?”
“小土茶。”
“小土茶?”
这一反问令不明就里的青年一脸迷惑。
“什么县?”
“富山县。”
富山县,怎么会被人从大阪带到这里来。开车也要五、六小时才到得了呢!
“对不起,有电话吗?”
“在后面。”
床头上就放着一具白色的电话机。
我坐起来,拿起话筒。我必须尽快告诉别人这件事。
可是,告诉谁呢?警察?要怎么解释才好呢?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会当真吗?对了,梅尔卡朵。
梅尔卡朵是一位侦探朋友,他曾几次解决过一些棘手的难题。他是个杰出的侦探,但个性孤傲,认为自己以外的人都是笨蛋。是那种让人不愿亲近的人,但是他又有极优秀的才能,因此我也就不即不离地和他保持友谊至今。
我用疲软的手指按了他的电话号码。可是事与愿违,接电话的是机器。平常几乎令人厌烦的人値此要紧时候竟找不到人!
“可恶!”我说着,挂上话筒。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了?”青年的眼神有点不安,问道。
“没什么。”
“和这个香烟盒有关系吗?”
青年拿出大黑给我的香烟盒。似乎是从我外套里找到的。经长途跋涉外套已有些污脏,此刻正挂在墙壁的挂钩上。
“这是我哥哥大黑的东西吗?”
青年的话令我意外。
“你是大黑的弟弟?”
“对,我叫浦泽美纪弥。”他回答。表情神秘,同时紧紧握着大黑牌香烟盒。
“原来如此。我是美袋三条,和大黑是学生时代的朋友。”
这是巧合吗?不,不是。不可能是巧合。那么,是有意?又是谁的主意?而且目的何在?是大黑吗?
事情的意外发展,让我顿生许多疑问,但都只是没根据的臆测,找不到任何答案,只是一片混乱。
“那,大黑住这儿?”
“……他,还没回来。”
美纪弥脸上有一抹暗影掠过。
“还没?”
一种不祥的预感。
“是的。十天前他说要外出写生,就没有回来了。因为他常出远门,我也就不以为意。可是昨天他一票画画的朋友来找他玩,他却仍未回来。起先以为是有事耽误了,但却都没有连络。这时候你又带来了哥哥的香烟盒……”
哥哥会不会出事了?美纪弥憔悴的脸上仿佛写着这些字。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我向美纪弥说明香烟盒在我手上的因由,却不知他相信几分。
但美纪弥的表情是听进去了的。
“所以你也没有见到家兄?”
“没有,这是连同一封信寄来的。”
美纪弥一听,一脸失望。我似乎惹他悲伤了,心里不大自在。
大黑寄来香烟盒是三天前,这期间他出了什么事?无法对外联繋?遇害?
“家兄是否卷入什么是非了?”
“或许。我也这么想。但却不知是何事。我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
“对了,”美纪弥浅浅地笑,“你一定还没吃饭吧,到楼下吃晚饭吧!”
“方便吗?”
“只要是家兄的朋友我都欢迎。而且他那些绘画朋友们也都很担心家兄,你下去跟他们谈谈,如何?”
“朋友?”
原来这里还住了四个客人,他们和大黑一样都加入了东京某个绘画组织。大黑为了逃避父亲面躲到富山县来,但与画友的交流没有中断,每年此时大家都来这里相聚并避暑。大黑也衷心期待,但是今年他却还没返家,令人不由起疑。
“我很乐意。大家集思广益也许能得出个结论来也说不定。”
仿佛是抓到了什么光明希望,我支着床沿站了起来。
“你的身体状况还不能回去,今晚就暂且住下吧!”
就这样,在自己也不甚了解的状况下,我在富山县的一栋山中洋楼里住下来了。
留下一团未解之谜。
在餐厅与另四位访客讨论后回到二楼的房间已经十点多了。但是并没有讨论出什么来。他们对我的出现一样惊讶不已。大家也都不知道大黑的下落。不管他们是否相信我说的话,有一位叫吉井的倒是频频以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除了醒来后发生的这一切。
因为是避暑地,外面吹着凉风。白天如何不得而知,晚上倒是不必开冷气就能入眠。纱门外贴着几只褐色的飞蛾,那是它们向光的本能。
我也一样。濒死边缘被光亮引导至此,一切只基于求生意志,却因而遇上大黑的朋友。只是大黑却不在。他托我保管香烟盒之后便杳然无踪。
我想起大黑的笑脸迎人。当他独自沉思时,总是显得忧郁。
这时候如果梅尔卡朵在的话就好了。再打一次电话,结果相同。本来这种时候他的“特异功能”很能派上用场的。有他在,状况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呈现一团谜的。
但是现在能做什么呢?这时候美纪弥敲门进来了。
“你好点了吗?”
美纪弥的细心和粗线条的大黑完全不同。不知是因担心哥哥的下落或个性使然。
“是的。吃过晚饭后好多了。”
“太好了!”
“麻烦你这么多真不好意思。”我致谢。
“别这么说。”
美纪弥缓缓拉过一张椅子来坐在我旁边。
“你明天要回家了吗?”
“家人在担心,而我也关心大黑的事……对了,大黑还是没回来吗?”
“没有。家母也很担心,打算明天去报警。”
“我有一个朋友当侦探。我回去之会和他好好商量看看。”
“谢谢。不过,也许他只是有事耽搁,以致未能如期回来而已。”
“令尊怎么样?”
不知他父亲如何看待此事。我忽然想到他父亲会不会大怒,说“那个只会画画的废人担心他做什么”。
“父亲两年前去世了。现在只有母亲和我们。”
“是吗?”
原来是他父亲死了,他才能尽情的沉醉于绘画。
“是呀,父亲对我不错,却不知为何与家兄处不来。”
“好像是这样,学生时代令兄也经常向我抱怨。”
他究竟有没有成为画家的才能不得而知。也许他父亲的反对是正确的。父亲死了诚属不幸,但大黑也因此恢复自由之身。
“……对了,”美纪弥探身向前又说话了,表情紧张,“你看那些人怎么样?”
“怎么样?”
我不明白他的问题,只能重复他的问话。
“……我总觉得家兄的失踪和他们有关系。”
原来美纪弥在怀疑他们。
“所以你才叫我和他们一起吃饭?”
美纪弥惶恐似地说:“对不起,因为我想看看你的反应。”
“没关系,我也一样——可是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大约一个月前家兄向我透露过。他说:‘诸石真的是自杀的吗?’”
“诸石?”
“抱歉,你不认识。诸石也是会员之一,大约半年前从大楼屋顶跳楼自杀身亡。警方分析他是精神异常而自杀,但家兄并不如此认为。因为他死前一个月画画社开个展时,有一个人的画被诸石的挤掉了。”
大黑曾说其画如人。既然大黑如此,美纪弥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催他往下说。
“当然,警方不相信从画可以看出什么。”
“于是他自己去找证据?”
“大概吧!”他的表情认真,压低声音说。
“那,大黑是因此而——”
美纪弥猛点头。
“也许反而因此被他们其中的人……”
“他有线索吗?”
“我也不知道。家兄没说太多。当时我想家兄也没什么证据。”
即使大黑有特殊的直觉认为诸石不是自杀,可是没有证据也是徒然。这可以了解,而这是个很可能的动机,或许真有人为了掩饰杀人真栢得逞而暗自亲喜。
“可惜我没想那么多,所以不太注意……那你认为谁可疑呢?”
美纪弥起初不愿说,犹豫了半晌才说:“吉井。”
就是那个用怀疑的眼光看我的鬈发男子。
“以前家兄说过诸石和吉井两人不太合得来。那些人现在也是彼此暗中较量。而且我也觉得他今天有点反应过度。”
我不能说什么。但我可以确定自己对他没有好感。
“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去向他们问个清楚,我一个人不敢。”
美纪弥的语调稍微嗅得到暴力的味道。
“不要太早下结论。就算他真的可疑,也不能因此认定是他,还是再观察一下吧!”
“可是,家兄——”
“我知道。如果可能,我也很想帮忙。可是不是现在……因为我还不清楚状况。”
美纪弥明显变得十分失望。
“知道了,我再想想吧!”
我不疾不徐的话令他失望透了,他机械式地站起来,反应冷淡。
“当然,刚才的话都是在家兄遇害的前提之下,所以请不要对别人说。”
“我不会。”
“谢谢。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而已。”
美纪弥深深鞠个躬。我突然感到抱歉,但实在也无可奈何。事情应该不是如此单纯的,此刻回想自己这二十四小时所遭遇的事情,不觉感到状况更复杂、可怕了。
“晚安。”
“晚安。”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美纪弥。
2
第二天早上叫我起床的不是美纪弥,而是会员之一的佐川。我张开惺忪睡眼起床,眼前是面色铁青的胡子脸。
“怎么了?”
“美纪弥他——”语带弦外之音。
“美纪弥?”
“被人杀死了。”
一听这话,我穿着睡衣从棉被里冲到邻房美纪弥的房间。难道他一个人去追问凶嫌之事?
房里开着灯,里头一个人,不,连一条虫也没有,只有美纪弥的尸体。
门口有三个怔然而立的男人。他们是画画社的会长原田、小个子的金子和鬈发吉井。
我推开他们奔向美纪弥身边。没有脉搏,像人偶一样又冷又硬。
他的眼睛睁着,嘴巴闭得死紧,似乎诉说着他的想法。后悔在我体内逆流。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如美纪弥说的,这其中有凶手?
我双膝跪倒地毯上,两手掩面。
从指间我看见一条细长绳索圏住他的脖子。他的脖子有一圏紫色痕迹,一见便知是勒死的。可能是从背后下手,因为绳子在颈后交叉。
这条浅褐色的绳子很眼熟,好像在我房里也有。
窗帘——是束窗帘的绳子。
不假思索往窗子看,对着阳台的窗户敞开,没有绑住的窗帘随风飘飞。
“是谁?”
我对着门口四人大叫,但是他们只是低头不语。
后来发生的事我不想说。
我感觉很不好。我交给美纪弥的大黑牌香烟盒竟然掉落在阳台。
这栋建筑物的二楼阳台是由两个房间所共有。虽然两房间隔有一公尺远。邻房的人可以偷偷越过阳台潜入房间。而美纪弥的邻室是我。
二十分钟后警车来了。
长得像中尾彬的刑警询问过每一个人后,果不其然认为我可疑。深夜突然来访,自称是大黑朋友的可疑男子。这就够惹人注意的了,更何况还有那个香烟盒。
“请各位回房,暂时不要出来。”
一个体格魁梧的中年男子威严地指示。
我被列为涉嫌人。难不成这是个嫁祸于人的陷阱?我真的搞不懂。只是这种事应该昨天就报警的。
听说美纪弥遇害时间是昨晚十一点至凌晨两点之间,距他离开我房间还不到两小时。死因是勒杀,凶器是窗帘绳。当然,深夜三点,谁会有不在场证明呢?我也是。漫不经心地在山中散步,累了就回房呼呼大睡。而佐川则带了日本酒到原田房间,两人聊到早上六点,不过那是十二点以后的事,很巧地与死亡推定时间错开,如果他有意杀人倒也有足够的时间。但这是否为佐川的意图就不得而知了。金子和吉井则在一楼客厅看电视直到一点,然后各自回房休息。他们也没有不场证明。
美纪弥的尸体是早上八点被人发现的,就在我被叫醒前十分钟。因为美纪弥的母亲迟迟未见他起床才去房间看看,不意竟发现他被人勒死陈尸房内。惊吓之余,现在还躺在床上休息。
房间没上锁,面对阳台的窗子敞开,可能是凶手杀人后急着离开而忘记关了,并且因而掉落了香烟盒。
我自知是清白,因此对歹徒所设下的圈套了然于心。可是警方当然不会相信我。
此刻只觉恨得牙痒。
我有足够的理由被怀疑。于是我落入圏套。
究竟是谁撒的网?一定是他们四人之中的一位——是美纪弥怀疑吉井吗?或是另有其人?我不知道。
房外有警员看守,我会不会因而被当作涉嫌人带回警局去?
我感到房里意外冷清。昨天还以为是神为我准备的摇篮,如今房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见。
我会怎么样?
不安的折磨,我双手抱头,不知如何是好。
中午刚过,房门竟开了,一个男子闯进来。男人身穿燕尾服,头戴丝质髙帽,像电影上一样耍弄着手中的手杖。
“梅尔!”我说。
他开朗地举起手,然后像旅途中遇见知己一样。
“你怎么会这里?”我劈头就问。
“不要想探我的情报网。这种事简单得很。”
梅尔卡朵笑得很愉快。
“听说你杀人了,今天是来和你道别的。下次相逢可能要隔着铁窗见面了。我个人是不会做这种事,但是希望你杀人也要用点推理作家的脑袋。总之,今天是来饯别的。”
梅尔拿下他胸前的玫瑰花递给我。
“你烦不烦!”
这家伙到底来干什么。昨晚打了一夜电话,偏偏他都不在。
“你也太沉不住气了,你这样可是很容易秃头的。还劳我专裎飞车从大阪赶来。也许到拘留所吃几顿冷饭菜可以纠正你的脾气。”
他一迳是嘲讽的态度,不过他的到来或许能为我的穷途末路带来一线生机。
“我没有杀人……救救我。”
他的人格暂且不论,拥有杰出的推理能力则是毋庸置疑。也许他可以为我洗刷冤屈、抓到真凶。
“很抱歉。”梅尔拒绝得很干脆。“我这么宝贵的头脑可不想浪费在这芝麻小事上。”
“拜托。我一生唯一的请求。”
“你以前就说过了。你到底有几个一生?”
他摇头又耸肩的,见死不救地嘲笑我,但立刻又改变主意。
“不然这样吧,听说你手上有诺克斯的手稿?给我吧。”
“……”
那可是我花了不少钱才弄到的,我不想拱手让人。可是此时我开始考虑答应梅尔的要求。因为他或许可以为我拨云见日。
“如何?”他微微一笑,催我回答。
“好吧。无条件。可是拜托你一定要为我解开谜底。”
“契约成立!”
梅尔神秘兮兮地脱下帽子,坐在昨晚美纪弥坐的椅子上,表情认真起来了。
“那就从头说给我听吧!”
“你还记得浦泽大黑吗?”
“那个立志当画家,被他老爸骂得狗血淋头的家伙。”
虽然不同系,但梅尔与大黑也是朋友。
“对。那个大黑寄了香烟盒给我。”
我将事情始末详细述说一次。从大黑寄来香烟盒说到我醒来留置在山中小屋的事,还有昨天在这儿遇见美纪弥,卷入谋杀案。
梅尔时而认真听我说,时而说个破坏气氛的笑话。待我说完,他轻轻点头,说:“原来如此。”然后动作优雅地整了整高帽子。
“我明白了。”他随即说道。
“真的?不是玩笑吧!”
“我是专业人士。”
他自信满满地露出笑容,站起来。
“在专业上我从不吹牛,这可关系着诺克斯手稿。让我见见负责调查这件案子的警官,我会找出凶手,并且还你清白。”
平常让我不舒服的态度,现在却令我感激不尽。
“谢谢你。”
“是呀,你是该感谢我。毕竟你我非亲非故呀!”
又是那调调。但是这时候我还能抱怨吗?
这时,那个长得像中尾彬的刑警面无血色地冲进来。一见到站在一旁、一副神圣不可侵犯模样的梅尔,立刻大声怒斥:“你是谁?”
“我是梅尔卡朵·鲇。你不认识我吗?”
他潇洒自若地自我介绍。
“谁认识你!”
刑警此刻的表情好像血管都快爆裂断了,愤怒已极的边用高分贝声音说道,边瞪着梅尔。
“是吗?那请你去问你们署长。署长级的人应该听过我的大名。你们的署长是仓田吧!”
“等一下。大门口的警员是被你弄昏倒的吗?”
“我有吗?”
梅尔还以惊讶的脸色。的确,警察怎么可能会让这个奇装异服的梅尔大大方方地进来呢。
“我只是想和你打个招呼而已,打扰了。所以给了他一点麻药让他休息一下。”
“什么?你妨害公务哦。”
“不要好吧?”
刑警话未说完,梅尔伸出稳健的手掌制止他。
“怎么回事?”
因先前提到过署长的大名,刑警有点收敛。
“我知道谁是凶手。”
“凶手?真的吗?”
刑警不相信地看着梅尔。这也难怪。
“你知道谁是凶手?”
“只是搜集到了一些线索而已。”
“可是你怎么知道?”
刑警眼尾余光扫向我。
“这个糊涂蛋是我朋友,我不能眼睁睁看他陷入绝境。”
“你可不能为了庇护他就胡说八道啊!”
“我才不会。这样岂不毁了我一世英名。我的名声比这个男的重要多了。再说最后下判断的还是你们呀!”
我不知道刑警的绰号是不是叫“瞬间煮沸器”。不过,过了这么一段时间,情况似乎缓和下来了。
他拉过先前梅尔坐的椅子一屁股坐下来。
“好吧,你说说看。”
“你真聪明啊!”
椅子被抢了的梅尔不满地看着刑警。
“说吧!”
“好吧!首先我要为美袋澄清一下。”
“如果你办得到的话。”
刑警板着脸抬眼看梅尔。
“美袋说美纪弥房间的灯开着,是吧?”
“是。”
“这就容易了。”梅尔转头看刑警,又说:“你认为美袋杀人之后从窗子出去,匆忙间忘了关窗?”
“这是很自然的事。”
“行凶时刻是晚上十一点到两点之间,对不对?”
“对。”
“如果窗子整夜都开着,虫子一定会飞进开着灯的房间,对吧?”
“所以呢?”刑警挑着眉问。
“所以窗子是天亮之后才开的。”梅尔像在对三岁小孩解释一样慢慢地说。
“可是这样也不能证明他不是凶手呀!”刑警思索了一下辩驳道。“而且,说不定虫子是天亮之后才飞出去的。”
“如果是夜行性的虫,天亮后太阳一出来就会躲到暗处。比方床下或桌下,它们不会往外跑。而且,如果美袋是凶手,他为什么故意把窗打开呢?这岂不是败露事迹?所以窗子是在凶案之后几小时的早上打开的。”
刑警想不出如何反驳,两手抱胸在椅子上思索。
“换句话说,由此可见是有人故意要陷害美袋、嫁罪于他才故意开窗的。”
“既然是半夜被杀,为什么窗子在早上才被人打开呢?你能解释吗?”
“很简单,美纪弥不是在房里遇害,开窗应该是为了瞒人耳目。还有,凶手是在黎明时将美纪弥的尸体放进来,所以窗子确实是早上才打开。至于灯是凶手开的还是美纪弥一直没关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他这么做反而是个败笔。”
“那窗帘绳又如何解释?”
“每个房间的窗帘绳都一样,所以只要带回自己房里替换就好了。搞不好就是在拆下绳子时想到要打开窗子的。”
“所以凶手是在自己房间杀死美纪弥的?”
我忘了自己的立场,忍不住插嘴:“有可能,也许是美纪弥去找他的。凶手行凶后再把美纪弥尸体带回他房间的。”
“为什么不在夜里搬运呢?晚上不容易被发现,不是比较安全吗?”刑警疑惑地反驳。
“这样美袋的嫌疑澄清了,再来说凶手的部分吧!”梅尔得意洋洋地挺了挺胸。“刑警先生,你现在问的正是最大的线索。他为何不在夜里搬运尸体呢?晚上大家都在睡觉最方便了。凶手一定也这么想,可是不行,所以他没有在晚上搬。这么说你了解吗?”
可是我不明白。一旁的刑警也在等待梅尔往下说。
“夜里无法搬尸体的家伙……昨晚不是有人突然被佐川绊住而在房里待到天亮走不开吗?”
这时刑警霍地站起来,仿佛梅尔的话是来自神的指示。“原田吗?”
梅尔缓缓点头。
“他杀死美纪弥后,佐川突然来访,使他不得不将尸体藏起来。也许就塞在床下,等佐川走了,他才把尸体移到美纪弥的房间。”
“……原来如此。我——向你道谢。”
刑警马马虎虎称谢一声,便冲出房间,大概终于明白梅尔的意思了吧。
“来去匆匆的人!我看他成不了大事。”
我左手持扇看着梅尔。“所以,杀死诸石的也是原田?”
洗清冤屈的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询问梅尔以确认。心情好极了,仿佛十分钟之前陷在绝境中只是噩梦一场。这家伙虽然不太近人情,但肯定是有才能的。
“也许吧!”
“可是原田为什么要杀美纪弥呢?美纪弥怀疑的是吉井而不是原田呀。”
“所以我说嘛,可能就是因为你犹豫消极的态度,他才去找会长原田商量的。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凶手。”
真是个不幸的巧合。如果是这样,当初我就该和美纪弥好好商量,说服他按兵不动,也许这样就不致发生这种惨事了。
我再次后悔不已。
半小时后,原田被逮捕了。并且供认他杀了大黑和诸石。大黑是在造访原田位于东京的家时遇害的,尸体埋在山梨县的山里。理由正如昨晚美纪弥猜测的一样——只是猜错凶手了。
真复杂。如果我没有来这房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桩不幸了。
可是——
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听说把我运来这里的不是原田。不只如此,他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原田以为我带香烟盒来此地是美纪弥的安排。因为我身上有大黑——已死之人——的遗物,以为我有什么目的而感到惶惶不安。岂止不安,简直恐惧。因为他曾伪造诸石自杀,所以以为美纪弥不是真心来找他商量,而是来试探的,因此心生疑惧才杀死了美纪弥。
“那到底是谁?”我问梅尔。
据刑警说,原田在大约十天前杀死大黑的。也就是他离开家之后第二天。若是如此,那么寄香烟盒的就不是大黑,因为他早就死了。
“既然不是原田寄的,就可能是与他立场对立的人。原田的担心是对的,但不是美纪弥。”
“那——”
“应该有线索。”
工作告一段落,梅尔显得意气昂扬,也许也因为诺克斯的手稿即将到手的缘故。看样子他似乎心里有底了。
“虽然你说过几次,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如果能明白,早就知道答案了,根本不必仰赖梅尔的协助,自己就可以找出凶手了。
“从大阪来到小土茶的富山县深山中,你想需要几小时?”梅尔若无其事地问。
“大概要五、六小时吧。即使搭飞机也快不了多少。”
或许是担心归程,我似乎说过是乘车来的。
“从你被人怀疑到我来这儿相隔多久?”
“三个小时吧!”
脑中轰然巨响。
难道说——
我看着梅尔的眼睛,他正在笑,笑得很开心。
“……是你吗?”我颤抖着声音问。
“你居然一直没发现,真服了你了。”
他用手杖敲我肩头,突如其来的一击,我差点站不稳。
“我当然不知道。对了,真的是你把我打倒的吗?还把我带到这儿来?”
“没错。更正确的说,是先打你后脑勺再给你嗅迷药,之后才用车载你来。”
“为什么?”
我虽不是那名刑警,但我一定也因为太生气而青筋暴露,血管几乎要爆裂了,如果再丧失一些理智,可能会和他打起来。
“十天前,大黑离开这里去找我商量他朋友自杀的事。虽然同是大学时代的朋友,不过,找推理作家不如找侦探有用吧!当然如果只是如此我也不会心动,所以我说可以看看。结果大黑上东京找原田后就失去联络了。我想他可能遇害了,尸体既然还没被人发现,一定是埋或沉在某处。但我没有确实的证据,除了他告诉我的话之外。所以我才会趟这趟浑水,先设计引起原田的猜疑和恐惧。寄给你的香烟盒是仿造的,是我请福冈的土产店寄来,还故意弄得旧旧的。正品恐怕还在尸体衣服的口袋里。”
梅尔总括地说:“不管是杀诸石或大黑,原田都做得很完美,连我也几乎找不出破绽。但这次事情发展快得令他措手不及。可说是门外汉的悲哀吧,他就这么被我识破了。正如我希望的。”
“……我是诱饵?”
“不只是这样。我需要你的帮助,可是你不会演戏。”
“我差点送命。”
拖着磨破水泡的双脚走山路、被黑暗包围、饿得寸步难行时,看见洋房的灯而喜出望外时、当目的一切迅速在我脑中闪过。这些、这一切居然都是眼前这个得意洋洋的梅尔一手导演的!
“不会,你不会死。因为越笨的人越长寿。而且真有万一的时候,我会出手救你,像刚才一样。”
我怀疑他说的是真假。
“等一下,你说正如你所希望的,那你也预见美纪弥被杀吗?”
“果然就是这样了。”
难道他一开始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虽然他是杀死大黑的凶手,但为了抓他,有必要做到这地步吗?”
为了抓一个杀死两个人的凶手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我不能理解。而且事后居然还能若无其事。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没有对手而已。”
梅尔志得意满。也许该说他对自己满意得不得了更贴切,他一点也不自责。现在我可以断言,他不会悼念朋友,搞不好还认为原田“干得好”呢!
“好了,工作完毕,回家吧!诺克斯还在等我呢!”
“什么诺克斯。一切都是你在导演,我才不会把这么重要的手稿交给你呢!”
“恶法亦法。说了就要做到。”
梅尔用铁竿似的手杖尖催我。
这时我注意到一个重大的可能。一件比眼见美纪弥被杀更重要的事情,不,是致命的……
是平安通过死荫幽谷的恐怖。就好像自己错过死亡班机,事后得知时一样。而拔掉机翼的人正是现在在眼前夸耀的梅尔。
我的身体不由得颤抖。
可是梅尔却摇摇头说没那回事,仿佛连这事也在他算计之中。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大叫。
“我的计划精准,丝毫不差。”
梅尔说,仿佛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一般。
脑海中的记忆中断,我陷入被朋友出卖的半崩溃状态——可是,这些并没有发生。这家伙还是一样。这一点也不意外。我回想过去,一种不信任感从过去逐渐蔓延到眼前。其实,今天只是更加确定而已。
“走,回去吧!”
梅尔只手高举手杖。我怎么会有这种朋友……看着他的背影,我真心地这么想。
——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原名:“彷徨える美袋”(收录于《メルカトルと美袋のための杀人》)(原作发表年代:一九九七年)
选自:《推理杂志》月刊·林白文化 译者:吴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