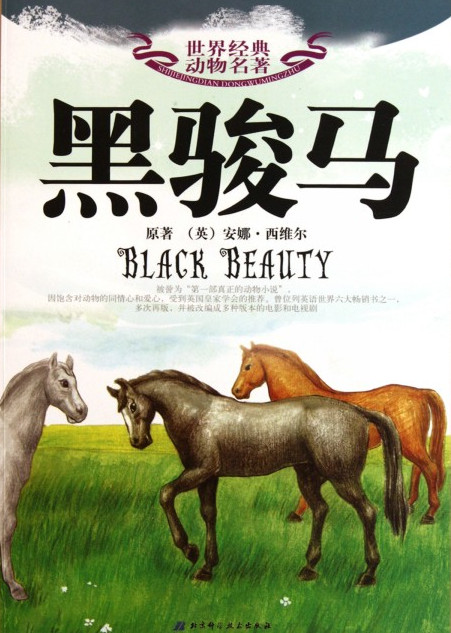麦拉在车子后座挺身坐直,捋平衬衫,推开杰克的手。
“怎么了,宝贝,”他笑着轻声道,“没事。”
“你没事吧,杰克。”她告诉他。“我不开玩笑,起开。”他的手不折腾了,胳膊还是腻歪地搭在她的肩头。麦拉不睬他,望向窗外。那是十二月底的一个周日傍晚,长岛的街道看上去死气沉沉。脏兮兮的积雪硬壳堆在路旁,酒铺里的纸板圣诞老人斜着眼往外看。
“我还是觉得让你们这么老远送我不太合适,”麦拉冲正开车的马提说,以示礼貌。
“嗨没事,”马提咕哝一声。他鸣笛,冲着前头一卡车添了一句,“让这孙子滚蛋。”麦拉有点不悦——为什么马提总是那么火大?——但是艾琳,马提的老婆,从前面拧过身来冲她友善地抿嘴一笑。“别理他,”她说,“让他礼拜天出来总比在家躺着强。”
“不管怎么说,我真特别感谢。”实际上她更愿意自己坐公车来,像往常一样。每周日来探望丈夫的四年间,她已经习惯了坐长途汽车,而且喜欢在汉斯德倒车回家的时候,到车站旁的小餐馆里点咖啡和蛋糕。但今天她和杰克去马提和艾琳家串门,饭吃得实在太晚马提不得不提出载她去医院,她也只好答应。艾琳和杰克自然都得跟着去,而且搞得像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不过你总得客气一下。“坐车确实是,”麦拉说,“比坐公车要——杰克,放手!”杰克说,“嘘——嘘,没事,宝贝。”她甩开他的手,身体扭开。看着他俩,艾琳咬着舌尖吃吃的笑,麦拉感觉有点脸红。其实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艾琳和马提知道她跟杰克的事儿,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也没人说什么(说到底,这跟守寡有什么区别?)——只是杰克不能太过分。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手看住,安分一会儿?
“好了,”马提说,“这下快了0”卡车转弯,他们加速前进,大街变成马路又变成高速,把街道和商店甩在身后。
“听听广播怎么样,孩子们?”艾琳说道。她按下一个按钮,一个人劝大伙现在,今晚,呆在家里好好看电视。她调台,一个人说,“没错,你的钱在克劳福百货更值钱!”
“给丫关了,”马提说,再次鸣笛,转入快车道。
汽车一开到医院里头,艾琳转过来说,“这挺漂亮的。不开玩笑,这多漂亮!你看,他们这有一圣诞树,灯什么的都有。”
“诶,”马提问,“怎么走?”
“一直,”麦拉告诉他,“开到圆环那,就圣诞树那儿。然后右转,过了行政楼然后一直走到头”。他这样开过去,快到那低矮狭长的结核病大楼时她说,“到了,马提,就这儿。”他把车靠边,她拣起给他男人带的杂志,踩在外头灰薄的雪上。
艾琳耸着肩膀抱着自己转过来,“哦喔,外边太冷了,啊?宝贝,你看多会能完事?八点?”
“对,”麦拉说,“那什么,你们回家吧,我跟以前一样坐公车就行。”
“你以为我有毛病啊?”艾琳说,“你当我愿意让杰克在后头纠结着这么一路回去啊?”她咯咯地笑,冲她使眼色。“你进去这会儿能哄他高兴就不易,更别提回家了。不,听着,我们在这转两圈,亲爱的,或者去喝两杯,然后八点准时到这接你。”
“也行,不过我其实……”
“就这儿,”艾琳说,“八点整,这门口。行,赶紧上去吧别把我们都冻死。”关上车门的时候麦拉冲车里微笑,杰克却一言不发,没有微笑,或者挥手。车子开走,她沿着小路和台阶走向结核病大楼。
巴掌大的等候厅里闻起来是水暖气和湿漉漉的胶鞋的味道。麦拉快步穿过,路过标有护士室-消毒区的房间,来到宽敞嘈杂的中心病房。病房里三十六张床被一条走廊分成两半,又被齐肩的隔断分成六个开放区域。为了和医院洗衣房里未污染的织物分开,床单被罩和病号服都染成黄色——这种黄色和墙上的惨绿掺在一起,麦拉总是不习惯。噪音也让人受不了,每个病人都有个半导体而且似乎同时在放不同的电台。一些床前有几撮来访者,一个新来的病人正搂着媳妇接吻——但别的床上看书听收音机的男人们都显得很孤单。
麦拉的丈夫直到她走到跟前才瞧见她。他正盘腿坐着,凝眉看着大腿的什么东西。“你好,哈里。”她说。
他抬起头。“哦,你好啊,亲爱的,没看见你过来。”她附过身,在他脸上快速地亲了一下。有时他们会亲嘴,虽说那违反医院规定。
哈里瞥了一眼手表。“你今天晚了。公车晚点了吗?”
“我没公车,”她说着,脱掉了外套。“有人送我来。艾琳,我班上的那个女孩,他跟他老公开车送我来的。”
“哦,真好。干嘛不让他们上来?”
“哦,他们呆不住——还得去别的地儿。不过他们问你好。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哦,谢谢,真棒。”他接过杂志,摊在床上:《生活》,《克里尔周刊》和《大众科学》。“真不错,亲爱的。坐这待会儿。”麦拉把外套搭在床边的椅子背上,坐了下来。“你好,钱司先生。”她对隔壁床上点头微笑的削瘦黑人说道。
“你好吗,威太太?”
“不错,你呢?”
“啊,抱怨不管用。”钱司先生说。
她隔着哈里的床,瞧见赖奥梅正在那躺着听收音机。“小赖,你好啊。”
“你好,威太太。没看见你进来。”
“你太太今天一会儿来吗,小赖?”
“她现在周六来。她昨晚上来了。”
“哦”,麦拉说,“替我问她好。”
“一定,威太太。”
然后她冲隔间另一头总是叫不上名字的老人微笑——她从来没见过有人来看他。他微笑致意,略带羞涩。她坐定,打开手袋找烟。“哈里,你腿上放的是什么?”那是个金色的木环,边上一圈木腿打着蓝色毛线。
“这个吗?”哈里说着,举起它。“这叫纺织环。”
“什么环?”
“纺织环。是这么回事,你用毛线针,这样把毛线绕在木腿上,一圈一圈的绕,最后出来一个毛围脖或者毛线帽。”
“哦,这样啊。”麦拉说,“这有点像我小时候用那种线筒,上头有勾子。把线绕着勾子缠好这么一拉,就出来一根粗线。”
“哦,是吗?”哈里说,“线筒?对,我想起来了,我姐姐也这么弄过。线筒。你说的没错,这个跟那意思差不多,就是大一号。”
“你想做个什么呢?”
“哦,不知道,弄着玩。帽子什么的吧。没想好。”他捧着自己的作品左右端详,然后俯身放进了床头柜。“找点事干呗。”她递烟过去,他抽出一根。他弯腰接火柴的时候,她从他敞开的黄色病号服里看到瘦骨嶙峋的胸膛,其中肋骨被移除的一侧塌陷进去。露出一部分最近一次手术刚刚愈合的难看伤疤。
“谢了,亲爱的。”他说着,嘴里的烟随之晃动。他往后靠着枕头,伸直套着袜子的双脚。
“你感觉怎么样,哈里?”她说。
“还行。”
“你看起来好多了,”她说了谎,“要是再胖点,你就跟好人一样。”
“拿钱”,半导体音幕中穿出一句话,麦拉回头,看见一个矮小的男人坐着轮椅沿走廊过来,像所有肺结核病人一样用脚拖行,以避免手推轮椅带来的胸部疼痛。他笑着朝着哈里过来,露出一口黄牙。“拿钱,”他停在床边说道。他胸腔上类似绷带的东西伸出一根胶皮管,用别针盘绕着固定在上衣,另一头接到沉沉坠在胸前口袋里的皮盖小瓶。“赶紧的,”他说,“拿钱。”
“哦对对对!”哈里笑着说,“忘了一干净,沃特。”他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块钱递过去,他接过钱,用细长的手指折起,掖到口袋里的瓶子旁边。
“成,哈里,”他说,“两清了?”
“两清了,沃特。”
他把轮椅倒回去调头,麦拉才看见他的胸背和肩严重畸形,向山峦一样突起。“打搅了,”他说着,露出疲惫的微笑。
她笑了笑,“没事。”他沿着过道走远,她问,“这是哪一出?”
“哦,周五晚上有人打架,我们打赌来着。我都给忘了。”
“哦,我以前见过他吗?”
“谁,沃特?见过吧。我还在外科动手术那阵你应该见过他,亲爱的。小沃在那呆了两年多,刚转到这儿。这孩子受了不少罪,挺有种的。”
“他衣服兜里那东西是干吗用的?那瓶子?”
“哦,他在做引流。”哈里说,靠在黄色的枕头上。“小沃人不错,他能回来我挺高兴的。”他放低声,偷偷说:“说实话,他这样的人不多了。老人儿都不在了,要不就是转到了外科。”
“你不喜欢这些新来的吗?”米拉也压低嗓音,不让也算是新人的小赖听见。“他们对我都挺好的。”
“哦,他们还行,”哈里说,“我意思是,你看,我和沃特这样的老病号更谈得来。我们在一块久了,经的事也多。我说不上。这些新来的有时说话吧,让人生气。你比如说,他们都对结核病一窍不懂,可是一个个都跟医生似的,你说什么他们都不听。这种事就特别气人。”米拉说她明白了,同时感觉不能再继续这个话题。“艾琳说这个医院很漂亮,圣诞树啊什么的。”
“哦,是吗?”哈里小心翼翼地伸手过去,把烟灰弹进床头柜上一尘不染的烟灰缸。长时间的医院生活把他所有的动作都变得一板一眼。“最近工作怎么样,亲爱的?”
“哦,还行。你记得我上回说的那个珍妮午饭吃太久被炒了,然后所有人都怕他们在半小时午休时间上头卡我们?”
“哦,我想起来了,”哈里这么说,但她看得出他不记得,而且没有在听。
“可是呢,这事好像又过去了,上礼拜艾琳跟三个女孩中饭吃了两个钟头,谁也没说什么。有个叫露丝的,盼着被炒鱿鱼都盼了几个月,什么事也没发生。”
“哦,是啊?”哈里说,“那倒不错。”谈话停顿了。“哈里?”她说。
“啊,亲爱的?”
“有没有新消息?”
“新消息?”
“我是说,你另一边需不需要动手术。”
“哦,不不不亲爱的。我说过了,最近一阵都不会有这种消息——我跟你解释过了对吧。”他笑着皱着眉,表示这个问题的可笑。很久以前,在她问道“你什么时候能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表情。他接着说:“你瞧我上一次手术还没好彻底。这种事急不得,术后恢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特别是像我这些年——四年了吧——有这么多次反复的病例。所以他们得再等半年,或者更长,我不知道,看这半边的情况再考虑另一边。谁也不能打保票,亲爱的,你知道的。”
“没错,哈里。对不起。我不是想瞎问。我只是想问问你感觉怎么样。你还痛不痛?”
“不痛了,一点也没。”哈里说。“只要不把胳膊举得太高就没事。有时睡觉翻身也痛,但是只要我保持那种……正常的姿势那样就,一点也不痛。”
“那好,”她说,“听到这我太高兴了。”他们谁也没再说什么,就这样好像过了很久。他们的缄默在半导体,笑声和咳嗽声中显得异样。哈里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翻着《大众科学》。麦拉看着他床头的一个相框楞神,这张扩印的快照,是新婚之后他们在密歇根州娘家的后院照的。照片里的她风华正茂,穿着那条1945年的裙子显得双腿修长,她不会穿衣甚至不知道怎么站,满脸稚气,笑容无忧无虑。但是哈里——奇怪的是——他在照片里却显得比现在还老。可能因为脸盘更宽体格更壮,当然也得益于深色镶边的艾森豪威尔夹克和锃亮的皮靴。哦,他那时这么帅气,沉稳的下巴,刚硬的灰色双瞳——比起那些块头过于结实的男人——比如杰克——要好看得多。不过日渐消瘦让他的眼神不再犀利,嘴唇的线条也软了下来,像个瘦瘦的小男孩。他的脸色现在很衬身上的病号服。
“你这本杂志带的太好了,”哈里说手里那本《大众科学》,“正好有一篇我想读的文章。”
“好,”她这么说,但心里说:“就不能等我走了再看?”哈里在面前翻着杂志,强忍住想看的念头,说道:“别的怎么样,宝贝?工作之外的,我意思是。”
“还好啊。”她说,“那天收到我妈的一封信,祝圣诞快乐之类的。她问你好。”
“好,”哈里这么说,不过杂志还是取得了胜利。他又翻开它,找到那篇文章随便地看了起来,好像为了确定就是那一篇——不一会就看了进去。
麦拉用烟屁新点了一支烟,拿起那本《生活》,开始翻看。不时抬头看他:他躺着看,咬着指甲,用蜷起来的脚趾挖另一只脚底袜子上的洞。
他们就这样度过了一小时探视剩下的时间。快到八点的时候,一群人沿着过道,费力地推来一架装有橡胶脚轮的钢琴——周日晚红十字会合唱团。带头的是波拉切克太太,她高大和蔼身着制服,演奏钢琴。一个面色苍白总是嘴唇湿濡的年轻男高音推着钢琴,身后跟着女歌手:滚圆的女高音身着塔夫绸礼服,显得双臂粗大,清瘦的女低音不苟言笑,夹着一个公文包。他们把钢琴推到病房中央,正好是哈里的床边,开始整理乐谱。
哈里从杂志里抬起头,“晚上好,波太太。”她的镜片对他闪着光。“今晚好吗,哈里?想不想听圣诞颂歌?”
“好极了。”收音机一个一个地收声,闲聊也消声灭迹。但就当波女士奏出第一个音符之前,一个矮胖的护士砰砰地踩着胶底鞋走进过道,张手拦住钢琴,要说些什么。波拉切克太太向后坐下来,这名护士伸长了脖子对病房一头喊道:“探视时间结束!”,然后转向另一头,“探视时间到!”她在消毒麻布面具之后对波太太点头示意,又跺着脚走开。和乐队开小会之后,波太太开始演奏《铃儿响叮当》的前奏,她随之摇摆,来掩盖探病者离开的干扰,有的歌手低声咳嗽,等待观众安静下来。
“天,”哈里说,“没想到都这么晚了。来,我送你出去。”他慢慢坐起,两脚摆向地下。
“别,不用,哈里。”麦拉说。“你躺好了。”
“不不,没事。”他说着,把脚挤进拖鞋里。“帮我把那睡衣拿来,亲爱的?”他站起身,她帮他套上一件老兵医院的条绒睡衣,有点显小。
“钱司先生,晚安。”麦拉说,钱先生微笑点头致意。她跟赖奥梅和那个老人道别,经过沃特的轮椅时,她说了声晚安。挽着哈里骨瘦如柴的胳膊,她心里感到恐怖,并小心翼翼地和哈里保持步调一致。等候厅里气氛尴尬,他们俩面对面站在流连的人们之间。
“那好,”哈里说,“好好的,宝贝。下周见。”
“唔——唔”,谁的母亲说了一句,缩着脖子往门外挪,“今晚上够冷的啊。”她转身向儿子招手,然后攥住丈夫的胳膊,走下积雪的台阶。有人扶着门让其他人出去,放进来一股飕飕的冷风。门关上了,厅里只剩下麦拉和哈里。
“好吧哈里,”麦拉说,“赶紧回去,躺在床上听音乐吧。”他地站在那里睡袍敞开,看上去弱不经风。她伸出手来,齐整地把袍子在合在胸口,把晃荡的腰带紧紧扎好,而他就这么低着头,笑着看着她。“赶紧进去,免得着凉。”
“好吧,晚安,宝贝。”
“晚安”,她说,然后掂起脚尖,亲了他的脸颊。“晚安,哈里。”她在门口转过来,看着哈里走回病房,高腰睡衣紧紧包裹着他。她出来走下楼梯,一阵寒风袭来,她竖起衣领。马提的车还没来,路上空无一人,只剩探视者远去的背影,他们从路灯底下向行政楼旁的公车站走去。她走近大楼,裹紧外套以躲避寒风。
“铃儿响叮当”一曲结束,掌声寥寥。接着,乐队开始真正卖力演出。钢琴奏出肃穆的和弦,歌声响起:“听!那天使的歌声,歌颂新王的诞生……”突然间麦拉喉咙一堵,街灯模糊起来。她咬着指节,悲戚地啜泣,缕缕哈气消散在黑中。她花了很久让自己停住,每次的抽噎很远都听得到。终于她停下来,或者就快停下来了,她控制住颤抖的肩膀,擦干鼻子收好手绢,用一种让人放心的,置身事外的姿态,“啪”的合上手包。
车头灯照亮了进来的路。她迎着跑过去,站在风里等。
车里一股温热的威士忌气味,萦绕在樱桃红的烟火之间,艾琳高声地说,“唔呼!赶紧上车,关门!”门一关上杰克就把她搂了过来,低沉地耳语道:“你好啊宝贝。”他们都有一点醉,连马提也眉飞色舞的。“坐好了各位!”说着,他们拐过行政楼,路过圣诞树,在直路上开始提速。“大家坐稳了啊!”艾琳的扭过脸来叨咕,“麦拉,亲爱的,你看,我们在前头找到一个特好的地儿,那种路边小店,不过特便宜。那什么,跟我们上那小喝一杯怎么样?”
“好,”麦拉说,“没问题。”
“你看啊,我们比你先进入状态了,而且我也想让你看看这个地方……马提,悠着点!”她笑着说。“换别人喝那么多开车我早慌了,不过马先生从来都没问题。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喝了没喝,没区别。”但是他俩没在听。深吻之中,杰克的手溜进她的外套,熟练地穿过层层阻碍,来到她的胸前。“还生我气吗,宝贝?”他嘴对嘴地咕哝道。“去喝一杯吧?”她紧紧攫住他的后背不放。然后让自己被转过来,这样他的手就可以向她大腿深处偷偷进发。“好,”她耳语道,“但是就喝一杯,然后……”
“行,宝贝,没问题。”
“然后,情儿,咱们直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