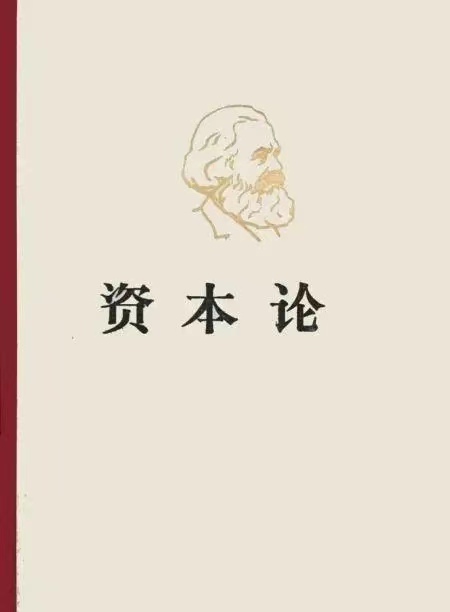冬季最短促的、使人昏昏欲睡的白天的首尾,是毛茸茸的、昏暗的晨光和暮色;当城市在冬夜的迷宫中越来越明显地出现,被短暂的黎明不情愿地摇醒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被遗失,出卖和交给另一个领域了。
他的脸和脑袋上长满着密密麻麻的、乱蓬蓬、硬扎扎的灰色毛发,一绺绺、一撮撮,不规则地直立着,从他的疣子上、他的眉毛中、他的鼻子眼的通道中钻出来,使他的模样像一头坏性子的老狐狸。他的嗅觉和听觉敏锐得异乎寻常;人可以从他的紧张、沉默的脸上的表情中看出,通过这两种官能作媒介,他同耗子洞、黑暗的角落、烟囱口和地板底下尽是灰尘的空间所形成的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保持着永远的接触。
他对窸窣声、黑夜的吱吱嘎嘎声,对秘密的、折磨人的室内生活是个具有警惕性和关心的观察者,是个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的共谋者。他被那种生活吸引得那么出神,完全陷在一个别人没法进入的领域里;他甚至不打算同我们谈论那个领域。
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的种种现象显得太荒诞的时候,他常常轻轻地弹手指头,对自己发出温和的笑声;接着,他同我们的那只猫交换会意的眼色;那只猫也了解那些神秘的事物,会抬起它的冷冷的、玩世不恭的条纹脸,闭上倾斜的眼眶,显出一副冷漠和厌烦的神情。
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正在就餐,我父亲突然会把刀叉放在一边,餐巾仍然系在脖子上,动作像猫似的悄悄地从桌旁站起身来,踮起脚走到通往隔壁房间的门前,极小心谨慎地从钥匙孔中张望。接着,他会流露出腼腆的微笑,回到桌旁,稍微有点困窘,含糊不清地喃喃呐呐、轻声轻气地说着话,那种语调同他的心思完全被迷住了的内心独白是相配的。
我母亲为了让他散散心,使他摆脱这种病态的胡思乱想,会强迫他在黄昏时刻出去散步。他默不作声地出走,不反对,也不起劲,神思恍惚,心不在焉。有一回,我们甚至大家一起到戏院去。
我们发现自己待在一间灯光暗淡、肮脏的大厅里,充满使人昏睡的人声和没有目标的混乱0不过,我们一路穿过群众后,在我们面前出现一片巨大的淡蓝的幕,像另一片天空。一个个巨大的、鼓起着脸颊的、漆成粉红色的面具在一块巨大的帆布中摆动。人造的天空向两个方向展开,被悲哀的情绪和伟大的姿态的强有力的拂动鼓起着,被在引起回声的脚手架所搭成的舞台上创造出来的虚构的泛光灯世界的气氛鼓起着。颤抖传遍那一片辽阔的天空那块使面具复活和变大的巨大的帆布在飘动,显示那片天空的虚幻的特点,造成现实的振动,在那个超自然的时刻,我们感受到现实的振动微微闪烁的启示微光。
那些面具哆嗦着红色的眼睑,他们的色彩鲜艳的嘴唇无声地嘟囔;我知道那个时刻即将来到;到时候,神秘的气氛的膨胀力会达到顶点,鼓起来了的幕布的天空会确实迸裂,显示种种难以置信和叫人眼花缭乱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被允许经历那个时刻,因为在这时候,我父亲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流露出几分焦急的神情。他摸遍了所有的衣袋,最后说他把那个放钱和一些最重要的文件的钱包忘在家里了。
他同我母亲短短地商量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阿德拉的诚实受到匆促的评估;然后,提到了我,我被挑中回家去找钱包。按照我母亲的意见,开幕前,时间多着哩;何况我走起路来飞也似的,完全有机会及时赶回。
我走进被天空中的光照亮的冬夜。这是那种明亮的夜晚,星星闪烁的天空是那么辽阔,伸展得那么遥远,似乎被分割和拆散为许许多多各别的天空,足够装点整整一个月的冬夜的天空,而且提供一个个银色的和色彩鲜明的星球覆盖种种夜间的现象,奇遇、事件和狂欢。
在这样的夜晚,差一个男孩去干一件紧急而重要的事情,真是太缺乏考虑了,因为在半暗不明的亮光中,街道显得多起来了,变得纵横交叉,难以辨认。在城市的深处,那里展现着一条条相似的街道,大同小异的街道和虚假的街道。人的想像力被迷惑和引入歧途,为一些显然熟悉的地区制造出于错觉的地图;在那些地图中,街道有正确的位置和惯用的名字,但是由夜晚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提供了新的、虚构的外形。这样的冬夜的诱惑通常是从要想抄近道,走一条可以快些到达、不过比较不熟悉的道路这个天真的愿望开始的。可能走一条从未走过的支路,来缩短复杂的路程。这个有吸引力的念头从心里涌起来了。不过,从那时候起,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走了几步,发觉我没有穿大衣。我打算回去,但是接下来,我认为这是不必要地浪费时间,尤其是这夜晚一点都不冷;恰恰相反,我能感到一阵违反时令的热浪,像春夜的微风。雪花细小得像白色绒毛,像散发着甜美的紫罗兰香味的、柔和的羊毛。一团团相似的白绒毛飘过天空,月亮在那一团团绒毛上面大了一倍和两倍,同时显出一切月相和姿势。
那夜,天空在许多部分毫无遮掩地露出内在结构,好像近乎经过解剖的陈列品,显出光的螺线的螺层、浅绿的黑暗固体、空间的深绿玉髓,梦的组织。
在这样一个夜晚,不可能沿着壁垒街或者任何一条黑暗的街(那些街道正好在市场广场的四面,好像是市场的衬里)走,而不记得在这很迟的时刻,那些奇怪和最有吸引力的铺子有时候还开着;那些铺子,在平常的日子,往往被人忽略。由于那些铺子的墙上有黑沉沉的嵌板,我经常管它们叫肉挂色的铺子。
这些确实挺有气派的铺子夜晚开得很迟;铺子里总是有我最感兴趣的商品。阴暗和深沉的店堂里弥漫着油漆、清漆和供香的气息,弥漫着遥远的国家和稀有的商品的香味。你可以从商品中发现孟加拉烟火,魔盒,被忘掉好久的那些国家的邮票,中国贴花纸,靛青,从马拉巴尔运来的假宝石头,外国的昆虫、鹦鹉、巨嘴鸟的卵,活的蝾螈和蜥蜴,曼德拉草根,从纽伦堡运来的机械玩具,装在坛子里的矮人,显微镜,和望远镜;最特别的是,奇怪和稀有的图书,其中充满叫人惊奇的版面和叫人吃惊的故事的陈旧的对开本。
我记得那些神情端庄的老年商人;他们侍候顾客的时候眼睛向下,态度殷勤,默不作声,充满智慧和耐心,足以应付他们的顾客的最难以捉摸的、忽发奇想的怪念头。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有一家书铺里,有一回我悄悄地看到一些稀有的、被禁止流通的小册子,揭示种种人们极想知道、却一无所知的神秘行径的秘密会社的出版物。
我非常难得有观光这些铺子的机会——特别是衣袋里有一笔小小的但是足够的钱——我不可能放过我现在这个机会,尽管有重要的使命委托给我。
按照我的估计,为了走到那条开着那些夜晚营业的铺子的街上,我应该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经过两三条支路。那样走反而会使我离家更远,但是穿过盐场街,我可以抵销那些耽搁的时间。
观光肉挂色的铺子的想望使我加快步子;我拐到一条我认识的街上,不是在走,而是简直像在跑,提心吊胆地防止迷路。我经过三四条街,但是我要找的那个拐弯的地方仍然丝毫没有迹象。更严重的是,街道的面貌同我原来以为的不一样。也看不到丝毫铺子的影子。我所在的街上的房子都没有门,而且窗都关得紧紧的,由于月亮的反光,窗里的情况一点都看不见。那些房子的另一面——我想——从那条街上,一定可以走进去。我现在走得更快了,心里相当慌,开始放弃观光那些肉桂色的铺子的念头了。我现在要做的是,赶快离开这里,到城里我更熟悉的地区去。我来到街道的尽头,拿不准它会把我引到哪里。我发觉自己站在一条路面开阔、建筑物稀少的大街上,街道很长、很直。我觉得空旷地带的微风吹在我的身上。人行道旁,或者说花园中间,屹立着一幢幢式样别致的别墅,有钱人的私人住宅。在别墅和别墅中间,是一个个公园和果园的墙。整个地区看来好像是菜什尼亚思斯卡街比较低和难得有人来的那一部分。月光透过成千羽毛似的云,像天空中出现了银色灿烂的景色里显得黑沉沉的。
我向一幢建筑物凑得更近张望,发现我看到的是一所中学的后面;我以前从来没有从这一面看过那所学校。我走近大门,想不到门开着;门厅的灯亮着。我走进去,发现自己站在过道的红地毯上。我希望悄悄地穿过学校,不被人发觉,从正门走出去,这样就大大地缩短了路程。
我记得,在这样迟的时刻,在阿伦特教授的教室里,可能他在义务上课;冬天,在晚上很迟的时候,他总是义务开课。我们大家被这位出色的老师在我们心里唤醒了对艺术的热情;在这种热情鼓舞下,我们纷纷前来上课。
一小群勤奋的学生几乎消失在巨大而昏暗的课堂里;课堂的墙上突然出现我们的脑袋的庞大的黑影,那是被两支插在瓶里的小蜡烛发出的光投上去的。
说实话,在这样的课上,我们画得不很多;教授也不很严。有些男孩从家里带来垫子,直挺挺地躺在长椅上,短短地打个盹。只有我们当中最用功的人才围在蜡烛旁,待在那圈金色的亮光里。
我们通常得等好长一会儿,教授才会来到,所以我们总是用带着睡意的谈话打发时间。最后,通往他的房间的那扇门才打开,他会走进来——矮个子,留着小胡子,习惯于流露神秘的微笑和保持谨慎的沉默,散发出秘密的气息。他小心地随手关上他的书房门;能过那扇门,有短短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头顶上有一群石膏像,受苦的尼俄伯的子女、达那伊得斯姐妹和坦塔罗斯的儿子女儿等残缺的古典形象,奥林匹斯山上悲惨和绝嗣的全部形象,多少年来竖立在那个石膏像博物馆里调残。他的房间里的光线甚至在白天也是昏暗的,由于那些石膏头像的梦、那些空洞的眼神、苍白的侧面像和正在溶化在虚无中的沉思,显得阴沉沉。我们有时候喜欢站在那扇门前倾听——倾听承载着即将化为碎片的诸神的叹息和低语的寂静;诸神在他们暗淡的微光中厌烦和单调地衰亡。
教授带着非常庄严和兴趣浓厚的神情在一排排半空着的长椅间走来走去;我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长椅上,在冬夜的灰色的反光中作画。一切都是安静而舒适的。我的同学有几个睡着了。瓶子里的两支蜡烛已经燃烧得矮下去了。教授把身子伸进一个很深的书橱中,橱中摆满陈旧的对开本,旧式的版画、木刻和图片。他带着神秘的姿势给我们一幅古旧的石印夜景,月光下的树丛,以白色的月光为背景而显得轮廓黑黢黢的冬天公园中的大道。
在带着睡意的谈话中,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时光流逝得不均匀,好像一会儿在推移的过程中技术引进,一会儿在哪里把整个空着的一段段时间吞没。我们这伙人没有经过丝毫转折,发现自己全部走在回过的路上了,午夜已经过了好久,公园的小路上铺着白雪,小路两旁是漆黑、干燥的灌木丛。我们走着,两边都是一簇簇黑黢黢、毛茸茸的树;我们擦到像披着毛发似的灌木,在明亮的夜里,在虚假的乳白色的亮光里,比较低的灌木树枝被我们的脚嘎嘎地踩断。白雪、苍白的微风、乳白色的空间渗透出的弥漫的白光,好像一张印着版画的灰色的纸;在那张纸上,密密麻麻的灌木丛相当于浓墨的装饰线条。在这样迟的时刻,夜晚也模仿起阿伦特教授的画中的夜景来了,再现他的想象力。
在公园的黑黢黢的灌木丛中;在一簇簇灌木的长着毛发似的外表下,在许许多多长着硬皮的细枝下,有的是隐蔽的角落,壁龛,最深沉的、毛茸茸的黑暗所居住的窝,充满混乱,秘密的姿势,默许的神情。那里温暖和安静。我们穿着沉甸甸的衣服,坐在柔软的雪上嗑榛子;在那个春天似的冬天里,榛子可多着哩。整个小灌木林里,鼹鼠在寂静无声地转悠,还有貂和獴,毛茸茸的、善于搜索的、细长的矮腿动物,散发着羊皮的臭气。我们怀疑,在它们中间有学校陈列室里的陈列品,虽然那些动物内脏已经除去,而且正在脱毛,在这个白色的夜里,在它们的空洞洞的身内,感受到天长地久的本能的声音,求偶的欲望,回到灌木丛里来,过短短的一会儿幻觉生活。
不过,雪花像在春天里似的失去了光泽;接下来,它消失了,出现了一片密密匝匝的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有些人在温暖的雪地上睡着了;其他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找他们的家门,走进他们的父母和兄弟的熟睡中,走进连续不断的、很大的打呼声中;打呼声赶上了他们的迟归。
对我来说,这些晚上的绘画课有一种秘密的魅力,所以现在我不能放过向那个上艺术课的教室里看一会儿的机会。不过,我打定主意,我只看短短一会儿,决不待久。但是,我从后楼梯走上去的时候,杉木板在我的脚底下发出回响;我发觉我是在这幢做学校的建筑物的我完全不知道的一边。
甚至没有一点儿响声打破这庄严的寂静。这一边房子里的过道比较阔,铺着厚实的红地毯,漂亮极了。个个拐角上挂着灯光幽暗的小灯。在第一个拐角上拐弯,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甚至更宽敞、更豪华的门厅里。其中有一堵墙上开出一条宽阔的玻璃拱顶过道,通往房子的内部。我可以看到两边相对的长长的两溜儿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眼光在丝绸的帷幕、镀金镜框的镜子、高贵的家具和水晶枝形吊灯上转来转去,接着望到华贵的内部去,那里是一片柔软、光滑的天鹅绒世界,在闪烁的微光下,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华饰和含苞欲放的鲜花。这些寂静无声的空房间里充满着一面面镜子在互相交换的秘密的眼色,和在四面墙上高处奔跑、消失在拉毛水泥的白天花板中的饰带所造成的惊慌气氛。
我带着羡慕和惊叹的心情面对这一切富丽堂皇的排场,猜想我这次晚上的越轨行为出人意料地把我带到了校长住的那一边,带到了他的私人往所。我站在那里,心怦怦地直跳,出于好奇心,一动也不动,准备好只要听到一点儿响声,拔脚就逃。我这样晚闯进来,这样肆无忌惮地窥探,要是被人当场逮住的话,我会怎么辩解呢?那些长毛绒的深扶手椅,其中有一张上可能坐着校长的那个年轻的女儿,没有被人看见,一动也不动。她可能对我抬起眼睛——乌黑、神秘、安详的眼睛,没有人经受得住这双眼睛的凝视。但是,半途撤弃,不贯彻我安排的计划,那是怯懦的行为。再说,富丽堂皇的室内,在无法确定时间的朦胧的亮光映照下,一片寂静,声息全无。我在玻璃拱顶的过道上望过去,看到起居室的另一头有一扇通往阳台的玻璃门。处处是那么静,我突然感到胆子大起来了。走下那短短几磴台阶,走到同起居室一样平的地方,赶紧走几步,穿过昂贵的大地毯,走到阳台上,从那里我可以毫不困难地往回走,走到那条熟悉的街上,我认为这算不上是非常冒险的举动。
我就这样干了。我发现自己站在镶木地板上,一盆盆棕榈树下面;那些棕榈树高得碰到天花板的饰带,这时候,我注意到我确实处在中立地带,因为起居室没有前墙。它有点儿像大凉廊,几磴台阶把它同城市的广场连接起来,成为广场的一个拦开的部分,因为有几件公园里的家具直截了当地摆在人行道上。我从短短几磴石头台阶上跑下去,发现自己又同街道在一个平面上了。
天空中的星座都危险地颠倒立着;所有的星星已经倒转,但是月亮埋在羽毛褥垫似的云层下面——尽管月亮看不见,却照亮了云层——看来在它前面好像还有走不完的行程,而且它正在一心考虑它复杂的天空中的进程,并没有想到黎明。
几辆马车黑黢黢在街上渐渐出现,半破不碎、关节脱开,像瘸腿的、快要打瞌睡的螃蟹或是蟑螂。一个赶车的从他的高高的座位上向我俯下身来。他长着一张小小的、亲切的红脸。“乘车吗,少爷?”他问。这辆马车的有许多肢体的一切关节和纽带都在摇动起来,它的轻便的轮子滚动着出发了。
但是,在这样一个夜晚,谁会把自己交托给一个无法预测的赶马车的,听凭他的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安排呢?在车轴的卡达卡达声中,在赶车的座位和车顶的碰撞声中,我没法就我的目的地同他取得一致的意见。他对我说的一切都纵容地点点头,管自唱着歌。我们绕着城市转圈。
在一家小酒馆前,站着一伙赶马车的,他们向他友好地招手。他高兴地回答他们;接着,他没有停车,就把缰绳扔在我的膝盖上,跳下车去,同他那伙同行待在一起。那匹马,是匹聪明的拉车的老马,匆匆向周围望望,迈开单调、有节奏的步子小跑,继续前进。事实上,那匹马引起了信心——看来它比那个赶车的机伶。但是,我自己不会赶车,所以只得依赖那匹马的意志。我们拐进郊区的一条街,街两面都是花园。我们一路前进,那些花园慢慢地变成长着高高的树的公园,而公园又依次变成森林。
我将永远不会忘却这个最明亮的冬夜里的这次光明的行程。染了颜色的天空的地图扩展成为一个无边无际的穹隆,穹隆上隐隐约约地出现奇形怪状的陆地和海洋,用显著的潮流和涡流的线条作标记,用天空地貌的绚烂的纹理作标记。空气变得容易呼吸,像银色的薄纱似的微微闪光。能闻到紫罗兰的香味。从毛茸茸的羔羊皮似的白雪底下,颤抖着的银莲花冒出来了,每一个细巧的花萼中有一点月光。整个森林看上去好像被成千上万的亮光和在十二月天空中在大量陨落的星星照亮了。空气同一道秘密的清泉一起在捕动,同纯洁的雪和紫罗兰一起在捕动。我们进入一个丘陵起伏的风景区。一溜溜高耸着光秃秃的树尖的丘峦屹立着,好像天堂乐园的标志。我在那些幸福的斜坡上看到一群群闲逛的人,聚集在长满苔藓的沼泽地和灌木丛中间,在这时已被雪沾湿了的陨星中间。路变得陡了;那匹马开始在路上打滑,费了好大劲儿才拉动那辆吱吱嘎嘎的马车。我感到快活。我的肺吸收着空气中那道带来幸福的泉水、那种白雪和星星的清新感。马胸脯前那条堆着白色雪花的通路变得越来越高;马儿简直没法蹚过那大量洁白的新雪。最后,我们停住了。我从马车厢里出来。那匹马喘着粗气,耷拉着脑袋。我把它的脑袋搂在我的怀里,看到它那双大眼睛里含着眼泪。我注意到它的肚子上有一块圆的乌黑的伤痕。“你干吗不告诉我呢?”我低声问,哭了。“我最亲爱的,我是为你才这么干的,”那匹马说;接着,它变得很小,好像一个木头玩具。我离开它,感到轻松和快活极了。我反复考虑到底乘经过这里的慢车呢,还是走回城里。我开始从一条陡峭的小路上走下去,路在森林里弯弯曲曲地伸展,好像一条蛇;起先是迈着轻愉的、有弹性的步子;后来,变成光匆匆的、快活的奔跑,渐渐地越跑越快,直到像穿着滑雪板向下滑行似的为止。我可以随意调整速度,而且只要我的身子轻微地做个动作,就可以改变路线。
在城市的边缘,我放慢这次胜利的奔跑的速度,改成稳重的行走。月亮仍然高高地挂在天空中。天空在变形,它的穹隆显得多种多样,构造越变越复杂,这种形貌的变化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在那个具有魔力的夜晚,天空像一个星盘,显示它的内部机械装置,以无限的演变表明我的嵌齿和齿轮的数学运算。
在市场广场上,我遇到一些在散步的人。他们都被那夜的景象所陶醉,个个脸向着上空,脸上被奇妙的天空涂上一层银光。我完全不把父亲的钱包摆在心上了。我父亲被他的种种癖好所吸引,这会儿可能已经忘掉他丢失的东西;至于我母亲,我不怎么在乎。
在这样一个夜晚,在这一年里也只有这一个夜晚,人产生快活的念头和灵感;人感到被神圣的诗的手指所抚摸。我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和打算,想要走回家去,却遇到了几个胳膊底下夹着书的同学。他们被那一夜永远不会消失的光亮所唤醒,已经出发去上学了。
我们一起沿着陡峭地向下伸展的街道散步,街上弥漫紫罗兰的芳香;拿不准那到底是像银子那样绵亘在雪地上的夜的魔力,还是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