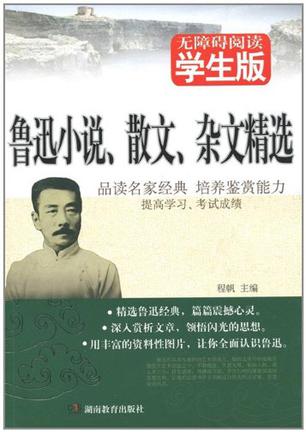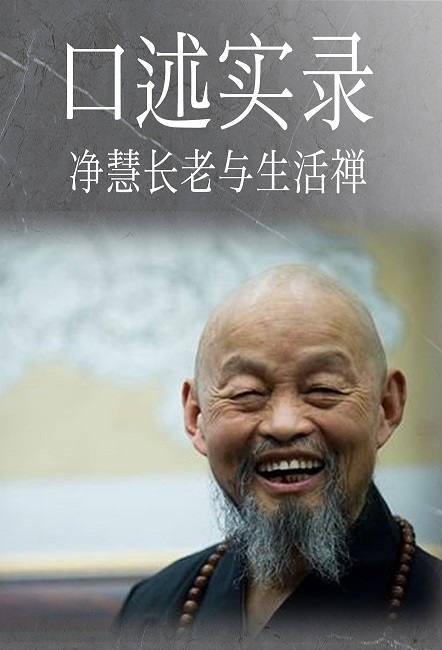【前言】武斗,文化大革命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在那个疯狂的红色年代,武斗进一步把人拉进了一个丧失人性、理智的深渊。我想这段历史应该是史上最荒诞、最无法律约束的时期!
本文作者给您讲述亲身经历过的保定关城武斗时期真实事件!

――【关城村往事】――
有惊无险的一夜
文:张燕晨
――【关城文苑】――
被第五届人大取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史称四大。
文革经历了四大之后就进入了武斗阶段,初级阶段的武斗以拳脚棍棒为主,由于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分别支持两个观点的派别,武装部和4800部队的军械库的枪弹随着武斗的升级,两派群众组织装备也随着得到改善。
武斗严重的时候真刀真枪的战斗经常发生。保定攻打河北农大的武斗还动了坦克。
南大冉一派包围了一派,一派又包围了圈,形成了三四圈的重叠包围,撤下来的战斗伤员,凑巧我在新安镇学校所见,和现在看到影视战地医院的场面一个样。
68年新安被围55天,解围的三十八军战士死伤多人。
淀南南冯村,一上午被打了60炮,都打在村外。没听说有伤人。
各村两派都有武斗小分队,关城公社的小分队当属东磊头XXX
带领的武斗队,装备齐战斗力强,经常参加各种规模战斗,打西向阳时就有伤亡。相比之下村里四个大队的武斗小分队势单力薄,虽然也有出村参加战斗的经历,基本也是凑人数没有实质性的开火实战。
关城公社夺权之后基本是斗批改掌权,反修派的人在村里不得势,两派群众都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怎么能一派服一派,什么事总有出头的,也叫派性强的。总在江湖上行走,难免磕磕碰碰,在那个无绪的社会环境中,一切行动都是革命行动,根本就没有了法律底线,结果有这么老几位 分别被打,有打的遍体鳞伤,有打的多处骨折,火棍穿到腿肚里,似乎挑了大荕。经常吃亏的人在村里呆不住了,安州镇是反修的大本营,人多战斗力强。集中了不少一个派的人。
我要说的惊险一夜,是发生在1969年的冬天,天还不算太冷,正是农闲季节,上面组织挖河的时候。村里年轻人有的出门挖河了。
这天,晚上公社里正在召开各大队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安州得到了消息,立刻精心组织,准备到关城干出点大动静来。一个装备整齐精干的小队伍,带着各种步枪和手榴弹。奔关城出发了,由关城村人带队,为了走近路,从独连村下道,走生地直奔关城,本想近道取快,不成想领错了路,反而耽误了时间,待队伍进村后,干部会议已经结束,散会了,安州的队伍,到了公社扑了空,接着分头进行搜捕,消息很快走漏,真佩服在没有手机的年代,这些战斗消息是如何及时获得,三大队队部和卫生所,经过搜捕没有发现人,个别人已经在大队部房上,也做好了战斗准备,多亏没开火否则这个场面还不知如何收场。几经查找也没有找到人,其他大队也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其实人都藏起来了,有的人上了房,有的人藏在了可靠人家,有人藏在了床底下。总之,一夜没有发生正面的充突,只是把公社广播员,张小国给捆绑在椅子上,有的人说身上绑了炸药,不知真假,挨顿打是少不了的,这次来扑了空,没有收获,不能就这么回去,队伍埋伏在了村外地里,就是现在出村的路西,村下坡。现在都盖房子了,天亮以后,人才撤。
后来是埋伏在村外的战斗员,不幸枪走了火,伤到了自己,拉回去不几天便死亡。
关城村有惊无险的一夜,就在村外随着走火的一声枪响而结束。
总之,关城村,在文革时期,特别是武斗期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件,没有死亡人。比较其它村还算稳定的。

>武装的红卫兵
战士眼中的文革武斗
1968年,我当兵入伍,来到了驻扎于保定的某部队。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两派尖锐对立的阶段,从1968年到1970年一段时间,两派武斗最严重,由开始的大刀长矛演变到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保定的武斗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为了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支持左派,制止武斗,我当兵不久就被抽调到部队支左第一线,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即支工、支农、支持左派和军管、军训,经历了当时的混乱场面,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再向前一步就开枪
我们参加支左工作,当时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共就我们三四个人,由一个干部带队。
我们的工作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促进两派大联合。当时的口号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的纪律是,对待革命群众要做到三不,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制止武斗不带枪。”
当时该厂分成两派,一派占据了工厂厂区,一派占领了工厂的办公区。楼房窗户全部用砖头堵起来,只留一线进光的缝隙,楼顶上架着机枪,都有全副武装的护厂队员警戒,守卫着各自的地盘,双方相互监视,互不来往,势不两立。有一天,我和指导员一起去工厂门口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想借此机会接近对立面,给他们讲解中央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一行三人刚走到距厂门口二十来米的地方,工厂里面的高音喇叭就喊起来了,并反复播放毛主席语录。这时,门里面走出来十来个小伙子,身穿劳动布工作服,臂带红袖章,手里拿着各式武器,有刀,有枪,有棍棒。他们朝我们迎上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气势汹汹地问:“你们要干什么?”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说:“不能进去!”这时我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也不让进?”对方有人说:“我们就是不让进!”,说着说着就一起朝我们围了上来。这时我们已来到距厂门十来米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围上来了,就说:“你们还要围攻解放军?” 这时对方有人威胁说:“不许过警戒线,再向前一步就开枪!”我们这才看到脚下地面上用白灰横着画了一条白线,算是他们的警戒线。为了不发生冲突,我们只好站在原地宣讲毛主席最新指示,我当时年轻气盛,还有点不服气,心里想“难道解放军还怕你不成?”
枪走火伤人
我们在这个工厂支左时,就住在用砖头堵住了窗户的办公楼上,造反派护厂队在楼下挖了地道直通外面兄弟单位。楼上住着护厂队员,都是些工厂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拿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各式武器炫耀,睡觉也抱着,警惕性可真高。
结果有一天,我们刚睡到半夜,就听到“啪”的一声枪响。怎么回事?大家都一咕噜爬起来往外跑,看是出了什么事?这时,一个人从楼道不远处的卫生间爬了过来,我们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他有气无力地说:“走火了!”。我们赶忙低头看去,血已经染红了整条裤腿,看来伤得不轻。我们领导赶快给团里首长打电话,要求派车来送伤者去医院。
汽车很快就来了,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地方牌照经过改装的解放牌大卡车,汽车前面及两侧都用钢板焊起来,只在前面留了两个长方形小孔做瞭望用,是土造的装甲车!我们很快把受伤的人抬上车,用最快的速度向营房疾驶。我们几个当兵的在车上担任警戒,手持冲锋枪,面朝两边外侧监视周围的动静,为得是防止路途遇到袭击。因为当时回部队营房要经过一座桥梁,这是必经之路,部队的车辆经常在此处遭遇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袭击,所以必须格外小心才是。
很快来到了团部卫生队,由卫生队的军医在急救室施行手术,由于条件简陋,也可能情况紧急,我们在外面等候过程中,只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阵撕牙咧嘴的喊叫声,看来伤员确实太难受了。
事后我们才得知,平时他随身带着枪,出事那天,他上厕所也带着枪,在蹲坑时把枪放在了大腿上,而且是子弹上了膛的,结果站起来时忘记了枪在腿上放着,一起身就把枪掉地上了,正巧子弹被击发打在了大腿上,幸亏抢救及时,而且没伤着大动脉,要不就要了小命啦!
“游击战”的伤兵
1969年夏天,我们团卫生队收治了一批“伤兵”,都是附近各个县里参加武斗被打伤的武斗队员,他们被临时安置在团直属队的营房里休养。有的伤了胳膊,有的断了腿,有的失去了脚,其状惨不忍睹。
我有一次回部队办事,无意中听到他们讲了亲身经历的武斗“故事”。他们一般队伍组织严密,必须是骨干分子,且自愿参加,经过挑选,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吸收的。看过地道战、地雷战的朋友都知道,在冀中平原,地形单一,一马平川,能够用以隐蔽的就是一些河沟、水渠、桥梁。他们在野外布置埋伏,像部队一样,下达口令,且经常变化,对上口令的就是自己人,对不上口令的,迎接你的就是一梭子弹,有几个就是对不上口令被击伤的。还有的人在外边打了胜仗,回来刚要休息一下,躺在炕上给旁人讲刚刚打仗的故事,说到高兴处,双脚往高一抬,就被窗外飞来的子弹打穿了脚腕。还有的伤员给我们讲了攻打碉堡据点的情景,对方守住据点,用粮库里的黄豆倒在进攻者必经的通道上,让他们采上去进退不得。

受害的解放军战士
在某地支左的负责人是个大胖子,他是炮连的事务长。一天,他带着几个战士去一个村里做工作。结果被对方围困起来不让离开,遭到一群人的围攻。更严重的是,看到这个带队的干部是个胖子,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当时没有军衔,干部战士都一样,只是在衣服几个兜上能区别出来),人家以为是我们的团参谋长,把他一个人隔离起来上酷刑,往肚子里灌辣椒水,往眼里撒石灰粉,折磨的死去活来,最后才被部队解救出来。
我们团有一次派人去保定城里拉军粮,结果在去保定拉粮的路上遭遇袭击,二连有一个班长被高射机枪击中脖子,大动脉被穿透,当场死在车上,就这样无辜地牺牲了。在汽车回来后,我们去看了汽车马槽上的枪眼,被打穿的洞有指头那么粗,密密麻麻布满马槽两侧。
部队战士在执勤中被推揉、殴打是常事,有的被把被子扔到水里,把帽子抢走,领章被揪掉。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
造反派抢武器
我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造反派抢武器的遭遇,时间大概是1969年春天。当时,我们团大部分连队都在保定市里各个单位执行支左任务,营房留守的人员很少。我所在的连队也不例外,当时我们连队只有我们一个班在营房留守,平时就是种种菜,溜溜马,站站岗,放放哨,管理一下连队的战备物资、战士的物品等,倒也自在。后来,保定两派武斗逐步升级,形势越来越严重,上级通知我们把自己用的武器全部隐藏起来。我们把武器用黄油涂抹,用塑料布包好,在营房自己寝室的地下挖成一米多深的坑,把武器埋藏起来。上面再用砖头铺好地面,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人动过。
除了自己使用的武器,我们团还存放着部队从各地造反派手里收缴的各式各样的武器,以及从省军区接管的各种武器。有轻机枪、重机枪、各式手枪、左轮、信号枪、迫击炮等,好些都是民兵在抗日战争和游击战争中使用过的。整整放满了一营、三营的大食堂,外面用铁丝网钉起来,门窗都封闭的严严实实。
团里做好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军人俱乐部前的操场上架起了高射机枪,支起了探照灯,平时有了情况就拉响警报并朝天开枪报警,为的是各个团相互照应、相互支援。
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警报齐鸣,枪声大作,探照灯亮了起来,有造反派来抢武器啦,我们紧急集合,保卫部队装备不能落入造反派手中。领导布置不准动用武器,我们只好把火炮的仪表连接杆拿在手中备用,以防万一。
结果,出乎我们的想象,来的人实在太多啦。他们赶着马车,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从四面八方朝部队营房涌来,我们所在的部队营房西围墙外面挤满了人。我奉连队首长的命令,趴在围墙上朝外向人群喊话:“造反派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解放军支持革命群众!”“反对打、砸、抢!”来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在一阵“一、二、三!”的号子声中,就听得哗啦啦一阵响,腾空冒起一股灰尘,约百十米长的营房围墙应声而倒!人们蜂拥而入。大部分人进到营房就朝团部的弹药库跑去,一会儿就听到弹药库被砸开的消息。男人、女人、老的、少的,肩扛、手抱,往外搬武器弹药。年轻女人把裤角扎起来,把子弹装在裤腿里,一步一挪地往外走,手里的各式小手枪、信号枪一抓好几把,被我们追得一路走,一路丢。有的人拿着铁丝做成的探条往地面下面捅,妄图想找到被埋下的武器。枪武器的群众一直到天快亮才全部撤走。天亮后,我们只好从营房周围的麦地里到处去捡被丢弃的武器、弹药。
就在这一次被抢武器的过程中,我们团有十几位战友负伤了。原来,正当大家奋力保护一营的弹药库时,三营的弹药库面临更大的威胁。造反派里三层、外三层把个库房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挤来挤去,眼看库房就有被打开的危险。抢武器的人群中有人把手榴弹帽拧开了,把拉线套在手指上,高举过头,威胁要爆炸。这时,突然手榴弹冒烟了,那人连忙把手榴弹扔在了战士们脚底下,只听得一声巨响,我们从老远向响声传出的地方看去,树上的树叶哗啦啦地往下掉。过了一会才听说有人负伤了。因为战士们都挤在一起筑起了人墙做防护,大部分都是炸伤了腿部,倒了一大片。我们有一位一起入伍的老乡就是这一次护卫武器中负的伤,他的一条胳膊神经被炸断,至今落下了胳膊萎缩不能动的残疾,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我经历的这些场景,只是沧海一粟,为了不忘这段史实,我把它记录下来。过去已成历史,往事不堪回首,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动乱,应当深入反思。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社会一定要前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是建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
写于二0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文革记忆之抢占荣大南货店
众所周知,“荣大”是一家地处江苏省常熟市中心的南货店,除了琳琅满目的食物,其中并没有敌人。但自从两派“大联合”,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另一派回城进驻西门县委大院之后,该店在派头头眼里则成了扼制异己东侵的理想屏障。我方营盘在城东垮塘桥旁的血防站,往北走六七分钟,往西经过新华书店,再往北总共拐两个弯,便是荣大南货店,从荣大往西走六七分钟,便是县委大院。
造反派头头五官端庄,威严英俊,中山装,一口普通话,活脱脱王洪文,让人肃然起敬。另外,抽烟姿势看上去挺有风度,弹烟灰动作别具一格。据说其父乃黄埔军校高材生。才一杯茶的功夫,祖传的三寸不烂之舌,便嚼得部下热血沸腾磨拳擦掌。当夜,我们就拿起木棍铁棒,走小街,迂回到西门大街近西城楼阁处,沿着大街往东走,示威性的跑过敌方的营盘——县委大院。一边跑,一边喊:五一六必胜!九七三必败!
老保闭门不出,没有开门拦腰截击,大概不知虚实,担心我们趁机铲他们的老窝。第二夜,我随几十位战友衔枚疾走兵不血刃占领了“东方的前哨”——荣大南货店!
毕竟乌合之众,人马进了店,大门没人关,大伙只顾上楼翻窗据守屋顶。有的忙里偷闲,朝瓦楞上撒尿,还有的踩着瓦片往远处走,估计想寻找战时临时厕所。要不是我和一老工人就地取材用装满红枣的麻袋堆封那几扇排门,坚守岂不成了儿戏!
不一刻,对方在西门大街的尽头出现了。黑压压的,估计有二三百人,步伐山响,倒海翻江的“欧欧欧”代替了冲锋号,一色藤帽铁棍,速度似神行太保戴宗,估计是九七三的中流砥柱——房管所“铁扫帚”。他们是九七三武斗的中坚力量,跟五一六“八一”队战斗力处于同一级别。这伙人很快出现在荣大店门前(说是说店门前,其实起码五十米开外)。我十分恐慌,呆在屋顶上,随着大伙漫无目标乱掷瓦块,以虚张声势。
我是近视眼,当时没钱配眼镜,是个深度睁眼瞎,不晓得掷的瓦块有无击中目标。等到胳膊酸痛的时候,对方后退一百米才停止呐喊。趁战斗间隙,我找无人之处方便了一下。一位看守荣大的职工,可能也是五一六观点或成员,指指咸肉缸,对大伙说,饿了烧咸肉。满满的两大缸咸猪肉,上面铺着盐花。让人怦然心动,我半生从未放开肚皮吃咸肉饭、咸肉汤,吃的老是黄萝卜饭榨菜皮,多么希望停止战斗,让我放开肚皮吃个饱啊!
我们自以为打退一次进攻,打电话报捷。指挥部说:“光明就在前头,战友们辛苦了!”我们说,“不辛苦,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后来远处聚兴面店的整甏黄酒被“老保们”搬往大街。对方不拘小节坐在街沿石上,象梁山好汉一般大碗喝酒。一边喝,一边不时高喊“九七三必胜!五一六必败!”借此下酒。我们懒得应腔,呆在荣大的屋顶上或吹牛或养神或喝糖汤嚼蜜枣,以等待对方的卷土重来和指挥部的夜点心。
半夜一点,人心惶惶,因为有消息说,老保占领新华书店,阻断了我们的退路。我头里乱糟糟的,想临阵脱逃,偷偷翻进附近的商店或民居,只是碍于面子、还有黑灯瞎火,才没有将懦弱付诸于滑脚。下半夜两点,对方曾迂回曲折钻进隔壁“美味春”点心店掘壁洞,掘得“荣大”的货架玻璃橱摇摇晃晃,后被老工人发现,用木棍撑住玻璃橱,大喊“捉老保!”偷袭才半途而废。
战斗”一夜,直至东方鱼肚白,“荣大”店前一片瓦砾,却不见一具尸体,唯见一顶孤苦伶仃的旧呢帽仰天躺在街上,里面粘糊糊的一滩瘀血。
书生投笔从戎,并没有成为自己的光荣历史与卓越功勋。后来形势变了,五一六被清洗,我隐瞒了这个武斗经历,沒受到什么惩罚,可能明知参加了武斗,对盲从的学生不予追究。当时有谣言,说我混水摸鱼,半爿咸猪猪趁乱掮到学校的七一兵团团部,还有一说,掮到了自己的家。说我有的是气力,毕竟码头工人子弟。我对毛主席保证没拿,没人相信,晓得除非开肚剖肠给人看,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现在回想少年时代的鲁莽,自告奋勇当炮灰,仍然后怕。因为武斗使用热兵器时,有人炸了屁股,有人打穿乳房。
使用冷兵器时,有个学生叫刘志军的,死在棍棒之下。此人为人豪爽勇敢,挺有威望号召力,一个领袖的料。他守卫荣大北面的工人文化宫,给对方切断退路,战友们一个个溜了,他没法撤退,死守楼顶,按理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没什么大问题,但倒霉的是,貌似公正的支左人员翻上楼顶,将其抱住,收缴所谓的武器,对方趁机冲上前去,战友们眼睁睁远处看着他死去。
(说明:关于刘志军之死另一种说法:刘志军死于 1968 年 3 月 10 日,不是被人抱住后打死的,是他坚守在文化宫影院屋顶,对方人员攻上屋顶后,他陷入绝境,对方大喊他投降,因他是一个号称”铁血兵团“的打手,好勇斗狠,手段残忍,结怨甚多,自知若被对方抓住决无好果子吃,说不定会被打死,慌不择路时竟从屋顶往下跳,不幸堕落的身体在半空中被树挂了一下,顿时头朝下重重摔在下面的石凳上,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死时他左臂上还戴着物资公司造反派的红袖章,也溅上了血。这一天称为”310武斗“,共死了三个人,也是常熟市两大派最后一次死伤人命的武斗)

说实在的,参与这次武斗,固然由于年轻,思想给人左右,糊里糊涂去“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另外,也因家境贫寒,自己馋痨,厌倦了父母长年供应的薄粥、酱油萝卜,才主动走进己方的“兵营”。每天八菜一汤,八人一席,坐的是长板凳,吃的是流水席,像走进了共产主义食堂(不瞒大家,有次我看见一麻袋一麻袋的粮草从米厂运进总部,感到分外高兴)。打打牌,吹吹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吃饱喝足之后,晚上集合,你说能不上战场吗?
来源:卿卿幽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