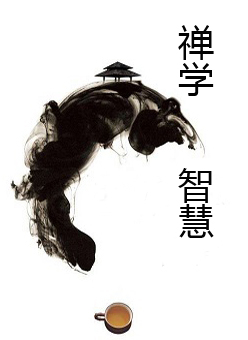吴法宪,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身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同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他曾经跻身于中共领导的最高层。但不久,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将他和成千上万的军事将领卷向了政治的深渊。
该书是作者用十年的时间,以过人的记忆力而着成。他用亲身经历的大量史料,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讲述了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很多精彩片段并揭示了其中的很多必然关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指导下,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而文化大革命则使之一系列运动达到了顶点。
做为当时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作者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在那一特殊时期,很多中共领导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作者也因此大起大落,最终饱受十年铁窗之苦。正是如此的坎坷经历,才使其得以对政治和人生都另有领悟,并将其切身感受以及亲身经历详细记载于该回忆录当中。
第一章 我的一家人
一、 四世同堂
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及弟妹们。曾祖父的名字叫吴遐渭,是个十分老实的农民,他的一生都是在劳苦之一中度过的。我八岁那年,曾祖父去世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曾祖父去世后,我们一家人及亲戚把他送到我们家后面一座小山上去埋葬的情景。那一年,曾祖父正好八十岁。这在当时已经称得上是相当高寿了。
曾祖父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吴芳德,即我的祖父。次子即我的叔伯父,但叔伯父叫什么名字,我却不记得了。
祖父曾在一个姓李的地主家当长工二、三十年,积蓄了五、六十块钱才娶了我祖母陈氏。婚后,祖父租了这个姓李的地主家七、八亩地种,不再出去当长工。地租很贵,是倒四六开。每年的收成,六成要交给地主,我家只得四成,大约每年要交十二担的租谷。年景好的时候,自己还能剩下七、八担谷子,这点粮食也就够全家人吃半年,其余则要靠秋季种地瓜和豆类来补充,以瓜菜来过半年。年景稍差一点,就连半年的粮食都吃不上。祖父一个大字识,但是有点手艺,会用地瓜粉做粉皮,每年的秋后,他都靠做粉皮来挣回一点钱。
祖母陈氏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家里的房子很大,但是却破落不堪。由于家境败落,祖母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到祖母的娘家去玩,她娘家里都无法招待我,只好拿蕃薯给我吃。祖母会纳鞋底,鞋底纳得又结实又好看,因此有很多的人来找她纳鞋底。她当时给人纳一双鞋底,一般是收两个银毫子。这样每年也可以掐挣回一点钱。另外,为补贴家用,祖母还在家里养了一些鸡和兔子,同时还养了一、两口猪。
我家祖辈都居住在兴国县的南坑乡,那是山凹里的一个村子。以后祖父和叔祖父分了家,我们一家便迁居到离南坑乡约三十里的水丰县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曾祖父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大安村,同我们一起生活。
我父亲名叫吴功信,是个独子,小的时候念过几年书。十六岁时,父亲结了婚。母亲曾氏,是个家庭妇女,那年也是十六岁。
一九一五年,母亲在二十岁生下了我,家里已经有了好转,刚盖起了六间屋子,其中一间厅房,一间厨房,其余四间用来住人。另外,还建了三间用来装稻谷的两层楼仓库。以后,家里又逐渐买了三亩地,一头牛和一些农具。由于我正好是盖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新福生,认为是我给家里带来的福气。
我出生一年半之后,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妹妹,接着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到我参加红军那一年,母亲又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妹妹。这样,我家一共有二男三女五个孩子。我弟弟叫吴臣洋,小名叫九生保。由于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三个妹妹都没有名字。当时可以说是我家的全盛时期。我们五个孩子,加上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一共十几口,真的是一大家子人。
由于我父亲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能写对联,也会记帐,所以总希望我也能读书识字,将来能成为一个耕读之家。于是,我七岁那年,父亲送我上了学。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未亮,鸡刚刚叫时,父亲就拿了一盏灯笼,扛着一张桌子,叫我去"发蒙"(我们家乡把孩子第一次上学叫"发蒙")。那天,他把我送到了马古州张贤左先生家支读私塾。
张先生大约收了二十多个学生。他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中庸》、《幼学琼林》,以及孟子、曾文教界正公的书等,还学了珠算。在张先生家,我一共上了五年私塾。
上学之前我就在家里负责放牛,上学以后,每天清晨我依然出去放牛,放完牛后才去上学。由于家中的烧柴都归我负责,所以下午放学回家后,还要上山去砍柴。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名叫铁炉下的村子。我十二岁时,铁炉下村的人在村内的胡家祠堂办了一个小学。学校办起来后,父亲就把我送了去。当时,铁炉下村小学只设甲、乙两个班,过去读过几年书的上甲班,没读过书的上乙班。这样,读过五年私塾的我就上了甲班。我在铁炉下村小学又学习了两年,学了一些简单语文和数学。
一九三0年五月,祖父因病去世,享年月才六十岁。祖父去世后,我们把他安葬在住屋后面的小山上,跟曾祖父葬在一起。
随着祖父的去世,我们家也开始日渐衰落。由于给祖父治病,我家欠了百余元的债,家境日渐衰落。家中仅靠父亲一人劳作已难以支撑,于是我不得不辍学参加农田劳动,逐渐学会了各种农活。
二、十五岁参加红军
一九三0年,我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村里也闹起了革命。开始组织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妇女会等。组织和动员劳苦民众积极起来参加革命。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我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任队长。从此以后,我天天参加革命活动,无论是开会、斗土豪劣绅、游行示威,还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写标语等,都非常积极。那年的六月,为配合红军的行动,我们还曾到离家一百二十里的永丰县荇田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没想到,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把队伍打散了。轰炸完了以后,我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找不着了,只好自己一个走了百十里路回家。
不久,我们村又开始打"AB团"。什么是"AB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些乡苏维埃的干部和村苏维埃的干部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里糊涂。我还看到一些人被杀,像我们小学校长胡风章、教员胡泽凡等都被杀了。这么些人的被抓和被杀,使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过了几个月,又把一些未被杀的人放了出来,说是搞错了。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放松了下来。
打完"AB团"后,我们村就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里的两个恶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来,召开全村大会进行斗争,当场把他们两个杀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座茶山。斗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就更加高了。那年的村苏维埃选举,我们选举了村里的贫农许泰仁担任村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0年十一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许泰仁代表村苏维埃,动员全体村民同红军一起,参加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保卫家乡。经过动员,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都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当时红军部队集中在于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我当时还是村里的儿童团长,我们被派去为红军带路、送信、站岗、放哨、抬护伤员和准备粮草。
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进到了离我们村仅二十里的地方,红军开始反击。战斗打响前,我们村的担架队被派到小别村,负责抬伤员。我便带领村里的儿童团,抬着三十副担架,跟着村长,准备收容伤员。
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战斗打响了。到上午十一点,伤员陆续下来了,我带着担架队赶紧抬着伤员回到村里。每家三、四人,一共住了一百多。伤员的医治是由红军医生负责的,他们到各家去救治。
就在那天晚上,上面传来消息,说红军打了大胜仗,将国民党十八师全部消灭,还活捉师长张辉瓒。我们村里的"老表"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连夜赶到龙岗一带的山上,帮助把红军伤员抢运到后方,并协助部队打扫战场。在龙岗,我们抢运伤员,为红军收集枪枝、子弹、炮弹和军用品,还掩埋死者,以及搬运一些国民党的伤病员。我们儿童团捡了成千上万的子弹壳交给红军。这次打扫战场的工作,一共进行了四、五天才结束。这是我首次参加战勤工作。
在协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以后,我参加了共青团。从这时起,我就一直想参加革命。一九三0年十二月,村苏维埃主席许泰仁召开全村大会,动员村里的青年参加红军。在这次大会上,我和许泰仁的侄子许元怀等十七人一同报了名。
知道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红军,父亲倒是很开通,表示完全同意,而母亲却只是在一边给小妹妹喂奶,一句话都不说。只有祖母在听说我要参军后,哭得很厉害。在我离家参军时,祖母一直眼泪汪汪地站在家门口,默默望着我远去。我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所以她最疼我。
在离家去参军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诉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后要靠他了,要他一定要放好牛,多砍柴,帮助父母多干一点活。当时他才十二岁。
三、全家受到迫害
我参军后,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双布鞋。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父亲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我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我父亲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我父亲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乡得到解放。家乡解放之时,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我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我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父亲收到了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兴,并很快给我回了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我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一九五0年六月,我接到调令,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让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我,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我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父亲接过来。不料想,我们于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还在信里说,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他们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地将我父亲埋藏了事。
我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病,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为我们始料不及。我后悔不已。但我当时也只能用以革命利益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道理来安慰自己。
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我手头没有钱,只好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给了我二百八十块钱的救济款。我将这笔钱转寄给了吴臣贤,要他代我给父亲买口棺材盛敛,并请他在重新埋藏我父亲后做个坟头,立一块墓碑。我还请他代我用这笔钱还清我父亲生前欠下的欠款。后来我听说在安葬父亲的那一天,乡政府还给老人家开了一个追悼会,对此,我从内心里深深表示感激。
四、解放后回家,只见一个个坟墓
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一头骡子代步。
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们家的祖居地,那里有我们吴家的祖宗祠堂。在我们到达南坑以后,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我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和一枝钢笔都送给了他们。
从南坑到我家还有三十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们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我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双岭下,我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一把雨伞来接我。离别三十年,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两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
我的家没有了,我们一行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木凳和一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我还联想到,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一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我。李文福的父亲七十岁了,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了。
许元茂、李文福告诉我,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
这时,村里的一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的情况,还对我说起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二十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帮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一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我们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罗卜,我们的这一顿晚饭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一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我向吴臣贤借了十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表示我的感谢。对其他邻居,我就只好说抱歉了。
刚刚吃完饭,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一九三一年初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我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我,尽管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我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从此便同他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我们悲喜交集,感概万千。
许元怀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这次,他带着十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
与许元怀见过以后,我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我在每一个坟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给亲人们尽的一次孝,请亲人们原谅我吧!
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一个仓库。这样,我们一行又走了两里路,过了一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我们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我们拿来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一口大锅,又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当晚,我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