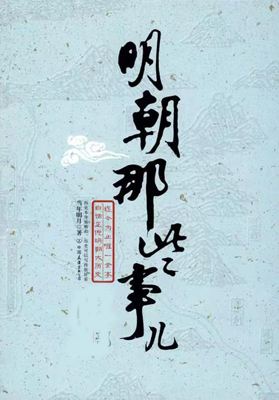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虽然没有去参加会议,因为我只是个总支书记,没有直接挨批斗,但我的心里同样很不好受。我问会上有没有提到我给谭政写的信,他们说,谭政没有上报、也没有把信交出来,所以没批我,如果谭政在会上把我的信拿出来,那就肯定撤了我的职。黄永胜还对我说:“好险,老吴!”
头天下午挨批,第二天就开始过草地。过草地时,右路军是由红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军团部跟着二师,我们一师又跟着军团部前进。在一师的行军序列中,是按一团、二团、三团排列的,我们三团又是走在最后面。草地十分危险,我们既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北针,而且就是有地图,也不可能在地图上找到草地上哪些地方下面没有泥沼可以通行。因此要过草地,就必须要找向导。
二师开始行动之前,军团部给他们找了一个向导,是个藏族老大娘,大概有六十多岁了,这个藏族老人曾走过由毛儿盖到班佑的这条路,知道该怎么走,不过因她的年岁大了,所以一路上都是由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她。就这样,我们靠着这位老人的指引,一个跟着一个,踏上了草地。
过草地的每一天,我们三团是跟着前面的部队走,我们后面就没有什么部队了。二师走了,军团部走了,一师师部、一团和二团都走了,三团跟在最后面。第一天走的都是大路,而且走得也不远,只走了五、六十里路就宿营了。沿途上一户人家都没有,但走的都是平路。向北走,没有什么高山,都是高原草地。一般的山都只有几十米高,就像是起伏不大的丘陵。
第一天的行军途中,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原始森林,都是些松树和柏树,树长得才怪呢!很粗,三个人都抱不过来,但不高,树枝很长,一根松枝有三、四丈长,也有四、五丈长的,而且枝繁叶茂,能把整个的山头山凹都覆盖上。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这样的树底下露营,下雨都不怕。大家都很高兴。我就跑到团部去向黄永胜和林龙发说,真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在这样的树下宿营比住房子还好。
晚上大家烧火做饭时,都互相告诫,一定要注意在地下挖灶。千万不要把森林给烧了。当晚,团部煮了一大锅的青稞,我带着政治处的人去打了一桶回来,里面放着盐。接着,我把一直留着没舍得吃的腊肠,切了一小段,用脸盆炒熟后,倒在那桶煮熟的青稞里拌好给大家吃。政治处的人吃了都很高兴,说我们今天的晚饭不仅有盐,还有油,真是一顿“美餐”,大家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早晨没有吃饭,队伍就出发了。再往前走,就再也没有森林,也看不见大树了,只有像小孩那么高的一些矮树,其它都是草。走到中午,我们看到前面草地上有野马和野鹿在跑来跑去,大家都说,要能打到一头该多好啊,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其实,你看着前面跑着的野马、野鹿好像很近,实际上相距很远,而且路边的水草下有很多吃人的沼泽泥潭。所以,即便你看到了野马、野鹿,也是可望而不可及,根本就打不到。
中午时分,我们过了一条河。说是河,其实也就是条小沟。河水从北往南流,水很清。看到河,队伍就休息了下来,并拿出缸子舀水喝。大家在河边一边喝水,一边就着炒过的青稞麦,一口水一口青稞,就这样吃了一顿饭。
在毛儿盖,供给处长弄到了一牛皮袋的炒面,临出发前他分给了我一斤。我一直都没有舍得吃。这时,我倒了一点在缸子里,放点水一搅,就吃起了炒面糊。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连载)
142009-05-30 14:50那天晚上的宿营地是个小山包。在这个小山包上,全团的队伍摆开露营,大家找点干柴草往地上一铺,就睡在了上面。由于是分头做饭,那天晚上的小山坡到处都是火。晚上我们刚刚睡下,就下起了雨。大家都没有雨具,只好干挨淋。我们政治处的几个同志,把一块演戏用的幕布挂在树枝上,七、八个人就在那幕布下蹲了一个晚上。后来还好雨停了。
第三天继续走,还是晚上煮点青稞麦吃,留下一碗到第二天再吃。这天就看见路有牺牲的同志了。有的用土埋了,插上一块小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牺牲同志的姓名和籍贯。这些同志从江西出发,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没有在战斗中牺牲,却这样饿死病死在草地上了。那天一路走来,大概看到了十几个这样的坟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这一天部队的情绪都不太好。因为人就埋在附近,大家都看到了。
晚上宿营后,我就向黄永胜和林龙发提出,要给部队做点工作,他们两人都说是应当做点工作。这样吧!把各连的指导员找来谈一谈,就谈这么几条,第一条,据前面部队传来的消息,过草地的时间,大概需要半个月,我们已经走了三天,队伍没有什么减员,这很好。第二条,对前面的路程,要有足够的估计,要准备再走个十五天。各连要好好调查研究一下,一个人一个人地去摸一摸,包括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和机关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所带的粮食好好计算一下,以班为单位讨论讨论,看看怎样才能使所带的粮食保证吃到十五天。第三条,要尽量使体弱有病的同志跟上队伍。由于体弱,这些同志没有搞到多少粮食,如果他们没有吃的了,要以连为单位自己调济一下,帮助这些伤病员同志解决一点困难。第四条,所有连里的干部,包括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都要轮流走在连队的后面,帮助督促战士跟上队伍。
那个时候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把病号都带出来,因为没有担架抬他们,马也少了。黄永胜他们都没有马了。那原来的马呢?自从过夹金山以后,我们走的都是崎岖小路,根本就不能骑马。有时过河,河上的桥就是一根木头,马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过梦笔山时走的那条路,人勉强能走,马却走不过去。所有有马的人,都将自己的马交由马夫带着绕道走另一条路。结果连马带人都没有回来,从此便杳无音信,连放在马背上的行李也丢了个干干净净。从此,就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走。
到第四天继续走的时候,牺牲的同志就多了。牺牲的人一多,就没有人去个个都埋了。这样一来,就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单位的。有一次,我一下就看到了五、六个人死在一起,心里真是不好受。
越往前走,水草地就越多,走得不好,一踩都是水,有点像走在摆动的浮桥上,一挪步脚下就摇晃,地上的泥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粘,非常难走。最可怕的是,有的地方就像磁铁,人一陷进去马上完蛋。我们陷进泥沼的人究竟有多少难以统计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得宿营。还是晚上做饭,吃一顿,留一点第二天到了有水的地方,再喝点水,吃点青稞麦。
到第五天,牺牲的同志就更多了。一路上,不时都可看到路旁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五个牺牲的同志倒在那里。还有一些人拿根棍子,在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我们在后面看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呀?就去动员他们说,同志,走呀!你是那个单位的呀?坚持走吧,早一点过去就好了,关键就是这个草地,过完草地就好了。他们却说,同志们,你我走吧,我们“革命已经成功”了,我们不能走了。问他们是不是有病,他们说没有病,主要是饿的,饭得实在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当我们提出照顾他们一下,分给他们一点粮食,让他们跟我们走时,他们说,我们要是为了照顾他们,把粮食分给他们,就会连我们也走不出草地,大家都会饿死在里头的。他们还说,为了保存点革命力量,为了革命胜利,让我们不要管他们,继续往前走。
这种话说得我们很难过,听后不由得泪如泉涌,但无论如何你再怎么劝、怎么拉、他们也不走。有时候,我看见两、三个人一起口口伞坐在路边,就那样死在伞下面了。这种情况,一天至少能看到六、七起。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常常一边走、一边流眼泪。
对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我们政治处就把他收容起来。有一次我们就收容了三个。那些实在不愿走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他们认为走下去也是死,就不愿意走了,只要求我们将来若是走到他们的家乡,就告诉一下他们的家里,他们已经死在草地上了。当时我们还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单位,以及家里的地址。其实,那是空的,是没有办法一一去通知他们的家里的。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真是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为革命为国为民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到第六天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多了。虽然那些走不动的同志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但由于人数太多,我们确实无力再去照顾那么多,只好妒忌痛走开。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因掉队而出现的部队减员,有时一看到前面的路不好走,哪怕这时的太阳还挂在半空中,我们就露营。一宿营,我们就召集连长、指导员开会,了解剩下的粮食情况。每次开会就是一件事,除了谈粮食,还是谈粮食,粮食这两个字就像是幽灵一样,老跟着我们,没完没了。开完会,大家就出去找野菜,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大草地上,也跟毛儿盖的那块盆地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野菜。有像白菜,也有像野葱、野蒜、野韭菜、野苋菜的,还有一种苦菜,虽苦,但没毒,能吃。另外还有一种叫蒿子的,长得和韭菜差不多,只是下面多了个疙瘩头。每天一到宿营地,我就和政治处的技术书记郭成柱、俱乐部主任萧元礼、青年干事蔡文福等人,一起到处去挖野菜。挖来以后,用脸盆一煮,没有油,也没有盐,就和着炒过的青稞麦粒吃一点,就算是一顿饭。由于长期缺油少盐,营养不良,虽然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才二十来岁,但全身没劲,走不动路,扛不动枪。
有的野菜有毒,部队上当不少,吃了那些有毒的野菜后,脸上乃至全身发肿,轻的拉拉肚子,严重的发烧、头痛甚至昏迷。后来就统一由供给部门找人专门鉴别,哪种野菜有毒,哪种野菜没毒,再分别通知各个连队。这样一来,中毒的现象才减少了。
有的同志实在没有吃的了,就吃自己的皮带。他们把皮带用水泡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和着青稞麦粒一起煮来吃。不过有皮带的人很少,吃皮带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当时,我们还听说不少高级干部把仅剩下的马杀了,和大家分着吃马肉。
有时候,由于实在没有吃的,一些掉队的战士就开始拣人家大便里的青稞麦粒吃。因为吃这种没有磨过的青稞麦粒,很难消化,常常是吃麦子粒就拉麦子粒,雨一淋,麦子就露出来了。放进河水一洗,就再吃第二次。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能走出草地。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连载)
152009-05-30 14:59草原的气候时时变化无常,常常一下子天晴,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刮风,一下子下冰雹,有时还飘雪花。有时太阳当空,一下子就会变得乌云满天,狂风暴雨。可不到半点钟,天就又晴了,但衣服已经湿了。一天来这么几次,弄得我们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中午一走路就出汗,但早晚却冷得不得了。
在过草地以前,我们凡是抓到了羊,就把剥下的羊皮留起来做衣服穿。我也弄到了一块。怎么做衣服呢?就在羊皮的中间挖个圆窟窿,从头上套下去,然后在两边腋下各缝上一条带子,把这两条带子一系,前面后面靠身就成了一个羊皮背心。就靠这块羊皮,我过了草地。草地晚上非常冷,睡觉又没有被子,每天晚上,我们都缩成了一团,我就靠这块羊皮保护了身体,没有生病。但到后来身上还是没有劲儿了,也快走不动了。
就这样走了九天多,到第十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了一大片用牛粪糊成的房子,就跟我们在毛儿盖住的房子一样,比那个要大。当时我们都很惊异,大家都说:“天哪,草地上还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是中午十二点钟到达了那个地方,就在那些“牛屎房”子里一边休息,一边做饭吃。但究竟还要走多远才能走出草地,谁也不知道。我就去问黄永胜。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不过他告诉我,队伍暂时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他已经派人到前面侦察去了,到山那边去看看有没有村庄。他还分析说,既然有“牛屎房”,就会有牛,就会有人家。
结果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翻过山二十里,就是一片好地方,那里两边沟里都有房子,还有村庄。地里有萝卜、白菜、葱、蒜、豆子什么的,长得好得很。听了侦察员的报告,黄永胜高兴地说”“这下有希望了!”他下令部队马上出发往那里走。得知前面有人家,大家的情绪马上就起来了,脚下的路也变得轻快了许多。这二十五里的路,我们只走了两个小时。
翻过了一座小山,走不远,就来到那条沟,沟两边都是人家,牛、羊、鸡、鸭、麦子、萝卜、青菜、碗豆,什么都有。这一下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都说,好家伙,这下有吃的了!我们把剩下的一点青稞麦通通都吃了,吃了一个饱,不再留了,到了这样的好地方,还留它干什么!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们赶到了一个村子。一到,就赶紧去搞粮食。没想到那一带藏族的土司、头人早作了准备,让藏民们把家里的东西都藏到了山上。除了地里长的以外都藏了起来,剩下的就只有个把鸡、没有来得及赶走的个把猪,还有狗。那些狗咬人咬得很厉害。不过地里有东西。碗豆、萝卜、土豆、大蒜等都有,。最重要的是土豆,一挖一大堆。有了土豆,我们就挨不了饿了。有的弄到羊就吃羊,弄到牛就吃牛。
这时,大家都在问:是不是我们已经走出草地了,前面究竟还有没有草地?最后终于传来消息说,前面已经没有草地了,前卫部队已经到达了班佑和巴西。大家这才总算是松了口气:真不容易啊,我们总算走出了这个饥饿和死亡的地带!
这一阶段,确定是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也是红军北上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是艰苦的一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吃的,只能吃野菜、喝冷水。那水真凉,是从雪山上下来的水。有的人受不了,喝了这水就拉肚子。我当时仗着年轻、身体好,安然无事地过来了。
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我认为藏族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和红军。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和放养的牛羊,我们就活不了,就过不了草地,就到不了甘肃,北上抗日也只是一句空话。当然在藏族同胞中,有些当奴隶的,家无寸铁,身无片布,就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子,看到我们队伍来了就跟着走的也有。但是是极个别的。有的就一直跟着我们到了陕北,成了干部,成了共产党员。但他们没有出过远门,要他们带路,还是带不了。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是很难用语言或文字完全形容得出来。当然,各个部队、各个人所遇到的情况、所吃的苦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稍好一点,有的就更苦。对高级干部,总还是有点照顾,最苦、最困难的是下面的普通战士。有的部队经过的地区好一点,吃的苦就少一点;有的部队经过的地区比较差,吃的苦就更多一点。有的部队走在前头,就好一点;有的部队走在后面就差,能吃的东西都被前面的部队吃了,后面的部队要找到吃的就要困难得多。如二师一直担任前卫,就比我们一师好一点;一师的一团、二团走在前面,就比我们三团要好一点。另外,各个部队走的路也不一样。我们行进时,是多路并进。有的路就好一点,有的就差一点。我们红一方面军只过了一次草地,而红四方面军到了阿坝又南下过草地,最后又翻过草地北上,前后共过了三次草地,那就比我们更艰苦了。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连载)162009-06-01 11:05二十、 向腊子口进发
草地的那边仍然还是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我们看到的情况也跟毛儿盖、菠萝茨差不多;有村庄,有庄稼,但还是见不到人。
过了草地的第二天,我们沿着一条河,一直向北向腊子口方向前进。那天没有太阳,我跟着后面的二营,准备收容掉队落伍的战士。二营的后面是个伙夫担子。这时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突然山上打开了枪,左一枪、右一枪地直往我们中间打来,我就喊:“队伍快走啊!前面发生情况了!”。大家拼命地跑,总算赶上了前面的部队。
我们刚过完,藏民们就从山上下来了,抓走了我们一些掉队落伍的人。等后面的大部队来到,他们又都上了山。后来听说,二团在我们前面遭到袭击,连团长龙振文都被藏民们从山上打冷枪打死了。这种打法,弄得我们挺难受。他从山上打你,看得清,打得准,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一枪就把一个团长打掉了。
第三天又继续走,晚上宿营的地方叫卧藏寺,是个喇嘛庙。我们三团跟师部住在一起。那时师长是刘亚楼。团里派出一连在离我们两里远的地方放了个连哨。当时一连还有五十多人,由连长、指导员带领着,执行警戒任务。放连哨的那个地方是个路口,没有人家,一连就在那里一边露营一边放哨。
由于当地的老百姓把粮食通通都埋了起来,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带着团直属队的一部分人,和全团队伍一起,到二十多里外的地方去搞粮食。他们出发前交待我,要我照顾留在后面的直属队机关和伙夫担子、行李等。他们走时天未亮,是早晨六点多钟。
天亮后不久,一个被刀砍伤了脑壳的一连战士,突然之间血淋淋地跑到我的屋子里,对着我“啊、啊”地乱叫,他已被砍得不能说话。那是干什么呀!我就赶紧派人去察看。原来是藏民趁
大部队没有回来的时候,从山上下来一百多人,个个手持大刀,把我们在那里放连哨的五、六十个人,包括连长、指导员在内全都砍死了,所有的枪支弹药,包括两挺轻机枪也都叫他们拿走了。损失真大呀!好不容易走过了草地,我们二团的团长却在这里被打死了,三团的一个连也被搞掉了,实在是令人十分痛心!
等黄永胜、林龙发带着部队回来,我们做了一个大坟,把牺牲的同志全都埋在了里面。在坟前插了一块木牌,上写“红军一师三团一连全体战士”。埋葬完了一连的同志以后,我们三团全体指战员立正向牺牲的同志表示哀悼,黄永胜、林龙发两人还讲了话。然后,部队继续出发北上。由于一个整连都被人搞掉了,所以团长、政委和我的情绪都不好。
部队继续向腊子口进发。突然从前面传来消息,说二师四团(即王开湘、扬成武率领的那个团)已经把腊子口拿下来了,而且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十四师鲁大章的一个团。这下可好了,因为腊子口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拿下了腊子口,我们就可以顺利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再也用不着重返草地了。这个消息极大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士气。
来到腊子口一看,嚯,那可真是天险!腊子口两侧的山崖都是悬崖峭壁,山势几乎是拔地而起。峭壁下有一条腊子河缓缓流过,河的右岸还有座小山,有百多米高。国民党军在隘口小山上修有碉堡,真有一夫守隘,万人难敌的气势。听说四团最后是从后面爬上最陡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打掉了小山上的碉堡,才消灭了国民党守军的。他们下面的强攻只是牵制住敌人的火力而已,根本就无法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
登上那座小山,我们向东一看,只见一坦平原豁然就在眼前,庄稼、森林都很多。看到这一景象,大家的情绪突然之间就起了变化,高兴了起来。
二十一、 哈达铺缩编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我们来到了腊子口附近的哈达铺。哈达铺是甘肃岷县的一个小镇,镇上只有一条小街。
哈达镇所在的那个地区是一块起伏不大的高原丘陵,有小山,但不高,村庄稠密,庄稼也多,是一个回、汉民族杂居的地方。回族同胞头上都戴白帽子,会说汉语。当地百姓说的基本上都是北方甘肃、陕西这一带的话,我们都能听懂,而且还不难懂。在走出腊子口之前,我们在藏族地区差不多有四个月没有见到什么老百姓,一到哈达铺,见到了这么多的回民和汉民群众,可以互相通话,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们三团住在哈达铺附近的两个小村子里。一住下来,指战员们就积极地向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群众也热烈地欢迎我们,给我们送来了粮食和各种食物,使我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
从这以后是真正恢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了。为了同前一阶段不讲纪律的现象和思想彻底决裂,我连续召开了团里的政工会议,先解决这一问题。我要求各级政工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广大指战员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和争取群众。
到达哈达铺的当天晚上,黄永胜和林龙发去师部开会,回来后他俩向我们传达了部队要进行缩编的决定。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部队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以后,红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斗争。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张国涛对一方面军很瞧不起。他认为,四方面军有七、八万人,而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从江西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来到四川,队伍十分疲劳,沿途打仗很多,减员很大,剩下的也就一万多人,人少兵弱,力量不大。当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则不这么认为。四方面军同志普遍认为,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增加了红军的力量,加强了领导,因此十分欢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