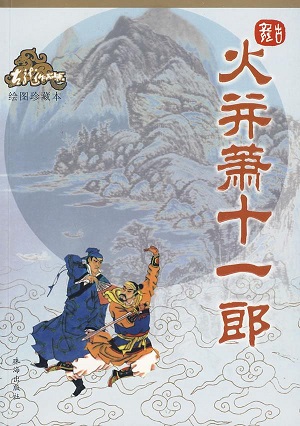头颅的价格Price of Skulls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帕内特没有什么财产,他拥有的也就是他的名字和一身棉布衣服。帕内特总是仔细地让他的衣服完好无损,就像保护他的名字一样,因为白天他要穿它,晚上还得拿它当卧室,除此之外帕内特就只剩下酒瘾和一脸红红的络腮胡子了。不过他还有一个朋友。这年头,除非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品质,否则没什么人能赢得友谊,就算在友善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也是如此。或者强壮,或者幽默,或者邪里邪气,反正一个人总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才能让他的朋友认得出,记得住。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商船上的苦力卡来卡这个土著对帕内特毫无所求的照顾呢?这可是福浮堤海滩的一个未解之谜。
在福浮堤,帕内特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他不和人吵架,更不会跟人动拳头。显然他也从没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白人,随时都有权力把一个土著踢到一边。帕内特甚至没骂过任何人,除了自己和那个中国混血儿,那个中国混血儿卖糖果给他,但那些糖果糟得没法吃。
除了这些,帕内特没什么明显的长处。长期以来他已经忘记了热血沸腾的感觉,甚至连乞讨也不会了。他从来不笑,不跳舞,也从不显示出哪怕一点简单的怪癖来使得人们宽容地对待一个醉鬼。如果这个帕内特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都会经常挨揍,但命运使他漂泊到这个生活像唱歌儿那样轻松的海滩,他奇特的命运甚至还给他一个朋友。于是他天天喝个烂醉。除了这些,他什么也不干,活像泡在酒精里的一堆潮乎乎的肉。
他的朋友卡来卡是个巴格维勒群岛的异教徒,在他的家乡有吃人肉的风俗,有时那些尸体还被熏好,储备起来以备将来之需。
不过在福浮堤,尽管是个美拉尼西亚黑人,卡来卡和别人也没什么两样。他严肃,能干,小个子,眼窝深陷,长着一头刷子似的头发,总在腰上围一条棉布头巾,鼻子上还穿着个铜环,平时总是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
卡来卡的酋长把他弄到福浮堤的贸易公司,替他签了三年合同,还吞掉了他的工资、面包和烟草。三年之后,卡来卡会被送回800英里外的巴格维勒,那时他还是一无所有。当地人都这么过来的,不过说不定卡来卡或许也有自己的一些打算。
南太平洋的黑人极少显示出让人尊敬的品质。忠诚、谦恭都只能来自那些肤色介于黄色和巧克力色的人种,而黑人总是那么神秘,让人不可捉摸。卡来卡把这个一文不名的帕内特当作自己的朋友着实让福浮堤的人吃了一惊,他们还以为自己多少对这些黑鬼有点了解呢。
“嘿,你。”那个中国混血儿莫·杰克叫道,“你最好把这乡巴佬弄走,他又喝多了。”
卡来卡正待在干椰肉棚的阴影里等着捡掉下来的椰肉。他闻声站起来,腋下夹着那些椰肉向海滩跑过来。
莫·杰克站在门槛上,冷冷地看着他说:“我说,你干吗便宜那醉鬼,把珍珠卖给我,我给你一个好价钱,你觉得怎么样?”
莫·杰克一直心烦,因为他得拿酒和帕内特换那些珍珠,然后帕内特就喝得如烂泥一般。而他知道这些珍珠是卡来卡从礁湖里捞上来交给帕内特的。他和帕内特的交易并不坏,但他想如果用烟草直接和卡来卡交易会赚得更多。
“是什么让你非得把珍珠给那个该死的乡巴佬?他狗屁不值,早晚会死掉。”莫·杰克气势汹汹地说。
卡来卡没吭声,只盯了他一眼。有那么一刻,有一股奇特的亮光从他的灰暗的眼珠中闪出,活像十尺深的海底里鲨鱼冲你眨眼。混血儿的调子立刻变成了小声咕哝。
卡来卡背着他的朋友向他的家——一个小草棚走去。他小心地把帕内特放到席子上,把他的头枕好,然后用凉水给他洗干净,把他头上和胡子上的脏东西弄掉。帕内特的胡子是真正的络腮胡,反射着太阳光,就像亮闪闪的红铜。卡来卡把他的胡子梳好,然后坐在他旁边,用一把扇子替这个酒醉的人赶走苍蝇……正午过后一点,卡来卡忽然跑到空地上抬头看了看天空。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注意着天气的变化,他知道有些变化说明贸易风会越来越强,直到完全取代那些平和的侧风。现在他看到一片片阴影让沙滩模糊了,云彩也挡住了太阳。
整个福浮堤都在午睡:侍者在阳台上打呼噜;商务代表在他的吊床上做梦,梦见大堆的椰肉装船运走,然后是大把的奖金向他飞来;莫·杰克则趴在他的小店里。没人会疯到在午睡时跑到船上去,除了卡来卡。这个不驯的黑人从来不关心午睡或者美梦。他奔来忙去,海浪拍打礁石的轰轰声把他轻轻的脚步声淹没了。他活像个无声无息的鬼魂,在福浮堤的梦乡里忙着自己的工作。
卡来卡很早就打探出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储存室的钥匙放在哪儿,还有一件是步枪和弹药放在哪儿。他打开储存室,挑了三匹土耳其红布、几把刀、两桶烟叶还有一把小巧的斧子。还有不少东西可拿,但卡来卡并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
接着他用斧子劈开步枪柜,拿了一把温切斯特牌步枪以及一大盒弹药。然后卡来卡要干的就是把船棚里的一条大船和两条小划子的船底劈穿,这样它们就好多天都不能用了。那真是把好斧子,一把真正的战斧,它锋利的刃口让卡来卡充分体会到了干活儿的乐趣。
海滩上停着一条大的独木舟,是巴格维勒群岛上卡来卡族人用的那种,它就像一弯新月,船头和船尾高高翘起。上个季节的季风把它刮到岸边,贸易代表命令卡来卡修好了它。现在他把这条船弄到海里,再把他的战利品装上去。
他仔细选择了所带的食物,包括大米、甜土豆,还有三大桶可可豆,此外还有一大桶水和一盒饼干。他在搜索贸易代表的柜子时看到12瓶珍贵的爱尔兰白兰地,尽管他知道它们的价值,但只看了看,没有拿。
准备好一切之后,卡来卡回到他的小棚子,叫醒帕内特:“伙计,跟我走。”
帕内特坐了起来,看了他一眼,就像精神病人看到自己脑海里的幻影,然后说:“太晚了,商店都关门了。我说,告诉那帮混混儿晚安,我要,我要睡觉了。”然后他又像块木板一样倒在床上。
“醒醒,醒醒,嘿,别睡了,醒醒。啊!朗姆酒,你的朗姆酒来了,真的,朗姆酒。”卡来卡不停地晃着他。
但帕内特还是一动不动,像聋子一样,连这句平时最管用的咒语也听不见。
卡来卡弯下腰,像扛个大肉袋一样把他扛到肩上。帕内特足有250磅重,而卡来卡还不到100磅。但这个小个子黑人灵巧地把他扛起来,让他脚拖着地,向海滩走去,一直到把他放到船里。独木舟往下一沉,然后离开了福浮堤的岸边。
福浮堤还在午睡中,因此没人看见他们离开,当贸易代表从午睡中醒来,暴跳如雷的时候,他们早已消失在贸易风里了。
第一天,卡来卡努力让船迎风前进,灰蒙蒙的海上,大风卷起一阵阵海浪,只要卡来卡稍微有一点疏忽,就有海水灌进船里。卡来卡是个不懂指南针,更不懂经纬度的异教徒,但他的先祖曾靠人力和浅底小船完成了远航,他们的成就使哥伦布的远航看起来就像乘渡船的旅游。现在他用锅把水舀到船外,用席子和桨坚持航行,但他们确实在前进。
直到第二天日出,帕内特才从船底的污水里抬起头来,但只看了一眼四周,就又呻吟着躺下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试了试,还是徒劳,于是他转过头,看见卡来卡蹲在船尾,浑身都是海水。“酒!”他叫道。
卡来卡摇摇头,帕内特的眼里开始闪现出渴望的目光,他继续哀求着:“给我酒,给我一点酒,就一点……”后来的两天,他就这么一直神志不清,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什么一分钟之内同一条船如何变换了47种航行方式,还说这是他的重大发现,航海史会出现革命……直到第三天他才清醒了一点,肚子里空空的,身体十分虚弱,只是精神还不错。这时风已经小了,卡来卡在静静地准备吃的。帕内特给自己来了两杯白兰地,然后才发觉喉咙里是可可奶,于是又叫起来:“我爱朗姆酒,不,给我朗姆酒。”
没人回答他,他四周打量了一下,但除了长长的水平线,什么也没看到,他终于感到有点不对劲,问道:“我怎么会在这儿?”
“风,是风送我们来的。”卡来卡说。
帕内特却没心思听他的话,也没留意他们并不是因为钓鱼时迷了路才被吹到这儿的。他的脑子里在想别的东西,一些粉红色、紫色,带条纹像彩虹一样花里胡哨的东西,这些东西真是让他其乐无穷。把一个在酒里足足泡了两年的人和酒精完全分开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海面变得平静起来,船轻快地滑行。帕内特的手脚都绑在船板上,他就不停地动他的嘴,颠三倒四地背小时候学的诗。可惜听众只有一个卡来卡。他可不关心诗的韵脚,只是偶尔泼点海水在帕内特头上,或者给他盖上席子挡住阳光,或者喂他几口可可奶,当然,每天还替他梳两次胡子。
他们平静地航行着,但贸易风越来越强,船也越来越慢,卡来卡只好冒险向东航行。这时帕内特的脸色也渐渐地开始恢复了正常的颜色,而不再像腐烂的海藻。
卡来卡一有机会就登上一些小岛,用锅煮一些米饭和土豆,但这是很危险的。有一次两个白人划着小艇把他们截住了,卡来卡来不及隐藏逃亡黑奴的痕迹,他也没这样做,他只是在对方划到五十码左右的时候,用步枪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对方中的一个被打死了,他们的船也给打沉了。
“我这边有个弹孔,你最好把它堵上。”帕内特叫道。
卡来卡解开他的绳子,堵上那个弹孔。帕内特伸了伸胳膊,好奇地东看西看。
帕内特瞪着卡来卡说:“我说,你是真的,不是个幻影。看来我好多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问:“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芭比。”卡来卡回答。这是巴格维勒的土语名称。
帕内特吹了声口哨,驾驶这种连篷都没有的船跑上800英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不禁对卡来卡肃然起敬,这个小个子黑人真的很了不起。
“那么,芭比是你家?”帕内特问。
“是的。”
帕内特说:“好吧,船长,继续前进,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但我想我会知道的。”
起初帕内特还很虚弱,但卡来卡的可可豆和甜土豆使他恢复了力气和神智。后来他品着咸咸的海水居然能好几个小时完全忘记酒这种东西。而且奇怪的是,当酒精在他体内渐渐消失,福浮堤的经历也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了。这真是两个古怪的水手,一个土著,另一个是正在康复的病人,但他们相处得还很不错。
第三周时,帕内特注意到卡来卡有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他们的食物吃光了。
“嘿,不能这样。你把最后一点可可豆也给我了,你得给你自己留点。”他叫道。
卡来卡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不喜欢吃。”
海天之间只有海水拍打船底和船板的咚咚声。帕内特一动不动地想了好几个小时,想了很多事,有时眉毛痛苦地皱成一团。的确,思考并非总是旅途良伴,尤其被拉回过去的记忆不见得那么好受。但帕内特现在却不得不回忆起他荒唐的过去,他一次次地想逃离它们,但他现在觉得无处可逃,他想自己只有面对过去,然后击倒它们。
在第二十九天,他们所有的吃的只有一点点水。卡来卡用可可豆壳舀上这点水,让帕内特喝下去。现在,这个异教徒又承担起了照料帕内特的责任,直到他把桶板上的最后一点水刮到刀刃上,滴进帕内特的喉咙里。
在第三十六天,他们看见了格塞尔岛,那岛就像一堵绿色的墙从水平线上冒了出来。卡来卡可以松一口气了,他已经航行了整整600英里,而且用的这条船没什么航海装备,甚至连海图也没有。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他们并没停留多久,很快他们又出发了。
早上风还不错,但到中午就停了。海水变得像油一样黏稠,空气让人发闷,卡来卡知道风暴就快来了,但他别无选择,他只能继续前进。他把所有东西都绑在船上,然后集中力量划桨。不久,他看见前面有一个带白色沙滩的小岛。最后,距离岛还差两英里时,风暴来了,尽管如此,他们已经算比较幸运的了。
这时卡来卡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帕内特也只能勉强抬起胳膊,而海浪就像从礁石上冒出来的火苗,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向他们的船打来。没人知道卡来卡是怎么干的,但他最后还是让船靠岸了。
就像是命中注定,那个白人一定要被他一次次救下来。当他们上岸时都快晕过去了,不过都还活着,而且卡来卡一直紧紧地抓住他白人朋友的衣角。
他们在这个岛上待了一个星期。帕内特用岛上无穷无尽的可可豆把自己养胖。卡来卡则在修补他的船。船严重进水了,但他的货物完好无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磨难快到头了,巴格维勒岛,卡来卡的家乡,就在海峡的对面。
“芭比就在那边?”帕内特问。
“没错。”卡来卡回答他。
“哦!上帝!太好了。这儿就是大英帝国管辖权的尽头了。老伙计,他们只能到这儿,他们过不去了。”帕内特叫道。
卡来卡也很清楚这一点,如果世上有一件事让他害怕,那就是斐济高等法庭的治安法官,他有权对任何违法的行为采取行动。
在海峡这边,卡来卡还会因为偷窃而被起诉,但到此为止,卡来卡知道,在巴格维勒岛,他可以干任何一件他想干的事,不会受到惩罚。
至于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帕内特,他的身体慢慢复原了,而且洗得干干净净,甚至他灵魂中那些邪恶的东西也被洗掉了。湿润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使他重新充满活力,使他有力气到水里游泳或者帮卡来卡修船。没事的时候,他就花上几小时在沙滩上挖个坑,或者欣赏小海贝壳的古怪花纹,要不就唱着歌在海滩上游荡,享受他从前很少留意到的生活的可爱之处。
唯一始终让他迷惑的是卡来卡,不过这并没让他感到什么不安,他像孩子一样对此一笑了之。他想到的是不知道怎样回报卡来卡为他所做的事。最后,帕内特还是开始猜想卡来卡为什么要带他到这儿来。为了友谊?一定是这样的。想到这里,帕内特把头转向那个不爱说话的小个子。
“嘿,卡来卡,你是不是怕他们起诉你偷窃,别理他们。你这老家伙。如果他们敢找你的麻烦,我一定跟他们打一仗,我甚至可以告诉他们东西是我偷的。”
卡来卡没吭声,只是埋头擦他的步枪,就像个天生的哑巴那么安静。
帕内特见他没回答,自己小声咕哝着:“不,他没听见,我真想知道你脑袋里在想什么。老家伙,你像只猫一样独来独往。上帝证明,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想——”他忽然跳起来。
“卡来卡,你是怕自己逃跑连累我,你是怕一个奴隶逃走连累他的朋友才带上我,是这样吗?是吗?”
“嗯。”卡来卡含混地答了一个字,看了一眼帕内特,又看了一眼对面的巴格维勒岛,然后低下头继续擦他的枪。这个海岛土著真像一个谜一样。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巴格维勒岛。
在绚烂的朝霞中,他们的船开进了一个小小的海湾,这时海岛还在睡梦中,缓缓地一呼一吸。帕内特跳下船,跑到一块大石头上,看着眼前壮丽的景色,觉得真是美得难以形容。这时小个子卡来卡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他卸下布、小刀,还有烟草,然后是子弹盒、步枪,以及他的小斧头。这些东西稍微受了点潮,不过所有武器都擦过了,在清晨的阳光里闪闪发亮。
帕内特还在喋喋不休地试图描写他看到的景色,直到一串串脚步声在他身后停下来。他转过身,惊讶地看到卡来卡站在背后,背着枪,还拿着斧子。
“嘿!老伙计,你想干什么?”帕内特快活地叫道。
“我想,”卡来卡慢慢地说,眼里又闪过莫·杰克先前见过的古怪的光——就像鲨鱼冲你眨眼,“我想要你的头颅。”
“什么?头颅?谁的?我的?”帕内特惊奇地问。
“是的。”卡来卡简短地说。
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所有谜团的答案。这个土著迷上了这个流浪汉的脑袋。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帕内特被自己的红胡子出卖了。在卡来卡的家乡,一个白人的头颅,熏好的头颅,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比钱财、土地、酋长的荣誉和姑娘的爱情都让人更羡慕。所以这个土著制订了计划,耐心地等待,使用各种方法,甚至像个保姆一样给予这个白人照顾,给他喂食,给他梳胡子。他所做的就是要把帕内特平安、健康地带到这儿,然后安全、从容地摘取他的胜利果实。
帕内特很快就明白了所有的一切是怎么回事,这些是如此惊人,几乎没有白人曾想到过。但他现在正清醒地身处事中。没人知道帕内特在想什么,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从胸腔深处发出,就像他刚刚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笑声穿透隆隆的海浪声,把海鸟从峭壁上的寂寞中惊起,久久地绕着阳光飞翔。
最后,修正的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帕内特的财产清单为:名字,一身破烂衣服,一部漂亮的红胡子,还有就是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是在他唯一的朋友的帮助下恢复了健康、活力。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帕内特转过身说:“想要我的头颅,那么开枪吧,该死的。真是个便宜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