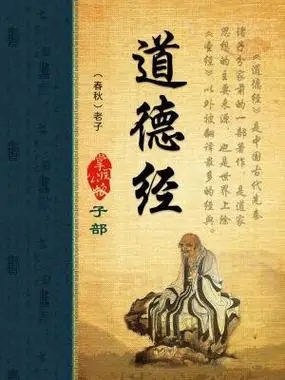01
莎车河是我此次旅行见到的最为壮丽的河流,水流舒缓、质地清澈。《汉书·西域传》中关于莎车有“出青玉”的描述,看来此言的确不虚。
河流如此,横跨两岸的铁桥也显示出一派雄伟的气势。宽阔的桥面如同柏油马路一般,令人感到无比舒爽。
《大唐西域记》称这条河为“徙多河”,看来玄奘似曾走过。不过其中并没有莎车城的只言片语,也许是他穿越了河流却未入城吧。
关于莎车,还有一点我颇为关注,因为很多人的游记中都有该地附近居民颈上长瘤的描述。赫定也好,大谷探险队也好,在他们的报告中都有确切的说明。此外,大谷光瑞的《帕米尔游记》中有一段值得关注:
该地居民下巴下面长瘤者甚多。究其原因,赫定博士认为和不洁饮水有关,但我仍不敢妄下定论。
13世纪到此旅行的马可·波罗也曾有过类似的记载,并在七百年前就提出了“水质存在问题”的看法,看来这种病确实年深日久。
从英吉沙到莎车,只要透过车窗看到人影,我都会下意识地看他们的喉结周围,休息时看到的行人我也会往他们的颈部瞄上几眼。当我确定他们脖子上没有瘤后,方才放下心来。(其实并未真正放下心来。虽然过了莎车城区,但目前仍在其管辖范围内。)
我一边担心着碰到脖颈有瘤的人,一边又继续往车窗外面眺望。毕竟在莎车的维吾尔语“Yeken”中,“Ye”即土地,“ken”即广大的意思。所以虽然过了城区,但郊区依然广阔。
过了莎车河,我便放心了许多。那种数百年,或许延续了更长岁月的地方病应该不会出现了吧!
实际上除了关注他们的颈部外,我也会扫视一下他们的脚。虽然这样做有点儿荒谬,但这皆源于马可·波罗的奇妙描述:大部分莎车人的脚都是明显的一大一小,故而走起路来很不便。
颈部长瘤是近些年也时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双脚一大一小是怎么回事呢?莫非又是因患脚气而致使脚部肿胀?所幸的是,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脚掌一大一小的人。
吉普车开进了一个不起眼儿的街道,就像西部剧中出现的农村景象一般。
“这是泽普县,维吾尔语念作Poskam,是一个县城。”老阿告诉我。
穿过泽普,再次进入水田地带。我们俨然已经沉醉在这一半是田园、一半是沙漠的独特风光中了。
“快到了。”老阿看着手表说。
“快到了吗?”我也看了看手表,发现时间刚刚过了正午。其实,我们也正在靠近问题地点。
我本想着目的地近在咫尺,不料一条河流却横亘在眼前。河滩旁边是一处高地,正好遮住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绕过高地,谁知又被河滩阻隔。
在河滩边,未曾见过的一辆吉普车超过了我们。
“哈哈哈……能否渡河,就看前面那辆吉普车了。”老阿笑着说道。
虽然不知道那辆吉普车从何而来,但看起来好像是解放军的军用车辆。我们的两辆吉普车都放慢了速度,而那辆解放军的吉普车却开足马力驶向对岸,看那架势是想冲过去。
河对岸蹲着四五个维吾尔族大爷,似乎正在闲聊。看到吉普车阻在河中,他们便走了过来。为了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也向前开了一大段。
原来是上游的桥正在修缮,目前业已完成了三分之二。两三个小时内完成不了作业,但吉普车是可以临时通过的。
“如果现在无法渡河的话,也没必要再迂回三百公里,莫不如在这里悠闲地等待片刻,待桥修好后再走。”我想。
维吾尔族的老大爷和前面那辆吉普车的司机大声交流着,我全然听不懂。问后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这条河并不深。维吾尔族的热情每每令我为之动容,他们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并不求任何回报。
“太伟大了!”我不禁感慨。
“什么?其实热情好客是维吾尔族人的天性。”老阿告诉我。
我问老阿“好客”用维吾尔语怎么表达时,他告诉我说是“mehmandost”。听完后我豁然开朗,因为这是源于波斯语中的词汇,“mehman”是“客人”,“dost”是“朋友”,合在一起就是“友好”的意思。
我又开始注意那辆不认识的吉普车,对我们来说,它多少带有探路的作用。这时,一名维吾尔族老大爷已经挽起裤腿走入河中。河水看起来并不深,约莫刚刚没过他的膝盖。他在车前比画着说着什么,和他同行的人也都大声吆喝。
那辆吉普车发动后直接一股脑儿地冲入水中,将河水劈成两半。此时,三位老大爷站在河里,他们依然大声喊着什么,并指挥吉普车努力向对岸行驶。吉普车在他们的指导下顺利地过了河。
“漂亮!”我激动地说道。那辆未曾谋面的吉普车终于靠了岸并成功上路。既然那辆车可以,我们的车子想必也无大碍。
轮到我们了。
老司机艾拉夫打头阵。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刚才那辆车的冲天气势,但终究姜还是老的辣,车辆穿行河流如履平地,丝毫不逊色。我们这辆车的司机小吴看起来多少有点儿紧张。我坐在他的后面,发现他似乎几度耸肩。
“准备好,我们要冲了!”小吴说道。
车子开始前行,希望就在眼前。由于前面已经顺利通过了两辆,所以此次维吾尔族老大爷们并没有再指导什么。
车内的踏板渗进了水,但无论如何只要车轮转动着往前走就不会有大碍。我们通过了险阻,小吴也不再耸肩了,他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过了!”小吴说道。
我们的车子总算有惊无险地顺利上岸了。
02
我们走了五六公里的冤枉路。也许是他之前路过时没有注意到吧,驶离渡河地点三公里左右的时候,老司机艾拉夫觉得路线有点儿不对劲儿。于是,他向对面走来的维吾尔族青年询问叶城怎么走。
“你们走反了,叶城在那边。”维吾尔族青年告诉他。
老阿和艾拉夫听得很仔细,老杨虽然不是维吾尔族人,但也能听懂。于是,两辆吉普车随即掉头向右行驶。我们又回到了刚才的渡河处,便赶忙询问依旧停歇在那里的老大爷们。
“去叶城?为什么返回来呢?叶城在那边,就是你们刚才走的方向。”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从老大爷们的语调和手势我也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老阿和艾拉夫表情愤愤地走下车来,想再详细地确认一遍。问清楚后才知道,其实那名青年和老大爷说得都没错。
原来车辆应该在这条路前方两公里处左拐,但由于那条路比较狭窄,而且入口拐弯处又被茂盛的树木所遮挡,不仔细观察极易与其失之交臂。而我们正好没在意那个地方,所以走过头了,因此那名青年告诉我们往回转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他没说清楚,而我们也囫囵吞枣地听了个大概。
除了观察当地人的颈部和脚部之外,我也经常会观察他们的脸,发现他们五官都长得十分周正。为我们指路的青年也好,热心助人的老大爷们也好,他们的脸庞都呈现出了清晰的轮廓。根据1865年曾到此地做调查研究的罗伯特·肖的说法,叶城人本属于鞑靼化了的雅利安人种。在古代中国的汉族人眼里,包括通古斯人在内的塞外民族都被称为鞑靼。欧洲人眼中的“Tatar”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中国的鞑靼一般指蒙古裔,欧洲的“Tatar”指的是土耳其裔而已。
按照罗伯特·肖的说法,吉尔吉斯人属于纯种的鞑靼,而乌孜别克族则属于雅利安化了的鞑靼。因为鞑靼是古语词汇,所以日语中也已弃之不用,而是直接将西方语言中的“Tatar”音译为“タタール”。在新疆主要的十三个民族中就有鞑靼族,但他们都是近代化早期的土耳其裔,所以只能算是狭义的称呼,应该和汉民族广义的鞑靼概念区分开来。
如果我们沿着最初走错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便会到达昆仑山间的小城塔什库尔干。在《大唐西域记》中,塔什库尔干被称为朅盘陀国,玄奘从印度归来时曾路过此地。玄奘之前的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又将其称作竭叉国,并由此借道印度。看来,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南下印度的交通要道。
塔什库尔干大体相当于《汉书》中的蒲犁地区,如今已经成了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吉克族属于雅利安人种,而塔吉克语则和伊朗语近似。
车子在田间小道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又驶入平坦大路。只不过在小路上行驶的时候,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那辆吉普车不知何故掉进了沟里。
那条沟看着很宽,像是一条水渠,只是现在并非灌溉时期,所以渠中并没有水。如果有水的话,水渠上通常会搭一条木板。村民们向下走到这条斜度并不太大的沟渠之中,试图帮忙把车子推上去。而那辆吉普车也顺势先向下开到堑壕状的渠道中,然后加足马力打算冲上去,却没有成功。
村里人用铁索绑住吉普车,然后开来拖拉机牵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吉普车才冲上了沟渠。
“我想冲一下,大家先下来。”虽然前面的那辆车失败了,但小吴还是想努力强行通过。为了减轻车身重量,我们先下车,然后走到沟渠对面为他加油助威。
年轻的小吴一口气冲入渠道,然后又一口气完美地冲了上来。见此情景,聚集在旁边的村民无不拍手称赞。跟在后面的老司机艾拉夫一扫往日的沉稳,也一次性成功冲过来了。
田间小道的经历饶有趣味,令人难忘,那种场景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行驶到大路后,我反而有点儿恋恋不舍了。
03
下午1点半左右,我们到了叶城。喀什和莎车两地的城墙被拆除之后,交通得到了缓解,通风效果也明显变好,但叶城不一样,因为这里原本就没有城墙。
我们先来到了叶城县一家环境不错的招待所,当地接待人员安排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然后用午餐。
从行政区划上来说,这里属于喀什最东端,再往东就是和田地区了。虽说只是在这里中转,但从整个行程上来看,中午休息一阵已经算是停留了较长时间了。
“一路辛苦了,现在请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吃饭的时候我再来拜访您。”叶城县政府的穆沙耶夫主任和马福马德·史铁克副主任来这里迎接我们,并带来了热情的问候。
穆沙耶夫主任周到的安排让我充满了感激。已经走了七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穿越沙漠,因而我们身上就像是灌满了沙子一样。离2点左右的开饭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分好房间后,我先跑到阳台上迫不及待地拍打起衣服来。其他人也都在不约而同地做着同样的动作。虽然每个房间都有隔墙,但阳台却是连着的。旁边的阳台上,儿子也在那里拍打着衣服。过了一会儿,老阿微笑着出现在对面的阳台上,巧妙地将上衣挂起来。看着他拍来拍去,我不得不由衷地叹服久在沙漠的人,其拍打技法果然娴熟。
拍打完衣服上的沙尘之后,我走进洗手间,发现洗澡的热水已经准备妥当,这让人感到无比贴心。看完地图,我才惊讶地发现我们才走了整个旅行路程的一半不到,但已经风尘仆仆了。不管怎样,先用这一汪清水洗去一路上沾染的沙尘吧!
叶城在《汉书·西域传》中被称为西夜国,国王名为子合。公元401年法显去印度途经此处,在这里滞留了十五天,他的大作《佛国记》将这里称为子合国。《佛国记》中还说从于阗(和田)出发到此要走二十五天,而今天之内我们也将出发去往和田。当然,途中我们还得继续忍受风沙的肆虐。
桌子上的大果盘里摆放着西瓜、甜瓜、鲜桃、葡萄等各种水果。我吃了一块西瓜便躺在了床上。和之前在半道休息时因天气过热而索然无味的西瓜相比,这里的西瓜真是甜美无比,清凉爽口、沁人心脾。
终于到了开饭时间。饭前,先是一阵啤酒下肚,将肠胃都清理了一番。
不仅如此,接下来的烤串也让我们大饱口福。说实话,刚刚端上来的时候我还有点儿望而生畏,因为肉块实在太大了。乌鲁木齐和喀什的烤串切一刀就可以入口,而这里的肉串不仅连着骨头,而且有拳头大小,看起来似乎确实无法一口下咽。但尝了一口后我不禁为这样的美味拍手叫绝。虽说对美味的品尝因人而异,但后来谈论时,我们一行人都认为叶城的烤串最好吃。就连不善评头论足的老阿也说“这儿的羊肉可真鲜美”,看来这确实是他对美食的最高褒奖了。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羊肉,只有这样的羊肉才能做出这般可口的烤串。”彻头彻尾的美食评论家老杨用肯定的语调评论道。
说起叶城的肉,我倒想起一个故事来。在法显去世的一百多年后,玄奘出生的一百多年前,即公元519年,北魏有个叫宋云的人也曾到此。《宋云纪行》中曾提到于阗以西千里,莎车之南三百里有朱驹波国,我想必然是现在的叶城无疑。另外,《新唐书》中也有如下记载:
硃具波亦名硃具槃,汉子合国也。
依《宋云纪行》来看,当地五谷丰登,居民以面食为主,虽然也偶尔吃肉,但所食之肉大都来源于死去的动物。可见在一千四百六十多年前,当地人几乎是不怎么吃肉的。这也片面地印证了当时这里的人基本不杀生。
吃饭的时候,他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叶城的逸闻趣事。岁月的车轮转过了一千四百多年,不好杀生的当地居民也变成了烹调羊肉的行家,但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这里的农业依旧富庶如初。
只顾着将羊肉的鲜美大写特写了,其实这里的鸡肉也毫不逊色,而蔬菜更是合我口味。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自己已经吃撑了。
“出发时间大概在三点半到四点……”他们定了一下大概的出发时间,也可能是考虑到让我们能在饭后休息得充足一些吧。
04
出叶城之后,就意味着我们要告别喀什地区而踏上和田的热土了。
“接下来的沙漠可就是正儿八经的沙漠了。”代表喀什一路陪同我们的老杨的这番话,好像是在提醒自己故土渐远,他乡的天空就在眼前。
从叶城出来,沙漠的气息较以前确实浓厚了许多,但好在休息后我们的体力已经恢复,即便接下来将要经历一段辛苦的旅程,但想必也是有惊无险吧。
满是沙砾的荒野被称为戈壁,而颗粒细小的沙原就是通常所说的沙漠。从叶城到和田,一路上既有戈壁纵横其间,也有沙漠横亘千里。泛黄的沙漠中,灰色的大道笔直地延伸开来,仿佛直通天边。
旋风时而卷起黄沙冲向天空,时而裹挟沙粒形成沙柱在大漠中肆虐横冲。有时候,也会看到沙柱旋转着从吉普车前穿过。
“这个没事吧?”我有点胆怯,便不假思索地问起了司机小吴。
“我都是计算着旋风的移动而控制车速的,您就放心吧。”小吴告诉我。
“那都是小儿科,这里的龙卷风能卷起吉普车,不过现在是安全季节。”老阿说道。
“什么时候是危险期呢?”我好奇地追问。
“大概从三月到五月,这三个月的龙卷风十分厉害,可不像现在这样小打小闹的一样。”老阿补充道。
离开叶城两小时后,我们进入了皮山县境内。皮山县也就是汉代所谓的皮山国,维吾尔语音译过来即“固玛”。虽然我们行驶的线路距离县城还有些远,但沿路两旁的农家院落却零星可见。
我们决定在靠近农家的地方小憩一会儿。虽说是略做调整,但也许是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走得太久而渴望看到人间烟火吧,几户农家院落也足以让人放松身心。沙漠绿洲中的居民也经常外出踏上旅途,所以他们十分清楚旅客的心理。而他们热情的待客之道,似乎也是基于自身刻骨铭心的体验吧。
有农家的地方,街道两旁都栽有景观树。这些树不仅仅只有一排,而是两排、三排,甚至四排、五排地站立着。因为考虑到树荫可以为行人提供绿荫,所以面向道路的第一排都是白杨,第二排往后都是桑树。
老阿伸手摘了几颗桑葚,但没嚼几下就吐了出来。他感慨地说道:“桑葚已经熟过头了。还是五月好,那时候的桑葚比任何水果都好吃。”
这里的桑树并不是为了采食桑葚而栽种的,茂密而林立的桑树其实正在诉说着这里过往丝织业的繁荣。
丝绸之路沿线的居民总喜欢强调“我们也会做丝织品”,而沿路两旁的桑树似乎也给了他们最为有力的证据。当我们觉得这里只盛产原料时,当地人却予以了坚决的否认。这种否认透露着他们的自尊心,而自尊心又是能量的源泉。至今所看到的农业和工业如火如荼地发展,也许就是他们将无尽能量转化成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吧。
在树荫下,我们吃着穆沙耶夫主任精心为我们挑选的西瓜和甜瓜。因为只在车子里放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味道依然十分甜美。
忽然一阵毛驴的叫声传来,那种奇妙的“嗯昂、嗯昂”的声音,向我们传达出附近可能有人正在忙着农耕的信息。漫长的沙漠之旅后,这样的感觉着实令人怀念。此时,我也即兴吟诵出俳句一首:
夏食甜瓜果,
丝绸之路快乐多,
毛驴叫声过。
因为行程比较紧张,所以我们休息了十五分钟后便匆匆上路了。吉普车开始驶离皮山一带,再次向广袤无垠的沙漠出发。
有时候会看见一两户人家孤零零地坐落在沙漠之中,实在难以理解在这种生存难以为继的地方他们是如何度日的。那时,我就尽量将目光转移到整齐成排的电线杆上苦思冥想——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毛驴的鸣叫探知人们的生活气息,那么通过成排的电线杆也自然可以领悟到人类生活环境的无边无际。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无意中看见沙漠中一个身着黑衣的人突然倒在了地上。
“啊,中暑了……”我惊呼,然后催促小吴赶紧过去救他。但那个倒下的人又忽然站了起来。
“他是在做礼拜。”副驾驶上的老阿虽然目视着前方,但仿佛也觉察到了我的疑惑,所以特意解释给我听。
难道他是在向太阳祈祷?沙漠上空的太阳已经西倾,小吴和艾拉夫就像夸父追日一样纵情疾驰。这里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交警巡查,所以两辆吉普车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一路飞奔似的向东行驶。
在沙尘和暑热之间,必须忍受其中一种。也就是说对于到底要不要开窗的问题,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强忍沙尘开窗透气。虽然道路没有修整,但毕竟是用沙石铺成的,所以总强过满是黄沙的路。而且两辆车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以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扬沙的影响。我们的车子在疾驰中,后方会卷起沙尘,但前方绝不会浓烟滚滚,而前面的那辆吉普车和我们的距离刚好可以让他们激扬起来的沙尘稀薄很多。不过迎面驶来的车却会造成巨大的麻烦。于是,我密切注视着前方,一旦有车辆迎面驶来的话,我就会在两车靠近的时候迅速关窗。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迎面而来的多是运输货物的卡车。
05
“和田就在眼前,看看那些人的帽子就知道了。”老阿告诉我。
听完老阿的话,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发现戴着软绵绵的黑色帽子的人还真不少。看来即使是夏季,和田人也依然保持着这样特殊的习惯。
“可真是一派原始风貌呀!”我多少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
“在他们看来,太阳晒到头顶之前,其热气就会被羊毛吸收掉……确实是一种奇怪的逻辑。”老阿边说边摇头,可见他对和田人的风俗习惯也多有困惑。虽然同属维吾尔族,但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各处风俗习惯却早已发生了变化。
一路上,我已经习惯了沿途的剧烈颠簸。不一会儿,周围的景物也逐渐由大漠孤烟变为绿洲村落,水田也多了起来,看来和田也是一个水源富足的城市。对于西域诸城来说,其规模大小也许就是根据附近的水源流量决定的吧。
虽然已经过了九点,但暮色尚未西沉,前方的雄伟铁桥依然清晰可见。铁桥坐落在大河之上,桥这边的道路中央竖立着一个指示牌,上面醒目的箭头是一个右行的标志,下面用维、汉两种文字写着“道路施工,请绕行”的标语。
我们的吉普车按照箭头指示方向行驶,后来才知道因道路施工而多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和田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人到桥对岸迎接,只因天色渐暗双方都未曾注意,懊悔不已。虽然桥梁正在施工,但工事大体已经完成,除了载货的重型卡车外,吉普车通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多想,而只是机械地遵从了路标的指示。
从和田开来的欢迎车在桥对面,所以他们并没有看到指示牌,想着我们肯定会从桥上通过。过了好一阵子没等到我们,他们才注意到对面的绕行提醒,于是急忙打电话跟我们联系,然后重新派车从另一路迎接。这样一来二去,着实给当地平添了不少麻烦。
虽说我刚才写到因为多绕行了半个小时而有些懊悔,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有幸欣赏到近郊农村的样子,后来还为此兴奋了好一阵。吉普车的右手边,大约三米深的水渠正在灌溉,渠堤略高于路面。孩子们脱得精光,一个个从渠堤上“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痛快地游了起来,俨然一幅祥和的景象。
因为是乡间小路,有时候吉普车看起来几乎都快碰擦到左边的低矮房墙,那时司机会放慢速度缓缓行进,以至于路边的情景都能看清楚——这一家的老头儿坐在阳台上摇着团扇;可能是因为天热的缘故,另一家的老太太将炭炉搬到院子里,看样子正在准备做饭;有一家的母亲正在呵斥着自己的孩子;而另一家年轻的母亲正在哄着自己的宝宝入睡……女人的活动最引人注目,而她们也是平凡生活中的主角。
我们在看着别人,也有人在看着我们。特别是诙谐逗笑的顽童,吐着舌头做着鬼脸,说着维吾尔语,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真够顽皮的。”老阿说道,同时耸了耸肩,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其实,这里呈现出来的完全是真真切切、毫无修饰的生活场景,怎么都欣赏不够。虽说是无奈绕行,但沿途却毫无枯燥之感,毋宁说收获颇丰。
过了这条悠长的小路后在平坦大道上行驶了一会儿,我们便看见等在那里的和田接待方的车。
“是喀什地委的车吗?”前方大声询问着。
当地的车在前面引路,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在幽暗的道路上我们一路紧随其后。
途中,有一座小城灯火辉煌,而且街道林立,我以为是到了和田市区,后来才觉得那里应该是墨玉。
当我们终于来到和田地区招待所时,已经十点半了,从自喀什宾馆出发算起,我们已经走了将近十七个小时。除了中途休息了两个半小时,乘车时间差不多有十五个小时。
“真是辛苦你们了!”
我们坐车虽然比较疲劳,但开车的老司机艾拉夫和小吴要比我们辛苦很多。在叶城县我们小憩的时候,小吴一直在忙着修车,几乎没有休息。对于他们的付出,我无以言表。
“真是辛苦你们了!”我带着深深的感激,由衷地向所有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