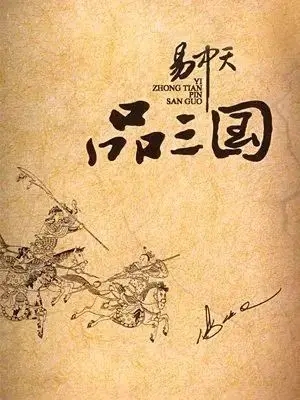01
玄奘并没有记载库木吐拉千佛洞的事迹,但库木吐拉千佛洞却留下了玄奘的印记,因为据说“唐僧”曾到过此地讲经说法。
在西域,要说起唐僧,大家都会想起玄奘。为了等待天山上的冰雪消融,他在库车待了整整六十天。据说当时的库车境内也有数十名高昌人修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寺院,玄奘就住在那里。大概是因为他觉得小乘寺院非己所长,而高昌人建造的大乘寺院才更适合自己的缘故。这里所说的高昌人就是汉人。
从第六十八窟到第七十二窟,五座洞窟由回廊连成一个整体,当地人称之为“讲经堂”,据说是玄奘讲经的地方。
这五座洞窟周围的布置和喀什的三仙洞十分相似,洞窟前似乎曾建有堂宇。方形的石孔分布在石窟周围,也许就是搭建的讲台,善男信女坐在台上,便可专注地聆听玄奘的讲释。当时的佛教圈通用梵语,那么,玄奘到底是用汉语弘法,还是用他擅长的梵语讲授,我们也只能揣测一二。
在第六十九座石窟的正面,“法轮常转”四个汉字勉强可以辨认。第四十二座石窟中除了有“南无□殊□利菩萨”(□代表残缺)几个汉字外,还有一些我们无法识别的龟兹文字。
唐朝立国之际,龟兹王遣使入长安庆贺。那时派遣使节并非是一种臣属关系的表现,而是想保持睦邻友好。
玄奘在离开天山南路的两年后,高昌王鞠文泰亲赴长安。他是汉人,所以国内民众对他前往中原并没有反对。同年,即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据史料记载,库车曾向唐王朝进献骏马,这大概也是托高昌王所为的吧。据唐朝文献记载,当时的西域诸国都想通过高昌王“遣使入贡”。唐太宗本想应允,但宰相魏征以“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之言劝谏,太宗只得作罢。
只是高昌王一人前来,唐朝朝廷就会花费大量钱财。虽然入朝者会带来贡品,但唐朝会回赠多于其数倍的财物,以彰天朝大国之繁荣。此外,每个随行人员也会收到赠礼,所以魏征觉得不应为塞外蛮夷劳民伤财。若入朝者有十国之多,其随行人员必有千余人。西域诸国若入朝献贡,一国随员就有百十人,这是普通定制。如果是商旅往来的话还好,但招待来使确实靡费过甚。况且大唐立国不久,民生多艰,不应以此来撑起国家的体面。唐太宗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接受了魏征的谏言,拒绝了西域诸国遣使入贡的意愿。
鞠文泰之父鞠伯雅于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入朝,受到了隋朝的隆重款待。所以虽然唐朝依据当时自身的国力对鞠文泰礼遇有加,仁至义尽,但和隋朝的礼遇比起来依然有天壤之别。
鞠伯雅入隋,是在日本使者持国书(国书开头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来中国朝见的前一年。
当时的隋朝正值隋炀帝当政时期,朝廷上下奢侈成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召集外藩诸王、首长齐聚洛阳端门街,欣赏盛大的杂耍表演。据说当时整个会场方圆八公里,从晚上到第二天清早一直灯火通明。坊市里的商品堆积如山,就连卖菜者的坐垫都是精美的龙须席(用龙须草编织而成的席子),街旁的风景树装饰着丝绸,在酒肆用餐也不用花钱。
对于用餐不用花钱的事情,衙门特意做了提醒,以此来向外邦炫耀隋朝国力之雄厚、谷物之充盈。其实在这些外邦骑马或坐轿来到洛阳之前,他们也看到过许多苍凉之景,洛阳的流光溢彩遮挡不了艰辛岁月中的贫苦大众,用丝绸包裹的景观树也掩盖不住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饥饿百姓。
虽然外国的酋长、使节都看穿了为这种演出所做的太平粉饰,但他们依然对隋朝倾力铺张中展现的国力敬畏由衷。回国之后,他们将隋朝令人惊叹的繁华景象传达给了国人。
二十年后,鞠文泰来到了唐朝国都。由于唐朝初期实行与民生息的简朴务实之策,所以他并没受到想象中的盛大礼遇,大唐的境况显然和他父亲口中的隋朝差之千里,也和当时跟随他父亲远赴朝阙的侍从所说无法相比。
“唐朝国力落后隋甚多矣,大可不必在意。”
鞠文泰心想。但是对于隋亡的原因,他却似乎充耳不闻。
十年后,高昌和西突厥结盟袭击了焉耆。虽然鞠文泰知道焉耆和唐朝的关系,但依然断定唐朝尚无实力向西域派遣远征军。然而注重实效而轻视浮华的唐朝在十年间到底积蓄了多大的力量,鞠文泰却一无所知,这注定了高昌即将面临悲剧性的命运。
高昌灭亡后,唐朝在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对其实行直接管辖。这样一来,焉耆的内外情势就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之前两国曾亲密无间,但由于高昌灭亡后唐军势力扩展到吐鲁番一带,焉耆开始对此感到惴惴不安。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也面临同样的境遇。
因为焉耆国王之女嫁给了西突厥重臣之弟,焉耆也相当于攀附上了另一个超级大国。为了强化和西突厥的同盟关系,焉耆甚至决定停止向唐朝纳贡。这种苗头被安西都护郭孝格发现,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亲赴长安建议朝廷采取强硬措施。
对于臣服大唐还是依附西突厥,当时的西域各国基本都分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派。焉耆因国王之女嫁到了西突厥,所以自然形成了一股亲西突厥势力,与之对立的是国王之弟颉鼻叶护和栗婆准等代表的亲唐派。后来亲西突厥派占据上风,亲唐派骨干担心受到迫害,被迫逃亡到唐军管控下的安西都护。看到这种情形,唐朝中央断定焉耆国内已经发生内讧,于是接受了郭孝格的谏言,决定出兵征讨焉耆。
02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郭孝格率军攻破焉耆,国王突骑支被擒,夫妇一同被送往洛阳。那一年,玄奘正在回国路上,正行走在西域南路的和田或者楼兰一带。
此时,龟兹承担了焉耆的后援工作。因为龟兹国内的亲唐势力微弱,西突厥的影响十分强大,龟兹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西突厥的属国。龟兹王派兵支援焉耆和唐军的战斗,唐朝和龟兹的关系也急剧恶化。
焉耆灭国过程中经历了诸多繁复的插曲。郭孝格俘虏了焉耆国王突骑支后的第三天,西突厥援军进入焉耆。郭孝格扶植亲唐的栗婆准代为摄政,但在西突厥的兵势之下,失去了援助的栗婆准政权也成了昙花一现。西突厥又随即选择了听命于自己的阿那支为王,并将栗婆准送往龟兹。栗婆准和龟兹国之间似乎曾有过什么过节,不久便被处死。
龟兹处死了亲唐派的栗婆准,唐朝和龟兹的关系因此雪上加霜。不过,唐朝此时正忙于征伐高丽,唐太宗御驾亲征,所以并没有立即发兵龟兹,也根本无暇顾及西域事宜。
其实在这期间,龟兹国内一直战战兢兢。三年后的公元647年,龟兹国王苏伐叠去世。他曾向唐太宗进献宝马,也曾在玄奘进入该国时热情相迎。对于苏伐叠,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评价如下:
智谋寡昧,迫于强臣。
也就是说他智谋短浅,为人暗弱无能,常常被实权派大臣所左右。
龟兹国以前王苏伐叠之死为契机,谋求缓和与唐朝的对立关系,所以将一切罪责都推到了已故的苏伐叠身上。同年,龟兹二度遣使向唐入贡。龟兹政权的继任者未免过于天真。高丽之战结束后,唐朝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并整合安西都护郭孝格所辖将兵,总计十万大军,讨伐龟兹。
阿史那社尔本为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有过和西突厥作战的经验。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归顺唐朝的阿史那社尔被封为左骁卫大将军,并迎娶太宗之妹衡阳公主为妻,唐朝对他的荣宠也由此可见一斑。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远征高昌之时,阿史那社尔便是其军中的一名主将。
当唐军兵进焉耆时,曾经迫害过亲唐派的焉耆王阿那支弃国逃至龟兹境内。唐军继而攻破龟兹,阿那支被俘后枭首。
龟兹国内以国王诃黎布失毕为首,宰相那利亲统大军五万御敌。两军在龟兹都城五百公里外的碛口展开会战,结果龟兹大败。龟兹人本想退守国都,但唐军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喘息之机。无奈之下,国王离开国都向西逃窜。阿史那社尔在占领龟兹城后,命郭孝格镇守此处,自己则率精兵追击龟兹残余势力,最终逼降了潜入拨换城的龟兹军。国王诃黎布失毕被掳,宰相那利侥幸逃走。
那利逃走后,借来了西突厥兵勇进攻郭孝格镇守的龟兹城。一时间,箭如雨下。郭孝格亲自率军在城外和那利军激战,而此时龟兹西门的战斗最为悲壮。顺便要说的是,当时西门有一座接近三十六米高的巨型佛像。表面看起来来势汹汹的那利军其实只是困兽犹斗而已,当三千名士兵横尸龟兹城下时,那利不得不下令撤退。即便如此,那利仍旧没有死心。后来他又集结了北山地区的龟兹人万余众,再一次发起攻袭龟兹城的战斗。此次战斗,那利军惨败,军士死亡八千余人,他单人单骑仓皇鼠窜。可笑的是,这次他并没有那么幸运,那利被生擒并被送到了唐军阵前。
就这样,龟兹成了大唐的势力范围。阿史那社尔奉命拥立龟兹王之弟叶护(并非人名,而是官职名)为新王。此人缺乏统御全局的能力,导致后来的王位纷争此起彼伏。无奈之下,唐朝将俘虏的前王诃黎布失毕及宰相那利等人送回了龟兹,让其重掌朝政。
唐朝拥立的焉耆国王婆伽利死后,焉耆民众向唐朝请愿,希望焉耆也能像龟兹一样迎接前王突骑支复位,唐朝中央政府准许了这一请求。此事发生在唐太宗驾崩之后,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
复位之后的龟兹王于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赴长安谒见。然而,留在龟兹国内的王妃阿史那氏和宰相那利趁机私通,龟兹国内的派系斗争也因此持续不断,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都分别派遣使者到长安游说正名。
对此,唐朝命那利到长安澄清此事,趁机抓捕了他,并将龟兹国内的军权交给国王诃黎布失毕。然而,那利一派的大将羯猎颠勾结西突厥,阻止了国王还朝的计划。国王被困在龟兹东边的泥师城,进退维谷。见此情景,唐朝派左屯卫大将军杨胄率军救援。此时,虽然国王已死在泥师城中,但杨胄还是借机消灭了羯猎颠一党,并立诃黎布失毕之子素稽为新王。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唐朝将泥师城改名为龟兹都督府,让龟兹王素稽兼任都督一职。
同年五月,唐朝将设在吐鲁番交河城中的安西都护转移到龟兹。自此,唐朝管辖西域的中心向前方推进。
武则天统治时期,有人曾以“沙碛荒绝”为由建议废除安西都护府,但并未获准。
03
安史之乱期间,大唐的西域经略受到了严重影响,但西域都护府却未曾中断。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北庭都护府因吐蕃的攻袭而覆灭,节度使杨袭古携残兵败将逃到了西州(即吐鲁番)。后来他想重整旗鼓,夺回北庭,却不幸又遭惨败,后被他的同盟颉干迦斯出卖而死。
在这种背景下,龟兹境内的安西都护府也和唐朝失去了联系。至于安西都护府何时被撤销尚无可稽考。吐鲁番也好,龟兹也好,就连攻占它的吐蕃也好,都没有留下相关记载。
在公元790年之前,安西都护府还存在。照此粗略算来,安西都护府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在这期间,唐朝以龟兹为中心西越帕米尔,极大地扩充了国土范围。后来和西方大国阿拔斯王朝的战争,也是以龟兹为后勤据点。高丽出身的大唐将军高仙芝,也曾多次来到这里。
纵观安西都护府的百年历史,无不是以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来辐射四方的。虽然后来在政权更替下,昔日的繁华迹象已经难以寻觅,但仍有不少精美的石窟壁画被保留了下来。
佛教经西域传入东土,来自西方的因素自然凝结成了其中的主流。正如人们经常谈论的那样,比起敦煌,库车周边的石窟壁画更具浓厚的巴米安风格。此外,相比印度、伊朗的影响,克孜尔千佛洞中的壁画风格更有欧洲的韵味。比如,大谷探险队所盗、如今收藏于东京博物馆的著名佛像画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话说回来,成型于唐代的石窟壁画仍然留有很多“唐风”,所以也有专家认为相比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石窟群的“唐风”更明显。
东西绵延约两公里、拥有二百六十个石窟的克孜尔千佛洞和库木吐拉石窟群一样,都位于渭干河旁边。两者水路相距十五公里,当地人分别将其称为“上千佛洞”和“下千佛洞”。
十五公里并不算太远,但水路可能会因季节影响而无法行舟。如果驾车翻山越岭从库车县城到克孜尔千佛洞则需两个半小时;要是骑马驾驼,就要走上三天左右了。相比较而言,县城到库木吐拉石窟群就近很多,一天之内便可到达。
克孜尔千佛洞和库木吐拉石窟群相比,后者受唐文化影响更为明显,这可能和其所在国的国都距中原较近有关系。
镇守龟兹的安西都护府有三万唐军,汉族人居多,但未必没有其他民族。不过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唐文化的代表,而他们的文化所波及的范围正好涵盖了一天之内所能到达的地方。
文化是否会带来影响,其影响是大是小,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其判定结果会因人而异。
佛教自西向东传入中原,龟兹就是其中的一个中转站,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后来自东向西的文化传播。比如,吐鲁番盆地出土的维吾尔语佛典就不是由梵语直译而来,而是由汉语译本转译的。此外,如果说壁画之中有唐文化影响的印记,那么这也算得上是对佛教美术的一大补充。
佛教壁画中,似乎佛本生(梵文音译为“阇陀迦”或“阇多伽”等)题材最多,主要讲述释迦牟尼佛前世的各种经历。此外,包括死后舍利分配在内的释迦牟尼佛生平故事及说法图,天宫伎乐图也不在少数。佛本生故事是种十分优秀的说话文学,其中有许多内容相同的故事都是通过佛教传播的,即从印度经中亚,然后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这种超越语言和民族差别的文学题材,已经为我们所共享。
我们在石窟中看到了一幅久违的佛本生故事图——舍身饲虎。舍身饲虎图在库车近郊的石窟壁画中较为多见,和日本玉虫厨子[玉虫厨子:厨子,即佛龛,乃安置佛像、经卷的器具。玉虫厨子是安置于日本法隆寺的飞鸟时代佛龛。因其装饰有玉虫之翼,故称之。]上所描绘的图案也颇为一致。在干燥的西域,确实可以发现一些文化传承的纽带。面对这些壁画,也许还会有人回想起我们的祖先阅读龟兹人鸠摩罗什汉译佛典的场景吧。
在风土人情迥然不同的地方发现共有的文化标识,着实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这种文化标识中,隐含着人类深层次的共性追求,而这种共性联系又必然成为深入探讨地域性特征的契机。
04
沿着苏巴什古城一直向北走,就会进入山中,然后再驱车五个小时左右,便会来到一个叫作“龙池”的地方。龙池分大小两个,其实并不是什么历史遗迹,只是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有所提及,所以我们才不惜路远,驱车一看的。根据玄奘所说,大龙池中有多条蛟龙,其变身之后和雌马相交,然后生下龙驹。“龙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这个故事有力地表明了库车自古就是宝马良驹的产地。
关于龙,库车境内还有一则传说。一般人无法骑乘龙和马所生的龙驹,当然更没有驭龙的本领,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如此。
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
我在前面已经提过,据学者冯承钧研究,唐史中的“苏伐勃驶”的龟兹语为“金花”的意思,他很可能就是龟兹王苏伐叠的父亲。在大唐建国伊始,他便率先入朝敬贺。
在“金花王”苏伐勃驶去世之前,他鞭触龙耳,龙因此而潜隐起来,以至于今日仍未显形。
凡圣贤之人才能驭龙,平庸无能之辈会有危险。苏伐勃驶也许觉得自己的儿子并非明君圣主,所以他有意在自己归西之前让这条可能伤及儿子的龙潜藏起来。他的儿子正如玄奘所说,是一个缺乏智谋却听信权臣、胡作非为的君主。
我想,玄奘在龟兹待了六十天后,他先穿越天山,然后西行再绕道向北,而龙池位于库车正北方,因而他应当未曾亲身到此,他的记述也应多为传闻。龙池周围本来有城,玄奘到达时早已成为荒凉之地,杳无人烟。对此,玄奘记载如下:
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构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一半取自传说,一半依据史实。其中,说当地人是龙和人的混血,这不足为信,他们勇敢强健倒是毋庸置疑。现如今我们透过车窗还能看见骑马挎枪的人,他们并非军人,而是当地普普通通的居民。龙池周边都是吉尔吉斯族的聚居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除了从事游牧之外,还以狩猎为业。古时候,龙池周边的居民经常绕行大山,因此他们的腿脚十分灵便,性格也比较彪悍。
所谓“不恭王命”,就是龙池周边的勇悍居民不服从王权政治,或者是他们被反国势力利用了。
龟兹王苏伐叠昏庸无能,连父亲都不敢将自己的御龙传给他,他也没有实力去征服那些不服王命的龙池居民,而只能借助突厥的力量将其赶尽杀绝。出兵协助的突厥,当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玄奘过境之后,龟兹曾向太宗进献宝马,那时的两国关系还算不错。但后来安西都护郭孝格讨伐焉耆时龟兹暗中相助,这也成了龟兹自取灭亡的导火索,而龟兹的所作所为很可能是西突厥在背后作梗。国王对西突厥俯首恭顺,也许就是因为当时西突厥在镇压龙池居民中有助力之功吧,那时的龟兹俨然是西突厥的臣属之国了。
大龙池美丽洁净,水底的绿藻清晰可见。
虽说惯于游牧的吉尔吉斯族多住在“包”中,但这里却以平房或砖瓦房为主,我们在这里品尝过羊肉、黄油、乳酪等美食。他们的烤串并不是直接放在炭火上烤,而是要离火三十厘米左右,不停地转动,主要依靠热气和烟熏来烤。这样的烤串确实与众不同,别有一番风味。
大龙池海拔两千五百米,氧气比较稀薄,所以观赏时不要急于奔走,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需要去克服的事情。
从库车县城到这里有五个小时的车程。山路行车虽有些辛苦,但沿途的景观却足以慰藉人心。当看到用汉字书写的“红崖”时,我还以为这里的山体都是绵延的红色,但实际上山峦通体都是绿色,只是没有草木的痕迹罢了。此外,还能看到一些小型的露天煤矿。
库车周边矿物资源丰富,玄奘就曾说这里盛产黄金、铜、铁、铅、锡等物。如今那锋利的“库车刀”依然名声不减。由此看来,大龙池周边居民和国王之间之所以发生冲突,也有可能是为了争夺矿产资源。
安西都护终止于何时尚无法断言,但应该是在公元8世纪的最后十年。而且与南边的藏族(即吐蕃)势力有关。
在这之前,西域东北地区的强大势力突厥分裂成东西两支,因而也失去了绝对霸权,其支配下的各部族于是纷纷自立。这期间,维吾尔族在西域强盛一时。
05
公元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借助维吾尔族之力平叛。刚开始维吾尔族被称为“回纥”,后来他们不大喜欢这样的称呼,唐朝便改称其“回鹘”。曾经挽救过大唐危机的游牧民族回鹘,最终也没有逃脱历史的周期定律——内讧。后来,吉尔吉斯族取而代之,成为雄霸蒙古草原的主人。
吉尔吉斯在唐初被称为“结骨”,后又改为“黠戛斯”。公元840年,吉尔吉斯十万大军急袭了回鹘,回鹘不敌,其中十四个部族向南逃走,十五个部族向西流落。后来,西去的部族赶走了天山南路的吐蕃势力,成了那里的新主人。
当然,吐蕃内讧也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宫廷政变导致吐蕃赞普(西藏藏王)朗达玛被杀,吐蕃因此开始飘摇。敦煌壁画中的张义潮就曾驱逐敦煌当地的吐蕃势力,在公元851年被唐朝封为归义军节度使。
西去的回鹘军控制天山南路,这发生在公元865年前后。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于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奏报朝廷:
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槙等城。
西州即之前的高昌,也就是吐鲁番盆地一带。他的奏报中虽然没有提及龟兹,但轮台就位于焉耆和龟兹之间。
就这样,西域迎来了维吾尔族统治时期。维吾尔族中的摩尼教信徒很多,但西域各地的佛教依然强盛。龟兹附近的也好,吐鲁番柏孜克里的也好,都是维吾尔族统治时期建造的石窟。
维吾尔的国都是高昌,还是高昌以北的北庭,史学家还没有定论,因为他们没有书写本国历史的习惯,留下的史料少之又少且不足为证。唐朝和五代之后的宋朝将其称为高昌回鹘或者龟兹回鹘,可见该政权有可能是种部族联合体。
维吾尔西边,土耳其裔的喀喇汗王国开始崛起,西域的喀什、莎车、和田都先后纳入了其统辖范围。12世纪时,天山南路进入西辽版图。西方人称之为喀喇契丹王朝。不过,喀喇契丹王朝对当地的统治仍然是游牧式的,即只要收取了税负,其他的内政一概不管。虽然本朝王室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但并没有干涉天山南路的伊斯兰教信仰。除了收取税负,他们似乎对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这为后来西域的彻底伊斯兰化埋下了伏笔。
13世纪,是成吉思汗叱咤风云、四处远征的时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仿佛就是一个世界帝国,他们对宗教信仰也异常宽容。虽然本民族似乎以信仰摩尼教为主,但并没有强制推行宗教一体化。
对于西域来说,他们乐见元朝这个世界帝国的出现,因为强大的政权可以保证交易的安全。此外,蒙古国内人才匮乏,在经济方面,他们常会任用西域人,这一点对西域也是一种恩惠。
元朝之后,帖木儿时代开启,西域在此时陷入了沉潜期。相比陆地,航海技术的发达让东西交易大多选择在了海上。
19世纪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崛起之际,西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沙俄连续征服了中亚的伊斯兰王国,并本能地图谋南下。企图控制印度的英国,又想阻止沙俄南下的步伐,两大帝国主义势力暗中较劲儿。此外,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占清朝领土,一度占领了西域南北两道。清朝虽然想平定阿古柏之乱,但远征军的出发却不及时。由于东南部的台湾风云又起,清军不得不先对付以西乡从道为都督的日本军队。虽然清军后来平定了叛乱,但却因故拖延许久,作为列强中的一员,日本的行动间接影响了西域的政局。
后来,沙俄以动乱为由趁机占领了伊犁地区。在平定了阿古柏叛乱之后,沙俄虽然撤兵,但根据《伊犁条约》规定,伊犁的一部分领土并没有归还给清政府。
月氏迁移、张骞行旅,或许可以说是军队远征、佛教未兴的时代;法显、鸠摩罗什以及后来的玄奘取经是佛教兴盛的时代;然后又经历了伊斯兰化席卷的时代……西域演绎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迁。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域地区迁移不断、融合不断,民族和语言也都在更替中摇摆向前。然而,在西域这条历史大河的底部,还有许多永远不会改变的细流,就像是塔里木河一样,它的根源将绵延不断地在地下悄然流淌。
这一片超越了宗教、民族、语言的西域就像当地守护神一样充满着力量,生生不息。而接近她、感知她,才能让我们体验到发自内心的激越和欢愉。
从东向西,又从西到东,新的文明流入然后又回流。
文明为何物?来到这里,就会面对这个问题,但似乎又不用刻意寻找,因为西域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无限遐想的空间和足以共振的灵感。这里让人们向往,让人们留恋再三,也将吸引世世代代的人们来此探究解疑。
西域包罗万象,诸如人的喜悦、悲痛、欲望、信仰……
在我们面前,她如今依旧风采依然,广阔无边。在鸣沙声中,仿佛正透露着极富魅力的问题和隽永深沉的答案。
最后,我愿以小诗一首来结束此文。
葱岭行
故城重叠对苍穹,葱岭连云映彩虹。
一带流沙人世外,三仙石窟在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