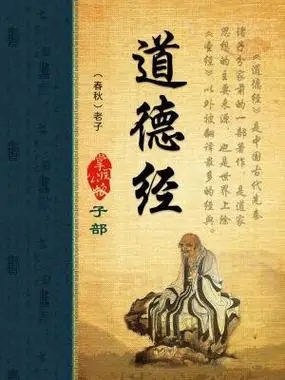01
喀什既是两个文化圈的交汇之处,又是西出帕米尔高原的起点,从帕米尔高原一方来看,这里又是崇山峻岭的终点。这种包含多重特征的地方,带给人们许多难解的神秘。
三仙洞位于喀什市西北十八公里处。和其他地方的石窟大多建在河两岸的崖壁上一样,这里的石窟也都建在恰克玛克河岸边。我10月份到访这里的时候正值枯水期,恰克玛克河河水很浅。站在河滩仰望三仙洞,只见洞窟位于绝壁之上,离地大约四十米,没有工具断然无法攀行其上。即使使用梯子,也必须多个相接方可,着实危险。过去曾有身轻如燕的年轻人借助悬梯攀爬上去,但近年来几乎无人涉险。
三仙洞的开凿年代据说是在公元3~4世纪。洞如其名,直立的崖壁上只有三个小小的石窟飘零孤悬。石窟群又通称千佛洞,大概是因为洞窟众多的缘故。千佛洞的维吾尔语是“Ming Öy”,即“千间房屋”的意思。而三仙洞只有三个洞窟,当然不能冠以千佛洞之名了。
三窟之中,左侧的石窟有壁画但没有供奉佛像;中间的石窟壁虽然已经被涂成了白色,但没有壁画,只有下半身佛像残留安放;右侧可能是个僧窟,里面空空如也。
在一千几百年前开凿这座三仙洞时,绝壁悬崖断然没有现在这么高,因为悬崖下靠近河滩的地方,肯定经过了严重的冲刷。若如现在这样,石窟断难建成。石窟的正下方有许多方孔,是专门夹塞木料的地方。因为最开始时,石窟前也曾建有堂宇。三仙洞中间的那座石窟壁被涂成白色却没有壁画,由此可以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个中途被放弃而未完成的石窟。据说20世纪40年代时,三仙洞对面的几处石窟因河流泛滥而惨遭毁灭。三仙洞附近还有三个小石窟,但每个石窟只开凿了洞孔,里面一无所有。这也可能是在营造途中因故被搁置使然吧。
作为佛教盛行的土地,现如今所剩遗迹屈指可数,让人看来极为孤独。1906年,二十八岁的保罗·伯希和来到喀什三仙洞。他雇用了很多人,后来发现绝壁石窟内空间较小,只能屈身进入。通过勘察,三座石窟内部相通的事实得到了印证。
玄奘取经返回时曾途经喀什。喀什在汉代时被称为疏勒,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称其为佉沙国,《新唐书》中疏勒、佉沙同时出现。不过,新旧《唐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
俗,祭祆神。
看来新旧《唐书》是把喀什当作了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国家。对此,玄奘又有另一番体验,他认为喀什是信奉小乘佛教的国家:
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虽然喀什也有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但通过实际见闻而发此言论的玄奘之说应该可信。玄奘也好,新旧《唐书》也好,关于喀什,他们都有“文身绿睛”的记载。看来这里的人喜好文身,而且都长着碧眼,给人以十分野蛮的感觉。不过,如今的喀什居民好客温顺。
玄奘之后,西域进入了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时代。所以说起西域历史,我们更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审时度势。据《隋书》记载:“(疏勒王)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即不育。”真是十分奇怪。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疏勒王裴国良亲赴长安谒见,后被授予折冲都尉,赐紫袍冠带。
虽然东汉时代的疏勒城并非佛教遗迹,但也是喀什市东南方仅存的历史遗产。
葱岭,即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易之道,也是佛教传来之路。然而,这里却没有留下任何佛教遗迹。法显和宋云都曾路过这里,玄奘在取经归来时也曾穿越葱岭。当时葱岭中的朅盘陀国就是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北魏时期,西域九国前往平城朝贡,其中就包括朅盘陀国。总体来说,朅盘陀国扼守东西交易的利害。
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记录如是。这里和喀什一样,都是佛教国家,而且都信奉小乘佛教。
如今,塔什库尔干地区主要是塔吉克族。他们是雅利安人后裔,这在新疆也不多见。他们使用的语言并非像维吾尔语那样的土耳其系,而是属于印欧语系。
公元9世纪上半叶,西域地区的居民还都在使用吐火罗语,其土耳其化源于公元9世纪后半叶。那么吐鲁番、库车、喀什等地先前的“胡人”都去了哪里呢?其实,这里的民族迁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以融合的形式产生了变化。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家就将这里称为土耳其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即土耳其裔的居住地之意。不过,居住在帕米尔山中的塔吉克族避开了土耳其化的影响,这一点在语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另外,他们还吸收了一部分来自塔克拉玛干以北的移民。
西域的民族大迁移也带来了宗教上的变革。11世纪初,维吾尔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喀什市以东约三十五公里的罕诺依古城遗址就是喀喇汗王朝某些君主的驻跸之地。除了建筑物的土基还依稀可见外,已看不到任何称得上是文物的东西。不过,这座遗迹却是西域由佛教圈转换为伊斯兰教圈的见证者。据说,用土耳其系语写成的最古老的文学作品《福乐智慧》(优素福·哈吉)就于1069年成书。
总而言之,佛教就退出了西域的历史舞台,留下的只有曾经辉煌的遗迹。如今我们很难在西域探寻到佛教的遗迹,大概就和当时的信仰更替息息相关。
帕米尔山中似乎没有修建石窟,或者说尚未被发掘。因为只有石窟才残留有佛教的遗迹,所以要在塔什库尔干有收获,当然是天方夜谭了。
塔什库尔干县城并没有城墙,宽阔的马路两旁的政府机构、招待所、电影院或运动场等并排林立。不过在县城附近,却有一个古城遗址。
02
西域最为奢侈的东西就是土地的使用。自家房子也好,村落也好,甚至是被称为县城的稍具规模的地方也好,只要陈旧一些或者感觉住得不舒服,他们就会果断地放弃,另觅新所,频繁地更换住地。不过,因为古时候都要修建城墙,所以住地并不会出现随意更换的情况。那时候他们要么用城墙将城市围起来,要么将居民收容到城堡之中,而塔什库尔干——古代的朅盘陀国应该属于后者。既然搬家不易,那么干脆将所在的城堡多多加固、加高。
可能是担心敌人来袭,所以他们才将城修得很高,或者是直接利用山势。如今塔什库尔干县城附近的古城遗址就是一座用土、石在平地上建起来的高城。《大唐西域记》对此解说如下:
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
在我看来,这座古城似乎并没有因势利行。后来当我问过当地文物管理所负责人后才知道,现在的古城遗址表面是六百年前增建的,表层下面还有更加久远的痕迹,而且分属多个时代。代代增建加高,才有如今的这个样子。
站在高大的城堡上,周围境况尽收眼底,如果敌人来犯,也可提早侦知。因为这座古城跨越了整个伊斯兰时期,所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遗迹。这座城同样在告诉我们,人类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下获得生存,就会努力发挥自己无穷的智慧。而我们参观这处遗迹的最大收获,也在于感受这份执着的努力。
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曾经商旅留宿的住所被当作历史遗迹保存了下来。以前的驼队一天内行进三十公里左右,所以大约每隔三十公里就有一处砖瓦改成的宿处。虽然是遗址,但也不到百年。其实这些居所都经历了好几个时代的增补。驼队商旅的住处必须有水草,而在西域,这样的地方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即使原始的居所已经残破,而新居也必建在原址上。由此推测,最早的商队居所应该跨越了千年的烟云。
玄奘将经文放在象背上经过此处,不想遇到了山贼。山贼出没,也印证了这里的商旅行人往来频繁。那么这里当时就必然已经有了专供行路人休息的居所。
游牧民族的帐篷也可以称为“居所”,但帐篷多用毛毡制成,而行旅商队所住之地一般都用砖瓦砌成,无法移动。这些固定居所可以容纳三十人横躺着,并有做饭的地方和排烟孔。如今我们都是坐车穿行,自然无须入住这些居所,但这些居所顶部的烟囱就像交河古城中普通民众家中的灶台一样,使人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气息。
当在遗迹中感受到这些生活气息的时候,我们脑海里的某种固有历史观似乎在不经意间开始动摇。
法显和宋云从莎车进入喀什,玄奘则是西出喀什前往塔什库尔干。这一段路上被皑皑白雪覆盖的高峰多在七千米以上,有时令人畏惧,有时令人神驰。
玄奘遭遇山贼后,驮着经文的大象受惊逃跑,溺亡在盖子河中了。回到长安后,玄奘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弟子,弟子们随即记录了下来。当我们来到盖子河畔时,不禁联想起了一千三百年前的这段往事。被记录下来的有据可寻,那么一路上未经记录的浪漫和悲凉还有多少呢?
03
我们将话题暂时拉回到库车上来。鸠摩罗什随吕光军队东行后,当时的龟兹国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具体细节实不可知。
吕光拥立的白震成为龟兹王,开始治国理政,那么逃亡的前王白纯行迹如何呢?和西域诸国一样,龟兹也没有书写本国历史的习惯,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其中的细节。
西域各国和中原王朝的接触在那时也比较频繁。比如,北魏太延元年(公元435年),西域九国遣使入朝,龟兹便是其中一员。但好景不长,后来北魏讨伐焉耆,龟兹再次被卷入战火。短暂的光明之后,黑暗再次来临,对此,我们不妨继续探索。
中国史料记载某年某国朝贡之类的事情较多,但对某地的佛教变迁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三藏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关于龟兹记录如下: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读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愕然。就在玄奘到此之前的两百多年前,龟兹有一位高僧大德鸠摩罗什,他专攻的应该是大乘佛教。在鸠摩罗什的影响下,该国大乘佛教盛极一时。但据玄奘的记载,鸠摩罗什离开龟兹后,这里却成了小乘佛教的天下。莫非是该国后来又出了一位杰出的小乘佛教高僧?其中原委,我们着实难以参透。
虽然玄奘说龟兹信仰小乘佛教,但龟兹周边的石窟壁画多以《佛本生经》故事为主题,带有浓厚的大乘色彩。而一向被认为是尊崇大乘佛教的高昌却出土了小乘经典《杂阿含经》,让我理不清头绪。
玄奘来到龟兹时,周边各地的石窟建造已经风生水起,但《大唐西域记》中却没有关于石窟的只言片语。莫非是他将石窟算在“伽蓝”之中了?即便如此,他也应该对石窟中的曼妙壁画心有所感吧?然而即便他后来在印度看到过阿旃陀石窟中的壁画,但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着实令人惊诧。
《大唐西域记》中的昭怙厘伽蓝就是距库车县城二十公里的苏巴什古城,如今已是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城墙外残留的全都是寺院的遗迹。想来城外是以伽蓝为中心的,而给寺院供给物资的商人或者工匠的住所都规划在城内吧。“接山河,隔一河水,有二伽蓝”的地形,除了苏巴什古城别无其他。所谓“一河水”就是指库车河。流经库车以西的渭干河又叫西河水,而库车河正好与之相对,又名东河水。西河水中有一座巨塔的残破遗迹,据辨认,塔上有壁画的痕迹。如今为了保护巨塔,专家正在对其进行修复。东河水边的情况基本大同小异,只不过那里的圆屋顶建筑较多。
由于库车河季节性涨水时很难通行,有时只能到西河看看。据说比我们一行早两个月的樋口隆康先生就没到东边的库车河畔。我们十月份到这里正好适逢枯水期,所以乘坐的小汽车轻而易举地便穿过了库车河。在参观完回去时却不幸陷入河中动弹不得,幸亏同行的吉普车用绳索牵引我们的车,才得以脱险。
我们所看到的西河周边地势开阔平坦,发展空间无可限量。但东河对面还有一条河流,两河相夹形成地理位置上的制约。依我看,苏巴什古城并非是因为扩张而形成的两座佛教城市,而是刚开始营建的时候就横跨了库车河两岸。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我想这是支配水流的需要吧。
在西域,有水就有了一切。没了水,人们就得离开原来的土地迁往别处安居。除河水外,那种通过人工水渠收集高山融水的“坎儿井”也有很多。据说古时候,这里的人有了钱就会投资修建坎儿井。有钱人一般既是地主又是“水主”,而贫苦的农民只有将仅有的一点儿钱拿出来从“水主”那里买水。如果说大寺院同时也是“大水主”,那么他们修建“跨河伽蓝”就不足为奇了。
在离苏巴什古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规模浩大的人工水渠。这条水渠并非像坎儿井那样埋在地下,而是用于灌溉农田,被称为“林基路大坝”。林基路是这条水渠的督造者,广东省台山县人,年轻时曾留学日本,1938年归国后赴任新疆。他出生于1916年,当年主持修建这条水渠时刚满二十二周岁。后人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条水渠。他在新疆工作了五年,于1943年受刑而死。
当时,盛世才在新疆几乎手握独裁大权,因为有苏联在背后撑腰,他一手遮天。当纳粹德国以势如破竹之力横扫苏联时,盛世才觉得苏联将难以依靠,于是对国民政府的态度由蔑视对抗变为百般讨好。为了向国民政府表达归顺之心,他派人将驻守新疆的三名中国共产党干部逮捕杀害。这三人分别是陈潭秋、毛泽民(毛泽东之弟)和林基路。
乌鲁木齐郊外有一座烈士陵园,三位烈士的墓碑赫然屹立其间。墓志由董必武题写,每个人的生前事迹都分别由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四种文字写成。这样的安排也充分体现了新疆的文化特色。
在新疆期间,共产党员林基路致力于将“大水主”手中的水收回到政府手里,然后由政府统一调配给农民。林基路大坝就是为了不让水渗透到地下,特意用石头铺设而成的水渠。
在维吾尔语中,“Su”为水,“bashi”为“头”。“Subashi”(汉语为苏巴什)这一地名在新疆随处可见,意为“水源”。从塔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通往喀什的路上,有海拔四千七百米的苏巴什山,翻越者必须体检合格后方可通过,以防高山缺氧。
玄奘所说的“昭怙厘伽蓝”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水源地,这一点从寺院跨越河流两岸便可知晓。我觉得寺院的水源应该和它旁边的林基路大坝一样,多数情况下都是向民众开放的。佛教之人讲究慈悲为怀,这么做再正常不过了,只不过我对自己此次的推测不十分自信。
西河水中的巨塔还残留着依稀可见的壁画,这一点我前面已经提过,但在1978年的时候,有人在这座塔的下面发现了古墓。据说墓穴当中有木质棺架,棺架上摆放着一副双重棺椁。当然,我们到的时候墓中之物早已被搬离,看到的只是空空的墓室。
04
棺架的木材被送到了北京的一家科学院,经过科学手段研究证实,古墓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也就是说这座古墓早于唐代,在北魏以前。
棺内的尸骨头枕北腿向南,几乎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但墓主人的身份却无从知晓,有可能是建造这座塔的和尚。由于墓室窄小寒酸,也有可能是为祭祀巨塔落成而被活埋在水下的人的墓。颇为引人注意的是,死者的头盖骨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头盖骨因前后受到挤压而呈扁平状,并非死后外力所致。如果是死后才受到挤压,那么头盖骨就会破碎,很明显,生前就已如此,就是在头骨还比较柔软的幼儿期就受到木片之类的东西前后夹封,是一种人为的畸形化。这可是一大惊人发现,因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库车的某种风俗就有所记述:
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 也。
“匾㔸”即扁平状。这真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风俗。此外,中原地区从宋代开始就让女子用布裹足,也算是奇事一件。难道是将头前后夹封后的扁平模样更能体现气宇轩昂?玄奘不仅提到了库车,喀什也是如此。在到这座古墓之前,西域地区的相关史料或者实物无法印证这样的风俗是否存在。库车有数百座石窟,石窟中的壁画更是不计其数。壁画中的人物都穿着库车当时的衣服,体现出一种写实的风格,但却没有一个头部畸形的画像。就连在超强立体感的塑像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特例。这种习俗其实也并非玄奘亲眼所见,而是采信了当地的传闻,以至于后世怀疑这种奇习是否真的存在。然而,这座古墓的出现,彻底证明了玄奘记载的真实性。
离龟兹古城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伽蓝都市,和王城保持了不远不近的距离,这让我想起了平城京和比睿山延历寺的关系,或者说这体现了一种王佛分离(即王道和佛道分开)的关系。
僧徒清斋,诚勤励。
对于这里的僧侣研习小乘佛教并严守戒律的情形,玄奘给予了肯定。
苏巴什古城的维吾尔语写作“SUBEXI KONA XӘHIRI”,但玄奘并没有将其称之为“城”,而是以“伽蓝”之名谓之。《大唐西域记》在讲述完这座伽蓝的故事后,紧接着又说了“大城西门……”要知道,这里的城并非是指苏巴什古城,而是库车的国都。
据说大城西门外路两旁都有佛像,其高九十余尺。唐代的尺和现在的尺相差无几,那么当时的佛像就应该有三十米左右。敦煌莫高窟有两尊弥勒菩萨像,其大小与之相仿。但敦煌的佛像在石窟里面,而玄奘所说的库车西门外的巨型佛像没有堂宇,直接展露在道路两旁。据说当地每五年举行一次大施会,会场就在路旁的佛像前。
在举行大施会的时候,九十余尺的佛像是如何展露呢?玄奘并没有写明。不过,从佛像的整体高度来看,一定十分雄伟壮观。也许还有金箔、银箔及各种彩色料子装饰其上,让人叹为观止。
克孜尔千佛洞的第七窟前曾经立有佛像,如今只有脚踝部分保留了下来,而且多数时间都埋在沙中。但从脚踝大小判断,完整的佛像即便没有数十米高,也要比普通佛像大许多。
如今漫步在库车县城周边,昔日佛教王国的面影早已荡然无存,天山南路的晴空下,只有屹立在库车大寺的伊斯兰寺院中的塔。
《大唐西域记》中说:
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
所谓会场,就是刚才提到的五年一度的大施会会场,有大佛像矗立其间。关于“阿奢理贰”这一寺院名,玄奘只是作注说“唐言‘奇特’”。
其实,“阿奢理贰”应该是梵语“āscharya”的音译。翻开词典,英语解释为“matter of wonder”,意思即汉语的“奇特”。那么这座“奇特寺”具体在哪里?玄奘只是概括地说在会场西北,渡河可至。据后世学者多方考证,认为它在库木吐拉千佛洞对岸。
在那里,有烧毁后残留的遗迹。保罗·伯希和还在那儿发掘出了书库,获取了大量婆罗米系文字的书籍。从库车去奇特寺确实得渡河,但行进方向并非是龟兹古城西北,而是正西。会场在西门外路,所以还得往南走。所经之河名为渭干河,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西川河。奇特寺建在渭干河西岸,如今早已化成了废墟。
庭宇显敞,佛像工饰。
寺中的庭院和堂宇宽敞明亮,佛像装饰精巧。对此,玄奘做了专门记录。不过昔日的鲜亮已经无法再现,留存下来的只有保罗·伯希和从地下发掘的古籍。与之相比,东岸悬崖上的石窟群却很幸运。
需要补充的是,库木吐拉千佛洞中的“库木吐拉”一词系维吾尔语译音,意为“沙漠中的烽火台”。在西域回纥化(或者说维吾尔化)之前,库木吐拉应该有对应的吐火罗B系语名称,或者作为佛寺它还有梵语叫法。因为玄奘只提到了渭干河西岸的奇特寺,却忽略了东岸的石窟寺,所以如今这一切只能凭空猜测了。
库车县城西边三十多公里处的库木吐拉千佛洞有一百六十个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紧邻渭干河,在河水泛滥时,低处的石窟会被淹没。因为离千佛洞不远的渭干河上游修有大坝,所以千佛洞附近的水位要比古时候高出许多。1976年,渭干河河水泛滥,冲坏了多座石窟。对此,中国政府于次年斥资三百万修建了防护堤。
据推测,库木吐拉千佛洞中的第二十四窟和第四十六窟建于南北朝,即公元5世纪,是众多石窟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
由于第四十六窟位置较高且地势险要,所以才没有被破坏,成为库木吐拉千佛洞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个。1978年,相关部门修建了专门的参观道路。那座洞窟中,有我十分喜欢的交脚菩萨画像。画像中,菩萨的胳膊只勾勒出了三分,颇似近代西洋画中的立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