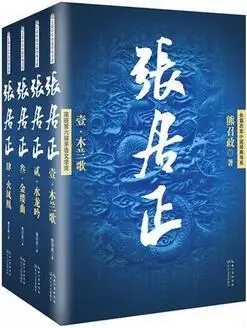这下把曾国藩吓慌了,连叫几声“润芝”,胡林翼没有睁开眼。亲兵赶忙把他抬到船上,曾国藩打发王荆七飞马去接医生。
正忙乱之中,从下游驶来一只大船,水师内湖统领彭玉麟由池州府赶来安庆。见此情景,忙来到胡林翼船上,与曾国藩见过面后,便守在胡林翼的身边。过一会儿,医生来了,忙了半个时辰之久,胡林翼醒过来了。他睁开失神的眼睛,望着站在眼前的曾国藩、彭玉麟,略微动了动嘴唇。彭玉麟想起梅小姑临终前的样子,也是这般憔悴干瘦,心里一阵难受。
“润芝,刚才还说得好好的,为何突然变得这样?”
“哎!”胡林翼服下两粒救急药,气色好了一点,“涤生、雪琴,我自知不久人世了,有一言要留给二位。”
曾国藩握着胡林翼冰凉的手,说:“润芝,这是什么话,你不过五十岁,报国的日子还长着哩!”
彭玉麟也说:“你素来身体强壮,这点小病,不要挂怀。”
胡林翼摇摇头说:“我自己清楚,我就要跟着大行皇帝去了。”说着,不禁凄然一笑,“长毛之乱,总在这两年可以平定,我不挂牵;我所担心的是,坏我大清江山的不是内贼而是洋人。涤生兄,你看刚才江上那艘铁舰,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我十条百条木船都不是他的对手呀!”
胡林翼说到这里,一口痰涌上来,两眼紧闭,气接不上了。好一阵才又苏醒,拉着彭玉麟的手,气息低沉地说:“魏默深说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真正的爱国志士的话,可惜这些年来没有谁去认真办。雪琴,我湘勇水师今后若要对付洋人,必须要有洋人那样的坚船利炮啊!”
彭玉麟双手握着胡林翼的手,用力地点了点头。曾国藩终于明白了胡林翼刚才昏厥的原因,十分感动。心想,十八省督抚都能有润芝这样的爱国之心和远见,中国何至于有长毛之乱,何至于有大行皇帝蒙尘热河,何至于有六岁孩童为天子的局面出现!偏偏这样的忠贞卓越之士,又不得永年!
待胡林翼稍微平息下来,曾国藩要亲兵抬胡林翼下船进城将息。胡林翼摇手说:“我身为鄂抚,当此国丧期间,哪有心思在安庆养病!船上平稳,不会出事,让我早点回武昌去吧!”
曾国藩情知留不住,便命令医生跟船到武昌,一路好好照料,又要船尽量划得慢些稳些,这才依依不舍地和胡林翼告别。
曾国藩默默地站在码头上,直到船消失在烟波中,才转过脸来与彭玉麟寒暄。这时,他才发现彭玉麟浑身素服。
“刚才见胡帅这般样子,只怕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不久人世了。倘若胡帅跟随大行皇帝而去,事情就更难办了。”
曾国藩默默点头,没有接腔。彭玉麟立时觉悟此地不是说话之处,便不再开口。
彭玉麟进了刚才胡林翼坐的轿子,随曾国藩进了城。来到督抚衙门,曾国藩带着彭玉麟进灵堂,行过了哭临仪式后,再与曾国荃、曾贞干等人一一相见。饭后,彭玉麟一人进了曾国藩的卧室。在池州府听到咸丰帝去世的消息后,几天来彭玉麟想了很多很多,他准备跟曾国藩谈谈,而曾国藩也有一件大事要征求彭玉麟的意见。
彭玉麟情感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深得曾国藩的赏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比一般。
“涤丈,夜里浑身痒得睡不着觉,如何过得?难道就没有药可治吗?”当曾国藩说起近来癣疾又发作了,常常痒得通宵不眠时,彭玉麟关切地问。
“此病已害了我三十多年,药渣都可堆满一屋了,总是好一阵丑一阵,不能断根,我也失去信心,再不吃药了。”曾国藩苦笑着说。
“涤丈,假使夜间有一个人替你搔痒,你会睡得安稳点吗?”彭玉麟忽然想起什么。
“从前在京师,纪泽娘就常常替我搔痒。有人搔,当然会睡得好些。”
“涤丈!”彭玉麟欲说又止,停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我给你老买一个妾来,专替你老搔痒、洗衣、做饭。”
“买妾也难啊!”曾国藩摇摇头。但彭玉麟已觉意外:只是说难,并没有一口拒绝呀!
近年来,欧阳夫人几次在信中提到此事,说自己不能在身边服侍,不如买一个妾来,女人家究竟比粗手大脚的荆七要好得多。曾国藩婉谢了夫人的好意。
他并不是一个六根清净得完全不思女人的苦行僧。年轻时,他也曾对歌楼舞女有过浓厚的兴趣。湘乡县城挂头块牌的粉头大姑死的时候,曾国藩还为她送了一副风流挽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进京后,他想到自己贵为天子门生,言行要多加检点,后拜唐鉴为师,做了理学先生的门徒,更加规规矩矩,谨言慎行,自觉地将歌舞声色摒弃于千里之外了。带勇之后,他立志要事事身先士卒。兵勇久离妻室,又手握刀枪,故历朝历代,军纪再严的部队都不可能杜绝奸淫。曾国藩决心把湘勇练成一支军容整肃的曾家军,先从自己做起,不近女色。欧阳夫人劝他,不少分统、营官自己想带女人,也怂恿他买妾蓄婢,曾国藩一概予以拒绝。
这半年来,他觉得自己更为衰老了,衰老最明显的标志是目力更加减弱,读书写字不戴眼镜就不行,右目时常发痛,他真担心这只眼睛不久会痛瞎掉。精力不济,中午非得小睡片刻不可;到了傍晚,又得闭目在床上躺半个时辰,夜晚才能治事。尤其在癣疾发作时,整夜整夜睡不好,白天提不起精神来,倒不如真的去买一个妾来!但买一个好妾也不容易。
“不难!”彭玉麟见曾国藩松了口,很是高兴,“涤丈,你要个什么样的妾,我去给你买来。”
“我这样一个满身癣疾的衰老头,哪个年轻女子愿意和我在一起。”曾国藩笑着说。
“什么衰老头,涤丈是当今第一号伟丈夫。哪个女子能被涤丈看中,真是她的福气。你老说说条件看。”
“条件嘛!”曾国藩兴奋起来,血涌涌的,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模样儿只要周正就行了,千万不要太漂亮的,性情则一定要温顺平和,最好还得识几个字,能帮我清点清点文牍。”
“好,我去细细访求。你老说有要事跟我谈,何事?”
“雪琴。”曾国藩望着彭玉麟,深情地说,“自咸丰三年你辞别老母,屈从我创办水师以来,和厚庵一起,把水师办得有声有色,功勋卓著,不是我当面夸奖你,我朝两百年来,还没有这样的水师,也没有你和厚庵这样的水师统领。”
“涤丈言重了,水师即算是有成绩,也是你老之功,玉麟不过是你老帐下一名供驱使的校尉罢了。”
“你是大才,不能老为鄙人所屈。自翁同书革职以来,皖省巡抚之位空缺已久,现省城已下,宜早定主人,我拟向朝廷推荐你为皖抚,想你不会推辞。”
“玉麟深谢涤丈的器重,但皖抚一职,则万万不能接受。”彭玉麟的态度似无可商量的余地,使曾国藩深为奇怪。
“雪琴,这又为什么?厚庵和你一起办水师,早已当了提督,连邓翼升都已升了副将,你至今只是个三品臬司,我心里为你过意不去。”
“涤丈,玉麟不是热衷禄利之徒,这点想必涤丈也知。”
“正因为你不慕禄利,我才荐你;倘若是热衷钻营之徒,我就不得荐你了。”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涤丈。涤丈知遇之恩,今生今世粉身碎骨难以报答。”彭玉麟激动而恳切地说,“我虽诸生出身,其实并无经纬之才,近十年来在江湖波涛中出没,更把学业荒疏,把脾气弄坏,把性情弄慵懒了。我只能短衣芒鞋在船上奔波,耐不了大堂高座、簿书应酬的生涯。先前接受广东按察使,是看在只挂个名,现在要为皖抚,则不能挂名了。还有,”说到这里,彭玉麟稍稍犹豫了一下,“这个世道太令我失望了,你老有依靠一二人做榜样,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宏愿,我没有这个想法。”
“你近来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曾国藩听出彭玉麟话中有话。
“涤丈,你老听说了吗?何桂清就要无罪释放了。”
“有这事?”曾国藩惊愕起来。
“大学士祁隽藻、彭蕴章联络十七名一、二品京官向皇上上书,说人才难得,请求宽免其罪,让他戴罪立功。”
“岂有此理!”曾国藩愤怒地站起来。
“祁、彭两个老头子还向皇上密奏,说让何桂清带两万绿营去围江宁,不能让湘勇得了攻下贼巢的首功,否则,湘勇将不可驾驭。”
“祁隽藻为何总是这样仇视我们湘勇呢?我跟他实在没有个人恩怨呀!”曾国藩想起祁隽藻数次在皇上面前进谗言的往事,心中又恨又怕。
“我们湘勇如此忠心耿耿地为皇上而与长毛血战,却要受到别人的猜疑;何桂清丢城失地,临阵逃命,反而被称为人才难得,且这些话出于所谓天下大老的两个大学士之口,尽管大行皇帝可能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但已足使志士灰心了。”彭玉麟两只手来回搓着,似乎要借此发泄胸中的积郁,“涤丈,这样贤愚不分、忠奸不辨的人把持朝政,我还去当什么巡抚?我感大人的知遇之恩,尽忠竭力统率水师,协助大人攻下江宁。一旦江宁打下手,我就回我的渣江去,不管什么官职我都不接受。”
“雪琴,祁中堂、彭中堂虽然糊涂,但朝政并不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且眼下大行皇帝远行,新主施政,自有一番除旧布新。”
“新主只有六岁,他晓得什么!”彭玉麟冷笑一声,压低声音说,“涤丈,湘勇水陆军威大振,今又攻克安庆,全国军民莫不仰服。大丈夫当意气纵横,不可仰他人鼻息。今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不待曾国藩回答,彭玉麟又说,“倘若涤丈有此心意,玉麟和全体水师愿效犬马之劳,虽赴汤蹈火,亦心甘情愿!”
如果说胡林翼、左宗棠尚只是试探的话,彭玉麟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这种赤裸裸地犯上作乱的话,若不是骨肉之亲、生死之交,谁敢说出口?彭玉麟是把自己的一颗心剖了出来,捧给你啊!曾国藩本想亲切热烈地拥抱彭玉麟,但理智使他清醒。他只是用深沉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位肝胆之友,面无表情、平平淡淡地说:“雪琴,你不要拿这种话来试探我!安徽巡抚一职,我明日就拜折推荐,请你不要再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