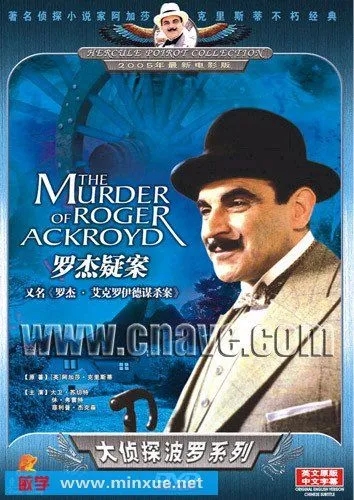一说到张爱玲的朋友,除了炎樱、邝文美,避不开的还有苏青。第一证据便是张爱玲写的《我看苏青》,这实际上是张爱玲为苏青的散文集《浣锦集》写的序:“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有物证也有人证。苏青的妹妹苏红回忆:“这两个女作家白天不写文章,常常相约去喝咖啡,她们无话不谈,非常要好。”
但事情又有点蹊跷。因为除了商业互吹,她们并无其他的交往细节。相比之下,和炎樱的AA制下午茶,写给邝文美信里的旗袍花样,才更像是女生之间的友谊。《我看苏青》里还有一句:“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
张爱玲和苏青的友谊究竟如何?是真友谊,还是传说中的“塑料姐妹花”?如果真如苏红所说“非常要好”,是什么事情导致了她们的分崩离析?
我一直认为,张爱玲是个不世故的人,尽管她一直假装世故。接待粉丝水晶,知道预备“一瓶8盎司重的CHANEL NO.5牌香水”,但一听水晶那番对于《海上花》的主观论断,她立刻“先微微一惊,然后突然大笑起来”,显然是不赞同。同样的香水,她也送了柏克莱大学的助手陈少聪。可是她为了不跟人家交流,就“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上司陈世骧请她去家里吃饭,她选择应邀前去,去了呆呆坐在沙发上,只和陈说话,其他人一概不理。最后还是夏志清去帮她解释:“(爱玲)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在对待苏青的问题上也一样。
《我看苏青》是苏青《浣锦集》的序言,作为一篇吹捧文章,整篇都充满着别扭。明明可以说“我很喜欢她”,偏偏说:“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明明可以说“《浣锦集》写得很好”,偏偏说:“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明明是表扬,偏偏要说:“也有两篇她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惆怅。”
要搞清楚这篇文章里的别扭,我们要先弄清楚该文的写作时间——1944年春。
1944年春天,作为作家的苏青是比作为作家的张爱玲还要红的。1943年5月开始连载的《结婚十年》印了三十六版,是出版业的奇迹。1943年10月10日,苏青创办的《天地》杂志首印三千册,五天即卖完,加印两千册,复一扫而空。作为出版人的苏青亲力亲为,不仅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还亲到报摊收款,真是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楷模。相比苏青的繁花似锦,张爱玲“小荷才露尖尖角”。1943年5月,她通过母家亲戚黄岳渊的介绍,在周瘦鹃的《紫罗兰》上发表了《第一炉香》,但周瘦鹃本人并不那么欣赏张爱玲的文字,她真正的伯乐是《杂志》,给她带来声名的《传奇》也是由《杂志》所在的上海杂志社在1944年8月出版的。1944年的小报评论说,苏青和张爱玲是“最红的两位女作家”,苏青在前,张爱玲在后。
所以,这段友谊的开始,并不是张爱玲屈就苏青,但确实是苏青上赶着结交张爱玲——为了约稿。
如果穿越回去,我一定要向苏青请教一个终极问题:如何催稿。我的前同事双红,人称“催稿婆”,她的催稿方式是天天催、日日催,用发红包的形式提醒截稿日期,时人叹服。比起苏青,双红就是小巫见大巫。跟周佛海的太太杨淑慧约稿,苏青知道她贵人多忘事,于是“再三劝说,每日催促”,终于在创刊号上约出一篇重磅《我与佛海》。跟《古今》社长朱朴的续弦梁文若约稿,苏青索性边吃边催,弄得人家不好意思,居然“在朴园午餐,餐毕草此”,简直立等可取。
杨淑慧是苏青的过房娘,所以苏青曾经带着张爱玲一起去周佛海家里,给得罪了汪精卫的胡兰成求情。杨和梁都是票友,非专业写作者,张爱玲是作家,不能强行约稿(所以请各位编辑以后也对我温柔一点),苏青就给她写信,用“我也是女人”这种“同性”同情法约稿,果然成功,这便是张爱玲在《天地》第二期发表的《封锁》。
在约稿之后,苏青和张爱玲的交往开始频繁。1945年2月27日她们曾一同出席座谈会谈妇女问题,苏青也到张爱玲家里去接受记者采访,就如同苏红说的那样,她们开始外出喝咖啡约会。潘柳黛第一次去张爱玲家,也是苏青陪着去的。
但《天地》也成为胡兰成和张爱玲“孽缘”的开始。在看过那篇《封锁》之后,他立刻给苏青写信问:“张爱玲系何人?”苏青的回复:“是女人。”这个回答非常妙。后来胡兰成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又问张爱玲,苏青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他。可以说,苏青算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媒人。
苏青何以迟疑?我初看《今生今世》时,以为苏青知道胡兰成是登徒子,看出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想把女朋友介绍给胡兰成。直到看了苏青的《续结婚十年》,我不禁感叹:我还是太幼稚了。
我承认我挺喜欢苏青的,因为她敞亮。
喜欢什么就说什么,毫不矫情,比如她说:“我爱吃,也爱睡,吃与睡就是我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在对女人要事业还是爱情这个问题上,她也一针见血:“一面工作一面谈恋爱的女人,总会较专心恋爱而不做工作的女人吃亏的。”甚至替捞女讲话,不怕挨骂:“要求物质是女人无可奈何的补偿,因为她们知道男人容易变心,而且变得快,还是赶快抓住些物质,算是失望后的安慰吧。好歹我总弄到他一笔钱,这是女人被弃后的豪语。”有人说她是“犹太作家”,大约是说她小气,她也堂堂正正回复:“犹太人曾经贪图小利出卖耶稣,这类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于不肯滥花钱,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人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了……我的不慷慨,并没有影响别人,别人又何必来笑我呢?”
连写自传性小说《结婚十年》,苏青也坦诚得可怕,如一卷画轴,不是徐徐摊开,呼喇喇一下尽收眼底:婚礼上忍受不能上厕所、丈夫和表嫂有染、生了女儿之后公婆不让自己喂奶……她写被丈夫填鸭喂食,只为了能下奶,效果不好,丈夫就埋怨:“你自己倒是越来越胖了,真是自私的妈妈!”我一个女朋友读到此处,居然潸然泪下,直说真切。
所以她读了《倾城之恋》,可怜因为香港沦陷才终于成为范柳原太太的白流苏,因为范柳原这样的男人,嘴上说着“执子之手”,却永远不会停下浪荡的脚步。但她理解白流苏的痛苦:“我知道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比求爱情的心来得更切。”
写这句话的时候,她丝毫不避讳,因为自己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苏青是主动离婚的。张爱玲评价苏青,说她谋生亦谋爱。乱世之中,谋生已经足够艰难,何况还要谋爱。这样看来,苏青骨子里是理想主义的。谋生,苏青靠的是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青眼:
和仪先生:
……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著安
---陈公博启
---六月十九日
据说,陈公博看到苏青在《古今》“周年纪念专号”上写的《上海的市长》,非常赞赏。“陈氏是现在的上海市长,像我们这样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绝对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的。不过我却见过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十六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长,我心中想,我们之间原有很厚的隔膜。”这篇文章惹得平襟亚大骂苏青,他和苏青是亲戚。平襟亚认为苏青和陈公博有一腿,因为她赞美陈公博的鼻子——在那时候的直男认知里,男性的鼻子是性能力的隐喻。
我觉得平襟亚吃瓜吃得莫名其妙,写文章的时候陈公博压根还不认识苏青呢,况且陈公博的鼻子确实相当出名,当时的报纸画漫画,都突出他的鼻子,所以苏青注意到也没有什么奇怪。
不过,很多人看到陈公博的信,还是疑心陈公博有其他想法,“办办私人稿件”,意在让苏青做私人秘书——陈公博的情妇莫国康便是做他的贴身秘书的。有人善意劝阻苏青,认为莫国康“手段毒辣”,苏青不是她的对手。莫国康北大法学院毕业,确实手段了得。抗战胜利后市面上出版的《汪精卫的艳史》,莫国康排行仅次于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居然比陈公博太太李励庄还要靠前。
最终,苏青选择了做一个专员,而不是秘书。陈公博不仅给了苏青官做,还支持苏青办杂志——这便是《天地》的由来。
《天地》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的。
——苏青《做编辑的滋味》
藏家谢其章曾经买到友人转让的《天地》,“是昆仑影业有限公司的旧藏本,借阅登记卡片上还有‘冯和仪’的名字(冯和仪即苏青),自己写的书要请别人帮忙复印,自己办的杂志要从图书室去借阅。”
《续结婚十年》里,苏青坦诚,陈公博(书中为金总理)给了自己十万块。黄恽先生考证,陈公博还给了苏青配给纸:“特别可贵的是,他给了钱,又给了纸,却并不插手来控制苏青的办刊,并不预先给定一个什么核心价值观……”这是难得的信任了。《续结婚十年》的坦诚不仅如此,苏青甚至老老实实地描述了自己的“艳史”,黄恽先生曾经在《万象》杂志专门撰文,猜出了书中各位男子的原型,我一一比对过,相当准确,在此不再赘述。
这其中便包括胡兰成。
《续结婚十年》有一节“黄昏的来客”,里面便有谈维明(胡兰成)和苏青的一夜情,原文摘抄如下:
春之夜,燠热异常。房间似乎渐狭窄了,体积不断的在缩小,逼近眼前,使人透不过气来。我闭了眼睛,幻想着美丽的梦。美丽的梦是一刹那的,才开始,便告结束。天花板徐徐往上升,房间显得荒凉起来了,燠热的空气似乎发散开去,不久便使人心冷。谈维明抱歉地对我说:“你满意吗?”我默默无语。半晌,他又讪讪的说:“你没有生过什么病吧?”
我骤然愤怒起来。什么话?假如我是一个花柳病患者,你便后悔也已嫌迟了。我对他说:“我恨你。我恨不得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染给你。”他笑道:“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不要以为你朋友都是有地位的,其实愈是有地位的人愈有患此等病的可能。这是一种君子病。君子讳疾忌医,所以难以断根。”我恨恨的说道:“然则你不是君子,你该不会有什么病吧?”他凑过脸来笑对我说:“不信请你验验看。真的,我要请你验个明白才好。”
我开始讨厌他的无聊,转过脸去,再也不肯理他。他轻轻问:“你疲倦吗?”我心里暗笑男子的虚荣可怜,无论怎样在平日不苟言笑的人,在这种场所总也是爱吹牛的。从此我又悟到男人何以喜欢处女的心理了,因为处女没有性经验,可以由得他独自瞎吹。他是可怜得简直不敢有一个比较的,他们恐怕中年女人见识广,欢喜讲究技巧;其实女人的技巧有什么用?你的本领愈高强,对方的弱点愈容易因此暴露出来,结果会使得你英雄无用武之地。女人唯一的技巧是学习“一些不知道”,或动不动便娇喘细细了,使男子增加自信力,事情得以顺利进行。欢场女子往往得有“小叫天”“女叫天”等雅号,大概是矫枉过正,哼得太有劲了,所以别人如此调侃她,这种女人是可怜的;男人也可怜,假如他相信她的叫喊真是力不胜任的话。
谈维明见我良久不说话,心里也觉不安。但是他却不甘自承认,只解嘲似的诿过于对方说:“怎么啦?你竟兴趣索然的,渐渐消失青春活力了?”我听了心中不悦,也就冷笑一声,反唇相讥道:“是老了,不中用了。”他敷衍片刻,也就披衣起床。
……
“你恨我吗?”他严肃地说。
“……”
“恨我什么呢?”
“你不负责任。”
“我要负什么责任?”他忽然贴着我的脸问:“同你结婚吗?”
“谁高兴同你……”
“这样顶好。”他又严肃地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要同你结婚过。你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怀青。谁会向你求婚便可表明他不了解你,你千万别答应他,否则你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又何必要结婚呢?就是男人也是如此……”
“那末你又为什么同我……?”
他哈哈大笑道:“这因为我欢喜你。怀青,你也欢喜我吗?”
我骤然把脸闪开来,笑道:“我是不满意。在我认识的男人当中,你算顶没有用了,滚开,劝你快回去打些盖世维雄补针,再来找女人吧。”
难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恋爱的女人五花八门,简直集邮一般,独独没有苏青,原来如此不堪,忍不住给苏青点一千八百个赞。也因为这个原因,在胡兰成打算去找张爱玲的时候,苏青有一些不高兴——即使是一夜情,也有女人天生的嫉妒。
胡兰成和苏青的一夜情,发生在胡兰成勾搭张爱玲之前,这还是张爱玲的《小团圆》告诉我们的。在《小团圆》里,苏青是文姬:
她(九莉)从来没妒忌过绯雯,也不妒忌文姬,认为那是他刚出狱的时候一种反常的心理,一条性命是拣来的。文姬大概像有些欧美日本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样。她那么浪漫,那次当然不能当桩事。
“你有性病没有?”文姬忽然问。
他(邵之雍)笑了。“你呢?你有没有?”
和苏青赤裸裸的描写相比,张爱玲显然向着胡兰成,她不仅修改了两人的对话,还把“是否有性病”这个问题的首问者由胡兰成转成了苏青。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被胡兰成骗了,还有一种是她知道真相,但刻意隐瞒。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毕竟,在《小团圆》里,她给苏青起的名字是“文姬”,我一开始以为是“归汉”的“蔡文姬”,细细咀嚼回味一下醒过神来,原来是“文化之姬”,姬者,妾也。所以她拿文姬和绯雯并列,绯雯的原型是胡兰成的妾,舞女应女士。还有一种可能是讽刺苏青,因为她在战后被小报称为陈公博的“露水妃子”。
张爱玲是什么时候知道事情的真相的呢?我们没办法知道具体时间了。胡兰成在收到苏青的《浣锦集》之后写了一篇书评《谈谈苏青》,在那里透露了一点细节:
她长的模样也是同样的结实利落:顶真的鼻子,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无可批评,因之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
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苏青“看书写字”的样子呢?只有在苏青的家里。倘若张爱玲足够敏感,也许就可以觉察出来。但那时两人正在热恋,胡兰成文中还故意提及张爱玲,这显然是暗戳戳秀恩爱。恋爱的人是盲目的,我猜张爱玲看出这段文字玄机的可能性不大。
在张爱玲前往温州,被胡兰成呵斥回到上海之后,她和苏青还有往来。1946年4月1日,上海《香海画报》发表署名“风闻”的报道《张爱玲欣赏名胜解决小便》,报道记录了苏青的谈话:
苏青提到她的同行张爱玲的小便问题。……张爱玲对苏青说:“我最不喜欢出门旅行,除非万不得已,我总不出远门的。假如出门的话,到了某一个地方,别人在那里赶着欣赏名胜,我却忙着先找可以解决小便的处所,因此别人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哪里有心去看风景呢,假若找不着地方小便……”
所以,两人友谊的结束,更大的可能是1947年2月,苏青出版了《续结婚十年》。以张爱玲和苏青的熟悉程度,她读到此书的可能性极大。此时,她虽然已经写过“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但看到这样赤裸裸的描写,她当然不可能再维持这段本来就是由业务发展起来的友谊——谁会再想见睡过前男友的女朋友啊!
但苏青显然更厚道一些,《续结婚十年》里,她写了那么多伪政府男女,唯独没有张爱玲,这是一种同情,她知道,那时候的张爱玲,顶着胡兰成“汉奸老婆”的名号,活得战战兢兢。她心里始终是有张爱玲的。
她们友谊的高光时刻,大约是1944年3月16日,《杂志》举办女作家聚谈会,会上有张爱玲、苏青和潘柳黛。当着潘柳黛的面,张爱玲和苏青的双簧唱得非常成功,苏青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张爱玲说:“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杰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潘柳黛听了便很尴尬,因为在场作家里,大家都认为她们三个人是朋友。后来潘骂张爱玲炫耀自己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类似“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时,也是苏青拿着文章提醒了张爱玲,张爱玲读后“一时气得浑身发抖,差点流下眼泪”。
和潘柳黛有过交往的沈西城先生在《喔唷!表妹来哉!》里说,张爱玲在被潘柳黛羞辱之后,曾经回应,潘柳黛“腰既不柳,眉也不黛”——实际上,这句话的出处是苏青。苏红在回忆苏青时予以了证实,这确实更像是苏青说出来的,就像胡兰成说的那样,苏青,是有一种认真的俏皮。(她曾经对《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讲,你这么胖,哪里“瘦鸥”,明明是“胖鸭”。)另一个说法是,张爱玲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这个方像是张爱玲的回答。还是王安忆说得好,苏青“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
1982年,苏青吐血去世,去世时没有人在她的身边。也是在这一年,北大学者乐黛云辗转托人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张爱玲拒绝了:“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
三年后,苏青的小女儿李崇美前往美国,行李箱里有一件特殊物品,乃是苏青的骨灰。那时的张爱玲正在为了无中生有的蚤子东逃西窜,她当然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
但她一定不会忘了,1945年2月27日,在张爱玲家,苏青和自己进行了一场对谈,她们谈了很多,当谈到“标准丈夫”的条件时,苏青认为要“本性忠厚”“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张爱玲则说“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那人应当有经验一点”。作为过来人的苏青说的是肺腑之言,这两条,胡兰成一条也没挨上。
苏青走了之后,张爱玲一个人站在黄昏的阳台上,忽然感慨:
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张爱玲《我看苏青》
那天是元宵节。
参考文献:
黄恽:《缘来如此》,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8
毛海莹:《苏青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
王慧:《苏青与张爱玲的“天地”情缘——兼谈生育问题特辑“救救孩子”》,学术交流2018-11-5
陈子善:《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书城2007-10
于亮:《1943:张爱玲与海上文学杂志》,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