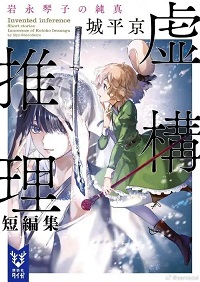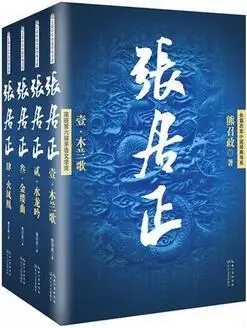武当山有一个山谷,叫逍遥谷,谷口有一尊老子骑牛的雕塑。雕塑和命名无疑来自道家,寓意得道后的状态,就是逍遥吧。
我喜欢这名字,也喜欢这寂静的山谷,然而我在那里并没有感到逍遥,即使午后下起了小雨,云雾飘渺,宛若仙境,也依然没有。我是个俗人,那时正被自己的问题困扰。
不仅我没有,溪涧匆忙的流水,山上拥挤的草木,如梦幽啼的虫鸟,爬满莓苔的石头,我觉得它们也都没在逍遥。一种森严的秩序统治着万物,不成文,不可见,它就在这里。

与我同行的是一位“道长”,其实是某武馆的馆长,身穿黑色道袍,没戴冠巾,头顶挽了个发髻,灰白胡须长及胸口,不知他是不是真的道长。他背着篓筐沿途采药,我问他是否相信长生不老,他说相信但很难做到。我了解,读过葛洪的《抱朴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如今更不知有几人能够出离。如果能做到,你想长生不老吗?我又问。他想了想,抬头望着雾中的山峰,神色寂寞地说他想在山里住一辈子。
我没问他为什么不能,有些事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他继续教太极,教武术,采药,寂寞,道袍和胡须也许是“人设”,也许是他灵魂的表征。
在逍遥谷游了一天,走了二十几里路,我什么问题也没想通,也没能放下,就那么又回到生活中。终于明白,人可以逃离全世界,但逃离不了自己,药不在山上,药在时间里,在人的心里。
《逍遥谷》(三书)
撰文 | 三书
桃花像一场魔法
《大林寺桃花》
(唐)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大林寺在庐山香炉峰顶,人迹罕至,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晚。是年孟夏,乐天与朋友共十七人,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登炉峰,初到大林寺,见山桃始华,涧草犹短,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口号绝句云。
以上是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所记,可作为诗的创作背景,序末写道:“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寥无继来者。嗟乎!名利之诱人也如此。”

其实也无须了解背景,因为这首诗再简单不过,地势高下不同,时节物候各异,海拔高处,孟夏四月如正二月天,此常理也。常理不是诗,诗始于惊异,在乎“恍然”之间。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两句就有好几重惊异。以为春天已经过去了,乍见桃花盛开,不觉惊异,而且欣喜,原来这里的春天才开始,原来春天没有过去,只是转到了山里。山寺桃花别有韵味,没有什么比桃花更能状春光之烂漫,开在山寺的桃花又别增明艳。
人间芳菲尽,山寺花始开,是不是还隐含着一层禅意?乐天时任江洲司马,仕途受挫,离开了人间,来到深山里,发现此间别有天地。辛弃疾《鹧鸪天》有句曰:“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可与互参。
“长恨春归无觅处”,入山之前,盖已伤逝,怨春光不驻,恨花落匆匆。“不知转入此中来”,始料未及,不期在古寺深山又见春天,原来春天不是消逝了,只是转入另一个世界。
这是个非人间的世界,盛开的桃花仿佛通往仙境的一扇门,如《桃花源记》中的忽逢桃花林,武陵渔人也是恍惚闯入了另一个时空。假如把桃花改成李花或菜花,恐怕就不行,李花的白,菜花的黄,都不容易制造幻境。桃花像一场魔法,桃花的红,桃花的静,桃花氤氲弥漫的香气,似乎才会对人产生那样的迷醉效应。
前人评诗的后两句曰,只恐“此中”亦不能久驻。梦醒,山寺的桃花毕竟不是在仙境,开一阵子也会零落,春天终会离去。奈何?唐代梅花尼子行脚归来,作诗《嗅梅》:“着意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花枝头已十分。”开悟后,她道破禅机,春不在远方,不在别处,就在离你最近的地方,心生万法,何须外求?!
明 佚名《山寺问道图立轴》
什么是庐山真面目?
《题西林壁》
(宋代)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很想与东坡居士谈谈,问问他:“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在巴黎,唯一看不见埃菲尔铁塔的地方,就是在铁塔上。您的诗也是这意思吗?”
据说莫泊桑反对在巴黎建铁塔,埃菲尔铁塔建成后,他却经常去那里用餐喝下午茶,当侍者问他为什么时,他便说了上面这句话。莫泊桑与苏轼本不是一个意思,然而单就这句话,却异曲同工,今人也多引用于类似的语境。
看不清一个事物,尤其是宏大的事物,因为你身在其中,只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就是说,你只能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即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

那要如何才能看到庐山真面目呢?按照字面意思,你得在山外面看。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整体,但是仍有问题,比如外面的视角也有远近高低的不同,站在五十米之外和五百米之外,从十层楼的楼顶和从一千米的高空俯瞰,庐山的整体形象都不一样。再者,朝暮四时,阴晴风雨,庐山的面目也会不同。
庐山究竟有没有一个“真面目”呢?话音刚落,我看见东坡在拈花微笑。没有真面目,也可以说都是真面目,非法非非法,是这样吗?东坡不语。不可说,不可说。
不仅庐山,任何事物若去较真,莫不如此。就拿桌上这个咖啡杯来说,“咖啡杯”只是我从功能角度对它的一个方便称谓,它也可以是茶杯,也可以是碗,花盆,或当作艺术品摆在那里,只要你愿意,它还可以是你的守护神,没有谁规定它只能是什么。它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呢?我可以勉强描述一下它的样子:白色,瓷的,敞口,有柄,容量约半升。你头脑中呈现的杯子是怎样的?白色有各种白,瓷的感觉也不一样,敞口有多大,柄是什么形状,等等,相信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象,构想出一只属于自己的杯子。可见,语言文字无法真正说出一个事物,所以禅师告诫我们:“开口即错”。
如果这个杯子在你眼前,你就能看到它的真面目吗?相信你会和我一样,越看越不知它是什么。同一个杯子,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眼中的样子,也许大部分人会说这是个咖啡杯,但这也只是经验的描述,像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咖啡更勿论咖啡杯,我可能会说水杯,也可能说不上来,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碗喝水的。这还只是就感官经验大抵相通的人类而言,若扩大到别的物种别的生命体,那么被我们称作杯子的东西,就更不知其为何了。
既已说到这么远,不妨再溯源一个问题:眼前这个杯子真的存在吗?你可能会说不论怎么叫它描述它,也不论别人或别的什么怎么看它,作为一个物体,它实实在在就在这里啊。那么晚上睡梦中,当你正在做梦而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的事物对于梦中的你,和现在你认为你醒着看到的这个杯子,在认知中是同样实在的。不是吗?
由此亦可推及所有人、事、物,以及整个世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活在自己的梦中,所谓“现实”不过是集体信念共享的梦境,和小孩子玩的过家家并无不同。

清 钱维城《庐山高轴》
山中与老翁别
《人月圆·山中书事》
(元)张可久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
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
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这是一首散曲,曲辞浅白,无甚余味。序文很长,洋洋洒洒,倒是写得新鲜有趣。在此删饬揣摩,撷其丽句,掇为现代诗一首,以飨读者:
折一身瘦骨,踩雨后的虹桥,进山。
山认樵夫给树,水认渔翁给鱼,我非樵非渔,
便拥有一切,无路则处处是路。
诗越读越厚,日子越读越薄,生命越读越轻。
明天有明天的飞花,后天有后天的落叶。
大约三个秋天之前,白须飘胸的老翁来访,
铜钱换酒,此后隔山说些阴晴圆缺的话。
松花酿新酒,我叫它花雕它就叫花雕。
欲借开春送酒话暖,孰料面对的
竟是一堆废墟,老翁已绝迹。
捡出一残破条幅,新纸鲜墨写着: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
一枝疏笔墨梅,点点梅瓣,拙得很有逸气。
千古兴亡,繁华一梦,他在山中避过这道风。
老翁与书,此去何往?山是空了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