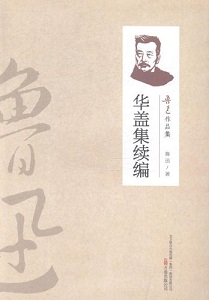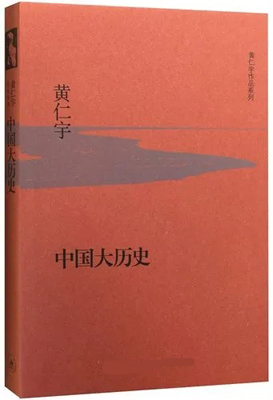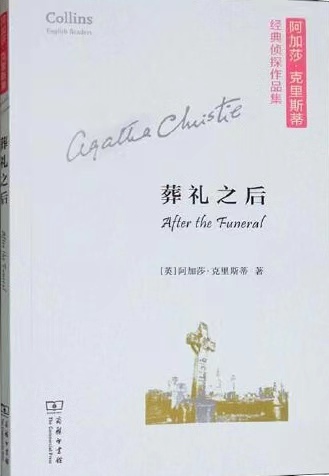我们的杂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继承了我们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比方说吧,文章的排列顺序一律遵循梁山好汉排座次的办法,对号入座: 尊者在前,卑者在后,不尊不卑者居中,各得其所。不用说,那打头文章的作者一定是那身份最高的人了。重要人物的文章一定是重要文章,理应打头,无可非议。
我是个技术编辑,从来不看稿子。我的任务是想办法使版面新颖活泼,端庄大方,注重形式美。内容方面的事情,那是“他人瓦上霜”,我是不愿去“管”的。
不过,技术编辑有时也会遇到大问题。比方说这一次吧,我在画版式的时候,发现打头文章没有署名,整篇文章一字未改,甚至连一个红点、红圈也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 这篇文章一定来头不小。 于是, 我拿稿子去请示主任。
“主任! 这篇打头文章没有署名。” “这是马老的大作。” 主任严肃地说。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学科领域有一个权威,大家都尊称他马老,从来没有听人叫过他的大名。可是,总不能在文章的题目下面署上“马老”二字吧!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追问了一句:“主任!那应该怎样署名?”
“那当然是署马老的名字呗! 这本来是你业务范围内的事情,还用问吗?”主任不耐烦地答道。“马老的名字是?”“怎么? 你连这位赫赫有名的权威也不知道?搞技术编辑的也应该学点基础知识嘛!”主任有点生气了。“我今后一定加强学习。”我连忙检讨说,“为了慎重起见,请您把马老的名字给写上吧!”“这……这……”主任说话有点结巴了,白净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刚才责问我时的那种如牛壮气,似乎也消减得多了。
尴尬的气氛是我造成的,当然也应当由我来缓解。于是,我给主任搬来了一架梯子:“主任! 名人一般都有几个笔名,马老的这篇文章究竟署什么名,恐怕还得请示一下。” 主任如梦初醒,连连说:“对,对,我马上请示! 我马上请示! 这是主编交给我的,我马上去找主编。”
一个小时以后,主任回来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小声地对我说:“主编刚才打电话问过马老,马老说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儿子的学生写的。马老的儿子托马老顺便带给主编,是为了征求意见。”
“那为什么不署名?”“马老说是为了听到不带偏见的评论。” “哦……”我默默地点点头。“那打头文章……”
“不碍事,我这儿还有一篇周老的。”
选自《北京晚报》1984年11月4日
【赏析】
在评说这篇微型小说之前,我们首先引用一位美国人在五十多年前的一段论述。
约翰·杜威在《人的问题》一书中这样说:
“这些发挥权威作用的势力在个人中是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一部分,以致我们没有想到或感觉到它们是外在的和带强制性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体现习俗传统的权威制度进行攻击,这自然会引起个人的抱怨;深深地抱怨这是对他本身中最深刻和最真实的东西所进行的攻击。”
这段话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
其一,是权威对人的潜在影响。
其二,是权威的制约力量由外在变为内心自发的要求。
当我们反观作品,反观作者对杂志社传统的交代,对“我”的下意识以及部主任乃至主编行为的展露时,竟惊讶地发现,这一切全都导向了我们所理解的两方面,作品似乎在做一种形象的诠释,我们被诉诸这样的观念: 权威的影响力量已经深入人心,部分或全部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以至于在举手投足之际他们都不得不考虑到它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马老们事实上的强大权威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我们所要做的当然不是满足于告诉读者这一现象,我们的任务还在于对事实本身作历史的剖视甚或批判。
必须承认,权威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权威代表社会组织的稳定性,个人藉此而获得方向与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因为质实而论,个人自由代表的是有意识地促使产生变化的各种力量,它与权威相生相克,成为永恒。
问题在于《头条文章》所展示的并非作为必然结果的权威以及它与自由间的矛盾,作者展示的其实是编辑、主任、主编们以抛却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为代价来接受权威,而且,如果说这种行为初始还渗和着勉强、不情愿的成分,那么,眼下却已进入了一种无比自觉的境界,也即“理所当然”(不能说出马老的真实姓名堪称展示其情感崇仰程度的妙笔)。
个体人格渐次衰退,代之以集体人格的逐步强化。在这种集体人格面前,马老们的权威被罩上灵光圈,甚至带有了人格神的色彩,人们禁不住要宣称彻头彻尾荒谬的不是人的神化,而是竟然敢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你”“我”“他”。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何方能廓清人们的“主体被动意识”,以现代精神之光烛照萎蔫的灵魂,真正做到在接纳权威的时候不失却自由。它要求我们思考,并进而校正自己的行为。
小说意义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