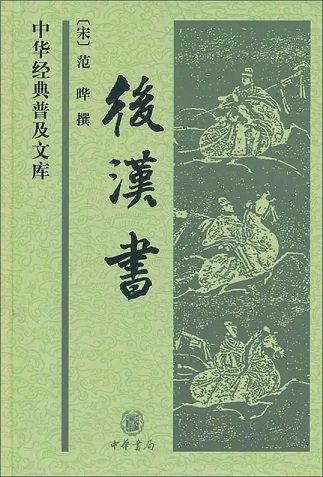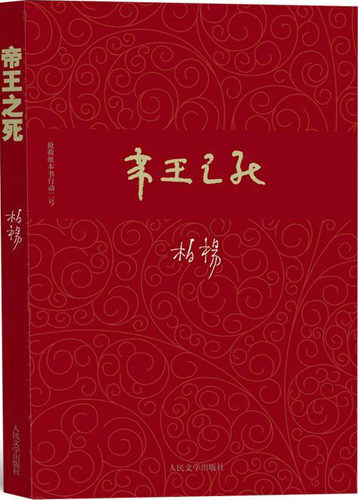第十四章 黑潮
地球上海水所占面积约为148百万平方英里,也就是约占地940亿英亩。海水的体积约为20亿立方英里,它可以成为一个圆球,这圆球的直径为2000英里,重量为300亿亿吨。想了解上面这个数目,就必须设想1030 同10 亿之比,相当于10 亿同一个单位之比,即1030 里包含的10 亿数的总和等于10 亿中所有的单位数。而海水的总量差不多等于40000 年中陆地上所有江河的水流量。
在地质学的纪年中,火的时期之后是水的时期。起初处处都是海洋;然后,在志留纪初期,山峰渐渐露出来了,岛屿逐步浮现出来,同时又在局部的洪水中淹没,重新再出现,结为一体,形成大陆;最后,才固定成为地理上的陆地,正如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般。固体大陆从流体海水所取得的面积为380万平方英里,即240亿英亩。
大陆的形状把海水分为了五大部分:北冰洋、南极洲、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
太平洋从北至南,处在南北两极之间,从东至西,是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经度范围为145°。太平洋是最平静的海洋,海潮宽大缓慢,潮水中等,雨量丰富。我的命运叫我在最奇异的情况下首先经过的就是这个海洋。
“教授,”尼莫船长对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先明确地记下我们现在的方位,确定这次航行的出发点。现在的时间是12点差一刻。我们要浮上水面了。”
船长按了三次电铃。抽水机开始把储水池的水排出,气压表上的针从不同的气压度数,指示出鹦鹉螺号的上升运动,接着,船停住了。
船长说:“我们到了。”
我走上通往平台的中央扶梯。我脚踏着一层一层的金属梯级,经过打开的铁盖板,到了鹦鹉螺号的上面部分。
平台仅仅浮出水面80厘米。鹦鹉螺号的前后两部分呈纺锤状,活像一根长长的雪茄烟。我看到船体的钢板相互层叠着,有如陆地上爬虫身上覆盖的鳞甲。因此我很自然就明白了,不管望远镜的功能有多好,这艘船总会被看成是一只海洋动物。
临近平台中央,那只半藏在船壳中的小艇,就像是一个微微突出的瘤。在平台前后,各装着一个不太高的笼子,向侧边倾斜着。笼子的一部分装着很厚的凹凸玻璃镜。其中的一个给鹦鹉螺号领航人使用,另一个装着强力的电灯,光芒四射,探照航路。
海上风平浪静,天空晴朗无云。长长的船身几乎感觉不到海洋大幅度的波动。一阵轻柔的东风吹皱了洋面。天际间没有一丝一毫的雾气,令人的视野极其开阔。
我们什么都望不见。望不见暗礁,望不见小岛,也望不见亚伯拉罕·林肯号的踪影,望见的只是汪洋的海水。
尼莫船长带了他的六分仪测量太阳的高度,因此可以知道船所在的纬度。他等待了几分钟,以让太阳跟地平线相平齐。他观察的时候,肌肉没有一丝颤动,仪器也仿佛握在铁石的手中一般,纹丝不动。“正午,”他说,“教授先生,您想要我们这时出发吗?”
我朝着这临近日本海岸那微微发黄的海面投去了最后的一瞥,然后回到了客厅中。
客厅中,船长在地图上记下了方位,极其准确地计算了经度,同时拿从前做的时角观测记录来校对。然后他对我说:
“阿罗纳克斯先生,我们现在是在西经137°15′……”
“您是根据哪种子午线算的呢?”我急切地问,想从船长的回答中知道他的国籍。
“先生,”他答复我,“我有各种不同的精密时计,根据巴黎、格林尼治和华盛顿子午线来计算都行。但因为您的关系,我以后将根据巴黎子午线计算。”
这个回答没使我得到什么,我于是点了点头,船长接着又说:
“根据巴黎子午线计算,我们现在是在西经137°15′,北纬30°7′,也就是说,距日本海岸大约300海里。今天是11月8日,就在这个中午,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海底探险旅行了。”
“愿上帝保佑我们!”我答道。
“教授,”船长又说,“我现在让您做您的研究。我的航线定在海面下50 米深处,东北偏东方向。这些是标记清晰的航海图,从上面您可以对照我们的航路。这个客厅供您使用,那么,恕我告辞了。”
尼莫船长对我行了个礼,然后出去了。我独自一人,默默地沉思着。我的思绪都集中在这位鹦鹉螺号船长的身上。我将来能否知道这个自称不属于任何国度的怪人究竟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呢?他怀有对人类的那种怨恨,那种惹恼了他的,且可能会令其寻求可怕报复行为的怨恨,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正如龚赛伊曾经说过的“有人给他受过痛苦的”那些被人轻视的学者、天才中的一位?是不是一位现代伽利略,抑或是一名像美国人莫利一样的,其学术生涯由于政治革命而夭折了的科学家呢?这我都还说不准。偶然的机会将我抛到了他的船上,我的生命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冷淡地,但却是客气地收留了我。不过,他从不握我向他伸出的手,而他,也从不向我伸出手来。
整整一个小时,我都沉浸在这些深深的思虑之中,总想揭开这使我十分感兴趣的秘密。后来,我的目光盯着摆在桌上的平面大地图,我把手指放在上面所指出的经纬度相交的那点上面。
海洋跟大陆一样,也有江河。这些江河是特殊的水流,从它们的温度、颜色便可以辨认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暖流。科学确定了地球上五条主要水流的方向:第一条在大西洋北部;第二条在大西洋南部;第三条在太平洋北部;第四条在太平洋南部;第五条在印度洋南部。当里海和咸海与亚洲各大湖汇流,形成一片汪洋的时候,在印度洋南部这个地方,恐怕还存在过第六条水流。
然而,从平面球图上标注的那一点起,伸展出上述暖流中的一条,就是日本人所说的黑水流。它从孟加拉湾流出,热带太阳光线的垂直照射使之变暖,它横过马六甲海峡,沿着亚洲海岸延伸,在太平洋北部呈圆弧形,直至阿留申群岛,顺流冲走樟树树身和当地物产,暖流那种纯靛蓝色与大海大洋波涛形成鲜明对照。鹦鹉螺号即将经过的正是这条水道。我目随着它,看着它消失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之中,我感觉自己正在同它一起奔流而去。而就在这时,尼德·兰和龚赛伊出现在客厅门口。
我的两个老实同伴看见堆在他们眼前的神奇物品惊呆了:
“我们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加拿大人喊,“是在魁北克博物馆吗?”
“如果先生允许的话,”龚赛伊答,“我觉得这看上去更像是桑美拉大厦呢!”
“朋友们,”我回答,同时做个手势,让他们进来,“你们不是在加拿大,也不是在法兰西,而是在鹦鹉螺号船上,在海底下50米。”
“先生这样说,那就肯定是这样了。”龚赛伊回答,“老实说,这个客厅,就是让我这个佛拉芒人看来也要感到惊奇。”
“朋友,你惊奇吧,你好好儿地看吧,因为对你这么能干的一个分类者来说,这里实在有不少的工作可做哩。”
我并不需要鼓动龚赛伊去做。这个老实人早就弯身在玻璃柜子上,同时嘴里已经低声说出了一串博物学家惯用的词汇:腹足纲、油螺科、磁贝属、马达加斯加介蛤种,等等。
这个时候,对贝类学几乎一无所知的尼德·兰问我关于我跟尼莫船长会谈的情形。他问我,我是否发现他是哪一国人,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把我们拉到多深的海底去?他问了许多问题,我简直来不及回答他。
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了他,或者还不如说,我把我所不知道的也全部告诉了他。然后我又问他,他看到了些什么或者听到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加拿大人回答,“就连这船上的人影都没有看见一个!真的,是不是他们都是电人?”
“电人?”
“说真的,我是要这样想呢。可是您,阿罗纳克斯先生,”尼德·兰问,他总是不忘记他的那个念头,“您就不能告诉我这船上一共有多少人吗?10个,20个,50个,还是100个?”
“尼德·兰师傅,这我可说不上来。而且您要相信我,现在您必须抛弃您那夺取或逃出鹦鹉螺号的念头。这船是现代工业的杰作,我要是没能看见它,我不知道会怎么遗憾呢!许多人要是能看看这些神奇事物,也就乐意接受我们的处境了。所以您必须保持镇静,我们要想办法观看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
“观看!”捕鲸手喊道,“除了这钢板的监牢,我们可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将来也看不见什么!我们是在瞎跑,我们是在盲目行驶……”
尼德·兰说这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客厅忽然全黑了,而且是绝对的黑暗。明亮的天花板失去了光辉,光亮熄灭得如此快速,我的眼睛有一种疼痛的感觉,这跟在相反的情形中,即从漆一般的黑暗中忽然出现最辉煌的光明所发生的感觉一样。
我们都默不作声,动也不敢动,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事件等着我们,是福还是祸呢?我们听到一种滑动的声音,仿佛鹦鹉螺号两侧的壁板动起来了。
“现在真的要完蛋了!”尼德·兰说。
“水母目!”龚赛伊低声说。
突然,光线透过两个椭圆形的孔洞,从客厅周围射了进来。海水在电光的照射下显得明晃晃的,两块水晶玻璃将我们同海水隔开。起初,我想到这脆弱的隔板会发生破裂,心里就不住地发颤,但强有力的铜框架支撑住了隔板,并赋予它近乎无限的抵抗力。
在鹦鹉螺号周围1海里的范围内,海水清晰可见。多么光怪陆离的景象啊!无论多么高明的妙笔也描绘不出来!谁能描绘光线穿过透明的水流所产生的奇特景象呢?谁能描绘那光线照在海洋上下两方渐次递减的柔和光度呢?
我们都知道海洋的透明性,我们都知道海水的清澈胜过山间清泉。海水中所含有的矿物质和有机物质,甚至可以增加它的透明性。在太平洋中的某部分,例如在安的列斯群岛,145米深的海水可以让人看见水底下面的沙床,十分清澈,而阳光的穿透力好像直至300米的深度方才停止。但是,在鹦鹉螺号所走过的海水中,电光则是在水波中出现。这就不再是明亮的水,而是流动的光了。
如果我们接受艾伦伯格的假设,认为海底是有磷光照明的,那么,大自然一定给海中的居民保留下了一种最奇妙的景象,而我现在看见这种光的无穷变化,就可以想象出这景象是多么的美丽。客厅的每一边都有窗户开向这未曾经过探测的深渊。客厅内的黑暗使得外面的光亮变得愈发明显,在我们看来,这片纯水晶体就像是一座巨大水族馆中的玻璃。
鹦鹉螺号好像不动了,这是因为水中没有了标识的缘故。可是,时时有那些船头冲角分开的水线纹,在我们眼前迅速地向后掠过。
我们简直心醉神迷了,胳膊肘靠在玻璃窗面前,我们谁都未曾打破这由于惊愕所引起的静默。这时,龚赛伊说话了:
“尼德·兰,您不是要看吗?现在您看吧!”
“真新鲜!真新鲜!”加拿大人说,他忘记了他的愤怒和他的逃走计划,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人们还可以从更远的地方来叹赏这般景象呢!
“啊!”我喊道,“我现在明白这个人的生活了!他自己另外造了一个世界,为他保留下最惊人的神奇!”
“可是鱼在哪里呢?”加拿大人说,“我看不到鱼呀!”
“尼德·兰,好朋友,”龚赛伊回答,“那没有关系呀,因为您不认识它们哩。”
“我不认识鱼?我可是打鱼的人!”尼德·兰喊道。
关于这个问题,这两个朋友间发生了争论,因为他们都认识鱼,但认识的方式却不同。
大家都知道鱼类是脊椎动物门中的第四纲和最后一纲。鱼类的确切定义是:“有双重循环功能的,冷血的,用鳃呼吸的,生活在水中的脊椎动物”。鱼类由不同的两类构成:硬骨鱼类,即脊骨是由硬骨脊椎构成的,和软骨鱼类,即脊骨是由软骨脊椎构成。
加拿大人也许懂得这种区别,但龚赛伊知道得更多,而现在他跟尼德·兰有了友谊,大家很要好,他不能承认自己的知识比尼德·兰差,所以他这样说:
“尼德·兰,不错,您是个打鱼能手,一位很能干的捕鱼人。您曾经捕捉过许多这些很有趣的动物。不过我可以跟您打赌,您不知道人们怎样把它们分类。”
“不,我知道,”捕鲸手很正经地回答,“人们把它们分为可吃的和不可吃的!”
“这是美食家的分类法,”龚赛伊回答,“请您告诉我,您知道硬骨鱼类和软骨鱼类之间存在的差别吗?”
“大概晓得吧,龚赛伊。”
“您知道这两大组鱼类的小分类吗?”
“我想我不至于不知道。”加拿大人回答。
“尼德·兰,请您听我说吧,请您好好儿地记下来吧!硬骨鱼类可分为6目。第一目是刺鳍鱼,上鳃是完整的,能动的,鳃作梳子状。这一目共有15科,就是说,包括已经知道的鱼类的四分之三。这目的典型是:普通鲈鱼。”
“相当好吃的鱼。”尼德·兰回答。
龚赛伊又说:“第二目是腹鳍鱼,腹鳍垂在肚腹下面和胸鳍后边,而不是长在肩骨上;这一目分为5科,包括大部分的淡水鱼。这目的典型是:鲤鱼、白斑狗鱼。”
“呸!”加拿大人带着不屑的神气说,“是些淡水鱼。”
“第三目是副鳍鱼,”龚赛伊说,“腹鳍是接在胸鳍的下面并且挂在肩骨上。这一目共有4科。典型是:鲽鱼、比目鱼、鳎目鱼、大比目鱼等。”
“美味的鱼!好吃的鱼!”捕鲸手喊道,他只是从口味的观点来看鱼类。
“第四目是无腹鳍鱼,”龚赛伊兴致丝毫不减地又说,“鱼身很长,没有腹鳍,身上有很厚的带点儿黏性的皮,这一目只有一科。典型是:鳗鱼和电鳗鱼。”
“味道一般,味道一般。”尼德·兰答。
“第五目是总鳃鱼。”龚赛伊说,“鳃是完整自由的,但由许多小刷子构成,一对一对地排在鳃环节上。这一目只有一科。典型是:海马鱼、尖嘴鱼。”
“不好吃!不好吃!”捕鲸手回答。
龚赛伊说:“最后第六目是固颌鱼,颌骨固定在颌间骨边上,形成上颚。上颚的颚弓与头盖骨缝联结在一起,固定不动。这一目没有真正的腹鳍,由两科组成。典型是:河豚,翻车鱼。”
“这些鱼,用锅来煮,连锅也丢脸!”加拿大人喊道。
“尼德·兰,这下您明白了吗?”博学的龚赛伊问。
“一点儿也不明白,龚赛伊,”捕鲸手回答,“不过请您说下去吧,既然您对这很感兴趣。”
“至于软骨鱼类,”龚赛伊很冷静地又说,“那就只有三目。”
“这更省事了。”尼德·兰说。
“第一目,圆口鱼,鳃合成为一个转动的圈环,鱼鳃开合有许多小孔,这一目只有一科。典型是八目鳗。”
“这鱼我们很喜欢吃。”尼德·兰回答。
“第二目,板鳃类鱼,它们的鳃类似圆口鱼的鳃,但下鳃活动。这一目是软骨鱼类中最重要的,共有两科。典型是:鲨鱼和鳐鱼。”
“什么!”尼德·兰喊道,“鲨鱼和鳐鱼是在同一目中?好吧,龚赛伊朋友,为了鳐鱼的利益起见,我劝您不要把它们放在一个鱼缸里吧!”
龚赛伊回答:“第三目是鲟鱼目,鱼鳃只由一条覆盖着鳃盖骨的缝开合,跟通常的鱼类一样。这一目分为四属。典型是:鲟鱼。”
“啊!龚赛伊好朋友,您把最好吃的放在最后了——至少我的意见是这样。现在您的话说完了吗?”
“是的,完了,尼德·兰,不过您得注意,尽管您知道了这些,却仍然是一无所知,因为科又分为属,属又分为亚属,分为种,分为变种……”
“好了,龚赛伊,”捕鲸手俯身到玻璃上说,“这不是各种各样的鱼都游过来了吗,快看!”
“真的!是鱼呀,”龚赛伊喊着,“我们就好像是在鱼缸面前呢!”
“不,”我回答,“因为鱼缸是一个笼子,而这些鱼却有如空中的鸟一般自由自在。”
“好哇!龚赛伊,您现在来说说这些鱼的名目吧,说说这些鱼的名目吧!”尼德·兰说。
龚赛伊回答:“那我可说不上来。这是我主人的事!”
诚然,龚赛伊这个人,这个狂热的分类家,并不是一个博物学家,我想他不一定能分别鲣鱼和金枪鱼的不同。总之他跟加拿大人正相反,加拿大人倒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出这些鱼的名字来。
“是一条引金鱼。”我于是说了。
尼德·兰回答:“是一条中国引金鱼。”
龚赛伊于是低声说:“引金鱼属硬皮科,固颌目。”
毫无疑问,要是把尼德·兰和龚赛伊他们俩合起来,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博物学家。
加拿大人并没有弄错。面前是一群引金鱼,身体扁平,皮肤粗糙。背脊上有针状物,在鹦鹉螺号周围游来游去,晃动着它们尾巴两边的四排尖刺。再没有比它们的外表更令人赞叹的了,上边灰色,下面全白,点点的金黄在波浪的旋涡中间闪闪发亮,多么美丽!在引金鱼中,还有几条鳐鱼,像随风招展的台布,翻来转去,在鳐鱼中我看到了我很喜欢的那种中国鲤鱼,它上半身黑黄色,肚子下面淡淡的玫瑰色,眼睛后面带有三根刺。这种鱼是很少有的一种,拉塞拜德当时甚至都不敢相信有这种鱼,他只在一本日本的图画书中看见过。
在两小时内,整整一大群的水族部队都围绕在鹦鹉螺号周围。它们在戏耍、在跳跃。正当它们以其美丽、光彩和速度作相互竞赛的时候,我辨认出了青色的海婆婆,有双层黑线的海绯鲷鱼,鱼尾呈弓形,白颜色,背上饰有紫色斑点的鰕虎鱼,身体是蓝色,头部是银白色的日本鲭鱼,它是这一带海中值得赞美的鲭鱼,仅以名字就胜过了所有描绘的辉煌的碧琉璃鱼,鱼鳍时而变蓝时而变黄的条纹鲷鱼,尾上配有一条黑带的线条鲷鱼,优雅状裹在六条带中的线带鲷鱼,确实像笛孔一般的笛孔鱼或称海山鹬,其长度达到了一米,日本的火蛇,多刺的鳗鱼,眼睛小巧而有神,大嘴里满是利齿的6 英尺长蛇,等等。
我们始终高度赞叹不已,我们不断地发出惊叹声。尼德·兰说出鱼的名字,龚赛伊加以分类;我就在这些鱼类活泼的姿态和美丽的外形面前,感到极大的喜悦,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机会,可以任意观赏这些动物,它们活生生地、自由自在地在它们生长的天然海水中游来游去。
在我昏花的眼前游过的各种类型的水中动物,简直就是日本海和中国海的全部标本,我对它们实在不能一一列举出来。这些鱼比空中的鸟还多,可能是受电光的吸引,全部向船边游过来了。
突然间,客厅亮了起来。船边的盖板关了起来。迷人的景象消失了。可是很久,我还似做梦般地想着,一直到我的眼光注意到那些挂在墙板上的仪器才清醒过来。罗盘仍是指着东北东方向,气压计指着5个大气压,表示船在50米的深处,而电力测速器表明船只每小时行驶15 海里。
我等着尼莫船长,但他没有出现。大钟正指着5点。
尼德·兰和龚赛伊回到了他们的舱房,我也走进我的房间。晚餐早在房中摆好了。其中有最美味的海鳖做的汤,一盘切成薄片的羊鱼的白肉,鲤鱼肝另做,非常可口,一盘金鲷鱼的肉片,我觉得味道比鲑鱼肉还好。
我晚上一直都在看书,写笔记,思考问题。一会儿瞌睡来了,我就躺在海藻叶做的床上,甜美地入睡。这个时候,鹦鹉螺号正在很快地穿过黑潮暖流,迅速地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