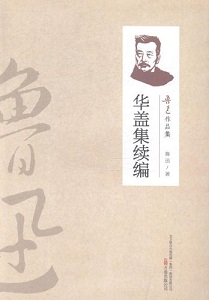思嘉尽管没有看见但却感觉得到,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的那个黑下巴开始在颤动,她不禁浑身震怒。这些女人贬低过南方的军队,滥骂过戴维斯总统,并且诬陷南方人虐待和残杀他们的奴隶,这些思嘉都带着默默的轻蔑听过去了。只要对她有利,她还能忍受对她个人品德和诚实的种种侮辱。但是听到他们用愚蠢的话语伤害这个忠实的老黑奴,她就像一包火药被点着了似的。她朝彼得腰带上挂着的那支大马枪瞧了一会,两只手痒痒地想去摸它。她们这些人该杀,这些傲慢无知、气焰嚣张的征服者真该杀啊!但是她咬紧牙关,直到两颊的肌肉都鼓出来了,仍然不断提醒自己时机尚未来到,到时候她要告诉北方佬们她究竟是怎样看他们的。是的,总有一天。天哪,一定!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呢。
“彼得大叔是我们自己家里人,”她的声音有点发抖,“再见。咱们走吧,彼得。”
彼得突然朝马背上抽了一鞭,把马吓得往前一跳,马车便颠簸着离开了。思嘉听见那个缅因州女人用一种困惑不解的语气说:“她家里人?不见得是她的亲戚吧?他黑得很厉害呢。”
该死的家伙!她们应当从地球上被清除出去。等到我有很多钱了,我一定要往她们脸上啐唾沫。我一定要——
她朝彼得瞅了一眼,看见有颗泪珠正从他鼻梁上淌下来。顷刻间一种因他受辱而引起的悲伤与怜惜的感情压倒了她,使她的眼睛也酸痛了,就好像看见有人毫无理智地虐待了一个孩子一样。这些女人伤害了彼得大叔——这个同老汉密尔顿上校一起参加过墨西哥战争的彼得,他曾经将濒死的主人抱在自己怀里,后来将媚兰和查尔斯抚养成人,接着又伺候不中用而愚蠢的皮蒂帕特小姐,逃难时保护她,投降之后又弄了一匹马越过战后的一片废墟,将她从梅肯带回家来——就是这样一位彼得呀!而她们居然说她们决不信赖黑鬼!
“彼得,”她把手放在他那瘦削的肩膀上,声音在发颤,“你要哭,我可替你难为情了。你管她们干什么呢?她们只不过是些该死的北方佬罢了!”
“他们当着俺的面说这种话,好像俺是头骡子,不懂她们的话——好像俺是个非洲人,一点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彼得说着,用鼻子响亮地哼了一声,“她们还叫我黑鬼,可从来也没有哪个白人这样叫过我。她们说我是老宝贝,说黑鬼一个也不能信赖!我不能信赖吗?老上校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你,彼得,请你照看我的孩子们吧。好好照顾你那年轻的皮蒂帕特小姐,’他说,‘因为她像个蚂蚱一样没有头脑。’这些年来俺就一直好好照顾她——”
“除了大天使加百列[1],谁也不能比你更会安慰体贴人了,”思嘉安慰他说,“没有你,我们简直就无法活呢。”
“是的,姑娘,谢谢你的好意。这些事情我知道,你知道,但他们这些北方佬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怎么跑来管我们的事呢,思嘉小姐?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咱们这些支持南部联盟的人。”
思嘉没说话,因为她那股在北方佬女人面前没有发泄出来的怒火仍然在心里燃烧。两人默默地赶车回家。彼得不再用鼻子吸气,他的下嘴唇开始慢慢突出来,直到长长地伸出来吓坏人了。如今最初的伤痛正在平息,他却越发气愤起来。
思嘉想:北方佬是些怎样该死的怪人啊!这些女人似乎觉得既然彼得是黑人,他就没有耳朵能听,就没有像她们那种脆弱的感情,容易受到伤害了。她们不懂得对待这些黑人应该亲切一些,把他们当做孩子,教导他们,夸奖他们,疼爱他们,责骂他们。她们根本不了解这些黑人,不了解这些黑人和他们原先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居然发动一场战争来解放他们。既然解放了黑人,他们又不愿和黑人打交道,只一味利用他们来恐吓南方人。他们并不喜欢黑人,不信任他们,也不理解他们,然而他们却还不断地在大喊大叫,说南方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同黑人相处下去。
不信任黑人!思嘉信任他们远远超过大多数白人,肯定比对北方佬要信任得多。黑人身上有忠诚、耐劳和仁爱的品德,这些是任何严峻的情势也无法使之破裂,金钱也无法买到的。她想起面对北方佬入侵时仍然留在塔拉的那几个忠心耿耿的黑人。他们可以逃走,或者参加军队去过闲荡的生活,可是他们却留下来了。她想起迪尔茜怎样在棉花地里挨着她干苦活,想起波克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去邻居鸡窝里偷鸡给全家吃,想起嬷嬷怎样陪伴她到亚特兰大来,不让她做错事。她还想起一些邻居家的仆人,他们怎样保护那些男人到前线去了的女主人,怎样护送她们逃过战争的恐怖,怎样看护受伤的人,掩埋死者,安慰生者,干活,行乞,偷窃,为了让餐桌上有吃的便什么都干。而且即使现在,“自由人局”向他们许了各种各样惊人的诺言,可他们还是牢牢跟着他们的白人主子,而且比过去当奴隶时干得更加辛苦。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北方佬都不理解,而且永远也不会理解。
“不过,是他们解放了你们呢。”思嘉大声对彼得说。
“不,小姐!他们没有解放俺。俺也不要让这帮废物来解放,”彼得生气地说。“我还是属于皮蒂小姐。要是俺死了,她也得把俺埋在汉密尔顿家的坟地里,因为俺是属于这里的呀……俺要是告诉皮蒂小姐,你怎样让北方佬女人侮辱了我,她准会非常生气的。”
“我可没有干这种事呀!”思嘉吃惊地喊道。
“你就是干了嘛,思嘉小姐,”彼得说着,嘴唇皮往外伸得更长了,“重要的是你和俺都没有理由去跟北方佬打交道,让他们可以侮辱俺。要是你不跟她们说话,她们就不会有机会把俺比做骡子或非洲人了。而且,你也没替俺责备她们呀。”
“我还是责备她们了呀!”思嘉说,显然被这种批评刺痛了。“我不是告诉她们你是我们家自己人吗?”
“这不算责备,只是事实罢了,”彼得说,“思嘉小姐,你没有理由跟这些北方佬去打交道。没有哪家的小姐像你这样。你决不会看见皮蒂小姐理睬那帮废物的。要是她听见她们说俺的那番话,她准会不高兴的。”
彼得的批评,比起弗兰克和皮蒂姑妈或者邻居们的话来,更使她觉得伤心。她感到那样恼火,恨不得使劲摇晃这个老黑奴,直到他那两片没牙的牙床碰得嘎嘎响为止。彼得说的倒全是真话,不过她深恨这些话出自一个黑人而且是自家黑奴之口。在自家仆人心目中都得不到尊敬,这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简直是最丢脸的事。
“一个老宝贝呢!”彼得嘟囔着说,“我想皮蒂小姐听了这种话决不会再让俺给你赶车了。肯定不会,小姐!”
“皮蒂姑妈还会让你照样给我赶车的,”她厉声说,“所以,咱们别再提这事了。”
“俺想俺的背快出毛病了,”彼得阴郁地警告说,“俺的背现在就痛得要命,几乎直不起来了。只要俺的背一痛,小姐就不会让俺再赶车了……思嘉小姐,要是咱自家人都不赞成你的做法,就算那些北方佬和白人渣滓都捧你,那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呢。”
这句话对于思嘉当前的处境可真是概括得好极了,致使她陷入一种无比愤怒的沉默中。是的,征服者们确实都对她表示赞许,但她的家人和邻居却不那样。她知道全城的人都在纷纷议论她。而现在连彼得也对她那样反感,甚至不愿跟她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了。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
在这之前,她对人家的议论是根本不在乎的,不但不在乎,而且有点瞧不起。但彼得的话在她心中点起了愤恨的怒火,迫使她采取守势,使她突然对邻居如同对北方佬一样厌恶起来。
“他们管我干什么呢?”她想道,“他们准以为我喜欢跟北方佬交往,喜欢像干农活的黑奴一样卖苦力吧。他们这样做,只不过给我难上加难罢了。但是,任凭他们怎样想,我不管它,我才不让自己去管呢。而且目前我也管不起。不过有一天——有一天——”
啊,总会有一天的!等到她的生活又有了保障的那一天,她便可以交抱着两臂舒坦地休息,成为跟母亲爱伦那样的贵妇人了。她会像贵妇人那样娇弱,躲在家里,那样一来,人人都会夸奖她了。啊,如果她又有了钱,她会变得多么了不起啊!到那个时候,她会让自己变得像爱伦那样和蔼可亲,处处为别人着想,处处都注意礼仪了。她不会再从早到晚地担惊受怕,因为生活会变得平静而悠闲呢。她将有时间跟她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听他们念课文。遇到冗长而暖和的下午,那些上等女人会来拜访她,在一片塔夫绸裙的窸窣声和棕榈扇刺耳而有节奏的噼啪声中,她会叫仆人给她们送上茶水和可口的三明治,以及蛋糕,等等,同她们悠闲地聊天,消磨时光。对于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她会十分和蔼地对待他们,给穷人送去一篮篮的食物,给病人送去羹汤和果冻,同时在漂亮的马车里向那些不如她得意的人“装腔作势”一番。她会像她母亲过去那样成为一个真正南方式的上等女人。到那时候,大家都会像爱爱伦那样爱她,会赞扬她多么无私,会称她为“慷慨的夫人”。
她对未来的种种想法感到很有乐趣,这一点,尽管她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想要变得慷慨无私或和蔼可亲,但总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她所希图的只是具有这些品德的好名声。不过她那副脑筋动得太粗了,根本辨不出这类细微的差别来。只要有那么一天,她有了钱,人人都赞许她,就足够了。
有一天!但不是现在。现在不行,不管人家怎么说她。现在还不是成为一个伟大女性的时候。
彼得的话果然说对了。皮蒂姑妈真的激动起来,彼得的背也一夜之间痛到确实无法再赶车了。从此思嘉只好自己一个人赶车,她手心上的茧子又重新磨起来了。
就这样,春天的几个月过去了,四月的冷雨天结束,温润芳菲的五月天气随之而来。这几个星期思嘉一直被一大堆工作和忧虑所包围。肚子愈来愈大,行动愈来愈不方便,老朋友们愈来愈冷淡,家里人则愈来愈体贴,愈来愈觉得焦急,愈来愈摸不着头脑,不知究竟是什么在驱使她这样干。在这些焦虑不安和奋力挣扎的日子里,她眼中只有一个人是可以依靠和能够理解她的,那就是瑞德·巴特勒。说也奇怪,在这方面居然所有的人中间偏偏是他,因为他这个人像水银一样飘忽不定,像一个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一样邪恶倔强呢。但是他同情她,而这一点是她从任何别的人身上都得不到而且也从不指望得到的。
瑞德经常出城,神秘地去新奥尔良,可从来不解释去干什么,只是思嘉总带点醋意,觉得肯定同某个女人——或者一些女人有关。但自从彼得大叔拒绝替她赶车之后,瑞德留在亚特兰大的时间便愈来愈长了。
在城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家名叫“时代少女”的酒馆楼上赌博,或者在贝尔·沃特琳的酒吧间里跟那帮比较有钱的北方佬和提包党人亲切交谈赚钱的计划,这使城里人对他比对他那班密友更加厌恶。他现在不来皮蒂家拜访了,这也许是为了尊重弗兰克和皮蒂的感情,因为思嘉现在的处境很微妙,男人去拜访会使弗兰克和皮蒂受不了。不过她几乎每天都会偶然遇见他。当她赶车经过桃树街和迪凯特街那段偏僻的路到木厂去时,他屡次骑马追上了她。他总是勒住缰绳跟她谈一会儿话,有时将马拴在她的马车背后,替她赶着车在两个木厂之间巡视一番。这些天来,她尽管不承认但实际上是比过去更容易疲劳了,因此也乐意让他这样做,心里还暗暗感激他。他每次都在他们回到城里之前便离开她,可是城里人还是全知道了他们相会的事情,因此这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些新的闲谈资料,在思嘉触犯礼仪的那一长列条目中也添上了新的一条。
她有时猜想,他们的这些相遇难道完全是偶然的吗?几个星期过去了,随着城里黑人闹事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他们相遇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不过为什么他偏偏在目前她的模样最难看的时候来找她呢?要是说从前他对她有过什么不良企图的话,那么现在他肯定没有,而且连以前究竟有没有,她现在也开始怀疑了。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嘲笑地提到他们在北方佬监狱中那令人气恼的场面了。他再也没有提起艾希礼以及她爱他的事,更没有说什么他“垂涎她”那类没教养的粗话。她想最好还是别无事找碴,不必去要求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经常相遇。最后她认定,瑞德是因为除了赌博没有什么别的可干,而且在亚特兰大又很少有知己,因此找她无非就是为了找个伴而已。
且不管瑞德的理由是什么,反正思嘉发现他这个伴还是最受欢迎的。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她发牢骚,说她怎样失去了顾客,怎样放了呆账,约翰逊先生如何欺诈她,以及休多么无能,等等。他听说她赚钱了,便鼓掌喝彩,而弗兰克听了只会溺爱地微微一笑,皮蒂更是茫然,只能“哎呀”一声完事。她很清楚瑞德一定经常在帮她揽生意,因为他很熟悉或认识所有阔绰的北方佬和提包党人。但是,他却始终否认自己帮了什么忙。她了解他的为人,而且从来也不信任他,不过只要看见他骑着那匹大黑马沿林荫路转弯过来,她便会高兴得打起精神,有点情不自禁了。等到他跳进她的马车,从她手里接过缰绳,对她说几句俏皮话,她更觉得自己既年轻又快活,又娇媚动人,尽管满怀忧虑,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也全不在意了。她对他几乎可以无话不谈,不用考虑隐瞒自己的动机或自己的真实意见,也从来没有过觉得无话可说的情况,像跟弗兰克在一起的时候那样——或者,如果她对自己坦白的话,甚至像跟艾希礼在一起似的。不过,当然,她同艾希礼的谈话中有那么多东西由于面子关系是不好说出来的,因此也就不好多加评论了。总之,有一个像瑞德这样的朋友,很使她感到欣慰,何况目前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又决定对她规规矩矩。这非常令人宽慰,因为近来她的朋友实在太少了。
“瑞德,为什么这个城里的人都这样卑鄙下流,都这样议论我呢?”就在彼得大叔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不久她暴躁地这样问他,“他们说得最糟糕的人,到底是我还是提包党人,都很难说了!其实我只不过管我自己的事,从没干过什么坏事,而且——”
“要说你没干过什么坏事,那只是因为你没有碰到机会罢了,而且也许他们模模糊糊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唔,请你严肃一点吧!他们都把我气疯了。我所干的也不过是想弄点钱嘛,而且——”
“就因为你所干的跟别的女人所干的不一样,而且你又取得一点小小的成就。正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这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宽恕的一种罪恶。只要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该死!思嘉,就因为你的木厂办得成功,这对于每一个没有成功的男人来说,便是一种耻辱。你要记住,一个有教养的女性应该待在家里,应该对这个复杂而残酷的世界一无所知才好。”
“但如果我一直待在自己家里,我就会没有什么好待的了。”
“总的说来,就是你应该高雅而自豪地去饿肚子。”
“嘿,胡说八道!你就看看梅里韦瑟太太吧。她在卖馅饼给北方佬,这可比开木厂更糟呢。埃尔辛太太在给人家缝缝补补,招些房客。至于范妮,她是在瓷器上画些谁也不要看的丑东西,可是为了帮助她谁都去买,而且——”
“不过你没有看到问题的点子上,我的宝贝儿。她们的事业都不得意,所以没有触犯那些南方男人强烈的自尊心。这些男人还会说:‘可怜而又可爱的傻娘们,她们干得多苦呀!不过那也好,就让她们去觉得自己是在帮忙吧。’再说,你提到的那些太太可并不觉得干活是一种享受。她们总让大家知道,她们现在干活是不得已的,一等到有个男人来解放她们,让她们摆脱这种不适合女人的劳动,她们就不干了。因此大家都为她们感到难过。可是你呢,你显然是喜欢干活的,而且显然不想让任何男人来管你的事,所以也就没有人会为你感到难过了。就为这一点,亚特兰大人也绝不会原谅你。因为替别人感到难过是一桩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呀。”
“有时我真希望你能严肃一点。”
“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句东方的格言:‘尽管狗在狂吠,大篷车继续前进。’让他们叫去吧,思嘉。我想什么东西也无法阻挡你这辆大篷车的。”
“但是我赚点钱,他们凭什么要管呢?”
“思嘉,你可不能什么都想要呀!你要么像现在这样不守妇道只管赚钱,同时到处受人家的冷笑,要么就自命清高,受穷挨饿,赢得许多朋友。可是你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我可不愿受穷,”她马上说,“不过,这是正确的选择吧,你说呢?”
“如果你最需要的是钱。”
“是的,我爱钱胜过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
“那么你就只有这个惟一的选择了。不过这一选择,就像你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那样,附带着一种惩罚,那就是寂寞。”
这话使她沉默了片刻。那倒是真的。她静下来想想,确实是有点寂寞——因为缺乏女性的伴侣而感到寂寞。在战争年代,她情绪低落时可以去找爱伦。自从爱伦去世之后,一直总还有媚兰和她做伴,虽然她和媚兰除了在塔拉一起干苦活以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现在一个伴也没有了,因为皮蒂姑妈除了她自己那小小的闲谈圈子之外,对人生是没有什么想法的。
“我想——我想,”她开始犹豫地说,“就跟女人的关系而言,我始终是寂寞的。但亚特兰大的女人之所以讨厌我,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在工作。反正她们就是不喜欢我。除了我母亲,没有哪个女人真正喜欢过我,就连我那些妹妹也是如此。我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不过即使在战前,甚至在我跟查理结婚之前,女人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就似乎都不赞成——”
“你忘了威尔克斯太太了吧,”瑞德的眼睛恶意地闪亮了一下,“她总是完全赞成你的嘛。我敢说,除了杀人,你无论干什么她都会赞成的。”
思嘉冷酷地想道:“她甚至也赞成杀人呢。”接着便轻蔑地笑起来。
“啊,媚兰!”她忽然想起,但紧接着就悲叹道:“只有媚兰是惟一赞成我的女人,不过那肯定也不是我的什么光荣,因为她根本连一只母鸡的见识都没有。要是她真有点见识——”她有点发窘,没有说下去了。
“要是她真有点见识,她会看到有些事情她是无法赞同的,”瑞德替她把话说完,“好了,你当然对于这些比我更清楚。”
“啊,你这该死的记忆力和臭德行!”
“对于你这种不公平的粗鲁劲儿,我理应不予理睬,现在就算了吧,让我还是言归正传。我看你得自己打定主意。要是你与众不同,你就得与世隔绝,不仅与你的同龄人,而且还得与你的父辈那一代,以及你子女那一代,全都隔绝。他们绝不会理解你,无论你干什么,他们都会表示愤慨。不过你的祖父母或许会为你感到骄傲,或许会说:‘这个女儿跟她父亲一模一样了,’同时你的孙子辈也会羡慕地叹息:‘我们的老祖母准是个十分泼辣的人物呢!’他们都想学你。”
思嘉给逗得大笑起来。
“有时候你真能悟出个真理来!我的外祖母罗毕拉德就是这样。以前我只要一淘气,嬷嬷就拿她来警戒我。外祖母像冰一样冷酷,对自己和别人的举止都很严格,但是她嫁了三次人,引起那些情敌为她决斗过无数次,她抹胭脂,穿领口低得吓人的衣服,而且没有——嗯——不怎么喜欢穿内衣。”
“所以你非常佩服她,尽管你还是尽量想学你的母亲!我有个祖父,是巴特勒家族的,他是个海盗。”
“不是真的吧!是让俘虏蒙着眼走船板的那种海盗?”
“我敢说只要那样能弄到钱,他是会让人蒙着眼走船板的。总之,他搞到好多钱,后来留给我父亲一大笔遗产。不过家里人总是小心地称他为‘船长’。在我出生之前很久,他在一家酒馆跟人吵架时被打死了。不用说,他的死对于子女倒是一大解脱,因为这位老先生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酒一落肚便忘记自己是个退休的船长,一味诉说过去的经历,把他的儿女们都吓坏了。不过我很钦佩他,而且竭力想更多地模仿他而不是我自己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位和蔼可亲的绅士,有许多体面的习惯和虔诚的格言——所以你看事情就是这样。我保证你的孩子们不会赞成你,思嘉,就像梅里韦瑟太太和埃尔辛太太现在不赞成你这样。你的孩子们或许会是些吃不了苦,缺乏男子汉气质的人,因为一般吃过苦的人的子女往往是这样。而且对他们更糟的是,你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大概已下定决心不让他们去经历你所经历过的苦难了。这可全错了。吃苦要么使人成材,要么把人毁掉。所以你就得等待你的孙子辈来赞同你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孙子辈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你这个‘我们’是不是暗示我和你会有共同的孙子辈呀?去你的吧,肯尼迪太太!”
思嘉立刻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脸涨得通红。叫她难为情的不只是他那句开玩笑的话,因为她突然想到了自己这愈来愈粗的腰身。他俩谁也没有提到她怀孕的事,因为她跟瑞德在一起时总是把膝毯一直盖到腋窝底下,即使天气很暖和也是这样;她总以女人的习惯安慰自己,觉得这样一盖人家就看不出来。现在发现他已经知道,便突然恼羞成怒,受不了了。
“你给我滚下车去,你这个下流坯。”她声音颤抖地说。
“我才不会做这种事情,”他心平气和地回答,“等你还没到家天就要黑了,这里又来了一帮新的黑人,就住在泉水附近的帐篷和棚屋里,听说都是些下流的黑鬼。我看你又何苦给那些容易感情冲动的三K党人制造一个理由,让他们今天夜里穿上睡袍出去奔跑呢。”
“你滚吧!”她喊叫着,使劲去夺他手里的缰绳,可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向她袭来。瑞德立刻勒住马,递给她两条干净的手帕,又相当熟练地把她那个歪在马车边上的脑袋托起来。傍晚的太阳从一片新长出嫩叶的树林中斜照过来,暂时织成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金黄碧绿的漩涡。当这阵发晕作呕过去之后,她便双手捧住头,不胜羞愧地哭起来。她不仅在一个男人面前呕吐——这件事本身就尴尬得可怕,足以把一个女人吓坏了——而且这样一来,她怀孕这一丢脸的事也就昭然若揭了。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勇气正面看他了。这件事偏偏发生在他跟前,在这个从来不尊重妇女的瑞德跟前呀!她一边哭,一边准备听他说出一些叫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粗鲁打趣的话来。
“别傻了,”他平静地说,“你要是觉得难为情而哭,那才傻呢。来吧,思嘉,别耍小孩脾气了。你本来就该知道,我又不是瞎子,早已看出你怀孕了。”
她以万分惊恐的语气“啊”了一声,然后用两手紧紧捂住绯红的面孔。“怀孕”这个字本身就把她吓坏了。弗兰克每次提到她怀孕时总是难为情地用“你那状况”来表示。她父亲杰拉尔德在不得不提起这类事情时也往往微妙地用“坐房”这样的字眼,而女人则体面地把怀孕说成“在困境中”。
“你要是以为我不知道,你可真是个小孩子了,尽管你总用膝毯把自己捂得严严的。当然,我早知道了。要不然你想我为什么老是——”
他突然打住不说了,于是两人都沉默着。他提起缰绳,朝马吆喝了一声,然后继续心平气和地说下去。随着他那慢条斯理的声调高兴地在她耳边浮动,她面孔上的红晕也逐渐消退了。
“我没想到你这样容易激动,思嘉。我原以为你是个有理智的人,可现在失望了。难道你心中还能有羞怯之感?我恐怕自己向你提起这件事情就不能算是上等人了。其实,我也知道我不是上等人,就凭我在孕妇面前竟不觉得发窘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明我觉得可以把她们当做正常人看待——为什么能看天看地或看任何别的地方,就不能看她们的腰围,然后却偷偷向那里瞥一两眼——我以为这才是最不礼貌的呢!我干吗要来这一套呀?这完全是正常的情况嘛。欧洲人就比我们明智多了。他们是要给那些快要做母亲的人道喜的。尽管我不想建议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做,不过那比我们这种设法回避的态度毕竟要明智些。这是一种正常情况,女人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而不需要躲在闺房里好像犯了罪似的。”
“骄傲!”思嘉压低嗓门喊道,“骄傲——呸!”
“难道你不觉得有个孩子值得骄傲吗?”
“啊,天哪,决不!——我恨孩子!”
“你指——恨弗兰克的孩子?”
“不——不管谁的孩子都恨。”
霎时间她对自己的再次漏嘴感到懊丧,但他还是轻松地继续谈着,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似的。
“那么我们就不一样了,我喜欢孩子。”
“你喜欢?”她抬起头来喊道,对他的话感到如此吃惊,竟忘了自己的窘境,“你多会撒谎呀!”
“我喜欢小毛头,也喜欢小孩子,要等到他们开始长大,养成大人的思维习惯和大人撒谎骗人的本领并变得下流之后,才不喜欢了。这对你也不会是什么新闻,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韦德,虽然他还不是个很理想的孩子。”
思嘉想这倒是真的,并突然感到惊异起来。他确实好像很愿意跟韦德玩儿,并且经常给他带礼物来呢。
“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可怕的话题谈开了,而且你承认不久的将来你就要有个孩子,那么我现在就把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想跟你说的话说出来吧。有两件事情。第一,你单独赶车是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一点,而且大家也跟你说够了。即使你个人并不在乎你是否会被人强奸,你也得考虑考虑后果呀。由于你的固执,你可能给自己惹出事来,那时本城一些豪侠的男人便不得不去吊死几个黑人替你报仇。这就会招致北方佬对他们进行惩罚,有些人也许会被绞死。你有没有想到过,那些上等女人之所以不喜欢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怕你的行为会给她们的儿子丈夫惹出大祸来?再说,要是三K党人把黑人处理得多了,北方佬便会对亚特兰大人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结果使人们觉得连谢尔曼也好像是天使了。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因为我一直跟北方佬关系很好。说起来也难为情,他们待我就像自己人一样,所以我听见他们公开这样说过。他们要彻底消灭三K党,为此不惜再次烧毁这整个城市,并且把十岁以上的男人全都绞死。这会伤害你的,思嘉。你的钱可能也保不住了。谁也说不准一旦大火起来会烧到哪里为止。没收财产,提高税金,对可疑的女人课以罚款——这些办法我都听他们提出过。三K党人——”
“你认识三K党人吗?像托米·韦尔伯恩,休,或者——”
瑞德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是个叛徒,变节者,流氓。难道我可能知道吗?不过我确实知道那些被北方佬怀疑过的人以及他们发动的一次冒失行动,这些人几乎都被绞死了。虽然我知道你对邻居们上绞架不会感到悲痛,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因为失去你的木厂而伤心的。我从你脸上的固执劲儿看,你肯定不相信我,因此我的话也等于白说了。所以我惟一能说的是请你经常把那支手枪带在身边——而且,只要我在城里,我会尽量出来替你赶车的。”
“瑞德,你真的——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我,你才——”
“是的,我亲爱的,是我那大肆宣扬的骑士精神在促使我保护你。”他那双黑眼睛里的讥讽神色开始闪烁,脸上那副一本正经的表情全都消失了。“还为什么呢?还由于我深深地爱着你,肯尼迪太太。是的,我一直在默默地如饥似渴地想占有你,站得远远地崇拜你;不过我同艾希礼先生一样,也是个高尚的人,我把这一切向你隐瞒了下来。因为,唉,你是弗兰克的妻子,为了名誉,我不能把这些告诉你。不过,就连威尔克斯先生那样讲究名誉的人,有时也免不了要露馅儿,所以现在我也在露馅,把自己的秘密情感向你透露,还有我那——”
“啊,看在上帝分上,请你闭嘴吧!”思嘉打断他说,因为每当他把她弄得像个自高自大的傻瓜时,她总是十分气恼,而且也不愿意把艾希礼和他的名誉作为他们的话题继续谈下去了。于是她说:“你要告诉我的另一件事又是什么呀?”
“怎么,当我正在暴露一颗热爱着、但却被撕碎了的心时,你却想改变话题了?好吧,另一件事是这样的。”他眼里的嘲讽神气又消失了,脸变得阴郁而平静。

“我要你对这匹马想点办法。这匹马脾气太倔,它的嘴像铁一样硬了,你赶起它来一定很累吧,是吗?嗨,要是它想脱缰逃跑,你根本无法制止它。而且如果你被翻到阴沟里,那可能使你和孩子都活不成了。你应该给它戴上一副最重的马嚼子,要不然就让我牵去给你换一匹口头比较嫩、比较驯服的马来。”
她抬起头来朝他那张没有表情但温和的面孔看了看,突然之间她的火气全消了,正如他就她的怀孕作了那番谈话之后她的羞怯反而消失了一样。刚才,当她还巴不得自己死了的时候,他却那样好奇地让她平静下来,心安理得了。现在他变得更加好心,连对她的马都想得非常周到,这不免引起她一阵感激之情,心想为什么他不能始终是这样呢?
“这匹马的确很难赶,”她温柔地表示同意说,“由于不断地使劲拉它,我的胳臂整夜痛得不行。你说怎样对付它最好,就照你的办吧,瑞德。”
他的两眼恶作剧地闪烁着。
“这话听起来倒满甜,很有点女性味道呢,肯尼迪太太。这完全不像你平时那种专横的腔调了。是的,只要对付得当,是可以使你成为一个乖乖地依靠男人的妇女的。”
她的脸一沉,又发起脾气来了。
“这次你非给我滚下车不行,要不我可用马鞭抽你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能容忍你——为什么总尽量对你那么好。你一点礼貌也没有。一点道德不讲,简直就是个——算了,你滚吧。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爬下车来,从车背后解开他那匹马,然后站在黄昏的马路上向她挑逗地咧嘴一笑,这时思嘉也不由得朝他咧咧嘴,才赶着马走了。
是的,他很粗鲁,又很狡猾,他不是一个你能放心跟他打交道的人。你永远也说不准你放在他手里的那把钝刀子,什么时候你稍不防备就会变成最锋利的武器。但是,尽管如此,他毕竟很有刺激性,就像——是的,就像偷偷地喝上一杯白兰地!
这几个月以来,思嘉已经懂得了白兰地的用处。每天傍晚回家,被雨水淋得湿透了,而且由于长时间在车上颠簸,浑身觉得酸痛,这时她除了想起背着嬷嬷那双贼亮的眼睛藏在衣橱顶层抽屉里的那个瓶子之外,便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撑得住了。米德大夫没有想到要警告她,女人在怀孕期间不该喝酒,因为他从未想到一个正派女人也会喝比葡萄酒更烈性的酒呢。当然,在婚礼上喝杯香槟,或者感冒很厉害时上床睡觉前喝杯热棕榈酒,也还是可以的。当然,也有些不幸的女人喝酒,因而使全家的人一辈子丢脸的,正如有些发疯或离了婚的女人,或者像苏珊、安东妮小姐那样相信妇女应该有选举权的女人,也常常喝酒。但是,尽管米德大夫对思嘉有许多地方不以为然,可他还从没怀疑她竟会喝酒呢。
思嘉发现晚餐之前喝一杯纯白兰地大有好处,只要事后嚼点咖啡,或者用香水漱漱口,是不会让人闻出酒味的。为什么人们竟那样可笑,不许妇女喝酒,而男人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得酩酊大醉呢?有时弗兰克躺在她身边直打呼噜,她又睡不着觉,当她躺在那里翻来覆去,为担心受穷、害怕北方佬、怀念塔拉和惦记艾希礼而受尽折磨时,要不是那个白兰地酒瓶,她早已发疯了。只要那股愉快而熟悉的暖流悄悄流过她的血管,她的种种烦恼便开始消失。三杯酒落肚之后,她便会自言自语地说:“这些事情等我明天更能经受得住以后再去想吧。”
但是有几个夜晚,甚至连白兰地也无法镇住她心头的疼痛,这种疼痛甚至比害怕失去木厂还强烈,那是因渴望见到塔拉而引起的。亚特兰大的嘈杂,它的新建筑物,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那挤满了骡马、货车和熙熙攘攘的人群的狭窄的街道,有时似乎使她感到窒息,受不了了。她是爱亚特兰大的,但是——啊,它又怎比得上塔拉那种亲切的安宁和田园幽静,那些红土地,以及它周围那片苍苍的松林啊!哦,回到塔拉去,哪怕生活再艰苦也好!去靠近艾希礼,只要看得见他,听得到他说话,知道他还爱自己,这就足够了。媚兰每次来信都说他们很好,威尔寄来的每一封短笺都汇报棉花的种植和生长情况,这使她的思乡之情愈加深切了。
我六月份要回家去。六月以后我在这里便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我可以回家住上两个月。她想着想着情绪便好起来了。果然,她六月回到了家里,但不是如她所盼望的那样,而是六月初威尔来信说她父亲杰拉尔德去世了。
[1] 按《圣经》,加百列是大天使之一,他慰劳人类并同情人类。他向但以理解释异象,向撒迦利亚预言其妻将生施洗约翰,向马利亚预言耶稣的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