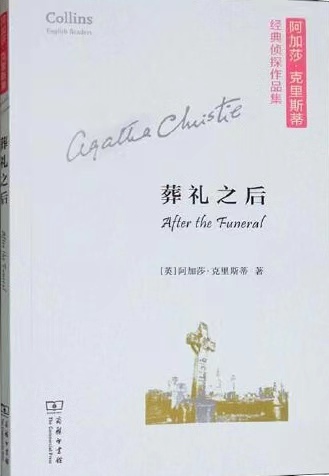第三十七章
四月的一个夜晚,外面下着暴雨,托尼·方丹从琼斯博罗骑着一匹汗水淋漓、累得半死的马来到他们家门口敲门,将弗兰克和思嘉从睡梦中惊醒,吓得心惊肉跳。这是四个月以来思嘉第二次敏锐地感觉到重建时期的全部含义是什么,而且更全面地理解了威尔说“我们的麻烦还刚刚开始”的意思,同时也懂得了艾希礼那天在冷风飕飕的塔拉果园里说的那些凄凉的话是多么正确——他当时说:“面对我们大家的是比战争还要坏、比监狱还要坏——比死亡还要坏的局面呢。”
她第一次与重建时期面对面地接触是她听说乔纳斯·威尔克森在北方佬支持下要将她从塔拉撵出去的时候。但这次托尼的到来以一种可怕得多的方式使她更深切地明白了重建时期的含义。托尼在黑夜里冒着大雨跑来,几分钟之后又重新消失在黑夜里,但就在这短短的片刻之间他拉开了一场新恐怖剧的帷幕,而思嘉绝望地感到这帷幕永远也不会再落下来了。
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来人把门敲打得如此紧急,思嘉披着围巾站在楼梯平台上往下面大厅一看,瞥见了托尼那张黝黑阴郁的面孔,但托尼立即上前把弗兰克手里的蜡烛吹灭了。她赶快摸黑下楼,紧握着他那双冰冷潮湿的手,听他轻轻地说:“他们在追我——我要到得克萨斯去——我的马快死了——我也快饿死了。艾希礼说你们会——可不要点蜡烛呀!不要把黑人弄醒了……我希望尽可能不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
直到厨房里的百叶窗被放下来,所有的帘子也全都拉到了底之后,托尼这才允许点上一支蜡烛,向弗兰克急急忙忙说起来,思嘉则在一旁奔忙着为他张罗吃的。
他没有穿大衣,浑身都湿透了,帽子也没戴,一头黑发贴在小脑壳上。不过,当他一口吞下思嘉端来的威士忌之后,那双飞舞的小眼睛又流露出方丹家小伙子们的欢快劲儿,尽管在当时情况下,它有点令人寒心。思嘉感谢上帝,幸亏皮蒂小姐正在楼上大打呼噜,没有被惊醒,否则她看见这个幽灵准会晕过去的。
“该死的杂种,不中用的家伙,”托尼咒骂着,一面伸出杯子想再喝一杯,“我赶得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要是我不赶快离开这里,我的这张皮就完了,不过这也值得。老天爷作证,真是如此!我现在得设法赶到得克萨斯去,在那里藏身。艾希礼在琼斯博罗跟我在一起,是他叫我来找你们的。弗兰克,我得另外找一匹马,还要一点钱。我这马快要死了——它一路上在拼命赶呢——我今天像个傻瓜,像从地狱里出来的蝙蝠一样从家里跑出来,既没穿大衣又没戴帽子,身上一个子儿也没带。不过家里也真没有多少钱了。”
说着说着他笑起来,开始贪馋地吃着涂了厚厚一层冻黄油的凉玉米面包和凉萝卜叶子。
“你可以把我的马骑去,”弗兰克平静地说,“我手头只有十块钱,不过,要是你能等到明天早晨——”
“啊,地狱着了火,我可等不及了!”托尼加重语气但仍很高兴地说。“或许他们就在我后面。我是急急忙忙动身的。要不是艾希礼把我从那里拉出来,让我赶快上马,我会像个傻瓜似的还待在那里,说不定现在已经被绞死了。艾希礼可真是个好人。”
这么说,艾希礼也被卷进了这个可怕的莫名其妙的事件中去了。思嘉浑身发冷,心快蹦到喉咙里了。北方佬现在抓到了艾希礼没有?为什么弗兰克不问个究竟?为什么他把这一切看得如此平淡,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呢?她忍不住开口提问了。
“是什么事情——是谁——”
“是你父亲过去的监工——那个该死的乔纳斯·威尔克森。”
“是你把——他死了吗?”
“天哪,思嘉·奥哈拉!”托尼怒气冲冲地说,“要是我打算宰了某某人,你不会以为我只拿刀子钝的那面刮他一下就满意了吧?不,天哪,我将他碎尸万段了。”
“好,”弗兰克漫不经心地说,“我向来就不喜欢这个家伙。”
思嘉朝他看了看。这可不像她所了解的那个温顺的弗兰克,那个她发现可以随便欺侮、只会胆小地捋胡子的人。他此刻显得那么干脆、冷静,在紧急情况面前一句废话也不说了。他成了一个男子汉,托尼也是个男子汉,而这种暴乱场合正是他们男子汉显身手的时候,可没有女人的份儿呢。
“不过艾希礼——他有没有——”
“没有。他想杀那个家伙,但我告诉他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萨莉是我的弟媳。最后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同我一起去琼斯博罗,怕万一威尔克森先伤了我。不过我并不认为老艾会受到牵连的。但愿如此。给我在这玉米面包上涂点果酱好吗?能不能再给我包点东西留在路上吃?”
“要是你不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我可要大声嚷嚷了。”
“等我走了以后,如果你想嚷嚷就请便吧。趁弗兰克给我备马的这会儿工夫,我把事情讲给你听吧。那个该死的——威尔克森早就惹了不少麻烦。你知道,他在你的税金问题上做了些什么文章。这只不过是他卑鄙无耻的一个方面罢了。最可恶的是他不断煽动那些黑人。要是有人告诉我,说我能活着看到我可以憎恨黑人的那一天那就好了。那些黑人真该死,他们居然相信那帮流氓告诉他们的一切,却忘了我们为他们做的每一件活生生的事情。现在北方佬又在谈论要让黑人参加选举,可他们却不让我们选举。嗨,全县几乎只有极少几个民主党人没有被剥夺选举权了,因为他们又排除了所有在联盟军部队里打过仗的人呢。要是他们让黑人有选举权,我们就完了。该死的,这是我们的国家呀!并不属于北方佬!天哪,思嘉,这实在无法忍受,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得起来干,即使这意味着另一场战争也在所不惜。不久我们便将有黑人法官,黑人议员——全是些从树林里蹦出来的黑猴子——”
“请你——快点告诉我吧!你到底干了什么?”
“慢点包,让我再吃口玉米面包吧。是这样,传说威尔克森干的那些搞黑人平等的事走得实在太远了点。他成天同那些傻黑鬼谈这些事,他竟胆敢——”托尼没奈何急急地说,“说黑人有权跟——白种女人——”
“唔,托尼,不会吧!”
“天哪,就是这样!你好像很难过,这我并不奇怪。不过,地狱着了火,思嘉,这对你来说,不会是新闻了。他们在亚特兰大这里也正在对黑鬼这样说呢。”
“这我——我可不知道。”
“唔,肯定是弗兰克不让你知道。不管怎样,在这之后我们大家认为我们得在夜里私下去拜访拜访威尔克森先生,教训他一顿,可是还没等我们去——你记得那个叫尤斯蒂斯的黑鬼吗,就是过去一直在我们家当工头的那个人?”
“记得。”
“就是那个尤斯蒂斯,今天萨莉正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他跑到厨房门口——我不知道他跟她说了些什么。我想现在我再也不会知道他说些什么了。反正他说了些话,接着我听见萨莉尖叫起来,便跑到厨房里去,只见他站在那里,喝得烂醉像个浪荡子——思嘉,请原谅我说漏了嘴。”
“说下去吧。”
“我用枪把他打死了,母亲急忙赶来照顾萨莉,我便骑上马动身到琼斯博罗去找威尔克森,他是应该对此负责的。要不是他,那该死的傻黑鬼是决不会想到做这种事情。一路经过塔拉时,我遇见了艾希礼,当然他便跟我一起去了。他说让他来干掉威尔克森,因为他早想对他在塔拉的行为进行报复了。不过我说不行,因为萨莉是我死去的同胞兄弟的妻子,所以这该是我的事。他还一路上跟我争论不休。等我们到了城里,天哪,思嘉你看,我竟没带手枪!我把它丢在马房里了。把我给气疯了——”
他停下来,咬了一口硬面包,这时思嘉在哆嗦。方丹家族中那种危险的狂暴性格在本县历史上早就闻名了。
“所以我不得不用刀子来对付他。我在酒吧间找到了他,把他抓到一个角落里,艾希礼把别的人挡住。我首先向他说明来意,然后才将刀子猛戳过去,随即,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事情便完了,”托尼一边想着,一边说,“等我明白过来的第一件事是艾希礼让我上马,叫我到你们这里来。艾希礼在紧要关头是个好样的。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弗兰克拿着自己的大衣进来了,随手把大衣递给了托尼。这是他惟一的一件厚大衣,但思嘉没有表示异议。她似乎对这件事完全站在局外,这可纯粹是男人的事呀。
“不过,托尼,家里需要你着呢。的确,要是你回去解释一下——”
“弗兰克,你真是娶了个傻老婆呀,”托尼一面挣扎着把大衣穿上,一面咧着嘴笑笑,“她以为北方佬还会给一个保护女同胞不受黑鬼污辱的男人发奖呢。他们会发的,那就是临时法庭和一根绳子。思嘉,亲我一下吧。弗兰克,你可别在意,我也许和你从此永别了。得克萨斯离这里远着呢。我可不敢写信,所以请告诉我家里人,到目前为止,我还平安无事。”
思嘉让他亲了一下,两个男人便一齐走出去,进入倾盆大雨之中。他们在后门口又站了一会说了些什么。接着,思嘉突然听到一阵马蹄溅水的声音,托尼走了。她打开一道门缝,看见弗兰克牵着一匹喘着气、跌跌绊绊的马进了马房。她关上门,颓然坐下,两个膝盖仍在哆嗦。
现在她明白重建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就像明白如果家里被一群只束着遮羞布蹲在那里的光身子野人所包围时的意思一样。许多最近她很少想到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涌上了心头,譬如说,她听到过但当时并没有注意去听的那些话,男人们正在进行但她一进来便中止的议论,还有一些当时看来并没有什么意思的小事情,以及弗兰克枉费心机地警告她不要在只有虚弱的彼得大叔保护下赶车去木厂,等等。现在这一切汇在一起,便形成一幅令人害怕的景象了。
黑人爬到了上层,他们背后有北方佬的刺刀保护着。思嘉可能被人杀死,被人强奸,对于这种事很可能谁也没有办法。要是有人替他报仇,这个人便会被北方佬绞死,也无需经过法官和陪审团的审判。那些对法律一窍不通、对犯罪情节更不注意的北方佬军官们,只需草草通过举行一次审判的动议,便可以把绞索套到南方人的脖子上了。
“我们怎么办呢?”她绞着双手,处在一种恐惧无依的极端痛苦之中,“那些魔鬼会绞死像托尼这样好的小伙子,就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同胞而杀死了一个黑醉鬼和一个恶棍般的无赖,对这些魔鬼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实在无法忍受!”托尼曾经大声呐喊过,他是对的。实在是无法忍受。不过他们既然无所依靠,不忍受又怎么办呢?她开始浑身哆嗦,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客观地看待一些人和事,清楚地看到吓怕了的孤弱无助的思嘉·奥哈拉并不是世界上惟一要紧的事了。成千上万像她那样的女人遍布南方,她们都吓怕了,都是些孤弱无助的人。还有成千上万的男人,他们本来在阿波马托克斯放下了武器,现在又将武器拿起来,准备随时冒生命危险去保护这些女人。
托尼脸上有着某种在弗兰克脸上也反映出来的表情,一种她最近在亚特兰大别的男人脸上也看见了的表情,一种她注意到了但没有考虑要去分析的神色。这种表情同投降后从战场上回来的男人脸上那种厌倦而无可奈何的表情完全不一样。当时那些男人只想回家,别的什么也不管。可现在他们又在关心某些事情了,麻木的神经恢复了知觉,原先的锐气又在燃烧。他们正怀着一种冷酷无情的痛苦在重新关心周围的一切。像托尼一样,他们也在思索:“实在无法忍受!”
她见过多少南方的男人,他们在战前说话温和,但好勇斗险,在最后战斗的绝望日子里不顾一切,坚韧不屈。但是,就在短短的片刻之前,从那两个男人隔着烛光相对注视的面孔中,她看到了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使她感到鼓舞而又害怕的东西——那是难以形容的愤怒,无法阻挡的决心。
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同周围的人有了一种类似亲属的密切关系,感到同他们的忧虑、痛苦和决心已融为一体了。的确,实在无法忍受!南方是如此美好的一个地方,决不容许不进行斗争就将它放弃;南方是如此可爱,决不容许那些痛恨南方人、想把他们碾得粉碎的北方佬来加以践踏;南方是如此珍贵的家乡,决不容许将它交给那些沉醉在威士忌和自由之中的无知黑人。
她一想到托尼的突然来临和匆匆离去,便觉得自己同他有了血缘关系,因为她记起她父亲在一次对他或他的家族来说不算杀人的谋杀事件之后连夜匆匆离开爱尔兰的故事。她身上有杰拉尔德的血,暴力的血。她记起自己开枪打死那个抢东西的北方佬时那股激动的高兴劲儿。他们身上都有暴力的血,它危险地接近表面,就潜伏在那温文尔雅的外貌下。他们大家,她认识的所有男人,连那两眼矇眬的艾希礼和婆婆妈妈的老弗兰克也在内,都有那种潜伏在底下的气质——必要时都能杀人,都会使用暴力。就连瑞德这个没有一点道德观念的流氓,也因为一个黑人“对贵妇人傲慢无礼”而把他杀了呢。
当弗兰克淋得浑身湿透,咳嗽着进来时,她才猛地一跃而起。
“唔,弗兰克,像这种日子,到底还要熬多久呀?”
“只要北方佬还恨我们,我们就得过下去,宝贝儿。”
“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弗兰克用疲倦的手捋了捋湿胡子,“我们正在想办法呢。”
“什么办法?”
“干吗不等我们搞出点名堂以后再谈呢?也许得花好多年的时间。或许——或许南方将永远是这个样子了。”
“唔,不会的。”
“宝贝儿,去睡吧。你一定着凉了。你在发抖。”
“这一切什么时候才结束呀?”
“等我们大家都可以再投票选举的时候,宝贝儿。等每一个为南方打过仗的人都能投票选举南方人和民主党人的时候。”
“投票选举?”她绝望地喊道,“投票选举管什么用,要是黑人都失去了理智——要是北方佬毒化了他们,让他们反对我们?”
弗兰克继续耐心地向她解释,但是说通过投票选举可以摆脱这一困境,这道理实在太复杂了,她怎能听得懂呢。她十分感激地想起乔纳斯·威尔克森永远不会再对塔拉构成威胁了。她还在想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