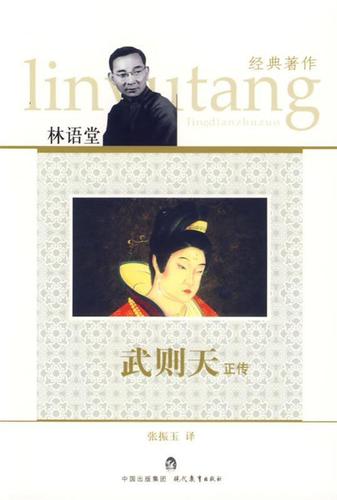第三十八章
思嘉亲眼目睹这种种情形,白天身临其境,夜间又带着它们上床睡觉,担心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知道由于托尼的事,她和弗兰克已列入了北方佬的黑名册,随时都可能大难临头。不过,尤其是现在,她可承受不起前功尽弃的损失——现在一个婴儿即将出世,木厂正开始有点赚头,塔拉还要她继续花钱,直到秋天收了棉花为止。啊,要是她会失去一切怎么办!或许她还得用那孱弱的武器,面对这疯狂的世界,一切从头开始呢!还得用她的朱唇、碧眼和狡猾而浮浅的脑子,同北方佬以及他们的一切主张做斗争啊。她实在担心得不耐烦了,觉得与其重新开始还不如自杀算了。
在一八六六年春天那一片破坏和混乱之中,思嘉将全部精力放在木厂上,一心一意要让它赚钱。在亚特兰大,钱有的是。盖新房的浪潮正在给她以所需的机会,她知道只要她不蹲监狱就准能发财。她不断告诫自己,处世得温和些,谨慎些,受到侮辱得逆来顺受,遇到不公平的事要让步,不要冒犯任何可能伤害她的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她跟别人一样,十分憎恨那些傲慢无礼的自由黑人,每次听到他们的辱骂或放声大笑时都要气得浑身不舒服。但是她从来连一个轻蔑的眼色也不敢向他们表示。她恨提包党人以及那些参加了共和党的南方白人,恨他们那样容易便发家致富,而她自己却在艰难地挣扎着过日子,但是她从来不说一句指责他们的话。在亚特兰大,没有人比她更厌恶北方佬的了,只要看到那身蓝军服便气得要命,但另一方面即使暗自在家里她也从不谈起他们。
我绝不做多嘴多舌的傻瓜,她冷峻地想道。让别人为往昔的日子和那些永不复生的人伤心去吧。让别人对北方佬的统治和因丧失投票权而愤怒去吧。让那些说了实话的人去蹲监狱,或者参加了三K党的人去受绞刑吧。(三K党这个名字多么可怕,对于思嘉来说,几乎就同黑人一样呢。)让别的女人为她们的丈夫参加了三K党而感到自豪吧。谢天谢地,弗兰克总算没有混到里面去!让别人去为那些他们毫无办法的事情烦恼、生气和出谋划策吧。过去,同紧张的现在以及没有把握的未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当面包、住房和争取不蹲监狱成了真正的问题时,投票选举又算得了什么?请上帝保佑,让我平安地过到六月,不要出什么事呀!
总得要到六月呀!思嘉知道到了六月她就得在皮蒂姑妈家待着休息,直到孩子生下来为止。人家已经在批评她,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敢在外面抛头露面。没有哪个女人怀了孕还在公开场合出现的。弗兰克和皮蒂早就求她不要再露面,不要给她自己——以及他们——丢丑,而她也答应他们到六月就不再工作了。
总得要到六月呀!在六月以前,她必须使木厂稳稳地站住脚跟,这才能够放心离开。在六月以前,她必须积攒足够的钱,对可能发生的不幸作一个小小的防备。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办,而时间却又那么短促。她希望一天能有更多的小时,并且争分夺秒地拼命弄钱,弄更多的钱。
由于她不断唠唠叨叨责骂胆小的弗兰克,那爿店总算现在有了点起色,连一些老账他也收了。不过思嘉还是将希望寄托在那家木厂上。当今的亚特兰大就像一棵被砍倒在地的大树,正在重新长出更茁壮的幼芽,更稠密的叶子,更繁茂的枝条。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可以供应的数量。木材、砖瓦和石头和价格在猛涨,思嘉经营的那家木厂从天一亮直到黄昏掌灯时分,始终忙得不亦乐乎。
每天她花费一部分时间在木厂里,盯着每一件事情,尽力制止她确信在发生的盗窃事件。但大部分时间她却坐着车在城里转悠,同那些建筑师、承包商和木匠周旋,甚至去拜访一些听说将来可能要盖房的陌生人,诱骗他们答应买她的木材,而且只买她一家的木材。
很快她就成了亚特兰大大街上一个常见的人物。她坐在一辆轻便马车里,旁边是一位神情严肃、但不大以为然的老黑人车夫。她把那条膝毯拉得高高地围着她的肚皮,那双戴手套的小手紧紧抱住膝盖。皮蒂姑妈给她做了一件漂亮的绿色短斗篷,可以遮住她的体形,还做了一顶绿色的扁平帽,和她的眼睛正好相配。她总是穿着这些合适的服装出去做生意,并在双颊上抹上淡淡一点胭脂,再轻轻洒一点科隆香水,这使她显得十分迷人,只要不从车里下来露出自己的体形就行了。实际上也很少需要她下车的事,因为她一微笑打个招呼,人们就会迅速跑过来,而且经常光着脑袋冒雨站在车旁同她谈生意经。
她当然并不是惟一看到做木材生意好赚钱的人,但是她并不害怕竞争者。她对自己的精明颇为自豪,深信跟别人不相上下。她是杰拉尔德的亲生女儿,父亲遗传给她的那种狡猾的经商本能现在由于需要而磨练得更精了。
最初,其他生意人都嘲笑她,觉得女流之辈哪会做生意呢,因此嘲笑中还带点和善的轻视。不过现在他们不再嘲笑了。一看见她驱车过来,他们便暗暗诅咒。实际上正由于她是女流之辈,事情往往反而对她有利,因为有时她装出一副毫无办法和恳求的样子,人们一看心便软了。在无论什么情况下,她可以毫不费力也无需用言语表达,就能给人一种印象,觉得她是个勇敢而又怯懦的上等女人,只是被严峻的环境所迫才落到了如此令人厌恶的地步;这样一个孤弱娇小的女子,要是顾客不买她的木材,她说不定会饿死呢。不过,一旦她那贵妇人式的风度取不到应有的效果时,她便会变得像个冷酷无情的生意人,为了招徕一个新顾客而不惜亏本,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出售木材。只要她认定不会被人发觉,她会将次等木料按上等的价格出卖,而且毫无顾忌地滥骂其他做木材生意的人。她会做出一副不太情愿揭露事实真相的样子,叹着气告诉一位可能与她成交的顾客,说她的竞争者们的木材价格实在太高,而且都是些烂木头,到处是节孔,总之,质量糟透了。
思嘉头一次这样撒谎时还觉得有点难为情,事后也不无内疚——难为情是因为谎言居然可以如此轻松地脱口而出,内疚是由于她突然想起母亲会怎么说呢?
爱伦对于一个撒谎和损人利己的女儿会怎样训诫,那是很明显的。她会大吃一惊,难以置信,然后说些刺人但又不失文雅的话,谈论应该如何对待名誉、诚实、真理和帮助自己的邻居,等等。思嘉一想象母亲脸上的神情,便禁不住畏缩起来。但是很快这个形象便变得模糊不清,被一种冷酷无情、不讲道德和贪婪的冲动所抹煞,这种冲动产生于塔拉那些贫困的日子,如今又在目前不稳定的生活中大大加强了。这样,她就跨过了这个里程碑,就像跨过以前那些阻止她的规范一样——她叹息自己已经不是爱伦所希望她做的那种人了,同时耸了耸肩,重复一遍她那句万应灵丹式的口诀:“我以后再去想这些吧。”
从此,在做生意方面她就再也没有想起过爱伦,也再没有对自己抢别人买卖的手段后悔过了。她知道用谎言去损害人家,对她自己来说是绝对安全的。南方的骑士制度保护了她。南方的上等女人可以用谎言去损害一位绅士,而南方的绅士却无法用谎言来损害一个上等女人,更不能说这个上等女人是撒谎者。其他做木材生意的人只能在心里发火,在跟家人一起时激动地声称,但愿上帝保佑能让肯尼迪太太变成男人,哪怕五分钟也好。
迪凯特街上住着一位开木厂的穷白人,他确实想用思嘉的那套武器来对付她自己,公开说她是个专爱说谎的人和诈骗犯。但这丝毫没有帮助,反而害了他自己,因为大家都感到吃惊,怎么一个穷白人居然能对一个出身名门的上等女人说这种坏话呢,即使这个上等女人的行为多么不合妇道。思嘉听到那个穷白人的指责时,先是不失身份地默默忍着,后来便渐渐将注意力转向这个人和他的顾客了。她如此无情地以比他更低的售价来抢夺对方的生意,而且暗暗心疼地抛出一批优质木材来证明自己的诚实,结果那个人很快就破产了。于是她便自己出价将对方的木厂高高兴兴地买了过来,使得弗兰克也惊恐不已。
一旦木厂到了手,便碰到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到哪里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经管呢?她不需要另一个像约翰逊那样的人。她知道尽管自己严加防范,他还是背着她在卖她的木材。不过她想,找个合适的人还是容易的。不是现在大家都穷得要命吗?不是现在街上到处都是没有工作的人吗?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去很富裕,可现在失业了。没有哪一天弗兰克不给一些饥饿的退伍兵以施舍,皮蒂和她的厨娘不包些吃的给那些骨瘦如柴的乞丐。
不过,连思嘉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她不想要一个这样的人。“我可不要那种过了整整一年还没找到事情干的人,”她想。“要是他们还不能适应和平时期,他们也就无法适应我。而且他们看上去全都那么畏畏缩缩,像挨了揍似的。我可不要挨揍的人。我要的是精明能干,像雷尼或托米·韦尔伯恩或凯尔斯·惠廷那样的,或者像西蒙斯家的一个小伙子,或者——或者任何一个属于这一类的人。他们没有士兵们一投降便什么事也不管的那种神气。他们看上去像是十分关心许多事情呢。”
但是西蒙斯家的小伙子们正在开办一个砖窑,凯尔斯·惠廷在卖一种从他母亲厨房里制作的药剂,那是可以使黑人最蜷缩的头发涂上六次就能平直的灵丹,他们居然都彬彬有礼地朝思嘉微微一笑,婉言谢绝了她的雇用,这叫她大吃一惊。她又试了试许多别的人,结果都一样。实在没有办法了,她决定提高工资,但还是遭到了拒绝。梅里韦瑟太太有个侄子甚至傲慢地对她说,虽然他并不特别喜欢赶大车,但大车毕竟是他自己的,他宁愿自食其力使事业有所发展,也不愿到思嘉那里去。
一天下午,思嘉的马车追上了雷内·皮卡德的馅饼车,看见瘸子托米·韦尔伯恩因顺便搭车回家也坐在雷内的车上,于是她就跟他俩打招呼。
“雷内,你看,为什么你不来我这里干活?经营一家木厂可比赶一辆馅饼车要体面多了。我想你大概觉得不太好意思吧?”
“我吗,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雷内咧嘴笑笑说。“谁算体面呢?我倒一向是体面的,直到这场战争将我像黑人一样解放了。我再也不必像过去那么高贵和闲得无聊了。我自由得像只小鸟了。我喜欢我的馅饼车。我喜欢我的骡子。我喜欢亲爱的北方佬,他们好心地买我岳母的馅饼。不,我的思嘉,我一定要成为馅饼大王。这是我命中注定了的!就像拿破仑一样,我听天由命。”他兴奋地挥舞起他的鞭子。
“但是你父母把你养大,绝不是让你来卖馅饼的,就像把托米养大不是来对付那帮粗野的爱尔兰泥瓦匠一样。而我那里的工作可要——”
“那我想你的父母准是把你养大来经营木厂的吧,”托米插嘴说,嘴角抽搐了一下,“是的,我正看见那个小小的思嘉坐在母亲膝头上,咬着舌头在背课文:‘要是次木料能卖好价钱,可千万别卖好木料呀。’”
雷内一听大笑起来,他那双小猴眼高兴地飞舞起来,他用力捶了一下托米的驼背。
“不要放肆,”思嘉冷冷地说,因为她听不出托米的话里有多少幽默,“当然我父母养育了我,可不是叫我来开木厂的。”
“我并没有放肆的意思。不过你是在开木厂呀,不管你父母养你时是不是就要你干这一行。而且你也确实干得很好。得了,依我看,我们中间谁都不是在干原先打算干的那一行,不过我想我们照样都还干得不错呢。如果生活不能完全如意便坐下来哭鼻子,那才是可怜虫,才是一个可怜的民族。思嘉,你为什么不去找个有魄力的提包党人来替你干活呀?上帝知道,树林里有的是!”
“我可不要提包党人。提包党人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不是烧得通红的或者钉得牢牢的,都会给你偷走。如果他们眼下很得意,就会待在原地不动,决不会屈尊到这里来捡我们的骨头。我要的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家出身的人,又精明能干又忠厚老实,还要——”
“你的要求倒还不算高呢。不过按你出的工钱,你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你说的那种人,除非是完全残废的,现在全都找到了工作。他们也许不适宜干目前的活,不过他们毕竟全都在干着呢。他们情愿干些自己的事情,也不想去替女人干活呢。”
“只要你了解底细,便会发现男人是没有多少头脑的,难道不是吗?”
“也许这样,不过他们还是很有自尊心的。”托米冷静地说。
“自尊心!我看自尊心的味道好得很,尤其在外皮容易剥落时放点蛋白糖霜,味道就更好了。”思嘉刻薄地说。
两个男人有点勉强地大笑起来,但思嘉似乎觉得他们作为男性在联合起来反对她。她想想托米的话是对的,这时她脑海中掠过一些她已经找过和打算去找的男人。他们全都很忙,忙着干某些事情,干得很辛苦,比战前他们可能想象得到的还要辛苦。也许他们干的并不是自己所愿意干、最容易干,或者曾被培养要干的事。可是他们毕竟是在干了。对于男人来说,这个世道的确太艰难,不能有什么选择。要是他们在为失去希望而悲伤,在渴望过去的生活方式,那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清楚。他们正在打一场新的战争,一场比上一次更加艰苦的战争。他们现在又关心起生活来了,以那种在战争将他们的生活切成两段之前激励过他们的同样的迫切感和强烈意识关心着。
“思嘉,”托米尴尬地说,“我刚才对你无礼了,实在不愿意再求你帮忙,不过我还是得求你。也许这对你也还有好处。我的内弟,休·埃尔辛在卖柴火,干得不太顺利,因为除了北方佬,现在谁都自己出来捡柴火了。我知道埃尔辛一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尽力帮忙,但你知道我还得养范妮,还有母亲和两个寡姐在斯巴达要我照顾。休这个人很好,你要的正是一个好人,而且你知道的,他又是好人家出身,人很忠厚老实。”
“不过——嗯,休没有多大魄力,要不然他的柴火生意是会成功的。”
托米耸了耸肩膀。
“你看事情的眼光可真够厉害的了,思嘉,”他说,“不过,你可以再考虑一下休。事情做过头了反而会更糟的。我想,他的忠厚老实和心甘情愿会弥补他的魄力不足,而且绰绰有余呢。”
思嘉在全城游说遍了没有成功,而许多想干的提包党人却跑来纠缠不休,但都被她拒绝了。最后她终于决定接受托米的建议,让休·埃尔辛来干。休在战争时期是位干劲很大、足智多谋的军官,但是打了四年仗,受过两次伤,他的全部智谋好像已经彻底干涸,如今面对和平时期这一严峻的现实,像个孩子般糊涂起来了。近来他挑着柴火到处叫卖时,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丧家犬的神色,看来根本不是思嘉所希望雇到的那种人。
“他很笨,”思嘉心想,“他对做生意几乎一窍不通,我敢打赌他连二加二等于多少都不会。而且我怀疑他也学不会了。不过,他至少是个老实人,不会欺骗我。”
这些日子思嘉并不怎么需要老实,不过她越是不看重自己的老实,便越发看重别人的老实了。
“可惜的是约翰尼·加勒格尔正同托米·韦尔伯恩合伙在盖房子,”她想,“他才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硬得像钉子,滑得像蛇,要是给他的报酬适当,他也会老老实实的。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我们可以很好地共事。或许等那家旅馆盖好之后,我便可以把他弄过来了。在这之前,我只好让休和约翰逊先生将就对付着。要是我让休负责新厂,让约翰逊先生留在老厂里,我自己便可以待在城里管推销,锯木和运输的事由他们去办。不过,要是我总留在城里,那么在请到约翰尼之前,还得冒约翰逊先生偷木料的风险。他要不是个贼就好了!我想将查尔斯留给我的那块地分一半盖个木料堆置场。只要弗兰克不在我跟前那么大声嚷嚷,我还准备用另一半地建一个酒馆呢!不管他怎样激动,只要拿到了足够的钱,我马上就要建酒馆的。要是弗兰克的面皮不那么嫩就好了。啊,天哪,要是我不偏偏在这个时候要生孩子,那多好呀!很快我的肚子就要大得不能出门了。哦,天哪,我怎么就要生孩子了呢?而且,天哪,要是那些该死的北方佬不来管我,要是——”
要是!要是!要是!生活中竟有那么多的“要是”,什么事也没有把握,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总在担心会失去一切,重新受冻挨饿。当然,现在弗兰克赚的是多了一点,不过弗兰克总爱感冒生病,经常一连几天得在床上躺着。说不定他会成为一个废人。不,她不能过多地指望弗兰克。除了她自己,谁也不能指望。而现在她能挣到的钱似乎实在太少了。哦,要是北方佬跑来将她的东西全部拿走,她该怎么办呢?要是!要是!要是!
她每月挣的钱,一半寄到塔拉交给了威尔,一部分还瑞德的债,其余的便自己存起来。没有哪个守财奴比她数钱数得更勤,也没有哪个守财奴比她更害怕失去这些钱。她不肯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因为怕银行可能要倒闭,或者北方佬可能要没收。所以她把钱尽量带在自己身边,塞在自己的紧身衣内,将一小叠一小叠的钞票藏在屋子周围,放在壁炉的砖缝里,放在废物袋内,夹在《圣经》的书页中。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因为每省下一块钱,到了灾难临头时,就会多丢掉一块钱啊。
弗兰克、皮蒂和仆人们对于她那种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的无名火都极为体贴地容忍着,将她的坏脾气归咎于怀孕,从没意识到真正的原因。弗兰克知道对于怀孕的妇女就得迁就,所以他抑制着自尊心,任凭她继续经管木厂,任凭她在目前这种任何女人都不该再出去抛头露面的时候继续在城里到处乱跑,绝口不提任何意见。她的行为不断使他感到很难为情,不过他料想再忍耐一段时间就差不多了。只要孩子一下地,思嘉又会成为当年他追求过的那个富于女性美的可爱姑娘了。但是不管他如何姑息迁就,她还是不停地发脾气,因此他觉得她很像是鬼迷心窍了。
究竟什么东西迷住了她的心窍,什么东西使她变得像个疯婆子,看来谁也不明白。实际上那是一种强烈欲望的表现,她要在自己不得不闭门隐居之前赶快将她的事情安排好,赶快尽可能多攒些钱以防万一,赶快建立一个坚实的金钱堤坝来防御北方佬日益高涨的仇恨浪潮。这些日子正是金钱迷住了她的心窍。要说有时她也想到孩子,那只是对孩子来得不是时候而莫名其妙地生气。
“死亡,纳税,生孩子!这三件事,哪一件也没有合适的时间容你挑选的!”
当思嘉作为一个女人开始经营木厂时,亚特兰大人普遍感到震惊。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家便断定她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她做生意使用的酷辣手段令人骇异,何况她那可怜的母亲还是罗毕拉德家的小姐呢。而且,当谁都知道她怀了孕的时候,她却照样在大街上到处奔跑,这就更加不合适了。无论哪个正派的白人或黑人妇女,只要一怀疑自己有了身孕,便几乎都不再迈出家门,因此梅里韦瑟太太愤慨地说,从思嘉的所作所为来看,她大概是想把孩子生在大街上了!
不过以前人们对她的行为所做的种种批评,同现在城里人对她的流言蜚语比较起来,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了。思嘉不仅同北方佬做买卖,而且无处不显得她是真正喜欢这样做呢!
梅里韦瑟太太和许多别的南方人也在同刚来这里的北方佬做生意,但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喜欢,而且明白地表示不喜欢。可思嘉却的确喜欢,或者说,似乎喜欢,那也一样是够糟的了。她确实在北方佬军官家里同他们的妻子喝过茶呢!事实上她什么事都干过,只差没邀请他们到她自己家里来了,而且全城的人都在猜想,要是没有皮蒂姑妈和弗兰克,她准会请他们去的。
思嘉知道全城人都在议论她,但她并不在乎,也顾不上去计较。她对北方佬的恨还是同当年他们想烧掉塔拉时那样厉害,不过她能够把这种仇恨掩饰起来。她很清楚,如果她打算赚钱,便只能从北方佬那里去捞,而且她也明白,用微笑和好言好语去巴结他们,准能把他们的生意拉到她的木厂来。
等到有一天,她十分富有了,而且把她的钱藏到了北方佬无法找到的地方,到那时她便可以告诉他们她对他们的真实看法,告诉他们她恨他们,厌恶他们,瞧不起他们。那会多高兴呀!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她还得同他们融洽相处,这是简单明了的常识。要说这是虚伪,就让亚特兰大人尽量利用这种虚伪吧。
她发现,同北方佬军官做朋友就像射击地上的鸟一样容易。他们在一个敌对的地方成了寂寞的流亡者,其中许多人渴望与女性有礼貌地交往,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正派女人从他们跟前经过时往往掉头不理,好像要啐他们一口才解气似的。只有妓女和黑人妇女才跟他们说话和气。但是思嘉显然是个上等女人,一个有门第的上等女人,尽管目前在干活,因此只要她嫣然一笑,那双碧绿的眼睛滴溜儿一转,他们就浑身激动了。
往往,思嘉坐在车里对他们说话,向他们摆弄两个酒窝,这时她实际上对他们厌恶极了,恨不得劈脸骂他们一顿。不过她还是克制住自己,而且发现将北方佬随意玩弄玩弄,一点也不比跟南方男子这样逗乐要难多少,只不过这不是逗乐而是一桩可恨的事罢了。她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在患难中的文雅温柔的南方贵妇人。她具有庄重而娴雅的风度,可以使她的受骗者与她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过她那和蔼的态度仍叫北方佬军官一想起肯尼迪太太便心里暖洋洋的。
这种暖意是非常有利的——也正是思嘉想要得到的。许多驻防的军官由于不知道自己在亚特兰大要待多久,把妻子和家眷都接过来了。由于旅馆和公寓早已客满,他们便正在自己盖房子,并且很高兴从这位和气的肯尼迪太太那里买木料,因为她待他们比城里任何别的人都更有礼貌。那些提包党人和无赖也正在用他们新捞到的巨款建筑豪华住宅、店铺和旅馆,他们也发现同她做生意比同原先联盟军的大兵们打交道要愉快一些。那些大兵虽然也很客气,但这种客气只不过比直言不讳的憎恨更加合法和冷酷而已。
所以,正因为她长得又漂亮又迷人,而且有时又显得很可怜无助,他们便都乐意光顾她的木材厂以及弗兰克的店铺,觉得他们应该帮助这位有胆量但显然只有一个无能的丈夫在养活她的小妇人。思嘉注视着她事业的进展,觉得不仅目前她在靠着北方佬的钱,而且将来还得靠这帮人庇护呢。
同北方佬军官的关系保持在她想保持的水平上,这比她所预料的要容易些,因为他们全都很怕南方的上等女人,不过思嘉也很快便发现这些军官的妻子引起了一个她没有料到的问题。同北方佬妇女联系并不是她所乐意的。她很想避开她们,可是办不到,因为这些军官的妻子一心要见见她。她们对南方和南方妇女怀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而且思嘉最先给了她们满足这一愿望的机会。亚特兰大的其他妇女根本不同她们发生任何联系,甚至在教堂里也拒绝向她们点头,因此每当思嘉为了生意到她们家里去时,那就好像是她们日夜祈求的事情实现了。往往,思嘉在一家北方佬门前坐在自己车里同这家的男人谈论木料和屋顶板时,这个男人的妻子便会跑出来搭讪,并坚持要她进屋喝杯茶。思嘉尽管心里老大不愿意,但很少拒绝,因为她总希望有个机会自然地建议她们去光顾弗兰克的店铺。不过她的自我克制能力多次受到严重考验,因为她们经常提出种种涉及私人的问题,而且对南方的一切都表现出一种沾沾自喜和好意屈就的态度。
北方佬妇女认为《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的启示仅次于《圣经》,所以她们全都问起南方人家养的用来追逐逃跑奴隶的那种猎狗。而且她们根本不相信她所说的她有生以来只见过一只猎狗,而且是一只温和的小狗,并非凶恶庞大的猛犬。她们还想看看农场主用来在奴隶脸上打印记的那种可怕的烙铁和用来打死奴隶的有九根皮条的鞭子。思嘉觉得她们对于纳奴隶为妾的问题表现出来的兴趣,实在非常庸俗和没有教养。尤其当她看到北方佬军队在亚特兰大定居以后黑白混血婴儿大量增加时,更是十分愤恨。
听到这类带有偏见的无知言论,亚特兰大无论哪一个女人都会气得要命,但思嘉却设法忍着,她所以忍得住,是因为她们在她内心引起的鄙视多于忿怒。她们毕竟是北方佬,谁也不会指望北方佬干出什么好事,说出什么好话来。因此,她们所表现的对于她的国家和人民及其伦理道德的种种轻率的侮辱,都始终未能深深地触动她,只不过从她心上轻轻擦过,引起一种很好地掩藏起来的轻蔑和讥笑,直到发生了一件叫她怒不可遏的事情为止。这件事向她表明,如果她需要什么表明的话,那就是南北之间的鸿沟有多么宽阔,而且要想跨越这道鸿沟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一天下午,她同彼得大叔赶车回家,经过一所住着三家北方佬军官的房子,这些军官正在用思嘉的木料盖自己的住宅。她驱车经过时,三个军官的妻子正好都站在门口,她们向她挥手,请她把车停下来。她们出来,跑到她的马车旁边同她打招呼,那口音又一次使她觉得,对于北方佬,除了他们那种声调之外,几乎什么都可以原谅了。
“我正想见你呢,肯尼迪太太,”一个来自缅因州的瘦高个女人说,“我想从你那里了解一点关于这个愚昧城市的情况。”
思嘉怀着理所当然的鄙视吞下了这种对亚特兰大的侮辱,勉强装出一副笑容。
“要我告诉你些什么呢?”
“我的保姆布里奇特回北方去了。她说她在这些她称为‘黑鬼’的人当中多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孩子们现在成天缠得我心烦意乱,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再找到一个保姆。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呀。”
“这并不难,”思嘉说着,笑起来,“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刚从农村来的还没有被‘自由人局’宠坏的黑人,你就会有一个最好的仆人了。你就站在这里,站在你家门口,询问每一个经过这里的黑女人,我保证——”
那三个女人气得大声嚷嚷起来。
“你以为我会放心将我的孩子交给一个黑鬼吗?”缅因州的女人喊道。“我是要一个爱尔兰的好姑娘呀。”
“我怕你在亚特兰大是找不到爱尔兰仆人了,”思嘉冷冷地回答说,“我自己就从未见过一个白种仆人,我家也不想要,而且,”她忍不住在话里略带讥讽的语气,“我可以向你保证,黑人并不会吃人,倒是很值得信赖的。”
“天哪,这可不行!我家里可不能用黑人。怎么能这样想呀!”
“我连看都不要看,怎么还能信任他们呢,至于让他们带我的孩子……”
思嘉想起嬷嬷那双亲切而粗糙的手,那双由于伺候爱伦、她自己和韦德而变得难看的手。这帮陌生人对于黑人的手能知道什么,她们哪里会知道黑人的手多么可贵,多么令人鼓舞,多么准确无误地懂得怎样去抚慰人、体贴人和逗爱人,她想到这里轻轻地笑了笑。
“真奇怪,你们会是这样想的。不正是你们大家把他们解放了吗?”
“天哪,可不是我呀,亲爱的,”缅因州女人笑着说,“上个月我来南方之前,还从没见过一个黑人呢,而且也不想再见另外一个了。他们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可不能信任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思嘉早就感觉到彼得大叔在急促地喘气了,他坐得笔挺,两眼牢牢盯着马耳朵。这时那个缅因州的女人偏偏突然大笑起来,指着彼得大叔给她的同伴看,这便促使思嘉更加注意彼得的神情了。
“瞧那个老黑鬼,像只癞蛤蟆似的,气得鼓鼓的,”她咯咯地笑着,“我敢断定他就是你家的一个老宝贝吧,是吗?你们南方人根本不懂得怎样对待黑鬼。你们把他们都宠坏了。”
彼得倒抽了一口气,眉头皱得更紧了,但两眼仍直勾勾地朝前看。他这一生还没有被一个白人叫过“黑鬼”。其他黑人倒是这样叫过他,可从来没有白人叫过。至于被看做“难以信任”和称为“老宝贝”,对于他这个汉密尔顿家多年来的庄严柱石更是从来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