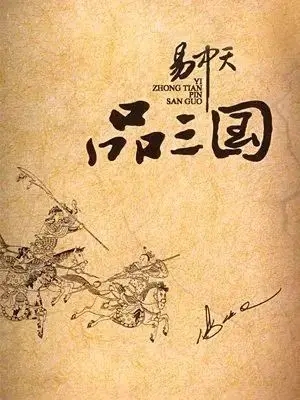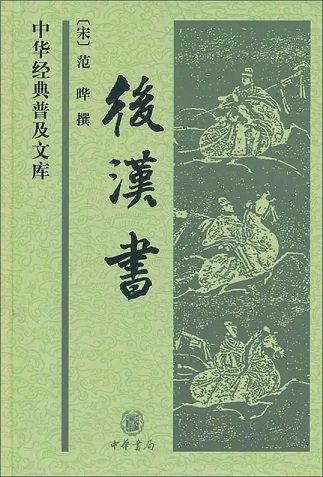“我一直想得到你,思嘉,自从我头一天在‘十二橡树’村看见你又摔花瓶,又咒骂,使我觉得你不是个上等女人,我就想得到你。我想不论用什么办法我也要把你弄到手。但是因为你和弗兰克积攒了一点钱,我就知道你不会再被迫向我提出借钱的要求。所以我觉得非娶你不可。”
“瑞德·巴特勒,你又在跟我开一个恶毒的玩笑吧?”
“我对你以诚相见,你反倒起了疑心。我不是开玩笑,思嘉,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承认这个时候来找你不大合适,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明天我就走了,而且要离开很长时间,我怕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嫁给另外一个有钱的人了。所以我想你为什么不嫁给我呢,我也有钱呀。真的,思嘉,我不能一辈子老等着你,希望在你更换丈夫的时候得到你。”
他说的倒是实话。这是肯定的。她琢磨他这番话的含义,感到唇干舌燥,一面咽唾沫,一面盯着他的眼睛,想从中看出一些端倪。他眼中充满了笑意,但在深处也还蕴藏着一点别的东西,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他坐在那里,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她觉得他正机警地盯着她,就像一只猫盯着耗子洞一样。她觉得在他平静的外表下面憋着一股劲儿,使她退缩,使她害怕。
他真是在向她求婚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她曾经想过,如果他求婚的话,该怎样折磨折磨他。她也曾想过,如果他提出这种要求,就羞辱他一番,让他知道她的厉害,她会从中感到乐趣。现在他提出要求了,可是她把原来那些打算却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她和过去一样,始终没能把他控制在手心里。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而她就像初次有人求婚的少女一样激动,脸也红了,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我不再结婚了。”
“不会的。你生来就是要结婚的。那为什么不能和我结婚呢?”
“可是,瑞德,我——我并不爱你。”
“这不是什么缺点。我记得你头两次结婚也没有多少爱情呀。”
“唔,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知道我是喜欢弗兰克的。”
他什么也没说。
“我喜欢他!我喜欢他!”
“这我们就不要争了。我走了以后,你考虑考虑我的要求吧。”
“瑞德,我不喜欢老拖着。我现在就答复你吧。我不久就要回塔拉去,英迪亚·威尔克斯留在这里陪着皮蒂姑妈。我回去要住很长时间,而且——我——我也不想再结婚了。”
“别胡说了。为什么呢?”
“唉,你就别问了。我就是不愿意结婚。”
“可是,傻孩子,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结过婚。你怎么会知道结婚的乐趣呢?我认为你是运气不好——一次是赌气,一次是为了钱。你想没想过为了寻求乐趣而结婚呢?”
“乐趣!净说傻话。结婚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没有?为什么没有?”
她的心情渐渐恢复了平静,说起话来也恢复了白兰地勾起来的她那固有的冲劲儿。
“结婚只对男人有乐趣——不过也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始终弄不明白。结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无非是有口饭吃,有一大堆活儿要干,还要忍受男人的胡闹——还得每年生个孩子。”
瑞德一听这话大笑起来,在寂静的黑夜里,回声特别大,思嘉听见厨房有人开门的声音。
“嘘!嬷嬷的耳朵和山猫一样尖,况且,刚——就这么大笑,也不像话呀。快别笑了。真是这样。什么乐趣!全是胡扯!”
“我说你是运气不好,你刚才的话也证明这一点。你先嫁了一个孩子,又嫁了一个老头儿。你母亲也一定对你说过,女人必须忍受‘这些事’,因为可以享受做母亲的愉快。我说,这都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嫁一个名声不好而又善于对付女人的漂亮的年轻男人呢?那是很有乐趣的。”
“你这个人又粗野,又自负。我觉得我们扯得够远的了。真是——真是粗俗得很。”
“也很有趣,是不是?我敢说,你从来没跟一个男人谈论过婚姻关系,甚至和查尔斯和弗兰克也没谈论过。”
她朝他皱了皱眉。瑞德知道的事太多了。他对女人了解得这么透彻,他是怎么知道的,思嘉感到纳闷。真是不正经。
“你别皱眉。说个日子吧,思嘉。考虑到你的名声,我并不要求马上结婚。我们可以等上一段像样的时间。顺便问一下,一段‘像样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议论这件事,也是很不像话的。”
“我已经告诉你我为什么现在来找你谈这件事。我明天就走了,而我又是那么热烈地爱着你,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也许我追你追得太急了。”
突然间,她吃了一惊。因为瑞德从沙发上往下一溜,跪在了地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胸口上,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对不起,因为我感情奔放,使您受惊了,亲爱的思嘉——我的意思是亲爱的肯尼迪太太。您不会没注意到,许久以来,我心中对您的友情已经发展成更深的感情,更加美丽,更加纯洁,更加神圣。我能告诉您那是一种什么感情吗?啊!是爱情,是它给了我勇气。”
“快起来,”她央求说,“看你那个傻样儿。要是嬷嬷进来看见你这个样子怎么办?”
“她头一次看见我这样文雅,会感到吃惊,甚至不敢相信呢。”瑞德一面说,一面轻巧地站起来,“我说,思嘉,你不是小孩子、小学生了,不要用正经不正经之类无聊的话来搪塞我了。答应我吧,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和我结婚,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对天起誓,不走了。我要在这里每天晚上在你窗前弹着吉他,扯着嗓子唱,出你的洋相,到那个时候,你为了保全面子,就非跟我结婚不可了。”
“瑞德,别不识相。我谁也不嫁。”
“谁也不嫁?你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不会是因为像女孩子那样胆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思嘉突然想起了艾希礼,仿佛看见他就站在身旁,他那光亮的头发,无精打采的眼睛,庄重的神情,和瑞德迥然不同。她之所以不想再结婚,其真正原因就是为了他,虽然她对瑞德并不反感,而且有时还的确对他有些好感。她觉得自己是属于艾希礼的,永远永远是属于他的。过去没有属于查尔斯,也没有属于弗兰克,今后也不会真正属于瑞德。她自己的全身心,她所做的一切,她所追求的一切,她所得到的一切,几乎全是属于艾希礼的,因为她爱他。艾希礼和塔拉,她是属于他们的。她过去给查尔斯和弗兰克的笑脸与亲吻,可以说都是给艾希礼的,只不过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有一种欲望:把自己留给他,虽然她明明知道他是不会要她的。
思嘉没有意识到自己脸上的表情是有变化的。她刚才陷入沉思的时候,脸上显得异常温柔,这是瑞德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表情。他看看她那眼角吊起的绿眼睛睁得大大的,流露出迷茫的神情,再看看她那温柔的弯曲的嘴唇,他的呼吸都暂时停顿了。他突然把嘴一撇,急不可耐地大声说:
“思嘉·奥哈拉,你可真傻!”
她还没有完全从沉思中摆脱出来,他的两只胳臂已经搂住了她,就像许久以前去塔拉的路上,他在黑暗中搂她搂得那么紧。她又感到一阵无力,只有顺从,一股暖流上来,使她浑身发软。艾希礼·威尔克斯那沉静的面孔模糊了,逐渐消失了。他使她把头往后一仰,靠在他的胳臂上,便吻起她来。先是轻轻地吻,接着就越来越热烈,使她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仿佛整个大地在摇动,令人头晕目眩,只有他是牢靠的。他顽强地用嘴分开了她那发抖的双唇,使她浑身的神经猛烈地颤动,从她身上激发出一种她从未想到自己会有的感觉。在她快要感到头昏眼花,天旋地转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已在用热吻向他回报了。
“行了,行了,我都头晕了!”她小声说,一面无力地挣扎着,想把头扭开。他一把把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时她模模糊糊地看了一眼他的脸。只见他两眼睁得大大的,眼神也不同寻常,他的胳臂在颤抖,真让她害怕。
“我就是要让你头晕。非让你头晕不可。这些年来,你早就该有这种感觉了。你碰上的那些傻瓜,谁也没有这样亲过你吧,是不是?你那宝贝查尔斯,弗兰克,还有那个笨蛋艾希礼——”
“快别说了——”
“我说你那个笨蛋艾希礼。这些正人君子——关于女人,他们了解什么?他们了解你吗?而我是了解你的。”
他的嘴唇又落在她的嘴唇上,她一点也没反抗就依从了他,她连扭头的力气也没有了,况且她本来也无意回避,她的心跳得厉害,震动着她的全身,他是那么有劲,使她感到害怕,而她自己是那么软弱无力。他打算干什么?他要是再不停下来,她就要头晕了。他要是停下来就好了——他要是永远不停下来就好了。
“你就说声好吧!”他的嘴向下对着她的嘴,他的眼睛也靠得那么近,显得大极了,好像世界上除了这两只眼睛,再没有别的东西。“说声好吧,你他妈的,要不——”
她还没来得及思索,一个“好”字已经轻轻地脱口而出。这简直就像是他要这个字,她就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个字。可是这个字一经说出,她的心情就突然平静下来,头也不晕了,白兰地带来的醉意也不那么浓了。她本来无意答应和他结婚,却答应了。她也说不大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不过她并不懊悔。现在看起来,她说这个“好”字是很自然的——很像是神明干预,一只比她更有力的手介入了她这件事,为她解决了问题。
他一听她说出这个“好”字,倒抽了一口气,低头仿佛又要吻她,她闭着眼,仰着头,等他亲吻。可是他突然收住了,这使她不免有些失望,因为她觉得这样被人亲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而且使人兴奋。

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依然扶着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仿佛经过一番努力,他的胳臂不再颤抖了。他松开了一点,低头看着她。她也睁开眼睛,发现他脸上刚才那种使人害怕的红光已经消失了。但不知怎地她不能正眼看他,心里一阵慌乱,她又低下头。
他又开始说话了,语调非常平静。
“你说话算数吗?不会收回你的诺言吧?”
“不会。”
“是不是因为我凭我的热情使得你——那话是怎么说的?——‘飘飘然’了?”
她无法回答,因为她不知说什么好,她也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把一只手放在她下巴底下,托起她的脸。
“我对你说过,你对我怎么样都行,只是不要说谎。现在我要你说实话。你究竟是为什么说‘好’的?”
她仍然不知说什么好,不过比刚才镇定一些了。她两眼朝下看着,显得难为情的样子,同时抿着嘴笑了笑。
“你看着我。是不是为了我的钱?”
“啊,瑞德!你怎么这么说?”
“抬起头来,别给我来甜言蜜语。我不是查尔斯,也不是弗兰克,也不是本地的傻小子,你只要眨眨眼,就上当。究竟是不是为了我的钱?”
“唔——是,但不全是。”
“不全是?”
他并没有感到不快。他倒抽了一口气,一下子把她的话引起的急切神情从眼角里抹掉了。这神情,由于她过于慌乱而没有觉察。
“是啊,”她无可奈何地说,“钱是有用的,你知道,瑞德,可惜弗兰克并没有留下多少钱。不过,瑞德,你知道,我们是能够相处的。在我见过的许多男人之中,只有你能够让女人说真话。你不把我当傻瓜,不要我说瞎话,有你这么个丈夫是幸福的——何况——何况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喜欢我?”
“嗯,”她焦躁不安地说,“我要是说爱你爱得发疯了,那是瞎话,再说你也是知道的。”
“有时候我觉得你对说真话也过于认真了,我的小乖乖。难道你不觉得即便是瞎话,你也应当说一声‘瑞德,我爱你’?言不由衷也没关系。”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她想不透,觉得更糊涂了。他的神气好像很奇怪,很殷切,很伤心,又带有讽刺的意味。他把手从她身上抽回去,深深地插到裤子口袋里,她还发现他握起了拳头。
“即使丢掉丈夫,我也要说真话,”她暗自下定了决心,她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了,只要瑞德一刺激她,她总是这样。
“瑞德,那是一句谎话呀,我们为什么也要按照那俗套子来做呢?我刚才说了,我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有一次你对我说你并不爱我,可是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是流氓,这是你自己说的——”
“天哪!”他轻轻地自言自语,把脸转向一边。“真是自作自受!”
“你说什么?”
“没什么,”他看了看她,笑起来,但那笑声并不愉快。“说个日子吧,亲爱的,”说罢,他又笑起来,还弯腰吻了她的双手。看到他不再心烦,情绪恢复正常,她松了一口气,也露出了笑容。
他抓着她的手,抚摩了一会儿,又朝她笑了笑。
“你在小说里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节:妻子对丈夫没有感情,后来才爱上了自己的丈夫?”
“你知道我从来不看小说,”她说,为了迎合他那轻松愉快的心情,她接着说:“况且有一次你说过夫妻相爱是最要不得的。”
“我他妈的说过的话太多了。”他马上顶了她一句,就站起来了。
“你不要咒骂呀。”
“这你可得适应一下,而且要学着骂。你得适应我所有的坏习惯。你说——你说喜欢我,而且还想用你那漂亮的小爪子抓我的钱,那就得付出代价,这才是代价的一部分。”
“你不必因为我没有撒谎,没有让你神气,就朝我发火。你也并不爱我,对不对?我为什么一定要爱你呢?”
“是的,亲爱的,你不爱我,我也同样不爱你,如果我爱你,我也不会告诉你。愿上帝帮助那个真正爱你的人吧。你会使他伤心的,亲爱的,好比一只残暴的破坏成性的小猫,不管不顾,为所欲为,甚至不肯收住自己的爪子。”
说到这里,他一把把她拉起来,又吻起她来,不过这一次与刚才不同,他似乎不考虑是否会使她难受——他似乎故意要使她难受,故意要侮辱她。他的嘴唇滑到了她的脖子底下,最后他的嘴唇贴在了她的胸前,他是那么用力,时间又那么长,所以虽然隔着一层府绸,她还是感到烫得慌。她用两手挣扎着把他推开,又气愤,又不好意思。
“你不能这样!你怎么敢这么放肆!”
“你的心突突跳得像只小兔子哩,”他讥讽地说。“我冒昧地说一句,我觉得如果只是喜欢的话,心也不至于跳得这么快吧。你也不必生气。你这好像处女一样羞羞答答的样子完全是装出来的。快直说吧,要我从英国给你带点什么回来?戒指?要什么样的?”
作为一个女人,她想把装模作样地生气这场戏再拖长一点,同时她又对瑞德说的最后这句话产生了兴趣,她犹豫了一下,说:
“唔——钻石戒指——瑞德,一定要买个特大的。”
“这样你就可以在穷朋友面前炫耀说:‘看我这是什么!’是不是?好吧,我一定给你买个特大的,让你那些不怎么富裕的朋友只能互相安慰,悄悄地说:看她戴那么大的钻石戒指,真俗气。”
他突然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她跟在后面,不知所措。
“怎么了?你上哪里去?”
“回去收拾行李。”
“唔,可是——”
“可是什么?”
“没有什么。祝你旅途愉快。”
“谢谢。”
他打开书房门,来到过厅里。思嘉跟在后面,不知怎么办好,感到有些失望,没想到这出戏竟这样草草收场。他顺手穿上大衣,拿起了手套和帽子。
“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是改变主意,就来信告诉我。”
“你就不——”
“怎么?”他急着要走,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你就不亲亲我,表示告别吗?”她小声说,怕别人听见。
“一个晚上,亲了你那么多次,还不够吗?”他反问道,并低头朝她笑了笑。“想一想你这样一个懂事的有教养的年轻女子——我刚才说了,是有乐趣的,你看,是不是?”
“啊,你真坏!”她大声嚷嚷起来,也顾不上怕嬷嬷听见了。“你永远不回来,我也不在乎。”
她转身朝楼梯走去,估计他会伸出温暖的手,拉住她的胳臂,不让她走。但是他却打开前门,进来一股冷风。
“可是我一定要回来,”他说完就走了出去,剩下她一个人站在头一磴台阶上,看着关上了的大门发愣。
瑞德从英国带回来的戒指的确很大,大得思嘉都不好意思戴了。她是喜欢华丽贵重的首饰,不过她仿佛觉得大家都说这只戒指很俗气,也确实俗气,所以她感到有些不安。当中是一颗四克拉的钻石,周围有一圈绿宝石。这戒指盖住了整整一节手指,好像重重地压在手上。思嘉怀疑瑞德是费了很大力气定做了这只戒指,而且不怀好意,故意做得这么扎眼。
瑞德回到亚特兰大并把戒指戴在思嘉手上之前,思嘉没有把她的打算告诉任何人,连家里人也没告诉。她把订婚的消息一宣布,顿时引起了一场风波,人们议论纷纷。三K党事件之后,除了北方佬和北方来的冒险家之外,瑞德和思嘉就成了全城最不受欢迎的人。很久以前,查尔斯·汉密尔顿死后,思嘉早早地把丧服脱去,就遭到了众人的指责。经营木材厂是一般女人不干的事,怀孕之后还抛头露面,也显得很不体面,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引起人们更加严厉的指责。可是自从她造成了弗兰克和托米的死,而且危害了另外十几个人的生活,人们的指责一下子就变成了公开的谴责。
至于瑞德,战争期间他搞投机生意,就受到全城的痛恨,后来投靠共和党人,也没有赢得人们的好感。可是说也奇怪,他救了亚特兰大几位知名人士的命,却遭到亚特兰大的太太们强烈的仇恨。
她们并不是悔恨她们的丈夫依然健在。她们强烈不满,是因为她们的丈夫之所以健在,要归功于瑞德这样一个人,要归功于那样使人难堪的计谋。一连几个月,她们受到北方佬的讥笑和鄙视,抬不起头来,她们认为而且直言不讳,如果瑞德真为三K党着想,他就会以更体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她们说,他是故意把贝尔·沃特琳扯进来,使得城里有威望的人名誉扫地。因此,他虽然救了人,人们既不感谢他,也不宽恕他过去的罪过。
这些女人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能吃苦耐劳,但是如果谁对她们的不成文法规稍有违反,她们是毫不留情的。她们的法规也很简单:拥护联盟,尊敬老战士,忠于传统,人穷志不穷,宽厚待人,痛恨北方佬。在她们看来,思嘉和瑞德违反了法规中所有的要求。
瑞德救出来的那些人为了顾全面子,也为了感谢瑞德,想让他们的家属保持沉默,然而难以办到。在瑞德和思嘉还没有宣布准备结婚的时候,他们俩就很不受欢迎了,不过大家表面上对他们还客客气气。现在就连这种冷淡的客气也没有了。他们订婚的消息就像炸弹一样炸开来,来得突然,威力又大,全城为之震动,就连脾气最好的女人也直言不讳,谈起来非常激动。弗兰克死了刚刚一年,她就又嫁人了,弗兰克还是她杀死的呢!她嫁的这个名叫巴特勒的男人开着一家妓院,还和北方佬和北方来的冒险家合伙干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俩,要是单独说来,大家还觉得可以忍受,但是这样肆无忌惮地结合在一起,实在让人受不了。两个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恶人。真该把他们赶走,不让他们待在这个城市里。
如果他们俩订婚的消息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宣布的,亚特兰大也许会对他们俩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可是眼下瑞德结交的那些北方来的冒险家和投靠北方佬的南方人在当地有名望的公民之中名声特别不好。他们订婚的消息在亚特兰大传开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老百姓反对北方佬及其追随者的情绪最强烈,因为佐治亚州反对北方统治的最后一个堡垒刚被攻破。四年前谢尔曼从多尔顿以北向南进军,由此开始的漫长战役终于达到了高潮,屈辱的生活遍及整个佐治亚州。
重建运动已经进行了三个年头,这是充满了恐怖的三年。大家都觉得情况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现在人们才意识到佐治亚州重建时期最苦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三年来,联邦政府一直想把自己的思想和统治强加在佐治亚州身上。因为它依靠军队强制实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这新政权完全是靠武力维持的。佐治亚州虽然是在北方佬的统治之下,但是没有得到本州人的同意。州里的领导人不停地斗争,要求本州按照自己的意志实行自治的权利。他们坚决抵制,不肯屈服,拒不接受华盛顿的旨意作为本州的法律。
佐治亚州政府从未正式投降,但是它所进行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节节败退。在这场斗争中,它是不可能获胜的,不过它至少推迟了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在南方别的州里,已经有大字不识的黑人身居高位,或者进入了黑人和北方冒险家控制的州议会。但是佐治亚顽强抵抗,至今仍能避免这种厄运。三年之中,州议会大部分时间控制在白人和民主党人手中。北方佬军队到处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除了抗议和抵制之外,很难有所作为。他们的权力是有名无实的,不过他们至少还能把州政府控制在佐治亚州本地人手中。现在就连这最后一个堡垒也被攻破了。
四年前,约翰斯顿及其部下从多尔顿往亚特兰大节节败退,一八六五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就是佐治亚的民主党人步步退让。联邦政府在佐治亚州的权力日益增大,干涉州里的事务,影响百姓的生活。动用武力的情况日趋严重,军方的命令越来越多,使得文职官员越来越无能为力。最后,佐治亚州沦为一个军事区,不论本州的法律是否允许,根据命令,选举一定要让黑人参加。
就在思嘉和瑞德宣布订婚前一个星期,举行了一次州长选举。南方民主党人的候选人戈登将军是州里最受人爱戴、最有威望的人。和他竞选的共和党人名叫布洛克。选举进行了不是一天,而是三天。一列一列的火车把黑人从一个城市拉到另一个城市,沿途在各个选区投票选举。布洛克当然获胜。
如果说谢尔曼拿下佐治亚,百姓怨声载道,冒险家、北方佬和黑人最后拿下州议会就民怨沸腾了。这是佐治亚州从未有过的情况。亚特兰大,乃至整个佐治亚,群情激昂,怒气冲天。
而瑞德·巴特勒却是人们深恶痛绝的布洛克的朋友。
思嘉一向是除了鼻子底下的事以外,什么都不注意,所以这次选举,她几乎不知道。瑞德并没有参与这次选举,他和北方佬的关系也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瑞德总归是一个投靠北方佬的人,而且是布洛克的朋友。这桩婚事成了以后,思嘉也就成了投靠北方的人。对于敌人营垒中的人,亚特兰大无意采取宽容或谅解的态度。他们订婚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只想到与他二人有关的种种坏事,好事就都不记得了。
思嘉知道全城都对她不满,然而不知道群众气愤到了什么程度。后来梅里韦瑟太太在教友的催促下自告奋勇出来对她进行规劝。
“因为你母亲去世了,皮蒂小姐又没结过婚,没有资格来——唔——来跟你谈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不能不提醒你,思嘉,巴特勒船长这个人,良家妇女都不应该嫁给他,他是个——”
“他救了梅里韦瑟爷爷的命,还救了你的侄儿呢。”
梅里韦瑟太太一听这话,气得鼓鼓的。一个钟头以前,她还跟爷爷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谈话。那老头儿说,即或瑞德·巴特勒投靠北方,是个流氓,也不能一点都不感谢他,否则就是不把他这把老骨头放在心上。
“他只是在我们身上耍了一个鬼花招呀,思嘉,让我们在北方佬面前出丑,”梅里韦瑟太太接着说,“这个人是个大流氓,这咱们都是知道的。他一向是个流氓,现在大家恨死他了。正经人是决计不会接待他的。”
“不接待他?这就怪了,梅里韦瑟太太。战争期间,他也是你家的常客呀。他还送给梅贝尔一件白缎子结婚礼服,对不对?要不就是我记错了。”
“战争期间情况可就不同了,善良的人接触的许多人都不怎么——那都是为了事业,是完全正当的。你千万不要嫁给这样一个人,他不但自己没有参军打仗,还讥笑那些参军的人,你说是不是?”
“他也是参过军的。他在军队里待了八个月。参加过最后一次战役,在富兰克林打过仗,是跟着约翰斯顿将军投降的。”
“这可没听说过,”梅里韦瑟太太说,看样子她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可是他没受过伤,”她得意地补了这么一句。
“很多人都没受伤呀。”
“像个样子的人都受伤了。我就没听说谁没受伤。”
这句话可把思嘉惹火了。
“你认识的那些人大概都是傻瓜,下雨不避,子弹不躲。现在请你听着,梅里韦瑟太太,你也可以转告你那些爱管闲事的朋友。我要跟巴特勒船长结婚,就算他为北方佬打过仗,我也不管。”
这位尊贵的妇人气呼呼地走了出去,帽子一翘一翘的。这时思嘉意识到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对她不满的朋友,而成了公开的敌人。但她毫不介意。无论梅里韦瑟太太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对她说来都无所谓。谁说什么,她都不在乎——只是嬷嬷的话例外。
皮蒂姑妈一听说他们要结婚就晕倒了,思嘉熬了过来。艾希礼听到消息,突然老了许多,向她祝贺的时候,连看都不正眼看她,她也挺了过来。波琳姨妈和尤拉莉姨妈从查尔斯顿来信,使她啼笑皆非,她们听到消息之后都吓坏了,连忙阻止这门婚事,说这不但有损于她自己的社会地位,还会危及她们的声望。媚兰紧蹙双眉诚心诚意地对她说:“巴特勒船长当然要比许多人想象的好得多。他又厚道,又有办法,这才救出了艾希礼。他也总算是为联盟战斗过。不过,思嘉,最好不要这么仓促决定,你说是不是?”思嘉对媚兰这番话一笑置之。
任何人的话她都不在乎,但是嬷嬷的话不同,因为嬷嬷的话使她非常生气,非常伤心。
嬷嬷说:“你做的很多事,爱伦小姐要是知道,会伤心的。我也很难过。不过这件事你做得最不像话。嫁给一个下流坯!我就叫他下流坯!你不必说他是什么上好的人家出身,那也没有用。上等家庭出来的下流坯,也还是下流坯。思嘉小姐,我看着你从霍妮小姐手里把查尔斯先生抢过来,可是你并不爱他。我还看着你从亲妹妹手里把弗兰克先生抢过来。你干了很多事,我都没吭声,比方说,把坏木头当好木头卖,说同行的坏话,一个人赶着车到处乱跑,招惹那些自由黑人,让弗兰克先生送了命,你还不让犯人吃饱,差点把他们饿死。这些事,我都没吭声,就连爱伦小姐在九泉之下也会责怪我说:‘嬷嬷,嬷嬷!你怎么不好好照看我的孩子呀!’好吧,那些事都过去了,可这件事,我不赞成,思嘉小姐。你不能嫁给一个下流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你这样干。”
“我爱嫁谁就嫁谁,”思嘉无动于衷说,“我看你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吧,嬷嬷!”
“是啊,我早就该这么办了。我要是不对你说这些话,谁会对你说这些话呢?”
“我一直在考虑,嬷嬷,我觉得你最好回塔拉去吧。我给你一点钱,还有——”
嬷嬷摆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
“我有我的自由,思嘉小姐。我要是不想去,你让我上哪儿,我也不去。让我回塔拉去,你得跟我一块儿去。我不能丢下爱伦小姐的孩子不管,说什么我也不走。我也不能丢下爱伦小姐的外孙,让那个下流坯做继父,来抚养他们。我反正待在这里,不走。”
“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冲撞巴特勒船长。我已经决定嫁给他,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要说的话很多。”嬷嬷慢条斯理地顶了她一句,她那充满泪水的老眼里露出了决心大战一场的神情。
“我从来不想对爱伦小姐家的人说这样的话。可是,思嘉小姐,你听着。你完全是一头骡子,配了一套马笼头。你可以把骡子的脚擦得光光的,把皮擦得锃亮,把笼头都用铜叶子包起来,驾到一辆华丽的马车上。可是骡子还是骡子,这是骗不了人的。你也是这样。你穿着绸子衣裳,开着木材厂,开着商店,又有钱,还摆出一副架子,很像一匹好马,可你终究是头骡子。你也同样骗不了人。那个巴特勒,家庭出身好,打扮得像参加赛马一样漂亮,可他和你一样,也是一头套着马笼头的骡子。”
嬷嬷目不转睛地盯着女主人。思嘉听到这样的辱骂,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你要是非嫁给他,你就嫁给他吧,谁让你和你爸一样固执呢。可是,你别忘了,思嘉小姐,我是不会走的。我要在这里待下去,看个究竟。”
嬷嬷没等思嘉答话,一转身就走了。如果她当时说一声“等着瞧吧”,那语调也会令人毛骨悚然的。
后来他们在新奥尔良度蜜月的时候,思嘉把嬷嬷的话告诉了瑞德。瑞德一听嬷嬷说的骡子套着马笼头,便大笑起来,弄得思嘉又惊讶,又气愤。
“我从来没听见有人用这样简洁的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他说。“嬷嬷是个很有头脑的老人,这样的人不多,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尊敬和谅解。不过我既然是头骡子,恐怕永远也不会得到她的尊敬和谅解了。婚礼之后,我兴致勃勃地给她一个十块钱的金币,可是她拒不接受。很少见到有人在金钱面前不发软的。可是她瞪了我一眼,谢了谢我,说她不是自由的黑人,不需要我的钱。”
“她干吗要那么激动呢?人们为什么要像一群老母鸡似地朝我咯咯乱叫呢?我和谁结婚,结几次婚,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我从来不爱管闲事,可有些人为什么老爱管别人的闲事呢?”
“我的小乖乖,世人什么都可以原谅,就是不能原谅不爱管闲事的人。可是你干吗要像一只烫伤的猫似的嗷嗷乱叫呢?你常说无论人家怎么议论你,你都不在乎。为什么不证明一下呢?你知道,你在小事上常常受人指责,在这件大事上,你怎么能指望躲过人们的非议呢?你早就知道,嫁给我这样的坏人,是要招人议论的。如果我是个出身卑贱,一文不名的坏人,别人可能没有多少话好说。可是我这个坏人又有钱,又干得红火——这当然就不可饶恕了。”
“我希望你有时候能认真一点。”
“我现在就很认真。好人要是看见坏人像芝麻开花一样兴旺发达,心里就难受,历来如此。你也不必烦恼,思嘉,我记得有一次你对我说,你之所以要很多钱,主要是为了能对任何人说见鬼去吧。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可是我主要是想对你说见鬼去吧。”思嘉一面说,一面笑了。
“你现在还想对我说见鬼去吧?”
“不像以前那么想说了。”
“你什么时候想说,就说吧,只要能让你高兴就行。”
“我并不感到特别高兴。”思嘉说,低头随便亲了他一下。他那黑色的眼睛朝她脸上闪了一闪,想从她的眼中找到什么东西,可是什么也没找到。他笑了笑,说:
“忘掉亚特兰大吧!忘掉那些老猫吧!我带你来新奥尔良,是为了让你高兴高兴的,我一定要使你感到高兴。”
[1] 引自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第2幕第2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