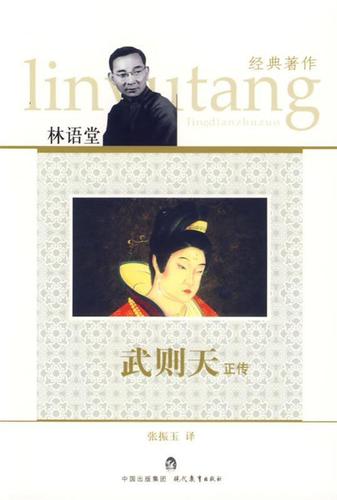第四十八章
思嘉在新奥尔良的确过得很愉快,从战前最后一个春天到现在,她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愉快。新奥尔良是一个奇异的热闹地方,思嘉就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突然获释一样,玩得痛快极了。北方来的冒险家在城里大肆掠夺,许多诚实的人流落街头,不知下一顿饭到哪里去找。一个黑人占据着副州长的位置。不过瑞德在新奥尔良带她去的地方,是她从未见过的繁华地区。她所见到的人,看上去都有的是钱,而且完全不必操心。瑞德介绍她认识了十几位妇女,她们长得漂亮,穿着鲜艳的袍子,两手细嫩,不像干过重活的样子,遇见什么事都要笑,从来不谈无聊的正经事,也不谈艰难困苦的日子。她见到的男人——多么令人兴奋呀!他们与亚特兰大的男人实在不同——都争着和她跳舞,不遗余力地向她献殷勤,好像她是舞会上的年轻皇后一样。
这些男人和瑞德一样,脸上都带着固执、鲁莽的神情。他们的眼睛始终很机警,好像很久以来生活在危险之中,不敢疏忽大意。他们似乎无所谓过去,也没有未来。思嘉有时想找个话题,就问他们来新奥尔良之前是干什么的,或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客气地把话题岔开。这本身就很奇怪,因为在亚特兰大,任何一个新来的体面人都急于把自己的经历讲一讲,炫耀一下自己的家庭,他们的亲属关系非常复杂,可以说遍布整个南方。
但是这些人都是沉默寡言的人,说起话来字斟句酌,非常谨慎。有时瑞德单独和他们在一起,思嘉在隔壁就听见他们的笑声,还断断续续听见他们的谈话,但她是听不明白的,只能听出零零碎碎的几个字,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其中有封锁时期的古巴和纳索,淘金热,非法侵占他人的采矿权,走私军火,海盗行为,尼加拉瓜和威廉·沃克,以及他如何在特鲁希略撞墙而死。有一次,她突然走进去,他们正在谈论匡特利尔[1]领导的游击队最近遭遇如何,见她进来,便连忙住口,她只听见两个人名字:弗兰克·詹姆斯和杰西·詹姆斯。
不过他们都文质彬彬,衣着考究,显然对她十分殷勤,因此他们这样时髦,她觉得无所谓。对她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瑞德的朋友,有宽敞的住房,有华丽的马车。他们带着她和瑞德去兜风,请他们吃晚饭,为他们举行晚会。思嘉觉得非常开心。她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告诉瑞德时,瑞德觉得很有意思。
“我想你是会这样的。”他一面说,一面笑。
“为什么不这样呢?”她和往常一样,一听见他笑,就起疑心。
“他们都是二流人物,是流氓,是恶棍。他们都是冒险家,北方来的贵族老爷。他们有的和你那亲爱的丈夫一样,做食品投机生意发了财,有的靠和政府签订非法合同或通过经不起调查的肮脏手段发了财。”
“我才不信呢!你在开玩笑吧。他们都是最老实的人……”
“城里最老实的人都在挨饿呢,”瑞德说,“他们规规矩矩地住在茅草棚里,要是我去看他们,我真怀疑他们会不会接待我。亲爱的,你知道战争期间我在这里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记性特别好,还没有把我忘掉。思嘉,你时时刻刻使我感到高兴。你总是喜欢那些不该喜欢的人,不该喜欢的事。”
“可是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啊!”
“唔,不过我喜欢流氓。我小时候就在内河一条船上赌博,所以我对这样的人是了解的。可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是看得很清楚的。然而你——”他又笑了起来,“你是没有识别人的本能的,下等人,上等人,你是分辨不清的。有时候我觉得你接触过的上等人只有你母亲和媚兰小姐,可是她们好像都没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媚兰!哎,她难看得要命,穿的衣裳也那么俗气,而且自己也说不出有什么看法。”
“太太,你还是不要妒忌吧。美貌不能使人高尚,衣着不能使人尊贵。”
“唔,真的吗?那你就等着瞧吧,瑞德·巴特勒,我要做个样子给你看看。现在我有了——我们有了钱,我要成为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尊贵的女性。”
“我非常乐意等着瞧。”他说。
思嘉会见的这些人固然使她兴奋,瑞德给她买的衣服更加使她兴奋。衣服的颜色、料子、款式都是他亲自挑选的。用圆箍撑起来的裙子现在已经不时兴了,流行的式样非常新颖,裙子从前面向后在腰垫处收拢,腰垫上装饰着花环,蝴蝶结,还有波浪形的花边。她觉得还是战争期间那种用圆箍撑起来的裙子好,现在这种新式裙子把肚子的轮廓全都露出来了,使她觉得有些难为情。那可爱的小帽子简直不像帽子,而是一个扁平的小玩意儿,斜着搭在一只眼上,上面别着花呀,果呀,走起路来羽毛跳跃,丝带飘动。(思嘉的头发像印第安人的发头一样硬,小帽子压不住,她买过一些假的发卷,想用来衬一下,可惜都让瑞德糊里糊涂地烧掉了。)还有修道院里做的精细的内衣,实在可爱,而且买了那么多套。还有一件件睡衣、睡袍、衬裙,都是用最细的亚麻布做的,上面绣着华丽的图案,纳着细碎的小褶。还有瑞德给她买的缎子拖鞋,后跟有三寸高,玻璃大鞋襻闪闪发光。长统丝袜有十几双,没有一双是棉统的。真阔气呀!
她毫无节制地花钱给家里人买礼物。给韦德买了一只圣比纳种的长毛小狗,因为他一直想要这样一条狗。给小博买了一只小波斯猫,给小爱拉买了一只珊瑚手镯。给皮蒂姑妈买的是一大串项链,上面挂着许多月长石坠子。给媚兰和艾希礼买的是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她给彼得大叔买了一套很像样的制服,包括一顶车夫戴的真丝高帽子,外带一把刷子,给迪尔茜和厨娘买的是衣料。给住在塔拉的人也都买了昂贵的礼物。
“可是你给嬷嬷买了什么呢?”瑞德在旅馆里把小狗小猫都赶到梳妆室里,一面看着床上摆的这一大堆礼物,一面问。
“什么也没买。这个人太可恨。她说咱们是骡子,干吗要给她礼物?”
“人家说的是真情实况,你何必怀恨在心呢,我的小宝贝儿?你一定得给嬷嬷一件礼物。你要是不给她礼物,就会刺伤她的心——像她那样的心是很可贵的,怎么能刺伤呢?”
“我什么也不给她买,她不配。”
“那我就给她买一件吧。我记得我的奶妈常说,她升天的时候要穿一条府绸裙子,这裙子要硬得能立得住,而且非常朴素,上帝一看会以为是用天使的翅膀做的。我就给嬷嬷买块红府绸,让她做一条漂亮的裙子吧。”
“她不会接受你的礼物的。她宁可去死,也不会穿的。”
“这我相信。不过我还是要做个姿态嘛。”
新奥尔良的商店里物品丰富,使人目不暇接,和瑞德一起买东西是令人兴奋的。和他一起下馆子,也令人兴奋,甚至更加令人兴奋,因为他知道点什么菜,也知道菜是应该怎么做的。新奥尔良的葡萄酒、露酒和香槟,对她说来都很新鲜,喝下去感到心旷神怡,因为她只喝过自家酿制的黑莓酒、野葡萄酒和皮蒂姑妈的“一喝就醉”的白兰地。这且不说,还有瑞德点的那些菜呢。新奥尔良的菜肴最有名。思嘉想到过去在塔拉挨饿的苦日子,又想到不久以前拮据的生活,吃起这些丰盛的菜肴来,觉得老也吃不够。有法式烩虾仁、醉鸽、酥脆的牡蛎馅饼、蘑菇杂碎烩鸡肝、橙汁烤鱼,等等。她的胃口总是很好的,因为她一想到在塔拉没完没了地吃花生、豆子和白薯,就想尽量多吃一些法式菜肴。
“你每次吃饭就像吃最后一顿饭似的,”瑞德说,“不要刮盘子呀,思嘉。厨房里肯定还有呢。只要叫堂倌去拿就行了。不过你要是老这么大吃大嚼,你就会胖得跟古巴女人一样,到那时候,我可就要和你离婚了。”
可是她只朝他吐了吐舌头,接着又要了一份点心。这点心上面是厚厚的一层巧克力,中间还夹了一层糖。
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不必一分一厘地算计,惦记着存钱纳税,或者买骡子,这可实在是痛快。交往的人都很高兴,很阔气,不像亚特兰大的人那个穷酸样儿,真是痛快。穿着窸窸窣窣的锦缎衣裳,显出腰身,露着脖子和胳臂,胸脯也露着不小的一块,而且还知道男人们对你垂涎欲滴,真是痛快。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没有人指责你缺乏大家闺秀的风度,真是痛快。香槟酒,想喝多少喝多少,也真是痛快。她头一次喝醉的时候,坐着敞篷马车,穿过新奥尔良的大街小巷回旅馆去,一路上高唱《美丽的蓝旗》。第二天清早,醒来以后,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想起头一天晚上那样出洋相,感到很不好意思。她以前连女人微有醉意也没见过。她只见过一个女人,就是那个名叫沃特琳的家伙,在亚特兰大失陷的那一天喝得酩酊大醉。她感到非常难为情,简直没有脸见瑞德,但他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无论她干什么事,他都觉得很有意思,仿佛她是一只性情活泼的小猫。
和他一道出去,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因为他长得漂亮。过去不知怎的,她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相貌。在亚特兰大,人们光看他的缺点,没有议论过他的相貌。可是在新奥尔良,她发现别的女人老拿眼睛盯着他,他弯腰吻她们的手,她们是那么激动。她意识到别的女人觉得她丈夫很有吸引力,也许还在羡慕她,这使她突然感到和他在一起十分光彩。
“唔,我们两口子都很漂亮。”思嘉想道,心里乐滋滋的。
是的,的确是像瑞德所说的那样,结婚是有很多乐趣的。不光是有乐趣,她还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件事说起来也很怪,因为她曾经认为生活不可能再教给她什么新东西了。可现在她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首先,她发现和瑞德结婚,与先前和查尔斯结婚,和弗兰克结婚,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尊重她,怕她发脾气。他们都向她乞求恩惠,她要是高兴,也就给他们一些恩惠。瑞德则并不怕她,而且她常常觉得瑞德也不怎么尊重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思嘉要是不喜欢,他就觉得很有趣。思嘉并不爱他,但和他生活在一起确实很有意思。最有意思的是,虽然他这个人发起火来有时让人觉得他有些冷酷,有时他倒是痛快了,别人却感到厌烦,他却总能控制自己的感情,驾驭自己的感情,就像有一副马嚼子似的。
“我想这大概是他并不真爱我的缘故吧,”她心里想,而且她对这种情况也是满意的,“我还真不希望他完全放纵自己的感情。”不过她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个想法使她既兴奋又好奇。
她和瑞德结合之后,了解到他许多新的情况,她原来还以为对他非常了解呢。她了解到他的声音可能一会儿温柔得像猫咪,一会儿又变成尖利的咒骂声。他可以表面上一本正经地赞扬在他去过的怪地方发生的英雄的、光荣的事迹和关于贞节与情爱的故事,马上又说一些最无情的玩世不恭的下流故事。她知道任何男人都不会对妻子讲这样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的确有趣,而且能在她身上引起一种粗俗的感情。他可以是一个热诚的几乎可以说是温柔的恋人,一转眼他又成了挖苦人的恶魔,把她那火药一般的脾气揭开盖子,点上火,引起爆炸,从中取乐。她了解到他的奉承话总有两层截然相反的涵义,他表现出来的最温柔的感情也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她待在新奥尔良的两个星期里,她了解了他各方面的情况,就是没有了解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有时他早上不用女用人,亲自用托盘把早点给她送到房里,一点一点地喂她,仿佛她是个孩子。他还把头刷从她手里拿过来,给她刷头发,刷得那乌黑的长头发噼啪作响。可是,有时候他早上突然把她身上盖的东西全掀开,挠她的脚,粗暴地把她从酣睡中惊醒。有时候他很认真地仔细听她述说生意中的各项细节,点头称赞她办事有头脑,有时候他就把她那些不是很正当的做法叫做捡便宜,叫做巧取豪夺。他带她去看戏,却悄悄地对她说也许上帝不赞成她到这种娱乐场所来,惹得她心烦。他带她到教堂去,却小声对她说些有趣的下流话,然后又责怪她发笑。他鼓励她有什么说什么,随便说,不拘束。她从他那里学了一些讽刺人挖苦人的字眼,而且逐渐喜欢使用这些字眼,觉得这样可以压人家一头。但是她还不会像瑞德那样,在恶毒之中搀上几分幽默,讥笑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讥笑别人。
他想让她玩儿,而她几乎已经忘了怎么玩了。生活一直是那么严峻,那么艰难。他是知道怎么玩的,于是就带着她一起玩。但是他不是像小孩子那样玩了;他是一个成年人,他的一举一动,她都是不会忘记的。女人看到尚有童心的男人做出滑稽可笑的动作不免要发笑,而思嘉是不能凭着女人的优越感看不起瑞德,朝他发笑的。
她一想到这种情况,就觉得不愉快。要是能比瑞德高出一筹就好了。她所认识的别的男人,她都可以置之不顾,以半带鄙视的口吻说:“简直是个孩子!”比如她父亲,比如好开玩笑、喜欢各种恶作剧的塔尔顿孪生兄弟,方丹家长着长毛,爱耍小孩子脾气的年轻人,查尔斯,弗兰克,所有在战争期间追求过她的人——实际上包括所有的人,艾希礼除外。只有艾希礼和瑞德是她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人,因为他们是成年人,身上没有孩子气。
她并不了解瑞德,也不想费事去了解他,虽然他有时候有些事使她迷惑不解。比如他有时以为她不注意,就偷眼看她,那眼神就很怪。她突然一转身,常常发现他在看她,眼中流露出机警、殷切与等待的神情。
“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有一次她不高兴地问,“好像一只猫盯着耗子洞!”
但是他立刻换上一副模样,只笑一笑。过一会儿,她就忘了,不再费脑筋想这件事,和瑞德有关的什么事也都不想了。他这个人反复无常,不必为他多费心思,生活也过得挺愉快——可是一想到艾希礼就不同了。
瑞德弄得她很忙,顾不上时常想到艾希礼。白天,她脑子里几乎就没有艾希礼,可是到了晚上,她跳舞跳累了,或者喝香槟喝得头晕脑涨——这时候,她就想起艾希礼来了。她迷迷糊糊地躺在瑞德怀里,月光洒落在床上,在这种情况下,她常常想,要是艾希礼的胳臂这样紧紧地搂着她,该有多好呀!要是艾希礼把她的黑发从自己脸上撩开,拢在下巴底下,该有多好呀!
有一次,她这样想着,叹了一口气,扭头朝窗口看去。过了一会儿,她感到脖子底下这只有力的胳臂好像成了铁的一样,在寂静之中听见瑞德的声音说:“上帝该把你永远打入地狱,你这个小妖精!”
说罢,他就起来,穿上衣服,走了出去。思嘉非常吃惊,拦他也拦不住,问他他也不理。第二天早晨,她正在自己屋里吃早饭,他又回来了。头发乱蓬蓬的,喝得醉醺醺的,不满的情绪依然很重,他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说明干什么去了。
思嘉什么也没问,对他十分冷淡。妻子受了委屈,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她吃完饭之后,瑞德用带着血丝的眼睛看着她换上衣服,出去买东西去了。等她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思嘉一直耐着性子,因为这是她在新奥尔良吃的最后一顿晚饭了,而且她还想好好享受一下龙虾的美味。可是瑞德老盯着她,使她吃也吃不痛快。不过她还是吃了一只大的,还喝了好多香槟。也许是因为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当天晚上她又做起了过去做过的噩梦。她醒来,出了一身冷汗,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塔拉,而塔拉是一片荒凉。母亲去世了,世上的一切力量与智慧也都随之消逝。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投靠,没有人可以依赖。有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追她,她就跑啊,跑啊,心都快炸开了,就这样在茫茫大雾之中一边跑,一边喊,模模糊糊地想在周围的雾里找到一个不知名的、没有去过的地方躲藏起来。
她醒来,发现瑞德正弯着腰看她。他什么话也没说,就把她抱起来搂在怀里,好像搂着孩子一样,搂得紧紧的。他那结实的肌肉给她以安慰,他那无言的低声细语使她感到镇静,过了一会儿,她也就不哭了。
“唔,瑞德,我刚才又冷,又饿,又累,而且怎么也找不着。我在雾里跑啊,跑啊,可就是找不着。”
“你找什么,亲爱的?”
“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又是以前作过的梦吗?”
“嗯,是的!”
他轻轻地把她放在床上,在黑暗之中摸索着点上一支蜡烛。在烛光下,他的眼睛带着血丝,他的脸上纹路清晰,像石头一样,看不出任何表情。他穿着衬衫,敞着怀,棕色的胸膛露在外面,上面长着厚厚的黑毛。思嘉还在吓得发抖,心里想,这个胸膛可是真坚强。她悄悄地说:“抱抱我吧,瑞德。”
“亲爱的!”他马上一边说,一边把她抱起来,坐在一把大椅子上,把她的身子紧紧搂在怀里。
“唔,瑞德,挨饿可是真可怕呀!”
“晚饭吃了七道菜,包括一只大龙虾,夜里睡觉还要梦见挨饿,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他笑了笑,不过眼睛里还是射出了和蔼的目光。
“唔,瑞德,我使劲跑啊,跑啊,找我要找的什么东西,就是找不着。躲在雾里,看不见。我知道,我要是能找到它,我就永远生活安定,再也不会受冻挨饿了。”
“你是在找一个人,还是在找一样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没好好想过。瑞德,你觉得我还会做梦想上生活安定的地方去吗?”
“不会的,”他说着,捋了捋她那蓬乱的头发,“我认为不会的。做梦不是这样做的。不过我认为你要是平时习惯于安定的生活,吃得饱,穿得暖,你就不会再做那样的梦了。思嘉,我一定使你过安定的生活。”
“瑞德,你真好。”
“感谢您的照顾,太太。思嘉,我劝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对自己说:‘我永远不会再挨饿了,我永远不会再有麻烦了,只要瑞德和我在一起,只要美国政府能维持下去。’”
“美国政府?”她吃惊地问,随着就坐起来,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
“过去联盟的钱现在已经变成了贞洁的女人,我用一大部分买了公债了。”
“我的老天爷!”思嘉喊道,直直地坐在他的腿上,刚才的噩梦也全然忘记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把钱借给了北方佬吗?”
“利息相当高啊。”
“百分之百的利息我也不管。你一定要马上卖掉。让北方佬用你的钱,亏你想得出。”
“那我这钱该怎么花呢?”他笑着问,这时他发现她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吓得睁着大眼睛了。
“怎么——怎么,你可以到五点镇去买地皮呀。我敢说,你那些钱把整个五点镇都买下来也够了。”
“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五点镇。现在冒险家的政府真正控制了佐治亚,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成群的秃鹰正从四面八方向佐治亚扑来,我不想逃避,我要和他们周旋,你明白吗,做一个像样的投靠北方的人就得这么干,不过我并不信任他们。我也不想把钱用来买房地产。我愿意买公债。公债可以藏起来。房地产就不那么好藏了。”
“你认为——”她问,因为她想起自己的木材厂和商店,脸都白了。
“我不知道。不过你不必这么害怕,思嘉。新上任的漂亮州长是我的朋友。现在时局太不稳定,我不想把很多钱投放在房地产上。”
他把她挪到一条腿上,微微向后一仰,伸手拿了一支雪茄,点上。她两只赤脚悬空坐在那里,看着他棕色胸膛上的肌肉伸缩,就把害怕的事全忘了。
“既然谈到房地产,思嘉,”他说,“我打算盖一所房子。你可以强迫弗兰克住在皮蒂小姐的房子里,我可不干。一天听她嚷嚷三回,我可受不了。还要,彼得大叔就是把我杀了,也不会让我住进神圣的汉密尔顿家的房子。皮蒂小姐可以请英迪亚·威尔克斯小姐去和她同住,免得坏人来捣乱。咱们回到亚特兰大以后,先住在民族饭店的新婚套间里,等咱们的房子盖好了就搬过去。咱们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就在跟他们讨价还价,准备买下桃树街上那一大片空地,就是莱顿家旁边那块空地。你一定知道我说的地方。”
“啊,瑞德,太好了。我多么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呀。我要一所特大的。”
“咱们总算在某件事情上有了一致的看法。盖一所白灰墙、铁花栏杆的房子,和这里的法式建筑一样,好不好?”
“唔,不好,瑞德。不要新奥尔良这种老式的房子。我知道要什么样的。我要最新式的,我看到过一个图样,在——让我想一想——在我看的一份《哈泼斯周报》上。是模仿一所瑞士chalet[2]。”
“一所瑞士什么?”
“chalet.”
“哪几个字母?”
她把这个词的拼法告诉了他。
“噢。”他一面说,一面捋了捋小胡子。
“非常好看。斜度不同分成两段的屋顶,上面有一溜栅栏,两头各有一个尖塔,是用彩色木瓦板盖的。尖塔上的窗户镶着红蓝玻璃。看上去可时髦了!”
“我想回廊上还有锯齿形的栏杆吧?”
“是啊。”
“回廊屋顶的边上还有木头做的云形花饰垂下来,是不是?”
“是的。你一定见过这么一所房子。”
“我是见过——但不是在瑞士。瑞士人非常聪明,对建筑艺术更有独到之处。你真的要这样一所房子吗?”
“啊,是呀!”
“我原来希望你和我结婚之后,能提高你的格调。你为什么不喜欢法式房子,或六根白柱子的殖民地式的房子呢?”
“实话对你说吧,看上去俗气的,过时的,我都不要。里面我要用红纸糊墙,用红天鹅绒做门帘。啊,我要好多高级胡桃木家具,还要华丽的厚地毯,还要——啊,瑞德,人人看了咱们的家,人人都会羡慕得脸色发青的。”
“有必要让大家都羡慕咱们吗?你要是高兴,可以让他们羡慕得脸色发青。不过,思嘉,你想过没有,现在大家都这么穷,咱们布置房子这样摆阔气,能算是格调高吗?”
“我就要这样,”她固执地说。“过去他们对我那么刻薄,现在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我们要大开宴会,让全城的人后悔当时不该说那样难听的话。”
“可是谁会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呢?”
“怎么,当然是人人都会来的。”
“那可不一定。这些保守派是宁肯死了也不认输的。”
“唔,你这是说什么呀!你只要有钱,大家就一定喜欢你。”
“南方人可不是这样。有钱的投机商要想进入上等人家的客厅,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至于投靠北方的人——我是说我和你,我的宝贝儿——要是不受到唾弃,就算走运了。不过你要是想试一试,我可以支持你,亲爱的,我也一定会为你所做的努力感到非常高兴。既然现在谈到钱,那就让我把话说清楚。家里过日子,买穿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要是喜欢首饰,也可以买,但是要由我来挑选,你的格调太低,我的宝贝儿。给韦德,给爱拉,想买什么,你就买什么。要是威尔·本廷种棉花种得好,我也愿意资助,帮你卸掉在克莱顿区你那么喜爱的那个沉重的包袱。这可以说是很公平了吧?”
“当然,当然。你是很慷慨的。”
“不过请你仔细听明白。一分钱也不能花在你那商店上,一分钱也不能花在你那劈柴厂上。”
“唔。”思嘉说,脸也沉下来。蜜月期间,她一直在想怎样提起这个话题,要一千块钱,再买五十英尺地,扩大木材厂。
“我记得你老吹嘘,说自己是个开明的人,我做生意,别人有些什么议论,你全不在意,谁知你和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就怕人家说我当家。”
“咱们巴特勒家谁当家,那是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疑问的,”瑞德慢条斯理地说。“傻瓜们说些什么,我是不介意的。其实,我缺乏教养,现在有个能干的老婆,也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我想让你继续经营你的商店和木材厂。给你的孩子们留着吧。等韦德长大以后,他会觉得不便让继父养活他,他就可以接过去,接着经营。但是无论是商店,还是木材厂,我一分钱都不给。”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资助艾希礼·威尔克斯。”
“你又来了,是不是?”
“不是。是你要问原因,我就把原因告诉你。还有一件事,不要以为你可以在账目上耍花招,蒙骗我,说你买衣服花多少钱,家里的开销要多少钱,结果却把钱拿去替艾希礼买骡子,或者再买一个木材厂。我要监督审查你的各项开支,什么东西多少钱,我是清楚的。唔,不要以为我是在侮辱你。你非这样做不可。我对你是不会放松的。实际上,凡是涉及塔拉和艾希礼的地方,我都不会对你放松。塔拉倒还无所谓。艾希礼可一定要划在界线以外。我正在缓缓地驾驭着你,我的宝贝儿,可是你不要忘记,同样也是有马嚼子和马刺的。”
[1] 威廉·克拉克·匡特利尔(1837—1865),美国南部联盟游击队领袖。
[2] 英语,意为:木结构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