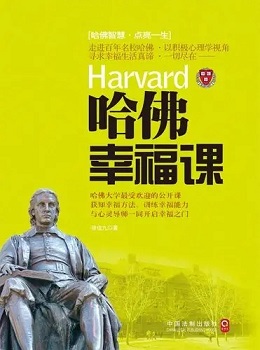第五十九章
谁心里都清楚,邦妮·巴特勒越来越野了,有必要严加管教,然而她又是人人喜爱的宠儿,谁都不忍心去严格约束她。她是在跟父亲一起旅行那几个月里开始放纵起来的。她和瑞德在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时,就得到允许晚上高兴玩到什么时候都行,常常在剧院里、饭店里或牌桌旁倒在父亲怀里睡觉。后来,只要你不加强制,她就决不跟听话的爱拉同时上床去睡。她和瑞德在外面时,瑞德总是让她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而且从那时候起,每回嬷嬷叫她穿细布长袍和围裙,而不让穿天蓝色塔夫绸衣裳和花边护肩时,她就要大发脾气。
一旦孩子离家外出,以及后来思嘉生病去了塔拉,便失去了对她的管教,好像从此就再也管不住她了。等到邦妮长大了些,思嘉又试着去约束她,想不让她变得太任性、太娇惯,可是效果并不怎么好。瑞德常常护着孩子,不管她的要求多么荒唐,行为多么乖僻。他鼓励她随意说话,把她当大人看待,显然十分认真地倾听她的意见,并且装作听从似的。结果,邦妮常随意干扰大人的事,动不动就反驳父亲,使他下不了台。但是瑞德只不过笑笑而已,连思嘉要打她一下手心以示警戒,他也不允许。
“如果她不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宝贝儿,她也就吃不开了,”思嘉郁郁不乐地想,明白她的孩子原来和她自己一样倔强,“她崇拜瑞德,要是他愿意的话,是完全可以让她变好的。”
可是瑞德没有表现出要教育孩子学好的意思。她做什么都是对的,她要月亮就给月亮,如果他能去摘下来的话。他对她的美貌,她的鬈发,她的酒窝,她的优美姿势,无不感到骄傲。他爱她的淘气,爱她的兴高采烈,以及她用以表示爱他的那种奇特而美妙的样子。尽管她有些娇惯和任性的地方,但她毕竟是那样可爱的一个孩子,他怎么忍心去约束她呢!他是她心目中的上帝,是她那小小世界的中心,这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他决不冒丧失这一地位的危险去训斥她。
她像影子似的紧跟着他。早晨,他还不想起来时她就把他叫醒;吃饭时坐在他旁边,轮换地吃着他和她自己碟子里的东西;骑马出门时坐在他面前的鞍头上;晚上睡觉时只让瑞德给脱衣服,把她抱到他旁边的小床上去。
思嘉眼看自己的女儿用一双小手牢牢地控制着她的父亲,心里又高兴又感动。谁想到像瑞德这样一条汉子,做起父亲来偏偏会如此严肃认真呢?不过,有时候思嘉也心怀妒忌,痛苦不堪,因为邦妮刚刚四岁,却比她更加了解瑞德,更能驾驭他了。
邦妮满四岁后,嬷嬷便开始唠叨,抱怨一个小姑娘不该骑着马,“横坐在她爸前面,衣裳被风撩得高高的”。瑞德对于这一批评颇为重视,因为嬷嬷提出的有关教育女孩子的意见,他一般都比较注意。结果他就买了一匹褐色的设特兰小马驹,它有光滑的长鬃和尾巴,连同一副小小的带有银饰的女鞍。从表面上看,这匹小马驹是给三个孩子买的,瑞德还给韦德也买了一副鞍子。可是韦德更喜爱他的那条圣伯纳德狗,而爱拉又害怕一切动物,因此这匹小马驹便成了邦妮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巴特勒先生”。邦妮的占有欲得到了满足,惟一遗憾的是她还没有学会像她父亲那样跨骑在马鞍上。不过经过瑞德向她解释,说明侧骑在女鞍上比跨骑还要困难得多,她便感到高兴而且很快就学会了。瑞德对她骑马的姿势和灵巧的手腕是非常得意的。
“等着瞧吧,到她可以打猎了的时候,准保世界上哪个猎手也不如她呢,”瑞德夸口说,“那时我要带她到弗吉尼亚去,那里才是真正打猎的地方。还有肯塔基,骑马就得到那里去。”
等到要给她做骑马服了,照例又得由她自己挑选颜色,而且她照例又挑上了天蓝色的。
“不过,宝贝儿!还是不要用这种蓝丝绒吧!蓝丝绒是我参加社交活动时穿的呢,”思嘉笑着说,“小姑娘最好穿黑府绸的。”这时她看见那两道小小的黑眉已经皱起来了,便赶紧说:“瑞德,看在上帝面上,你告诉她那种料子对她多不合适,而且多容易脏呀!”
“唔,就让她做蓝丝绒的。要是弄脏了,我们就给她再做一件。”瑞德轻松地说。
这样,邦妮便有了一件蓝丝绒骑马服,衣襟直垂到小马的肋部;还做了一顶黑色的帽子,上面插着根红羽毛,那是受了媚兰讲的杰布·斯图尔特故事的启发。每当风和日丽,父女俩便骑马在桃树街上并辔而行,瑞德勒着缰绳让他那匹大黑马缓缓地配合那只小马的步伐溜达。有时他们一直跑到城郊的僻静道路上,把孩子们和鸡呀、狗呀吓得乱窜。邦妮用马鞭抽打着她的“巴特勒先生”,满头纠缠着的鬈发迎风飘舞,瑞德则紧紧地勒着他的马,让她觉得她的“巴特勒先生”会赢得这场赛跑。
后来瑞德确信她的坐势已很稳当,她的手腕已很灵巧有力,而且她一点也不胆怯了,便决定让她学习跳栏,当然那高度只能是小马的腿长所能达到的。为此,他在后面场院里放置了一个栏架,并以每天二十五美分的工钱雇用彼得大叔的侄子沃什来教“巴特勒先生”跳栏。它从离地两英寸开始,逐渐跳到一英尺的高度。
这个安排遭到了最有关系的三方:即沃什、“巴特勒先生”和邦妮的反对。沃什是怕马的,只因为贪图高工钱才勉强应承教这只倔强的小马每天跳栏二十次。“巴特勒先生”让它的小女主人经常拉尾巴和看蹄子,总算还忍受得住,可是觉得它那肥胖的身躯是生来越不过那根栏杆的。至于邦妮,她最不高兴别人骑她的小马,因此一看见“巴特勒先生”被沃什骑着练习跳栏,便急得直顿脚。
直到瑞德最后认定小马已训练得很好,可以让邦妮自己去试试了,这孩子才无比地兴奋起来。她第一次试跳即欣然成功,从此便觉得跟父亲一起骑马外出没什么意思了。思嘉看着这父女俩那么兴高采烈,不禁觉得好笑,她心想一旦这新鲜劲儿过去,邦妮便会转到别的玩意儿上,那时左邻右舍就可以安静些了。可是邦妮对这项游戏毫不厌倦。后院里从最远那头的凉亭直到栏架,已出现一条踏得光光的跑道,从那里整个上午都不断传来兴奋的呐喊声。这些呐喊,据一八四九年作过横跨大陆旅行的梅里韦瑟爷爷说,跟一个阿帕切人[1]成功地剥了一次头皮后的欢叫完全一样。
过了一个星期,邦妮要求将栏杆升高些,升到离地一英尺半。
“等到你六岁的时候吧,”瑞德说,“那时你能跳得更高了,我还要给你买匹大一些的马。‘巴特勒先生’的腿不够长呢。”
“够长。我已经跳过媚兰姑姑家的玫瑰丛了,那高得很呢!”
“不,你得等等。”瑞德说,这回总算表现得坚定些。可是这坚定在她不停的恳求和怒吼下又渐渐消失了。
“唔,好吧,”有天早晨他笑着说,同时把那根窄窄的白色横杆挪高一些,“你要是掉下来,可别哭鼻子骂我呀!”
“妈!”邦妮抬起头来朝思嘉的卧室尖叫着,“妈!快看呀!爹爹说我能跳啦!”
思嘉正在梳头,听见女儿喊叫便走到窗口,微笑着俯视这个兴奋的小家伙,她穿着那件沾满了尘土的天蓝色骑马服,模样可真怪。
“我真的得给她另做一件了,”她心里想,“尽管天知道我怎能说服她丢掉这件脏的啊。”
“妈,你看!”
“我在看着呢,亲爱的。”思嘉微笑着说。
瑞德将孩子举起来,让她骑在小马上,这时思嘉瞧着她那挺直的腰背和昂起的头,顿时从心底涌起一股自豪感,不禁大声喊道:
“你漂亮极了,我的宝贝儿!”
“你也一样呢,”邦妮慷慨地回赞她一句,一面用脚跟在“巴特勒先生”的肋上狠狠一蹬,便向凉亭那边飞跑过去了。
“妈,你瞧我这一下吧!”她大喊一声,一面抽着鞭子。
瞧我这一下吧!
记忆在思嘉心灵的深处隐隐发出回响。这句话里仿佛有不祥的意味。那是什么呀?难道她记不起来了?她俯视着她的小女儿那么轻盈地坐在飞奔的小马上,这时一丝凄冷陡地掠过她的胸坎。邦妮猛冲过来,她那波翻浪涌般的鬈发在头上掀动着,天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
“这像爸的眼睛,爱尔兰人的蓝眼睛,”思嘉心想,“而且她在无论哪个方面都像他呢。”
她一想起杰拉尔德,那正在苦苦搜索的记忆便像令人心悸的夏日闪电般霍然出现,立即把一整幅乡村景色照得雪亮了。她听得见一个爱尔兰嗓音在歌唱,听得见从塔拉草坡上疾驰而来的马蹄声,听得见一个跟她的孩子很相像的鲁莽的呼喊声:“爱伦,瞧我这一下吧!”
“不!”她大声喊道,“不!唔,邦妮,你别跳了!”
正当她探身窗口时,一种可怕的木杆折裂声,瑞德的吼叫声,以及一堆蓝丝绒和飞奔的马蹄猝然坍倒在地上的声响,便同时传来了。然后,“巴特勒先生”挣扎着爬起来,驮着一个空马鞍迅速地跑开了。
邦妮死后第三个晚上,嬷嬷蹒跚着慢慢走上媚兰家厨房的台阶。她全身穿黑,从一双脚尖剪开了的大男鞋到她的黑色头帕都是黑的。她那双模糊的老眼里布满了血丝,眼圈也红了,整个笨重的身躯上几乎无处不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她那张脸孔皱巴巴的,像只惶惑不安的老猴似的,不过那下颚却说明她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
她对迪尔茜轻轻说了几句,迪尔茜亲切地点点头,仿佛她们之间那多年以来的争斗就这样默默地休战了。迪尔茜放下手中的晚餐盘碟,悄悄地穿过餐具室向饭厅走去。不一会儿,媚兰来到了厨房里,她手里还拿着餐巾,满脸焦急的神色。
“思嘉小姐不是——”
“思嘉小姐倒是平静了,跟平常一样,”嬷嬷沮丧地说,“俺本来不想打搅你吃晚饭,媚兰小姐。可是俺等不及了,要把俺压在心里的话跟你说说呢。”
“晚饭可以等一会儿再吃嘛,”媚兰说,“迪尔茜,给别的人开饭吧。嬷嬷,跟我来。”
嬷嬷蹒跚着跟在她后面,走过穿堂,从饭厅门外经过,这时艾希礼已端坐在餐桌上首,小博在他旁边,思嘉的两个孩子坐在对面,他们正把汤匙弄得丁丁当当乱响。饭厅里充满着韦德和爱拉的欢快的声音。他们觉得能跟媚兰姑姑在一起待这么久,真像是吃野餐呢。媚兰姑姑一向很和气,现在尤其是这样。小妹妹的死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影响。邦妮从她的小马上摔下来,母亲哭了很久,媚兰姑姑把他们带回家来,跟小博一起在后院玩耍,想吃时便一起吃茶点饼干。
媚兰领路走进那间四壁全是书籍的起居室,关好门,推着嬷嬷在沙发上坐下。
“我准备吃过晚饭就马上过去的,”她说,“既然巴特勒船长的母亲已经来了,我想明天早晨就会下葬了吧。”
“下葬吗,正是这个问题呀,”嬷嬷说,“媚兰小姐,我们都弄得没办法了,俺来就是求你帮忙呢。这世上事事都叫人心烦,亲爱的,事事都叫人心烦啊!”
“思嘉小姐病倒了吗?”媚兰焦急地问,“自从邦妮——以来,我就很少看见她呢。她整天关在房子里,而巴特勒船长却出门去——”
泪水突然从嬷嬷那张黑脸上滚滚而下,媚兰坐到她身旁,轻轻拍着她的臂膀。一会儿,嬷嬷便撩起她的黑衣襟把眼睛拭干了。
“你一定得去帮忙我们呀,媚兰小姐。俺已经尽了俺的力了,可一点用处也没有。”
“思嘉小姐——”
嬷嬷挺直了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