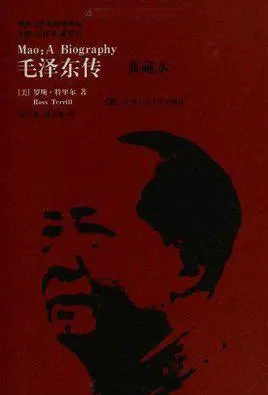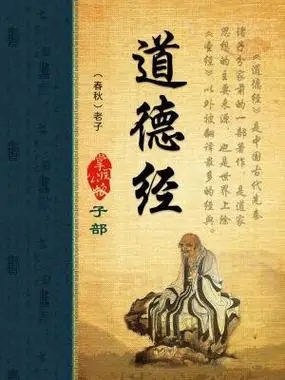第六十一章
思嘉是在马里塔时收到瑞德的加急电报的。恰好十分钟后就有一趟去亚特兰大的火车,她便搭上了,除了一个手提网兜没带任何行李,把韦德和爱拉留在旅馆里由普里茜照看着。
亚特兰大离马里塔只有二十英里,可是火车在多雨的初秋下午断断续续地爬行着,在每条小径旁都要停车让行人通过。思嘉被瑞德的电报吓慌了,急于赶路,因此每一停车都要气得大叫起来。列车笨拙地行进,穿过微带金黄色的森林,经过残留着蛇形胸墙的红色山坡,经过旧的炮兵掩体和长满野草的弹坑。在这条路上,约翰斯顿的部队狼狈撤退时曾经一步步苦战不已。对每一个站和每一个十字路口,列车员都是以一个战役或一次交火的名称来称呼。要是在过去,这会引起思嘉回想当时的恐怖情景,可现在她不去想这些了。
瑞德的电报是这样的:
“威尔克斯太太病重速归。”
火车驶进亚特兰大时,暮色已浓,加上一片蒙蒙细雨,城市就显得朦胧不清了。街灯暗淡地照着,像雾中一些昏黄的斑点似的。瑞德带着一辆马车在车站等候她。她一看他的脸色,便比收到电报时更惊慌了。她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毫无表情呢。
“她没有——”她惊叫道。
“没有。她还活着。”瑞德搀扶着她上了马车,“去威尔克斯太太家,越快越好。”他这样吩咐车夫。
“她怎么了?我没听说她生病嘛。上星期还好好的。她遇到了什么意外吗?唔,瑞德,情况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她快死了,”瑞德说,声音也像面色一样毫无表情:“她要见你。”
“媚兰不会的!啊,媚兰不会的!她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呀?”
“她小产了。”
“小——产,可是,瑞德,她——”思嘉给吓得说不出话。这个消息紧跟着瑞德宣布的濒危状况,使她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你不知道她怀孕了吗?”
她甚至连头也没有摇一摇。
“哎,是的。我看你不会知道。我想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她要叫人家大吃一惊呢。不过我知道。”
“你知道?她绝不会告诉你的!”
“她没有必要告诉我。不过我知道。最近两个月来她显得那么高兴,我就猜这不可能是别的缘故。”
“可是瑞德,大夫曾说过,如果再生孩子就要她的命了!”
“现在就要她的命了,”瑞德说,接着他责问马车夫:“看在上帝面上,你能不能更快一点?”
“不过,瑞德,她不见得会死的!我——我都没有——”
“她的抵抗力不如你好。她一向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除了一颗好心以外,她什么也没有。”
马车在一座小小的平房前嘎的一声停住,瑞德扶她下了车。她胆战心惊,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感袭上心头,她紧紧抓住他的臂膀。
“你也进去吧,瑞德?”
“不,”他说了一声便回到马车里去了。
她奔上屋前的台阶,穿过走廊,把门推开。艾希礼、皮蒂姑妈和英迪亚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思嘉心想:“英迪亚在这里干什么呢?媚兰说过叫她永远也不要再进这个门嘛。”那三个人一见到她便站起身来,皮蒂姑妈紧紧咬着嘴唇不让它们颤抖;英迪亚瞪大眼睛注视着她,看来完全是为了悲伤而没有恨的意思。艾希礼目光呆滞,像个梦游人似的向她走来,伸出一只手握住她的胳臂,又像个梦游人似的对她说话。
“她要见你,”他说,“她要见你。”
“我现在就去看她好吗?”她回头看看媚兰的卧室,卧室门是关着的。
“不。米德大夫在里面。我很高兴你回来了,思嘉。”
“我是尽快赶回来的。”思嘉将帽子和外衣脱了,“火车——她不是真的——告诉我,她好些了,是不是,艾希礼?你说呀!别这样愣着嘛!她不见得真的——”
“她一直要见你呢。”艾希礼说,凝视着她的眼睛。同时思嘉从他的眼神里找到了答案。顿时间,她的心停止了跳动,接着是一种古怪的恐惧,比焦急和悲哀更强大的恐惧,它开始在她胸膛里蹦跳了。这不可能是真的,她热切地想,试着把恐惧挡回去。大夫也会做出错误的诊断呢。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真的。我要是相信便会尖叫起来了。我现在得想想别的事情了。
“我决不相信!”她大声喊道,一面注视着面前那三张绷紧的面孔,仿佛质问他们敢不敢反驳似的,“而且媚兰为什么没告诉我呢?如果我已经知道,就不会到马里塔去了。”
艾希礼的眼神好像忽然清醒过来,感到很痛苦似的。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思嘉,特别是没有告诉你。她怕你知道了会责备她。她要等待三个月——要到她认为已经安稳和有把握了的时候才说出来,叫你们全都大吃一惊,并笑话大夫们居然诊断错了。而且她是非常高兴的。你知道她对婴儿的那种态度——她多么希望有个小女孩。何况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后来,无缘无故地——”
媚兰的房门悄悄地开了,米德大夫从里面走出来,随手把门带上。他在那里站立了一会,那把灰色胡子垂在胸前,眼睛望着那四个突然吓呆了的人。他的眼光最后落到思嘉身上。他向她走来时,思嘉发现他眼中充满了悲伤,同时也有厌恶和轻蔑之情,这使她惊慌的心里顿时涌起满怀内疚。
“你毕竟还是来了。”他说。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艾希礼便要向那关着的门走去。
“你先不要去,”大夫说,“她要跟思嘉说话呢。”
“大夫,让我进去看她一眼吧,”英迪亚拉着他的衣袖说,她的声音尽管听起来很平淡,但比大声的要求更加诚恳,“我今天一早就来了,一直等着,可是她——就让我去看看吧,哪怕一分钟也行。我要告诉她——一定要告诉她——我错了,在——在有些事情上。”
她说这些时,眼睛没有看艾希礼或思嘉,可是米德大夫冷冷的目光却自然地落到了思嘉身上。
“等会儿再说吧,英迪亚小姐,”他简单地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说你错了这些话去刺激她。她知道是你错了。你这时候去道歉只会使她烦恼的。”
皮蒂也怯生生地开口了:“我请你,米德大夫——”
“皮蒂小姐,你明白你是会尖叫的,会晕过去的。”
皮蒂挺了挺她那胖胖的小个儿,向大夫瞥了一眼。她的眼睛是干的,但充满了庄严的神色。
“好吧,亲爱的,稍等一等,”大夫显得和气些了,“来吧,思嘉。”
他们轻轻地走过穿堂,向那关着的门走去,一路上大夫的手紧紧抓住思嘉的肩膀。
“我说,小姐,”他低声说,“不要激动,也不要作临终时的忏悔,否则,凭上帝起誓,我会扭断你的脖子!你用不着这样呆呆地瞧着我。你明明懂得我的意思。我要让媚兰小姐平平静静地死去,你不能只顾减轻自己良心上的负担,告诉她关于艾希礼的什么事。我从没伤害过一个女人,可是如果你此刻说那种话——那后果就得由你自己承担了。”
他没等她回答就把门打开,将她推进屋里,然后又关上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陈设着廉价的黑胡桃木家具,灯上罩着报纸,处于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它狭小而整洁,像间女学生的卧室,里面摆着一张低背的小床,一顶朴素的网帐高高卷起,地板上铺着的那条破地毯早已褪色,但却刷得干干净净。这一切,跟思嘉卧室里的奢侈装饰,跟那些高耸的雕花家具、浅红锦缎的帷帐和织着玫瑰花的地毯比起来,是多么不一样啊!
媚兰躺在床上,床罩底下萎缩单薄的形体就像是个小女孩似的。两条黑黑的发辫垂在面颊两旁,阖着的眼睛深陷在一对紫色的圆圈里。思嘉见她这模样,倚着门框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不能动弹了。尽管屋里阴暗,她还是看得清媚兰那张蜡黄的脸,她的脸干枯得一点血色也没有了,鼻子周围全皱缩了。在此以前,思嘉还一直希望是米德大夫诊断错了呢。可现在她明白了。战争时期她在医院里见过那么多这种模样的面孔,她当然知道这预示着什么了。
媚兰快要死了,可是思嘉心里一时还拒不承认。媚兰是不会死的。死,对于她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当她思嘉正需要她、那么需要她的时候,上帝决不会让她死去。以前她从没想到自己会需要媚兰呢。可如今真理终于显现,在她灵魂的最深处显现了。她一向依靠媚兰,哪怕就在她依靠自己的时候,但是她以前并不清楚。现在媚兰快死了,思嘉才知道,没有她,自己是过不下去的。现在,她踮着脚尖向那个静静的身影走去,内心惶恐万状,她才知道媚兰一向是她的剑和盾,是她的慰藉和力量啊!
“我要留住她!我不能让她走!”她一面想,一面提着裙子在床边刷的一声颓然坐下。她立即抓起一只搁在床单上的软弱的手,发觉它已经冰凉,便又吓住了。
“我来了媚兰。”她说。
媚兰的眼睛睁开一条缝,接着,仿佛发现真是思嘉而感到很满意似的,又阖上眼,停了一会,她吸了一口气轻轻地说:
“答应我吗?”
“啊,什么都答应!”
“小博——照顾他。”
思嘉只能点点头,感到喉咙里被什么堵住了,同时紧紧捏了一下握着的那只手表示同意。
“我把他交给你了,”她脸上流露出一丝微微的笑容,“我从前已经把他交给过你一次——记得吗?——还在他出生以前。”
她记不记得?她难道会忘记那个时候?她记得那样清清楚楚,好像那可怕的一天又回来了。她能感到那九月中午的闷热,记得她对北方佬的恐惧,听得见部队撤退时的沉重脚步声,记起了媚兰说如果自己死了便恳求她带走婴儿时的声音——还记得那天她恨透了媚兰,希望她死掉呢。
“是我害死了她,”她怀着一种迷信的恐惧这样想,“我以前时常巴望她死,上帝都听见了,因此现在要惩罚我了。”
“啊,媚兰,别这样说了!你知道你是会闯过这一——”
“不。请答应我。”
思嘉忍不住要哽咽了。
“你知道我答应了。我会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上大学?”媚兰用微弱的声音说。
“唔,是的!上大学,到哈佛去,到欧洲去,只要他愿意,什么都行——还有——还有一匹小马驹——学音乐——唔,媚兰,你试试看!你使一把劲呀!”
又没声息了,从媚兰脸上看得出她在挣扎着竭力要往下说。
“艾希礼,”她说,“艾希礼和你——”她的声音颤抖着,说不出来了。
听到提起艾希礼的名字,思嘉的心突然停止跳动,僵冷得像岩石似的。原来媚兰一向就知道啊。思嘉把头伏在床单上,一阵被抑制的抽泣狠狠扼住她的喉咙。媚兰知道了。思嘉现在用不着害羞了。她没有任何别的感觉,只觉得万分痛恨,恨自己多年来始终在伤害这个和善的女人。媚兰早已知道——可是,她仍然继续做她的忠实朋友。唔,要是她能够把那些岁月重新过一遍,她就决不做那种事,对艾希礼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