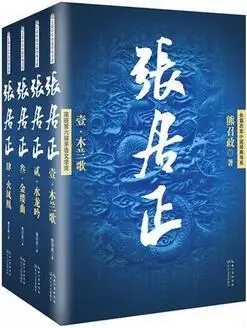大冯的成功,对于王钟儿意味着什么呢?她的墓志说:“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这里的“太和中”,应该是高照容死后的太和二十年(496)或二十一年(497),王钟儿已五十七八岁。当大冯接管元恪的抚养权,要扮演母亲角色时,元恪的生母高照容固然必须消失,长期服侍高照容、帮助她养育孩子的王钟儿也不能再留在元恪的世界里。墓志说王钟儿“固求出家”,实际上,很可能是被安排出家。不过,她虽然出家,却没有离开洛阳宫,墓志说“即居紫禁”,就是仍然生活在宫内。墓志后面说她老年生病时迁往“外寺”,那么在皇宫内的尼寺大概可称“内寺”。作为比丘尼,她获得了新的身份,法名慈庆。我们今后就用慈庆来称呼她。
当慈庆开启陌生的比丘尼生涯时,诸事顺遂的皇后大冯正在享受她的高光时刻。不过大冯一定想不到,她的高光时刻不会如她所愿的那样延续很久,事实上前后合起来还不到一年。
不赞成孝文帝迁都和改制的人一定很多,只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消极抵抗别无他法,少数胆敢走极端者如穆泰、陆叡等也几乎注定会失败。大冯废储夺宫一路走下来,得罪的人虽远不如孝文帝多,然而她显然是比孝文帝更容易针对的目标,而且很可能,她引发、招徕并凝聚的敌意更具体、更鲜明、更迫切。可以设想,个人性的愤懑与敌意会在适当的时候转化为社会网络,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目标明确的有计划行动。当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巨大的宫廷阴谋都不大可能留有文件,圈内人讳莫如深,圈外人茫然不晓,写史者无可得而措笔,读史者无可得而窥秘。正如元恂失去孝文帝信任及随后被废被杀的真实过程已无从复原,毫不奇怪的是,围绕大冯人生最后两年所发生的一切也相当怪诞离奇。
对孝文帝来说,大冯被立为后,一年多来高度紧张的洛阳宫终于安定,他可以专心对萧齐用兵了。一个半月后,即太和二十一年八月庚辰(497年10月7日),“车驾南讨”。送别的时候,大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一次致命的分别,正享受巅峰感的她完全意识不到,与皇帝的长时间隔离会给暗中的敌对者最大的机会。一年半后她才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而那时她的悲惨结局已经无可挽回了。
孝文帝在位的最后五年,差不多一半时间用在对萧齐用兵,要么身在南征军中,要么忙着筹划南征。他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把北魏的南部边境大幅前推,压迫萧齐的北方边境向南退缩,以便为首都洛阳制造更安全的战略空间。从孝文帝的军事安排看,他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在洛阳的正南方,面对萧齐的雍州(襄阳)重镇,必须夺取萧齐在汉水(沔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做到与萧齐隔汉水分境。第二个,是把魏境南推至淮河上游的桐柏山、大别山北麓,夺取萧齐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军镇义阳(今河南信阳)。第三个,是在东南方向攻占萧齐的淮南地区,把南朝防线挤压到长江南岸,实现与南朝隔江对峙。这三个目标,要用三个战役分别达成。三大战役可分别称为沔北战役、义阳战役和淮南战役。从历史发展看,孝文帝用半年多实现了第一个目标,紧接着启动义阳战役,想尽快实现第二个目标。然而后院失火,洛阳宫的动荡迫使他紧急班师。这样他就永远失去了实现第二个和第三个目标的机会。
从太和二十一年九月到二十二年(498)三月,北魏大军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南齐书·魏虏传》∶“(元)宏时大举南寇,伪咸阳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宝掌王元丽、广陵侯元燮、都督大将军刘昶、王肃、杨大眼、奚康生、长孙稚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其诸王军朱色鼓,公侯绿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鼙角,吹唇沸地。”《资治通鉴》把这段话简化为“众号百万,吹唇沸地”,其中“吹唇沸地”一词后来常见用于诗词。清末黄遵宪写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诗,有“压城云黑饿鸱鸣,齐作吹唇沸地声”之句。见《人境庐诗草》卷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黄遵宪集》,中华书局,2019年,第263页。],把南阳盆地的几个萧齐郡县戍城分割隔断,筑围攻击,先后攻克新野、赭阳、舞阴、南乡、南阳(宛城)和邓城,萧齐的沔北五郡尽数入魏,齐军据守的军城中,只剩下汉水边的樊城兀然独存。樊城依托汉水,南与襄阳相连,对于魏军来说,既难攻击,又难守御。孝文帝见好就收,满足于距离洛阳最近的萧齐势力已基本清除,于三月庚寅(498年4月15日)来到樊城城下,“观兵襄沔,耀武而还”。之后孝文帝马不停蹄地奔赴淮源,去实现他的第二个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当孝文帝亲临新野城下,指挥大军“筑长围以守之”,可谓戎马倥偬之际,他却抽出时间处理了一宗可能只有大冯才会关心的事务。太和二十一年十月乙亥(497年12月1日),“追废贞皇后林氏为庶人”。贞皇后林氏即元恂生母,被冯太后杀害已十四年,四年前因元恂被立为太子而追尊为皇后。元恂被废被杀时,似无人想起这位空有名号的皇后。现在孝文帝忽然有此决定,表面上是因“有司”上报,事实上只能是在洛阳的大冯想起此事,或被提醒,不能容忍有人分享皇后名号,才有这么一份报告出现在孝文帝面前。孝文帝批准追废林氏,固然有礼法依据,但也可看出他对大冯情义如故。不过半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

沔北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孝文帝命征南将军王肃开始围攻义阳城,这标志着第二个战役的开始。孝文帝在樊城城下耀兵沔上、南望襄阳之后,立即挥师东进,加入王肃刚刚启动的义阳战役。这次行军异常迅疾,半个月后,即太和二十二年三月辛亥(498年5月6日),孝文帝抵达义阳战役中魏军的大本营悬瓠城。这个悬瓠城,就是王钟儿(慈庆)被俘入平城宫之前长期生活过的那个汝河上游的军事重镇。
因萧齐援军渐至,速胜的机会已经丧失,孝文帝在进入悬瓠二十天之后,于四月庚午(5月25日)下诏“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这大概是因为,魏军不得不把相当兵力留在沔北,只好另外动员兵力投入义阳战役。这次动员的各地人力物力,包括北镇的高车部落。据此安排,来自各州郡的增援军队到八月中旬才能抵达悬瓠,因而对义阳的总攻只有到八月底以后才能展开,那么九月前的四个月,除战役筹备之外别无大事,孝文帝本人并无必要留在悬瓠。然而,孝文帝从三月底进驻悬瓠,到诸军齐聚的九月底突然宣布停止义阳战役,他竟然在悬瓠城住了整整五个月。这是极不正常的。
一个解释是孝文帝突然病重。《北史·后妃传》说大冯与宦官高菩萨私乱,“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据此,孝文帝病重在前,得知大冯失德在后。《魏书·术艺·徐謇传》:“(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驲招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孝文帝的确在悬瓠重病了一场,病因很可能是长期吃五石散或各种丹药(甚至可以说,北魏皇帝多壮年病死者,主要是因为食散服丹),因此急招擅长合金丹的御医(侍御师)徐謇到悬瓠。这一番忙乱,身为皇后的大冯自然知道了皇帝生病之事,所以《北史·后妃传》的叙事时序似乎有道理。不过,《徐謇传》载孝文帝九月间在汝滨为感谢徐謇举行的宴会上所下的诏书,明确说到自己生病的时间:“仲秋动痾,心容顿竭,气体羸瘠,玉几在虑。”可见孝文帝生病在八月,去三月底初至悬瓠已经四个多月了。因此,孝文帝久驻悬瓠,是别有原因的。
皇帝离开这么久,洛阳的确出了一些乱子,表面上看,最严重的是高级官员间发生了内斗。孝文帝留在洛阳处理政务(称为“留台”)的三个主要官员是尚书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和御史中尉李彪,冲突发生在李冲与李彪之间。论资历地位,李彪远逊于李冲。而且李冲还是李彪最主要的提携者。《魏书·李冲传》:“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虽然李彪是顿丘李氏,李冲为陇西李氏,本无宗亲关系,但李彪对李冲“倾心宗附”,便是以同为李姓而结宗致敬的意思。后来李彪得孝文帝重用,大概对李冲的“宗敬”颇不及初:“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魏书·李彪传》:“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按照《魏书》这种叙述,李冲对李彪的打击是出于个人原因,与国事关系不大。不过《魏书》又记李冲的态度是不寻常的愤怒:“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李冲一贯持重、温和,怎么会突然间性情大变呢?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一场蓄积已久的大爆发。
我认为,李冲这场大爆发是洛阳一连串针对大冯行动的一个环节,当然可能还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李彪是洛阳最高司法官员,掌握着洛阳城内外的治安警戒大权,宫内外各种秘密活动很难逃过他的眼线。正是因此,当针对大冯的大规模行动即将展开时,李彪是应该首先被除掉的。如此显要、深得皇帝信任的一个人物,怎么才除得掉呢?唯一的途径是让留台三驾马车自相残杀。只有这时,李冲与李彪的隐性矛盾才可能被利用、被放大、被引爆。
而且不要忘记,李彪正是导致废太子元恂最终被杀的举报人,是他“承间密表,吿恂复与左右谋逆”。无论李彪的举报是不是受到孝文帝指使,他的行为决定了他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大冯一党。也不要忘记了,元恂立为太子后,李冲一直担任太子少傅,所以太子被废,李冲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孝文帝谢罪。李冲对元恂被陷害一定有所察觉,只是无可奈何而已,而他提携起来的李彪直接助力了元恂之死,这当然会使他愤懑难抑。在皇帝缺席的洛阳,那些想除掉李彪的人,对这些情况必定了如指掌。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都是谁,但他们的确是存在的,而且历史地看,他们无处不在、十分强大。他们要做的,只是一点点撑大李冲和李彪之间的裂隙,在李冲那里火上浇油,促使他爆发。
李冲联合元澄对付李彪,“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书孝文帝,激烈地攻击李彪,甚至赌上了自己一生积攒的政治资本。李冲虽在上表中隐隐提及“往年以河阳事”(即诬告元恂事),毕竟不敢冒犯皇上,但最后说:“如臣列得实,宜殛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分明是不共戴天的决绝。孝文帝读表大惊:“何意留京如此也!”尽管为了李冲的面子不得不处理李彪,但还是留有余地。“有司处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而且,孝文帝还很不高兴地说:“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道固是李彪的字,仆射指李冲,意思是两人都不知谦谨,致有此乱。从孝文帝这一各打五十大板的评论来看,他似乎完全没有读出这一事件的重大政治含义。
李冲和李彪的这场冲突何时发生,史无明文,《资治通鉴》系于太和二十二年三月底四月初之间,把二人冲突的始末及因此李冲发病而死总而叙之,似是认为冲突发生在三月底之前。这样处理很可能是对的。无论如何,尽管这个事件相当严重,而且随后李冲死去,都没有影响孝文帝完成义阳战役的决心。只是随着李彪被除名,洛阳宫内外针对大冯的行动开始加速。大概是五月至七月间的某一天,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孝文帝的计划,逆转了五年来宫廷政治的发展方向。
不知道具体的日期[《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太和二十三年二月,只是为孝文帝终审大冯补叙前因,不可以当作编排年月的依据。陈留公主到悬瓠向孝文帝密告皇后,只会发生在前一年的夏天,很可能在五六月间。],一定是在夏季,一个下雨的日子。孝文帝的六妹,过去的彭城公主,现已改号陈留公主,没有官员陪同,没有士兵护卫,没有车队随行,只带着她自己的侍婢家僮,总共十几个人,“乘轻车,冒霖雨”,狼狈不堪的样子,突然出现在悬瓠城下。可能是在公主的要求下,和孝文帝谈话时,并无他人在侧(据《魏书·皇后传》,彭城王元勰因侍疾得以闻知)。公主向皇兄报告的内容,史书只说是皇后秽乱后宫,诸如“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等。当然内容未必限于这些,不过已足够让孝文帝震惊了。《北史·后妃传》:“帝闻,因骇愕,未之信,而秘匿之。”以孝文帝的聪明敏感与经验丰富,自然知道事关重大。如果皇后大冯真是一直在他背后另有一套,那么过去几年他自己在许多事情上的判断与处置,很可能都是错误的。其中包括自己的长子元恂,而这是任何为人父者都难以面对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是好几个月,孝文帝身在悬瓠,心在洛阳,秘密调查由此展开。之所以留在悬瓠不动,就是因为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为什么陈留公主会加入针对大冯的行动中呢?
大冯的生母姓常,常氏为冯熙生了两个孩子,即大冯和她的弟弟冯夙。大冯为冯夙谋划婚事,立意要让他“尚主”,就是娶一个公主。这时孝文帝诸妹中,陈留公主恰好新寡。《北史·后妃传》:“是时彭城公主,宋王刘昶子妇也,年少嫠居。北平公冯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于孝文,孝文许之。”大冯替弟弟向孝文帝求婚,孝文帝许婚,说明孝文帝对大冯仍然是信任和宠爱的。不过这一婚事的当事人之一陈留公主(即彭城公主)却是万般的不乐意,“公主志不愿”,就是看不上冯夙其人。只是既然孝文帝已许婚,身为后宫之主的冯皇后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公主的抵抗空间极为有限。正是被逼入绝境,且刻不容缓的形势,把陈留公主推向了皇后大冯的对立面,加入一个正快速发展的计谋网络中。
公主志不愿,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与侍婢及僮从十余人,乘轻车,冒霖雨,赴悬瓠,奉谒孝文,自陈本意,因言后与菩萨乱状。帝闻,因骇愕,未之信,而秘匿之。(《北史·后妃传》)
古代史料存在如何解读的问题,标点句读是难点之一。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和《北史》上引文的标点,“婚”字都从下句,作“婚有日矣”,似乎是已成婚一段时间了。如果是这样,陈留公主的反抗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是皇后大冯逼公主与冯夙完婚,即所谓“欲强之婚”,拖不下去了,公主不得不铤而走险,密赴悬瓠。后来关于陈留公主婚姻史的叙述,都只说她先嫁刘昶之子刘承绪,后嫁王肃,不提她嫁过冯夙。如果公主与冯夙成婚有日,那么即使后来离婚,也要算她嫁过冯家。[关于陈留公主,请参看我的一篇旧作《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后收入散文集《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
从陈留公主到悬瓠那天开始,孝文帝需要“日理”的“万机”中,优先项不再是义阳战役的筹备,而是洛阳宫隐秘诸事的调查。当然,非常可能的情况是,他的这一番调查,不过是发现了别人希望他发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