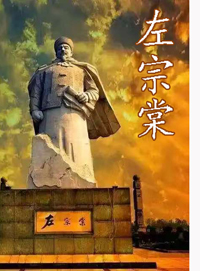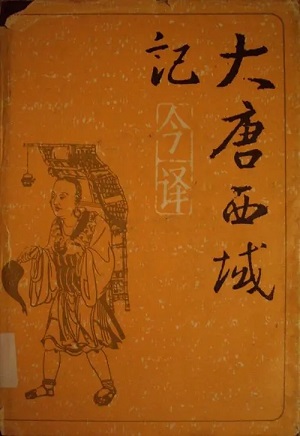第十六师团有关官兵所说的“真相”
铃木明所采访的第十六师团有关军官和士兵达十人之多,在此我不能一一论及,故列举该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谈话要点,研究一下中泽三夫是否说出了真相。
据说,中泽三夫先强调说:“所谓南京屠杀之谈,战后我在东京审判时才首次听到,为之一愣。”继而他又断言:“我们负责城内警备,因而无疑是知道的,比如,在难民区必设岗哨,不让士兵等入内。据悉,宪兵人手不够,但辅助宪兵则相当多,宪兵过于严厉,以致遭到其他部队的抗议。所谓来自难民区的表示不满的报告,从未听说过。在东京审判时引人注意的则是侵犯外国权益问题。然而,这却是由于中国人打着外国的旗帜企图蒙骗而引起的纠纷。揭发难民区内的便衣兵,这是日本军义不容辞的行动,绝无随意带走平民百姓而加以杀害之类的事情,而带走的士兵则以俘虏对待。当时,我恰在南京。如果因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而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那是大错特错了。”(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三四页)
中泽三夫虽然这样说,但他作为中岛师团长的部下,又是参谋长,果真对南京暴行一无所知吗?中岛师团长在南京攻陷战中,曾受到松井军司令官的指责,说“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长的战斗指挥违反人道”。可是,中岛不久便当上了南京警备司令官,使中国人觉得可怕。对此,据说同属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八联队的助川联队长也对铃木明说;“我记得,虽前往南京,但我对南京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听说自己也许要在东京审判时成为犯人(助川未被起诉)大吃一惊。对我来说,说是事件,真可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助川是佐佐木到一旅团长麾下的部队长官,而佐佐尔到一则是著有《一个军人的自传》的性格刚毅的将军,他掌握着“南京事件”的关键。这个助川还能说什么事实一无所知吗?而且,东京审判是审判甲级战犯的法庭,像助川这样的联队长担心成为被告,也令人可笑。因此,不言而喻,铃木明所注“助川未被起诉”并非是事实。
据说,当铃木明就田伯烈和埃德加-斯诺的著作提出问题时,中泽三夫简单地下结论说:“我们没有干过,仅此而已。”对此,铃木明说;“明快而又坦率,是无可反驳的发言。”铃木明并不否定南京事件的存在,却又为何对中泽三夫的全盘否定,写出“无可反驳的发言”这篇可理解为全面支持中泽三夫的文章呢?这篇文章是在欺骗读者。
这一点暂且不说,但我认为,在中泽三夫的谈话中否定暴行的每一句话,都是伪证,对此,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和本节后面所述,便一清二楚。
最后,我想对前面所引的前少将中泽三夫的谈话置一言。他在谈话结束时说:“中国方面从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说尸体有多少具。然而,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却是大错特错了。”说这话的人难道真是当时在场的负责人吗?连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占领南京的战果,也说遗弃尸体有八、九万具(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或说有八万四千具(昭和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人说,中国方面特地抛开坟墓,挖出尸骨,并把它计算在南京沦陷时的遗弃尸体中,等等。我们不妨想一想,中国人听到这种编造出来的谎言,将会多么愤慨!
※ ※ ※
铃木明在寻访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旅行中,必定已发现了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位名叫西田的士兵(住于三重县久居)每天写的随军日记。
对于西田所记之事,铃木明说:“他说得生动,较之军官说的更为出色”(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三页)。我们与其尊重三十五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尊重当时在场者的每天所记内容。介绍山田旅团长的笔记是铃木明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上刊登的采访报道的压卷之作。今后如能在杂志上原封不动地全文介绍这份稀有的宝贵资料,将不胜感激。《“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从西田手记中摘取了十一月份中的六天笔记作了介绍(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在占领南京时所记的日记却被人隐藏了,这样就无从知道事件的详细情况。
前军事有关人员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
第十六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接受了铃木明的采访,就南京事件发责了谈话。他在战后不久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亦曾作为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如此叙说,虽然偏离了对铃木明观点的批判,但我想在此让读者看一看日本军中有关事件的负责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采取了什么态度。
毋庸赘述,松井司令官不是下令屠杀俘虏、残兵败卒和对普通老百姓施加暴行的人。他力图阻止这种行为,那也是事实。然而,他的部下官兵却无视他的有关严肃军纪的训令,妄自采取了残暴行动。松井大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被追究其作为最高司令官应对部下的这种行为负责,判处了绞刑。我认为,这虽实属不幸,却也出于无奈。山下大将在马尼拉进行军事审判时自然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日本军在南京所犯大规模暴行是无可抵赖的确凿的事实。不言而喻,松井大将也在前面所引的手记和谈话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参照本书第二二八、二三七页)。尽管如此,松井大将为什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没有如实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呢?事实上,他可能离开南京后就卧病在床,因而不了解事件的整个情况。不过他非但没有一问三不知,而且对检察官就屠杀事件所作的审问,一口断定:“这绝对弄错了,决没有理由存在这种罪状。我能以名誉起誓担保,并陈述如上”(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审问调查书〔检证一0一0四〕,《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1,第七十七页)。此外,松井大将在宣誓供词(辩证二七三八)中也说:我相信,绝对没有进行过像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所主张的那种有计划的集体屠杀这一事实(《远速》,三二0号,载前引书1,二七六页)。他坚持这一主张,可能丝毫没有考虑要减轻部下和他本人的罪责。那末,他为什么不肯如实承认事实,向中国人民赔罪呢?
※ ※ ※
对于日本军的暴行,不仅松井大将,就是站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的华中方面军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加以否定。举例如下:
当时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少佐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说:
“我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前后赴南京时,巡视了市内,所看到的中国人尸体只有在下关附近一百具左右以及亚洲公园附近三十具左右,这可能是战死的中人的尸体。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平民的尸体和被屠杀的尸体。
听说,在南京俘虏约有五千名,而这些俘虏不仅没有被屠杀,而且据两军的报告,已妥善地释放到扬子江对岸。”(《远速》,二一四号,载前引书1,第二0四页)
当时在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大佐的审问调查书(检证第一0一0
五)中说:“我在南京正式入城时,随松井大将前往。而且,当时已发生了十至二十起事件……我决不相信,也难以想象会有几千起事件发生。”(《远速》,八十四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四页)
当时在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七)中说:“在南京根本不存在日本军有计划地进行强奸的事实。我知道,虽有少数触犯风纪的人,但这些人均已绳之以法.”(《运速》,三0九号, 载前引书1,第二四五页)
当时在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七)中说:“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二十日、年底三次巡视了南京城内, 从未在城内看到尸体,只是在下关附近看到几十具战死的尸体,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几万具被屠杀的尸体。”(《远速》,三0九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二页)
当时在第九师团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七中队代理队长大内义秀少尉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八)中说:“中国兵的尸体,我只是在扬子江岸边看到少许,未曾看到被屠杀的尸体等等。”(《远速》,三0九号,载前引书1,第二三九页)
当时在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三七)中说:“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前一直留在南京,但我的部下没有一个人犯罪……攻下南京后,未在南京城内外听到枪声。如果有机枪等扫射情况,理当听得见,但从未听到过这种枪声。”(《远速》,三0九号,载前引书1,第二三九页)
当时在上海派遣军参谋-原主计的宣誓供词(辩证二二三七)中说:
“所谓南京发生火灾,那也是日本军占领南京之前的事,占领后就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火灾。据我所知,只有极小部分地方失火,大部分市街并没有烧到。”(《远速》,三一0,载前引书1,第二五八页)
当时在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宣誓供词(辩证二七0八)中说: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中午左右进入南京,下午巡视了第十军的部分警备地区(南京城内南部)。当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其他尸体。”(《远速》,三一0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六页)
所举例子似乎有点过于繁冗,我觉得这些证词竟然说他们都是清白无辜的。可是,武藤章中将在上述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审问(检证一0一0五)后,于四月二十二日进行的审问(检证二二七三)中不得不承认发生过暴行事件,回答说:“在南京,原决定由两个或三个大队进入市内,可是结果全军都入了城,终于在南京发生了掠夺暴行事件。”(《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七二页)
※ ※ ※
关于前面所引小川关治郎法务官的证词,最近公开发表了他亲笔写的资料,颇为有趣地暴露了那完全是伪证。《军事警察(宪兵和军法会议)》第六卷作为《现代史资料续编》出版,第一次分发给订购者,书中收录了《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这份日志是不值一提的记录,但在附录“月报”中刊有小川的部分随军笔记却是引人注目的资料。值得庆幸的是,通过随军笔记可以检验小川宣誓供词记述内容的可靠性。
如前所述,前法务官小川在其宣誓供词中说,他在巡视第十军的部分警备地区(南京城内南部)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其他尸体”。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在这份随军笔记里记下了如下事实。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乘汽车外出,与兽医部长同车出发。
据说,到南京有十八里路程……驶近城墙南门(中华门。——《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注)。为货车、载客汽车、车辆等所阻,不能前进,停车约一个多小时……路上看到中国正规军士兵的尸体重重叠叠,并着了火在焚烧。日本兵看到足下横卧着的尸骸,也几乎都不以为然。由于路上全是尸体,有的士兵在行走时跨过正在焚烧的尸体,犹如对人类的尸体之类已无感知。渐至南门前(下午三时三十分。——《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注)……进入南门后,看到路边两侧中国兵的尸体成堆。
〔翌日十五日〕下午,外出视察市内情况。所有十字路口均设置了铁丝网,而在铁丝网旁边又有几个中国正规军的士兵倒毙在地,日本兵并在其衣服上点火焚烧。目睹此状,我别无异样感受。日本兵也几乎毫无感受,视之犹如路边之物,这种情景不是身在战场上所能看得到的,各处依然是熊熊烈火,黑烟冲天。
对两种记述作一番比较,便可看出供词的伪造情况,甚至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如果说不愿涉及与己不利的事实,尚情有可原,但在这里竟篡改事实,敢于作伪证。从这一例子中可以窥知,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如在法庭上宣誓后所提供的证言、宣誓供词等,大都令人难以置信。
且说小川这篇随军笔记,它是在现场每天记下来的,还是后来整理后加以誉写的,不看到原件则不可断言。可是,该随军笔记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却一无所知。
这点姑且不说,但可以推测,这份随军笔记是反映南京事件真相的重要资料。不知何故,至关重要的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的日记却没有介绍出来,令人不胜遗憾。
※ ※ ※
关于就日本军所犯违法事件的处置问题,两位负责人即两个军团的法务官在其宣誓供词中提供了如下证词。第十军于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南京城,同月十九日调防。该军的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说:“在驻留南京期间,我未曾听到关于日本兵有违法行为的传闻,而且也没有人对违法事件进行起诉。因为日本军处于作战状态之中,军纪颇为严格”(前引宣誓供词)。上海派遣军法务官兼检察官冢本浩次说:“对破坏军纪、风纪者则予以严肃处置。十二月和第二年一月中所调查的事件仅十起左右。在处分者中,军官有四、五人,其余大都是士兵所犯下的零星事件,从未处理过集体屠杀案犯。”(宣誓供词〔辩证一0七四〕,《远速》,第二—一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九二页)
松井大将也在他那前面介绍过的手记中说,受到军法会议处置的,包括军官在内有数十人。因此,我认为这两个法务官所说的情况基本上是事实。
且看小川法务官所说的情况。诚然,看了前面所说的《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可知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前,触犯风纪者,如对中国人进行杀人、强奸、猥亵、放火、掠夺等情况,收到宪兵队提交的报告有二十二份(此外,关于伤害军马、威胁上司、临阵脱逃者各一份),但在十四日至十九日第十军驻留南京期间却没有受理过一份搜查报告。也就是说,仅就军法会议而言,宣誓供词所说的并无虚假。
不过,不应该由于起诉的件数少,就说触犯风纪者也少;也不能由于在南京无一份搜查报告,因而说没有违法事件发生。法务部没有对罪犯进行搜查的权利,只有直属军司令部的宪兵押来嫌疑犯时才能起诉。因此,虽有违法事件,但宪兵不拟搜查,或者违法事件频繁发生,无法处理,这时审判等于零。最重要的是,当初在占领南京之际,甚至连非常重要的宪兵也寥寥无几,捉襟见时,这在前面已有详细叙述(参照本书第一0七页以后)。
日本军对俘虏和便衣兵进行集体屠杀,无疑是根据命令执行的,因而,这些执行者当然不能成为惩罚的对象。对普通老百姓的残暴行为,出于维护军纪的需要,理应根据从严惩处的方针加以处置。然而,如前所述,南京由于日本军的占领,已成为地狱。在那里,暴行屡屡发生,不计其数,陷入无法处理的状态之中,因而事实上不可能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于是,就发生的事件,提出不足几百分之一的例子,判处轻罪,敷衍了事。
※ ※ ※
以中泽三夫少将为首的许多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以辩护方面的证人身份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们都否认曾进行过大屠杀这一事实。这不只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证人的态度,而且也是当事人一致表现出来的态度。唯独一个有关人员肯定了这一事件的存在,他便是在南京的特别军事法庭上以大屠杀事件的负责人身份被判处死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以B-C级战犯而成为这起事件的被告人仅谷寿夫师团长一人,其他军司令官、部队长官以及参谋长等人均免予起诉。然而,谷寿夫中将虽认为自己无罪,却也承认有大屠杀之事实,并要求惩处大屠杀的负责人。谷寿夫中将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被宣判死刑的第二天提出上诉,说:“应当先向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许多部队长查明事实的全部情况,然后确定真正的犯人。”(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二三六页)
还有一份冈村宁次大将所作的有关记录,当时,他是派遣军首脑人物,他作了承认南京事件的发言。冈村宁次中将曾经于—九三八年八月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他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在上海登陆后一、两天内,从先遣部队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一九三七年七月任驻华使馆武官。——洞富雄注)、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那里听取了情况,总的情况如下:一、攻陷南京时,事实上确实发生了对数万市民大肆进行掠夺、强奸等暴行;二、第一线部队有以补给为名杀害俘虏之弊端。”(《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册,第二九一页)
对遗弃尸体掩埋表之怀疑以及市民受害之“实际数字”
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埋数字,铃木明对中国方面的主张也是持极端批判态度的。负责掩埋南京城内外遗弃尸体的,生要是慈善团体即红-字会和崇善堂。据它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认为处理的尸体数目惊人:红-字会处理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崇善堂处理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具。
铃木明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辩护团体一样,认为这个数字缺乏可靠性,他说:“即使充分理解红-字会和崇善堂的善意,南京有关人员也一眼即可看出这个数字是夸大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仅是铃木明,可能谁都会对这一过于庞大的数目,表示怀疑,都想说,在未看到原始资料前不能妄加评论。然而,日本方面理当预料得到,掩埋队提交的报告尚在,所以,可想而知不必担心中国方面也会向法庭提出虚构材料作证的。现在,我认为前面所说的数目是完全可信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数目问题,另参照本书第一编第6节以及以后的第三三四至三三六页、第四0七至四0八页)
总而言之,遗弃尸体的数目相当大。处理尸体花了近一年时间也丝毫不足为奇。因此,所谓“在业已清除过的中山门附近等地,五个月后不可能还有那么多尸体”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据说,五个月、十个月后,甚至一年半后,在部分小河里还填满了白骨(参照本书第一九八页)。
※ ※ ※
铃木明也批评了中国方面关于在特定地点遭受屠杀的说法。为此,我对此作一叙述。
据悉,在南京市当局编印的某本《南京大屠杀摄影集》里开头刊登的“大屠杀地图”上,在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对此,铃木明说,那里附近民房全部焚毁,绝无居民,即使后来有人被带到这里来遭受杀害,也不能认为是大量的。他还介绍了雨花台永宁寺住持的证词,说“决没有在这一带杀过人”,以为这是事实(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页),那是铃木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前后从前独立大队炮兵联队石松那里听来的。
诚然,南京攻陷战结束后,没有在雨花台进行大量屠杀的事实,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信的。不过,当时这一带几个月来遍地都是大量遗弃尸体,那也是事实。据崇善堂掩埋队留下的资料,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城外的兵工厂、雨花台地区掩埋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
这样多的遗弃尸体,可以说不是由于屠杀造成的,而是通过歼灭战这一正当的战斗行动导致的伤亡的结果。然而,中国方面看来,这却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说,在雨花台,有两、三万中国兵在撤退时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哭声连天、尸骨成堆、血流过胫,一片惨状(参照本书第二十六页)。
由此看来,在“大屠杀地图”上的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顺便介绍一下,从正面进攻雨花台的第六师团,分出其一部分部队迂回到南京城西侧,在该地区也取得了骇人听闻的“战果”(参照本书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
此外,据说在“大屠杀地图”上这样写着:在离南京城东北八公里左右的扬子江岸边燕子矶有数万普通平民百姓遭到屠杀,在其附近的观音门有三万普通老百姓遭到屠杀。对此,铃木明表示怀疑:数万普通老百姓逃进这一地势险要的山地,是“绝难想象”的。他还特地说,南京附近的人们若要躲避战火,是不可能向日本军进攻过来的东南方向或正东方向逃跑的。不过,日本军的进攻出乎意料地迅速,南京附近的居民如有人不能渡江到对岸,不能前往平地开阔的南面或西南面,那就要么进入南京城内,要么即使与日本军的进攻路线相遇,也宁可逃进东北面的“形势险要”的山地,认为那是“安全之地”。我认为这不足为奇。当然,正如我在旧着《南京事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参照本书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发生在燕子矾和观音门的这起大屠杀是怎么回事,由于检察方面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所以对牺牲的人数尚存有疑问。然而,不管怎样,总不能认为中国方面捏造了这种谣传。
※ ※ ※
关于金陵大学教授史迈思博士负责进行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结果(LewisS.C.Smythe,WardamageinNakingarea,December,1937toMarch,1938,Shanghai,1938.),前面已作了介绍,并进行了批判(参照本书第二一二页以后)。铃木明也提到了这个调查,他认为在每五十户房子中挑选一户进行调查是极为精确的实况调查(顺便说一句,人们经常谈论的视听率调查比例是在一万七千余人中挑选一个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九页)。根据这次调查,可以推算出南京城内居民的受害情况,即因日本军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五十人,受伤者三千零五十人,被强行拉走者四千二百人。被强行拉走者后来由于下落不明,这个数字与死亡的人数相加,估计有六千六百名市民遭到了屠杀。
如前所述,铃木明认为这次调查是“极为精确”的调查,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些数字在调查方法及其他方面有多大的正确性,现在无法断定”。但是,铃木不相信掩埋队处理尸体的数目,却断言:“仅就这起‘南京事件’而言,这是唯一重要的数字。”
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数字”暂且不论,就连那史迈思教授也意识到由此推算而得出的市民牺牲的人数太少了。于是,史边思教授在报告中注明,根据城内外掩埋的情况谨慎推算,结果表明有一万二千名市民遭到屠杀。关于一万二千名这一数目,同是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史迈思教授和我经过种种调查和观察,结果得出一致结论,即:在我们确切所知范围内,城内包括男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有一万二千人遭到杀害。”不过,这一万二千人仅限于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区”调查所得的数字。贝茨博士进一步作证说:“市内其他地区还有许多人遭到杀害,而我们无法调查这些人数。而且,在市区外被杀害的人也相当多。我前面所说的,不包括屠杀中国兵,也不包括屠杀曾经当过兵的几万中国人。”(《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九页)
可想而知,这次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在南京事件构成起诉原因而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毋宁说是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但是,辩护方面最终没有将这份报告作为书面证据提出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连辩护方面也对这份资料所示数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统计的有关死者的数字,不能照用,这在本书第一编第6节《关于牺牲人数的估计》中已有详尽的叙述,故在此不再重复。然而,一段时间来没有提到南京事件的铃木明,却又打破了沉默,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敬告〈人民日报〉总编阁下》。他在文章中重又提出了在史迈思的调查报告中所见到的受害市民人数的统计。当然,他一句也没有提及我对该调查报告所作的批判。对于他,只能将他定为是一个“企图蒙骗不太明了事实的读者”的人物(参照本书第二编第1节中的《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