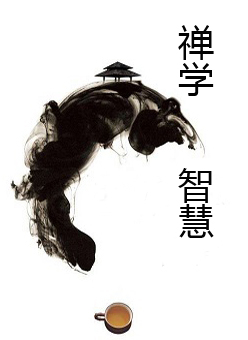01
库车(龟兹)留存下来的佛教遗址十分稀少。短短五天内,我只参观了克孜尔、库木吐拉和克孜尔尕哈三个千佛洞。无论走到哪里,解说员都会告诉我“最古老的洞窟为魏晋南北朝时所建”。
关于这些洞窟的年代,目前说法不一。克孜尔千佛洞有石窟二百三十六个,据说年代最为悠久的是第十七窟。以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为首的德国探险队员按照各个石窟的特点对相关石窟进行了命名,如“孔雀洞”“十六骑士洞”等。1953年,中国政府对这里的各个石窟进行了系统编号(当时总计二百三十五个洞窟,后来又发现了一个)。
对于最古老的第十七窟,有人说是始于三国时代,有人认为不早于西晋,而北京大学的阎教授认为是东汉末期开凿的。不管怎么说,这个画有交脚菩萨像的石窟在公元3世纪末期就已经成型。
出生于公元4世纪中期的鸠摩罗什,应该对这个第十七窟并不陌生。作为佛僧,他很可能参拜过这座佛窟。公元3世纪时期,佛图澄很可能仍在故乡龟兹,史书虽然没有记录他在那儿的活动轨迹,但那时正好和第十七窟的开凿年代重合。既然佛图澄素怀东方传教之志,并经年日久才从敦煌到达洛阳,所以对佛教如此虔诚的人很可能和这座石窟的建造有着很大的关系。
龟兹四周被荒凉的沙漠包围,即使走到尽头也没有任何别样光景。日本的佛教和龟兹出身的两位佛教巨人有着深厚的渊源,而这种关系时至今日依然在延续。石窟的文化氛围虽然没有原封不动地融入日本,但只要沿着这样的韵味往下探寻,就能感受到内中的脉络和承袭关系。
因为没有具体的文献记录,龟兹近边的石窟年代也众说不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敦煌石窟。据史书记载,敦煌石窟中最古老的洞窟始于公元366年,为乐傅所建。此外,敦煌壁画中也有许多年代可寻,而库车的千佛洞只能依据不同风格样式来推测其大概的建造年代。
敦煌石窟皆成排地连缀在鸣沙山的崖面上,看起来清晰流畅,而克孜尔、库木吐拉和克孜尔尕哈千佛洞好似嵌在大山怀中,其地形要比敦煌复杂许多。所以,如果说敦煌石窟是平坦马路,那么库车的千佛洞就是羊肠小道。我多年前曾到过敦煌,对其印象颇深。和敦煌相比,我总觉得库车的千佛洞似乎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我这个外行还想弄清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年代更久远一些呢?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然后经西域传到中原。所以按照一般的逻辑,西边的佛教传播应该早于东边,而石窟建造自然也是自西向东逐步发展。按照这样的逻辑,库车的千佛洞应该早于敦煌,不过这毕竟是外行分析法。其实,西域石窟西起阿富汗的巴米安,东至敦煌,几乎都建造于同一时期。这一点已成定论。
在公元三四世纪时期,库车已经融入了佛教圈,《晋书·四夷传》中的龟兹国部分就有“(龟兹城内)佛塔庙千余所”的记载。如果将当地大大小小的佛塔都计算在内,那么有上千座也并不夸张。
公元399年,法显为求取律藏,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两年后,鸠摩罗什带着律藏来到长安。这不得不说是天意弄人。
法显自长安出发时已是六十四岁高龄。当他到达张掖时,受到了张掖王的款待。据他所著的《佛国记》记载,张掖王为“改业”,其实大概就是“段业”的误写。段业就是那个曾是吕光参军,并随吕光远征龟兹,后来又奉命作《龟兹宫赋》的人。
从张掖出敦煌,然后在鄯善(即以前的楼兰国)停留一个月后,继续往乌夷国(即焉耆)方向行进,然后又在此居住两月余。但由其见闻来看,法显在此似乎受到了冷遇,并言此地之人多不知礼节。后来,他由此出发到于阗,然而他的行记中只提到往西南直行三十五日,而并没有涉及路径及路途见闻。
如果法显到过龟兹那样拥有华丽宫殿的西域大国,那么他的相关著作中就应该会有文字提及,如今却没有发现只言片语,那么就意味着他应该没有途经那里。但从路线判断,他的足迹必然经过龟兹附近。
对于法显对焉耆不知礼仪的评价,《晋书·四夷传》记载如下:
好贷利,任奸诡。
王有侍卫数十人,皆倨慢无尊卑之礼。
吕光西征之际,焉耆不战而降,在讨伐龟兹时焉耆又出兵援助。也许是两者互为邻国吧,龟兹和焉耆之间似乎矛盾很多。
西晋武帝太康年间,焉耆王龙安“遣使入侍”。龙安的夫人是狯胡国女子,其子单名会。龙安病重卧床之时,将儿子唤至身边,嘱咐道:“因龟兹白山之故,父忍辱负重,尔既为吾子,当勿忘以雪耻。”
我们无法得知龙安所说的耻辱具体是什么,但在其死后,其子龙会果然不负嘱托,攻取了龟兹白山,并占领了龟兹全境。后来,他又命自己的儿子龙熙驻守焉耆,自己则亲往占领地龟兹,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据说葱岭(帕米尔)以东,没有不臣服于他的国家。然而龙会恃强凌弱,恃勇而肆无忌惮,虽然他替父亲洗刷了耻辱,但同时又将屈辱强加在他国身上。对此,他并没有放在心上。有一天他出宫外宿,不料被龟兹人罗云所杀。
龙会死后,龟兹重新复国。吕光西征之时,龟兹奋起抵抗,就是因为他们要守护刚刚复国且来之不易的独立。据《晋书·四夷传》所说,向吕光献降的焉耆王乃是龙会之子龙熙,但《晋书·吕光传》却将其写成了“流泥”。龙熙的“熙”应该是颇有中原汉风的名字,而“流泥”则多是当地语言的汉语读音。
西域历史中的类似事件,仅仅记载在中原文献中,西域各国自身并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资料,或者确切地说,相关资料尚未被发现。
02
如果说西域自身有有关公元四五世纪时期信息的文献,那么就要数由婆罗米系文字写成的史料了。之前我已提到,这种龟兹文献中的斜体笈多文最后被学术界命名为吐火罗B语,最早源于6世纪。
婆罗米系文字多以石刻碑文的形式留存于世,纸质写本极少,或者说纸质本可能深埋在库车周边的沙漠之下。正是这份对未知的探求,成了到西域巡礼之人的一大期待。
多年后,法显从印度返回,此次他选择了水路。公元412年7月,他从青州(即山东胶州湾)登陆,公元420年前后圆寂。回国后,他分别在南京、荆州两地讲经弘法,圆寂前再也没有踏上长安的土地。一方面是由于南朝治下的佛教界对这位印度归来的高僧挽留再三;另一方面也因为长安局势不稳。那位在他出发后来到长安的鸠摩罗什,已经于多年前往生极乐了。
病重的姚兴于公元416年驾崩,后秦政权因此迅速趋于混乱,第二年,东晋大将刘裕直捣长安,后秦灭亡。由于刘裕觊觎司马氏的帝位,所以并不打算久居长安,而是只派了部下驻守,自己则迅速南撤。不久,匈奴赫连勃勃率大军南下,击退了东晋留守军队,自称夏国皇帝,定都长安。
除夏国外,西北地区还有鲜卑族的西秦和南梁、汉族李氏的西凉、匈奴族的北凉等割据政权。后来,这些地方政权都被北魏吞并。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了北方。
法显出行时最先到达的西域,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公元435年,当时西域依稀尚存的弱小政权遣使向北魏国都平成(今山西大同)朝贡。这些国家包括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朅盘陀、鄯善、焉耆、车师及粟特九国。
当时,北魏势力已逐渐渗透到西域地区,所以西域各国也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首先向其表达尊崇之意。不过,九国使节同时入朝自然是他们提前商议的结果。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王朝,但他们后来放弃了本民族固有的语言习俗,从根本上实现了汉化。作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势力,北魏政权延续了约一百五十年。在这期间,北魏曾两度出兵西域。
第一次为公元445年的讨伐鄯善之战。
曾以楼兰之名名扬于世的鄯善在十年前和其他西域八国一样遣使北魏表示臣服。在众多入朝的西域诸国中,鄯善离中原最近,所以对旁边的大国多有忌惮畏惧之心。在这之前,鄯善和北魏之间尚有河西地区的缓冲地带,但北凉灭亡后,鄯善再无屏障可依。
北凉灭亡之际,北凉王之弟安周逃往鄯善,并劝说鄯善王说:“唇亡齿寒,北凉之后鄯善危矣。”对于他的说法,鄯善王也觉得必须有所行动。往返于西域南路之时,鄯善是必经之地,所以自鄯善向北魏朝贡以来,鄯善国内的北魏使者,也就是国营商队随处可见。这就意味着这些商队经过鄯善时,自然能对鄯善国内部的风吹草动有所觉察。
虽然鄯善称得上是西域南路的大国,但国力依旧薄弱。如果北魏得知虚实,做出“鄯善可一举荡平”的判断时,那么鄯善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鄯善王终于决定采纳安周的建议,杀死了北魏的商队人员,堵塞了往来道路,并采取锁国政策,以此来阻止国内消息外露,西域南路也因此中断多年。对北魏来说,这可是有损国威的事情,如果听之任之,其他国家必然难以臣服。于是北魏朝廷派出散骑常侍万度归讨伐鄯善。当万度归率五千轻骑兵逼近鄯善时,鄯善王真达将自己绑缚起来出城献降。万度归见状,解了他的绳索,将其带到了平城。
此后,北魏任命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并封其为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实际上,北凉王之弟安周虽然是逃至鄯善,但他却是率兵前来的,鄯善王反而受其胁迫,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自主权。北凉灭亡后鄯善步其后尘,西域从此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韩拔于公元448年被任命为鄯善王,同年,焉耆造反。据《魏书》记载,北魏讨伐焉耆的理由为:
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
此时,已荣升为魏成周公的万度归,再次率军出征。
焉耆王战败,逃往龟兹。当时,焉耆和龟兹是姻亲。万度归继续穷追不舍紧逼龟兹,龟兹丧失二百余名士兵后投降。
所谓“颇剽劫中国使”就是掠夺北魏国营商队,其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两国之前就存在交易上的矛盾。万度归二度远征之后,西域和中原之间的贸易之路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公元5世纪时期的西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汉族在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国。自汉代开始,吐鲁番盆地就是屯田之所,同时也是戊己校尉的驻地,因此那里汉族居民众多。长期以来,高昌和西域诸国之一的车师前部国以及汉族开拓团在吐鲁番这块土地上和平共存。
西晋时,朝廷复设戊己校尉,并命赵贞任此要职。
“八王之乱”后,西晋政权分崩离析。公元313年,都城洛阳陷落。公元318年,西晋皇族、琅琊王司马睿在南京即位称帝,史称东晋。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南一隅,所以无力顾及远在千里之外的吐鲁番盆地,戊己校尉因此陷于孤立状态,不得不自立求保。
西晋时期,张轨之孙张骏已经在河西建立起了半独立政权,史称前梁。张骏对西域垂涎日久,然而戊己校尉赵贞并没附逆于他,于是他命李柏征讨但未获成功,无奈之下,张骏率军亲征,终于将赵贞俘虏。
接着,前梁在此设立高昌郡。戊己校尉一职,一直以来都带有殖民的性质,而“郡”则意味着和“本土”一样。
然而,吐鲁番盆地并没有因此长久太平,政权更替依旧频繁。从前梁到前秦,再到吕光建立的后梁,以及后来的西凉、北凉……如果将这种更替的历史一一说来,恐怕会搅晕脑袋。
曾经逃命到鄯善的北凉王之弟安周,不仅侵入汉族的聚居地吐鲁番,而且还继续将祸水西引,于公元450年促发了西域本土政权车师前部国的灭亡。此后,高昌郡变为高昌国,归属安周统治。但仅仅过了十年,北方的柔然(蒙古系,是一个从公元4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支配整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大兵压境,安周兵败被杀,柔然立仰其鼻息的阚伯周为高昌王。
北方政权在争斗中消涨不断。不久,高车(土耳其系)又力压柔然,封听其号令的张孟明为高昌王。说来道去,阚伯周和张孟明其实都是傀儡而已。柔然和高车都选择汉人为傀儡,可能也是考虑到吐鲁番地区汉人众多,游牧民族难以统治之故。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当地汉人的支持,高昌王就形同虚设。张孟明遭排斥被杀,高车再立汉人马儒为高昌王。马儒和北魏暗中联系,希望当地人能回归中原故土,然而吐鲁番盆地的汉人早已在此历经几代,已无归乡之念。于是马儒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
后来,众人立马儒的长史鞠嘉为王。比起前两个被杀的高昌王,鞠嘉显然要幸运很多。高昌的邻国焉耆因国内动乱难以控制,故焉耆人也希望鞠嘉兼任其王。对此,鞠嘉遂派次子掌控焉耆政权。这种不费吹灰之力主动献城的方式,使得高昌强大起来。
至唐太宗时期被灭,鞠氏王朝一共持续了一百四十多年。玄奘法师路经此地时,就正值鞠氏王朝统治时期。
不过,高昌的命运也如同一曲悲歌。如果他拂逆超级大国的意志,恐怕一天也无法生存,况且是夹在两个大国之间,更不敢有任何轻动之举。
03
高昌国都为“Qara-hoja”(维吾尔语),即所谓的高昌古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古城的墙壁、宫殿和寺院早已颓唐零落,而我们也只能据此依稀回忆古城当年的风采。
吐鲁番盆地海拔负一百五十四米,是世界最低的盆地。它像一个巨大的钵盂底部,因此夏季十分炎热,而冬季又极其寒冷,常年干燥少雨。这座残损的高昌古城是用砖瓦建造而成的,距今已有千年,能够保存到这个程度,也得益于这种干燥的气候。
高昌古城中的半圆形屋顶的建筑、带佛龛的寺院以及楼阁式佛塔等都带有浓厚的萨珊王朝时期的阿拉伯风格,甚至让人难以相信这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
也许是汉族人已经入乡随俗了吧,他们的生活已经染上了西域色彩。也许是因为缺乏木材的缘故,这里的木制建筑很少,即便有,在历经了千年之后也早已荡然无存。当然,也有可能被后世居民当作了燃料。也正是因为干燥,所以这里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高昌古城的旁边,便是阿斯塔那古墓群(高昌贵族墓地),这里的陪葬品被各国探险队盗挖。大谷探险队盗取的宝物存放于日本,而斯坦因盗走的一部分物品则将印度新德里国民博物馆的一间馆室摆满了。
首先,鞠氏王朝先后沿用了重光、章和、永平、建昌、延昌、延和、义和、延寿等颇具中国传统式的年号,并铸造了“高昌吉利”的流通钱币。其次,官制形式以中原为蓝本。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也融入了诸多西域因素。前高昌王马儒就因采取了“回归汉土”的政策,所以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由此可见,这里的汉民族俨然已经西域化了。
虽然高昌是汉族王朝,但这只意味着王室全是汉人,而百姓则未必全是。此外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多的操着吐火罗A系语的伊朗裔民族。从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陶俑来看,既有汉族女官,又有胡人武士。据相关材料记载,这里除了伊朗裔居民外,还有土耳其裔的驻铁勒官员。
毋庸置疑,高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统治这样的国家,就不难想象需要借助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威灵。除佛教外,这里还有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学校也用“胡语”讲授儒学教义,即训读式讲解。不仅是伊朗裔居民需要如此,就是常用吐火罗A系语的汉族三四世后代也需要以此种方法来理解儒家经典。总而言之,这里的人们为开辟美好生活而不断开动脑筋。
当然,吐鲁番盆地不仅有这座位于吐鲁番县城东约四十六公里的高昌古城遗址,在县城以西约十二公里的地方,交河古城遗址也清晰可见。
交河古城,顾名思义,就是古城位于河流的交汇之处。城前是交汇的河流形成的天然护城河,城后的悬崖绝壁笔直而陡峭,确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阻之地。不过和高昌古城相比,这座宽度只有三百米,长度也只有一点五公里的城池就会显得狭小很多。
比起在开阔之地建立的高昌城,身处要塞的交河城在军事统治上更具优势。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唐太宗在消灭了鞠氏王朝并将高昌纳入大唐国土时,才有意将安西都护府设在交河城内。
交河城虽然比高昌古城小许多,但由于废弃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遗留下来的建筑遗迹较多。高昌古城除了残留的城墙和城中的宫殿、寺院外几乎一无所有,而交河城中的普通民宅依旧有所保留。每所宅院中都有一处呈红褐色,那正是家家户户烧火做饭的灶台位置。
法显去印度时并未经过吐鲁番盆地,他在焉耆获得了符公孙的资助,才得以直接取道于阗。而同行的智严因在焉耆遭到冷遇,所以只得再到高昌求取一些行旅物资。去往印度如果要绕行至高昌,那么最终还得折返,但对当时的求法僧来说,为了能够获赠一些旅途所需,有时也会走一遭这条“之”字线路。
在法显来到西域的二百二十多年后,高昌迎来了前去印度求经的玄奘法师。“通伊吾(哈密)之道”,被请入吐鲁番盆地。玄奘到达高昌国的时候正值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当时的高昌国王为鞠文泰。从第一代高昌王算起,鞠氏王朝已历七世。鞠文泰对年轻的玄奘赞赏有加,故而想让其留在高昌,但玄奘取经之意坚如磐石,以绝食明志。高昌王无奈,只得许从。但两人同时立下约定:
归来再过高昌,在此供养三载。
玄奘本想履行盟约,但当他十六年后再来到此地时,高昌国已经不复存在。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命人消灭了高昌,而鞠文泰则死于破城前夕。关于高昌灭亡的来龙去脉,从头说起也许更易理解。当时玄奘虽然顺利通过了高昌,但在他之前的法显却显然没有选择同一路线。玄奘通过“伊吾之道”进入吐鲁番盆地,法显则走鄯善(即“楼兰之道”)绕过了吐鲁番盆地以西的焉耆。
“楼兰之道”在玄奘时期已经无法通行,所以“伊吾之道”就成了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主要道路。商队往来频繁,高昌因交通之利而富庶繁荣。
此时,焉耆向唐朝朝贡,请求恢复旧道。此路一开,焉耆就会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十字枢纽,其优势地位自然胜过只作为漫长道路上一个停靠点的高昌。如果商队分成“楼兰之道”和“伊吾之道”两条,那么这将为高昌带来巨大损失,其获利就会减半。为了阻挠旧道再开,高昌联合实力强大的西突厥攻袭了焉耆。我在前面曾提到过,高昌本来就有土耳其裔铁勒使者居住,他们借在突发之时负责协防高昌的安全为由,专责从交易中抽取渔利。
西突厥也属于铁勒的一支,如今在利益攸关的危急时刻,高昌当然会借助西突厥的力量阻止焉耆重开旧道。
然而,焉耆也早已和唐朝秘结。面对高昌和西突厥的联军,焉耆随即向东方大国唐朝求援。对此,唐中央先是派出了使者问罪高昌,高昌王表示愿意悔改前错。面对大国的时候,西域小国往往谦柔以对,这一点唐朝自然心知肚明,于是唐朝要求高昌王亲自到长安“入朝觐见”以证其诚,但高昌王以病为由未曾前往。
至此,唐太宗决定征伐高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薛万均为副大总管,大军于第二年8月直抵高昌城下。也许是因胆战心惊而忧虑成疾吧,未等唐军进攻,高昌王鞠文泰便一命呜呼。鞠文泰死后,其子鞠智盛即位,成为鞠氏王朝最后一代君主。
04
在当时的情形下,高昌的盟国西突厥有什么动作呢?他们陈兵可汗浮图城,摆出一副要救援高昌的样子。但那里在交河城以西一百八十公里,所以,与其说是救援,莫如说是声援。也许唐军只分兵少数进攻西突厥,但他们深知唐军实力,所以未曾迎战便撒腿西遁。此时,孤立无援的高昌只得献城投降。在经历了九代皇帝,国祚延续一百四十二年后,高昌灭亡。
唐朝宰相魏征曾向太宗进言,建议在高昌扶植一个傀儡王,对高昌实行间接统治,但唐太宗未采纳他的建议,直接将高昌改名西州,将其置于唐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样一来,唐中央政府就直接任命官员管理吐鲁番盆地,并将安西都护设在交河城。最后一任高昌王鞠智盛被唐军带回长安,受封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当然,这都是没有实权的闲职。
唐朝远征军中,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因对当地的掠夺默认不管,同时自己也将相关宝物中饱私囊,副大总管薛万均和高昌女子私通,两人均受到言官弹劾。结果,二人同时被免去军功,但并未被问罪。高昌城演绎了多少兴亡故事,如今皆被时光冲洗而去,高昌和交河古城的土黄之色映衬在西域蔚蓝的天空之下,显得格外醒目。
后来,西域地区全部伊斯兰化,地上的佛教遗迹几乎丧失殆尽,只有石窟保存下来了。
吐鲁番盆地的石窟分布广泛,但要数柏孜克里石窟群最为有名。该石窟群位于吐鲁番县城东北五十多公里,即火焰山中木头沟河岸,共计石窟五十七个,分佛窟和僧窟两类。其中,普通僧侣所住的僧窟中没有壁画,带壁画的石窟只有二十多个。遗憾的是,精致优美的壁画已经在二十世纪初期流失到海外了。
德国探险队掠走的壁画被收藏在柏林民族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部分壁画因空袭而被烧毁,但其中大部分因保护及时而幸免于难。斯坦因从这里带走的壁画和他在阿斯塔那古墓群盗走的文物都被收藏在新德里国民博物馆。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文物常常公开展览,但柏孜克里石窟的壁画却很少公开展览。
一般来说,如果要欣赏柏孜克里石窟的精品壁画,最好去柏林或者新德里的博物馆。不过我倒觉得石窟壁画还是应该去石窟里面观赏为妙,因为博物馆里的所见所感自然无法和身临其境相比肩。
和库车附近的石窟群远离县城一样,柏孜克里石窟距高昌古城也有一定的距离。来到这里,也许是信仰使然,也许是出于对美的眷恋。走过遥远的险路,嗅着脚下的土味,炎炎烈日当空,我们在石窟前一边吃着西瓜和哈密瓜,一边俯瞰着木头沟河缓缓流过。欣赏壁画的喜悦之情,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此行的意义。
柏孜克里的意思是“饰满绘画的地方”。这里的石窟最早建于公元6世纪末的隋朝,比敦煌莫高窟要晚两百多年,每个石窟都有编号,其中的第二十五号石窟建造时间最为久远。
20世纪初期,来到此地的外国探险队因一时难以将众多壁画全部盗出,又担心后来人将其运走,于是就将泥土涂在壁画上加以隐蔽。因为僧窟没有壁画,所以并没有发生这种闹剧。然而后来再没有外国探险队进入新疆,所以涂泥的壁画就原样保存了下来。近年来,专业人员去掉了壁画上面的“泥衣”,这绝妙之美才得以重见天日。当然,也有部分因黏着日久而担心剥泥会伤害壁画,故而暂留未动。建于宋代的第三十七号窟就是如此。
柏孜克里石窟是我最早见到的石窟,那是在去敦煌前两年的1973年夏天。根据观赏者所在方位的不同,柏孜克里石窟后的黄色沙山有时会像隆起的乳房,有时会像平伏的胳膊,有时还会像尖锐的三角……仅仅这些,就足以让我难以忘怀。虽然壁画因人为的破坏和岁月的剥蚀而略显惨淡,但周围的景色却多少让我感到一丝慰藉。
第三十九窟始建于宋代,该壁画画有外国使节,充分反映了丝绸之路的国际性特征。
05
柏孜克里石窟附近的火焰山之名曾在《西游记》中出现过,相关故事也可谓耳熟能详,饶有趣味。虽然我觉得《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来过这里,但火焰山的名称他必然听过。对于妖魔鬼怪各显神通的《西游记》来说,火焰山自然是不可忽视的绝佳舞台。
现实中的火焰山山体呈红色,侵蚀而成的沟壑纵排相连。烟霭升起时,山上就像燃起了飘舞的火焰一样。特别是盛夏时分,这里40℃以上的高温连日不断,从盆地低处望去,那红色的山体最易让人联想到熊熊的火焰。在这种酷暑难耐的山上营建信仰之地,也许正是为了证明信仰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
回国后,玄奘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在西域见闻中,他从阿耆尼国(即焉耆)开始写起,却没有将高昌列入介绍范围,那是因为当时高昌已经在唐朝建制之下。他在提到每个西域国家时,都会清晰地表明该国是信奉小乘佛教还是尊崇大乘佛教。虽然没有关于高昌的记载,但毕竟他在高昌受到了热情招待,临别之际,他向该国信众讲授了《仁王般若经》。由此可以推断,高昌应该信奉大乘佛教。
因为高昌汉人众多,所以该国有很多来自中原的汉译佛典,而佛教原典取自印度。有史料记载,《大般涅槃经》就是从印度直接传入的。这种既有自西而来的“顺流”,又有自东涌进的“逆流”,二者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佛教文化交流的主流。公元10世纪以后,吐鲁番盆地成为回纥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的维吾尔族人控制时代。因此,将佛典译为维吾尔语大为盛行。从目前吐鲁番盆地出土的维吾尔语译佛典内容判断,其主要归属大乘佛教。此外,相关专业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些维吾尔语佛典并非直接译自梵文原作,而是借助汉译本转译的。
柏孜克里石窟群中的众多洞窟营造于回纥时代者也不在少数。这些凿洞绘画之人,其信仰也多来自汉译佛典。信仰之外,石窟中随带的佛教美术作品显然既有西来的因素,也有东土的影响。
西域之路并非只是一方通行,特别是曾经汉人居多的吐鲁番盆地,东西往来者比其他地方更加频繁。《北史·西域传》有云: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
所谓“俗事天神”,很可能是蒙古或土耳其裔人的天神崇拜,也有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或基督教的教义。因为此地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也五花八门。相比较而言,佛教因其自身的特质,加之当政者的支持,所以发展得更为繁荣。
纵观多民族杂居的吐鲁番盆地的历史,其原住民杀死国王的血腥事件似乎发生了不止一次,然而却没有发现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也许就是佛教这条纽带的作用吧。
此外,吐鲁番盆地还有胜金口、吐峪沟等几处石窟群。虽然同是西域文化的中心,但除了喀什境内的“三仙洞”外,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佛教遗迹了。
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西域可以分为五大文化圈。
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南被称为西域南路,以鄯善为中心的罗布泊一带是我们熟知的“楼兰文化圈”,另一个就是“于阗文化圈”。
与之相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被称为西域北路。西域北路上,天山山脉横亘其中。而天山南北又被细分为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吐鲁番、库车和塔克拉玛干属于西域北路,以天山为基准的地区即天山南路。这两处分别是吐鲁番文化圈和天山文化圈。此外,兼有两个文化圈特征的喀什自成一体,一般认为它是独立的文化圈。当然,之前也有人将喀什列入于阗文化圈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