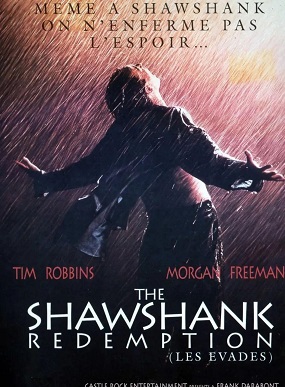上谕真的到了宿松:“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开了,驻扎在宿松的湘勇将官们纷纷前来祝贺,宿松、太湖、望江等县的县令们,一个个亲自坐轿来,连远驻徽州的左副都御史张芾也打发人飞骑奔来道喜。凡前来恭贺的人,曾国藩一律不见。他在大营墙上张贴了一纸告示:“本署督荷蒙皇恩,任重道远,无暇应酬,贺喜者到此止步,即刻返回,莫懈职守,本署督已祗受矣。”
因为事先早已知道,曾国藩对这道上谕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深感临危受命的重大责任。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石达开的二十万人马虽已进入川贵,但随时都可返旆东来,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合起来至少还有五六十万。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曾国藩,这些天来时常有一种苍凉之感。朝廷在江南大营溃败、四顾无人的时候,才想起依靠湘勇的力量,就在要依靠的时候,仍不愿干干脆脆把江督授予他这个湘勇的元勋,而要授给胡林翼。难道说,皇上对他的成见,一直耿耿于怀吗?每当想起这些,曾国藩便涌出一种强烈的委屈和失意之感。有一天深夜,凝视灯火,他居然信笔写出了一首这样的五言诗:“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写完后,他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会心灰若此!他想,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这种思想都要不得。他烧了这首诗,打起精神,考虑今后的用兵计划。
其实,这些计划,早在江南大营失败前,便和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那时只局限于湘勇及胡林翼所掌管的部分绿营的调配。现在不同了,两江地方的绿营都可以由自己来节制。当然,绿营还包括多年来和湘勇一起打仗的多隆阿部。
曾国藩将前些日子磋商的事理出个头绪来,作出了几点决定:首先,他清楚地认识到,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错误的,必须改为由西面进攻的策略,也就是两年前复出时所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即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长江在安徽境内有两座重要城镇,一为江北的安庆,一为江南的池州,占住了它们,即打开了攻破江宁的大门。拿下安庆,这是曾国藩复出后的第一个战略任务,可惜李续宾、曾国华辜负重任。十天前,经胡林翼提醒,曾国藩已拟定调九弟国荃去安徽。他密函九弟:把围安庆当作围江宁的演习,训练部属,积累经验,日后好抢夺攻克江宁的首功。曾国荃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接到大哥的信后,立即出发,一面又派人回湖南再募五千人。有了攻吉安的经验,他对下安庆充满了信心。曾国藩又把满弟贞干的贞字营扩大到两千人,也调往安庆。吉字营、贞字营,才是真正的曾家军。安庆方面可以放得心了。池州如何对付呢?
守池州府的是太平军左军主将定天义韦俊。太平军三下武昌,其中两次的总指挥便是他。咸丰六年,他在武昌城头亲自指挥打死了罗泽南。曾国藩既对韦俊恨之入骨,又佩服他是个难得的将材。韦俊是韦昌辉的弟弟,是不是不用武力,而用离间计,使韦俊挟池州投降呢?对此,曾国藩没有信心。太平军深受拜上帝教的影响,团结心强,要他们叛教投敌,怕是难办。
另一件大事,是两江总督目前驻节何处?朝廷严命赴江苏,江苏一时固然不能进,但也不能留在宿松不动,置朝命不理。曾国藩拿出李鸿章献的皖省地图,指划着由宿松向浙江方向前进的路线,他在祁门县境停住了手指。祁门处于丛山包围之中,一条大道贯穿县城,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景德镇,既有天然大山可以屏蔽老营,又可以与浙江、江西互通声息,是个驻节的好地方。
还有,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以及浙江四省的巡抚,是至关重要的大员,必须逐步地不露声色地替换,他们一定要是可靠的心腹,否则难收指臂之效。可任巡抚的人选,他心中已有两个:一个是彭玉麟,一个是赣南兵备道沈葆桢。沈葆桢字幼丹,福建闽侯人,林则徐的女婿,品行才干,都有岳丈之风。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咸丰五六年间,曾在湘勇营务处供职一年多。以福建人、名臣之戚而与湘勇有如此渊源,实为难得,既可引为心腹,又可免尽用湘人之嫌。还得再物色两个人,一年半载之内将现在的江西巡抚耆龄、安徽巡抚翁同书、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统统换掉。
另外,曾国藩还想到,江苏号为泽国,水师力量必须加强,除外江、内湖水师外,还须建立淮扬水师,攻取里下河粮米之仓,建太湖水师收复苏州,建宁国水师规复芜湖。
真个是百事丛杂,千头万绪,曾国藩靠着思虑周密和多年来的用兵经验,对已临的和将临的一系列大事小事,逐一作了细细的思考。待基本就绪后,他亲自草拟了一份谢恩折,并将收复两江、攻取江宁的用兵计划向皇上作了报告。为了使皇上采纳他的不从东面,而从西面进攻的策略,他很用心地构思了这样一段文字: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军皆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单薄,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须先克安庆,南岸则须先攻池州,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
曾国藩相信,皇上是会批准他这个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的,万一不同意,他也要据理力争。在这个重大的决策上,他不能作丝毫的妥协,直至辞去两江总督之职。
谢恩折拟好后,天将放亮,他吩咐王荆七将奏稿送到文书房誊写,便吹熄蜡烛,倒头睡下了。这一觉直睡到黄昏才醒来,在曾国藩的记忆中,从未有过如此安稳的睡眠。心里高兴,吃过晚饭后,曾国藩便打发荆七请康福来,今晚要和他围几局。
半年前,曾国藩从吉字营中选拔二百名朴实强壮的勇丁,由朱品隆带着来到他的身边,充当亲兵营。曾国藩任命康福为亲兵营统领,朱品隆为副。在康福、朱品隆的训练下,亲兵营人人武艺高强,一以当十,对曾国藩忠心耿耿。
康福带着祖传云子,应召而至,二人兴致勃勃地下起来。
“大人,你老的技艺大大提高了。”当曾国藩将被包围的两枚黑子拾起时,康福笑着说。
“比起那年在洞庭湖来是有些提高,这多亏了你的指点。”曾国藩今夜特别高兴,刚才又吃了两子,益发兴致高。
“大人夸奖。”康福边说边注视着棋子,现在对付曾国藩,他必须聚精会神,稍有不慎,便有失子的可能。
“价人,这几年来,你与不少将领们下过棋,你认为谁的棋下得最好?”
“下得最好的嘛,”康福略作思考,说,“以前是罗山先生棋艺最精,现在要数次青统领下得最好了,雪琴统领也下得不错。”
“我湘勇将官除打仗外,人人都会琴棋书画,这是古来少有的。”曾国藩得意地说。这也是实话。湘勇将官绝大多数出身书生,琴棋书画自是他们的本行。
“大人说得对。但我也听说,长毛中也有人围棋下得好。”
“真的吗?”曾国藩饶有兴致地问。
“听人说,长毛头领中精于围棋的,第一要数石达开。”
“这有可能。”曾国藩点点头,“据说石逆大不同其他人,不但会打仗,也会写诗。听人说石逆那年在九江浔阳楼上,即兴题了一首诗。就诗而论,写得不坏。”
“石逆的诗是如何写的?”康福好奇地问。
曾国藩想了想,把石达开的题诗背了出来:“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要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妖氛扫时寰宇靖,人间从此无啼痕!”
“口气倒不小!”康福微笑着,一瞬间,脑子里出现了弟弟康禄。他现在哪里?会不会跟石达开进了四川?
“说实在话,此人也是个人才,可惜做了贼首。”曾国藩从心底里为石达开惋惜,“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便要数韦俊了。”
“韦俊也会下围棋?”曾国藩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大为惊喜。
“是的,仅次于石逆,在长毛中坐第二把交椅。”
“好,好!”曾国藩习惯地用手梳理着胸前的长须,两眼凝视着前方,弄得康福莫名其妙,“价人,你和韦俊去下两盘如何?”
“和韦俊去下?”康福愈发摸不着头脑了。
“是的,你去下赢他!把杨国栋找来,你们一起去。”
康福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