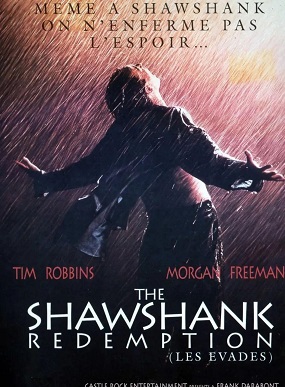五更未到,韦俊就醒了。近一个多月来,他常常都这样,每到这时,他心里就生发出隐隐痛楚。四年前,天京内讧,韦俊的二哥北王韦昌辉惨遭杀戮,韦俊在武昌城里吓得心惊肉跳,常觉不测之祸就要降临头上。幸亏他与翼王石达开很要好,翼王后来入京主持朝政,在天王面前竭力称赞韦俊能征惯战,功劳赫赫,又暗地叫韦俊上一道奏章给天王,表示坚决拥护天王诛杀韦昌辉,誓死效忠天王,又将三岁的儿子送到天京做人质。这样才取得天王的信任,不再株连到他的头上。韦俊终于安下心来。去年天王重新调整军事领导集团,任命他为左军主将。韦俊感激天王对他的信任,要从心底深处抹掉韦氏家族不幸的往事,全力去争取自己今后的前程。但今年来,许多事情使韦俊又陷于忧虑之中。先是五军主将中的其他四人,一个接一个地封王。中军主将蒙得恩是天王最宠信的人,在朝廷中扶持朝纲,封赞王,他不能说什么。陈玉成、李秀成战功卓著,全军敬佩,封英王、忠王,韦俊也没有意见。但李世贤参加起义时,不过才十来岁的娃娃,这些年战功平平,封右军主将犹不够格,现在居然也封侍王了。而他,始终只是一个“义”。论功劳,别的不说,单是两次下武昌的功勋,就让李世贤远远不及;论资历,癸好三年,韦俊就受封国宗爷,赏穿黄袍,而李世贤只是一个普通圣兵。李世贤凭什么封王?难道因为他是李秀成的堂弟;而自己不能封王,是否也因为是韦昌辉的胞弟?想到这里,韦俊浑身发冷,感到前途一片阴暗。最近,从天京传来消息,说天王族弟干王洪仁玕要追究他丙辰六年丢失武昌的责任,拟撤销他左军主将之职,召回天京。韦俊心里想,自己在天王心目中尚有点地位,凭借的就是手下八千子弟兵,倘若召回天京,离开了弟兄们,则如同鱼儿离开了水,成为别人砧板上的菜了。江南大营的溃败不仅没有给韦俊带来欢喜,反而使他又增一分恐惧。战事不利,天王要用他,一时还不会下手;打了胜仗,力量雄厚,就会想到要剪除异己了。丙辰六年的内讧,不正是发生在踏破江南大营之后吗?他天天忐忑不安,也曾暗暗想过,大丈夫岂能眼看着人为刀俎,己为鱼肉,而不思动作?但如何动作?学当今的翼王出走边徼,还是学前明的闯王遁入空门?他觉得都不好。天已放亮了,韦俊仍然心烦意乱。他起床,推开窗门。正是暮春季节,长江南岸的池州府草长莺飞,春意盎然。他想城外的春意必然会更浓,于是叫起侄儿韦以德,带着几个亲兵,背上弓箭,跨上战马,悄悄地出了城门。
果然是一派江南好春光:清溪河碧波荡漾,两岸杨柳叶暗,桃李花明,黄鹂欢啼,紫燕轻飞,江风阵阵,吹面不寒,细雨飘飘,沾衣欲湿。韦俊一时兴起,扬起马鞭子,那马飞也似的奔跑起来,穿过清溪镇,跨过五溪桥,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九华山地面。近看浓绿扑面,遥望山峰郁郁苍苍,韦俊连日来的积郁顿时散去,兴致极高地与侄儿打起猎来。韦俊箭法好,坐下又是千里挑一的神驹,凡在他的射程内的飞禽走兽,几乎没有侥幸逃脱的。午后,亲兵的马背上载满了羚羊獐兔,喜气洋洋地往回转。
一阵急驰过后,韦俊回首看九华山已在朦胧之中,忽然想起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作,遂在马背上高声吟诵起来:“风高角弓劲,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才过新丰市,忽到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韦俊觉得,此刻的自己,正是王维笔下的那个将军,不禁感叹起来:人生有此一日之乐,即不枉活在世上了。
正在得意之际,前面林子里忽然闪出一头梅花鹿来。那鹿毛色光滑,斑纹耀眼,头上长着高耸的角,甚是逗人喜爱。韦俊常常打猎,却从来没见过鹿,更不用说这样好看的梅花雄鹿了。韦俊吆喝一声,拍马冲上去,张弓便射。可惜,没射中!那鹿受此一惊,没命地奔跑。韦俊不气馁,夹紧马肚,风也似的追上来。鹿前马后,相距总在两三百步远。韦俊连射几箭都不着,他生怕梅花鹿逃进树林中,死命追赶,那马却偏偏不能超过鹿的速度。眼看前面真的现出一座丛林,韦俊急起来,又射一箭,仍不着。正在失望之际,草丛中突然飞出一镖,正中梅花鹿的后颈。那鹿四蹄挣扎几下,倒在一棵树下不动了。韦俊看在眼里,高喊:“好镖!好镖!”
这时,只见草丛中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背上背着一个蓝布包,面带微笑地朝韦俊走来。韦俊下马,对着汉子大声说:“兄弟,了不起,你真是一个神镖手!”
那汉子客气地说:“将军夸奖了,这只是偶尔碰中而已。将军身后猎物这样多,才真正是神箭手哩!”
韦俊见汉子身怀绝技而如此谦逊,甚为敬重,双手提起死鹿,说:“兄弟拿回家去吧,光这对鹿角就可以卖得百把两银子了。”
汉子忙推开死鹿:“将军说哪里话!这头鹿明明是将军的猎物,小人岂敢妄取。”
韦俊心里愈加敬佩,恳切地说:“兄弟,看你这身打扮,也不像有钱人,这头鹿拿回家去,可以保一家人几个月的吃饭,但对我来说,可有可无,你就不必推辞了。”
汉子说:“小人孤身只影,无家无室,用不着拿死鹿去换银子。若是将军硬不肯受,我和将军将此鹿驮回城里,一起献给韦将军如何!”
韦俊一惊,问:“你认得韦将军?”
“不认得。”
“那你为何要送给他呢?”
汉子笑道:“小人久闻韦将军是天国的名棋手,小人一生只好下棋,特到池州府来找韦将军对局,这头鹿正是一个见面礼。烦将军带路,引我去拜见韦将军。”
韦俊高兴起来,问:“兄弟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
汉子答:“小人叫米福,湖广人,多年来浪迹江湖,以棋会友。”
韦俊满脸堆笑地拉起米福的手说:“兄弟,我就是韦俊。今日真是天父安排我们在此见面。”
“您就是韦将军,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多冒犯。”米福刚要下跪,韦俊一把拉住。二人说说笑笑,一起进了池州府。
韦俊吩咐宰鹿款待米福。杯盏之间,韦俊知道米福不仅精于镖法,且于拳剑刀棍样样精熟,十分喜爱。吃完饭后,又特意留住米福下围棋。米福从蓝布包里取出一盒围棋来,韦俊立时被棋盒上那条穿云破雾的银龙所吸引。米福打开棋盒,取出几粒子来。韦俊接过棋子,摸摸掂掂,眼中射出惊奇的光彩。
“米福,你这棋子非比一般,不是寻常之物啊!”韦俊出身豪富,见多识广,虽说不出此棋的许多佳处,但见其色泽质地,已知它的价值。米福凑过脸去,小声说:“不瞒将军,这盒棋是前明宫中的御用之物。”
“噢!”韦俊又拿起几枚棋子,细细摩挲,瞪大双眼看着,“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
“将军,容米福日后慢慢禀告。久闻将军乃义军中围棋高手,今夜陪将军围几局如何?”
韦俊心想,他不告诉我,兴许是不服我的棋艺,今夜就请看看我的手段吧!
二人不再说话。纹枰对弈,静观默思,四周一片阒寂,唯一的响声,是棋子叩在木盘上所发出的铿锵声音。韦俊的棋艺,使米福心里称赞不已;而米福,则更使韦俊暗自佩服嗟叹。三局下来,韦俊一胜二负,他爽快地承认输了。
“哪里,哪里!将军运子,出神入化,今日偶失一局,岂能轻言‘输’字。若将军有兴趣,明晚再下如何?”
“最好,最好。”韦俊高兴地说,“你若不嫌弃,就住在我这里。你这身武艺,池州府里少有人可及。过几天立了军功,我提拔你做师帅、军帅。”
原来这米福就是康福。他与杨国栋二人带着几个亲兵,奉曾国藩之命,悄悄来到池州城外,已有些日子了。那天窥视韦俊外出打猎,便尾随其后,伺机行动,恰巧梅花鹿帮了忙。康福跟随韦俊进了城,杨国栋带着亲兵仍住城外。亲兵早晚进出,与二人互通声息。
康福在韦俊主将衙门一住半月。白天与韦俊一起讲兵法,谈武艺,巡视防守,夜晚二人闭门对弈。韦俊十分器重康福,康福亦百般曲奉韦俊,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康福有心,常趁韦俊不在的时候,细细浏览太平军的往来文书。当时太平军的文书档案管理不严密,在外带兵的将领就更散漫。康福恰恰钻了这个空子。不久,康福把这些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池州城外,杨国栋密切配合着,再次施展他的乱真绝技。
这天深夜,一个前胸绣有“两司马”字样的精干信使,叩开了池州府东门,一溜烟直奔主将衙门,看上去一副千里奔驰、风尘仆仆的模样。此人将一封印有云朵飞马的信函,交给主将衙门的亲兵。这种印有云朵飞马的信函,在太平军中唤作云马文书,是一种特急的重要文书。各驿站接到这种文书后,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要加盖印章,立即投到下一站。亲兵见信函上盖着沿途二十几个驿站的印章,一一验证无误,便开了一个回条。那两司马接过回条,拨马便走,并没有留下一句话。
亲兵将云马文书送到韦俊卧房。卧房里灯火明亮,韦俊正在与康福聚精会神地对弈。他离开棋枰,将文书放在烛火边,慢慢地化开胶封,从中取出一张纸来。一会儿工夫,韦俊的脸便变了色,呆站着,好久回不过神来。康福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轻轻地走过来,关切地问:“这么夜深了,哪里来的信件?”
“天京来的。”韦俊回过头来,神色忧郁。
“有紧急军情?”康福试探着问。
“要我火速回京。”韦俊的声音不太自在。
“将军在外日久,回京住几天也好。”
“兄弟,你哪里知道,此番回京,就会被人囚禁,再也出不来了。”韦俊的面容更沮丧了。
“这是怎么回事?”康福大惊。
“兄弟,你也不是外人,你看看,可千万不要传出去。”康福接过云马文书来,看上面写着:“遵天王圣谕,着左军主将韦俊,立即回京述职,不得延误。”下钤一长方形云龙边纹印:钦命文衡正总裁开国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玕。下面盖着一颗三寸见方的大印:旨准。
康福看毕,把云马文书放到桌上。二人都无心再下棋。康福问:“韦将军,文书上并没有囚禁的意思,你何必如此焦急。”
“兄弟,你不知道这中间的底细。”韦俊叹息道,“丙辰六年十一月,我困守武昌孤城四个多月后,终因粮尽援绝,不得已退出。事隔三年多了,前一向风闻干王要追查责任,怀疑我是因兄长被诛而有意放弃武昌,要我回京向天王陈述战事的经过。”
“有这等事!”康福惊道,“小人在江湖上,到处听说将军功高盖世。天国三克武昌,有两次的指挥者便是将军。论功劳,天国将官中难找得到几个;况且事过三年,还提它作甚!这干王何以非要与将军过意不去。”
“究其实,也不是干王的主意,完全是天王长兄信王、次兄勇王有意陷害。韦氏家族只剩我和以德二人,以德年幼不更事,信王勇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韦俊木然坐在棋枰对面,忧心忡忡。
“将军,不是小人多言,陷害将军的,名为信王勇王,其实就是天王。天王对将军一家太不公道了。”康福满腔义愤地站了起来,“小人听人说,北王当年与天王结为异姓兄弟,毁家起义,全家老小一百余口都加入了义军,从金田打到天京,战胜攻取,出生入死,其功不在东王之下。东王逼天王封万岁,当时北王正在江西督师,天王手诏北王、翼王、燕王回京勤王。北王杀东王,乃奉诏行事,名正言顺。谁知事情闹大了,天王却诿过于北王、燕王,杀二王来平息内乱,这已是大大的缺德。尔后,又定东升节,封幼东王,而将北王亡灵打入地狱,使天国数十万两广老弟兄心寒齿冷。如此天王,岂不太自私残忍?”
康福这几句话,说到韦俊的心坎里去了。他热泪盈眶,甚为感动,以手示意康福坐下来,小声点。康福坐下,压低声音继续说:“现在,他以为清妖江南大营溃败,天下坐稳了,又要来算计将军了。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将军,依小人看,这天王早已不是金田起义时期的传道先生了,他煞费苦心为洪氏一家一族谋私利,而不顾当年冒死从他起义的数十万兄弟姐妹的利益。将军,你心里难道还不明白吗?”
韦俊望着康福不作声,多年来心里想的,今日由康福嘴里痛快淋漓地说出,他感到非常的舒心。
“天国谁人不知天王长兄次兄庸劣贪鄙,翼王就是被这两个小人排斥出京的,但天王偏偏要封他们为王。最近又封恤王、对王,都是洪姓子弟。洪仁玕来京不过一月,天王不顾阖朝文武反对,便封他为军师、干王,总理朝政。一个未立寸功的白面书生,凭什么瞬息之间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还不是凭一个洪字。我前向在天京,听人说,天王进小天堂八年之间,只到过东王府一次,足不出王宫一步,终日在后宫淫乐,不管朝政。如此昏愦的君王,将军值得为他效忠吗?”
“兄弟,你不知道,当初起义时,我们韦氏全族人都起过誓的,决不背叛教义,决不背叛天王,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呀!”韦俊面色痛苦,看得出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哈哈哈!”康福放肆地笑了起来,韦俊忙用手捂住他的口。
“将军也太忠厚了。你们韦氏家族宣誓不背叛天王,天王却背叛了韦氏家族。这几年来,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将军。前年任命将军为左军主将,乃是迫不得已。现在稍一稳定,便露出真面目了。将军想过没有,五军主将,其他四人都已封王,唯独将军例外。将军受此奚落,有何威望去统帅士卒?有何颜面去见韦氏父老兄弟?”
这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韦俊的伤心处。他的心在汩汩流血,他的四肢在阵阵抽搐,好半天,他才从极度悲痛中苏醒过来:“兄弟,你真是一个有血性、有见识的好汉,干王的这道命令,你说我该如何处理?”
“不理睬!”康福不假思索地回答。
“天国军律:违令者斩。”韦俊摇摇头。
“学翼王,另树一帜!”康福很快指明第二条出路。
“人数太少,难成气候。”韦俊又摇头。
“再不然,改换门庭,投靠朝廷。”康福想了想,说。
“兄弟,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韦俊惊恐地瞪起眼睛,死盯着康福。
康福轻轻地一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束手待毙,做一个千古不瞑目的冤死鬼不成?我看只有这一条路了:弃暗投明!”
“你?!”康福“弃暗投明”的话引起了韦俊的怀疑,他呼地站起,陌生人似的将康福上下仔细打量一番,厉声问,“你是不是曾国藩派来的奸细?”
“将军,你说对了。”康福坦然地说,“我不叫米福,我是曾国藩曾大人麾下亲兵营营官康福,特来为将军指出光明大道。”
韦俊大惊失色,猛地从墙上抽出佩剑来,指着康福怒喝:“大胆清妖,你竟然钻到我的衙门里来了,老子砍了你!”
康福神色自若地说:“韦将军,你砍了我,就能救你的命吗?依我看,它不但不能挽救你,反倒加重了你的罪责。”
韦俊的手软下来,颓然倒在椅子上。
“韦将军。”康福换上了平和的语调,恳切地说,“请你息怒,暂且不要理会我的身份,你冷静想一想,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对不对?”
韦俊不作声,康福继续说下去:“韦将军,你那天不是问我,围棋是怎样到了我的手吗?我今天告诉你吧!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哪有可能得到前明御用之物。这副围棋是曾大人的,当今皇上亲手赏赐与他。他久慕将军棋艺,特地要我将这副棋子送给你,和你交个棋友。”
“有这事?”韦俊十分惊讶。
“曾大人思贤若渴,惜才如命,将军不只是棋艺受曾大人器重,曾大人更钦佩的是将军带兵打仗之大才。”
“我打死他手下第一号大将,他不恨我?”
“哪里的话!曾大人正是从此看出将军超群的才能,他特地要我向将军致意,若将军献池州府投奔朝廷,曾大人将奏请皇上,授将军总兵衔。”
“这怕是不可能吧,我的军队杀死湘勇何止千百,他曾国藩能不记仇?”
“曾大人想的是国家大局,从不计个人恩怨,不信,请将军看这个。”康福说着,从蓝布包里取出一幅字来,“这是曾大人送给将军的。”
韦俊展开。这是一张条幅,上首写“韦俊将军两正”,下首题“涤生曾国藩”。旁边一枚鲜红的印章,衬出两个清晰的白文:涤生。中间题着一首七律:
圣主中兴迈盛周,联翩方召并公侯。
神威欲挟雷霆下,大业常同江水流。
汉祖曾闻韩信勇,唐宗亦赐尉迟裘。
凌烟台阁方新构,杞梓楩楠一例收。
字迹刚劲谨严,韦俊以前见过曾国藩的字,知不是伪造。他卷起条幅,许久不说一句话。康福在一旁耐心等着,慢慢地将棋子收好,装进紫檀木盒里,双手递给韦俊说:“将军不必急,再从长计议,这盒棋和字请收好。曾大人要我多多致意,他愿意和将军交个棋友、诗友。我走了。”
康福说罢,迈步向门口走去。
“等等!”韦俊叫住,“康营官,这是件性命攸关的大事,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一直听的只是你一面之词,并没有见过曾大人的面,叫我如何拿得定主意!”
“将军要见曾大人?”康福兴奋地说,“那容易,我陪将军去!”
“不!”韦俊摆手,“让以德跟你去吧!”
“也好!不过,”康福说,“以德是将军的侄子,将军对他的生命安全,可能会不放心。这样吧,我留在将军身边做人质,另外再安排人陪小将军去如何?”
“那太委屈你了!”韦俊显然已被康福的诚意所打动。
第二天,杨国栋陪着韦以德离开了池州府。池州府距祁门不到三百里,骑马一天的路程。第三天,杨国栋又陪着韦以德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池州。以德向叔父叙述了曾国藩如何地倾心仰慕,如何地推诚相待,并答应韦俊手下的八千子弟兵,仍全部归他统带,不撤不换,这点最让韦俊放心。以德又带来了曾国藩赠送的两件礼品:六两长白山人参送给韦俊,一斤洞庭藕粉送给以德,均为御赏。韦俊大为感动。
过几天,韦俊带着侄儿和几个亲信部将,由康福、杨国栋陪同,来到祁门拜见曾国藩,将那头梅花鹿的角制成的一架鹿茸作为晋见礼,曾国藩乐呵呵地收下了。与太平军交战八年了,他们的许多底细都弄不清楚,韦俊是第一个投降的高级将领,且于打仗很有一套,在询问了一些有关当年内讧和现在天京政权的事后,曾国藩着重打听太平军的战术。
“韦将军,听说你们守城很有一套。”曾国藩和气地笑着说,俨然一个宽厚慈祥的长者。
“回禀大人,”韦俊欠身答,“我们守城有句话,叫作守险不守陴。即精锐人员不聚在城内,而在城外要塞守御。比如守武昌时,就在花园、虾蟆矶筑垒;守安庆,则在集贤关筑垒。”
曾国藩一怔,看来安庆的要害在集贤关。这真是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你们惯用的阵法是什么?”曾国藩又问。
“常用阵法有四种。”为讨曾国藩的欢心,韦俊滔滔不绝地详细谈开来,“一是牵线阵。行军时队伍按一条线行进,有敌情时,首尾蟠屈勾连,顷刻会集,互相救援。二是螃蟹阵。三队平列,中队人少,两翼人多,形似螃蟹,可以随时变阵迎战。三是百鸟阵。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全军分成数百个小队,散布如散星,使敌惊疑,然后突然进攻,常可取胜。四是伏地阵。在遇敌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忽一旗偃,千旗齐偃,转瞬间全军都贴伏地上,寂不闻声;然后一旗举,千旗齐立,全军从地上爬起,按旗号指点,如风涌潮奔,向敌军反扑,转败为胜。”
曾国藩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长毛并不简单,从前总以乌合之众视之,难怪常常吃败仗。百鸟阵、伏地阵,不见于前人兵书中,真是了不起的创造。曾国藩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继续问:“还有一些什么方法?”
韦俊竭力思索,想了一会儿,说:“以前我们常用的,还有以进为退的战术。每当要撤离一地时,必连日出队,打仗不息,前进几十里,逼近敌营下寨,使敌不疑。到了布置完备,忽然一夜之间安全撤退。当撤退时,必在城墙上或立草人,或立木桩,上顶竹帽;白天遍插旌旗,晚上虚张灯火。”
曾国藩想起那年石达开一夜之间撤离南昌时,正是用的这个战术,心里说:“这些个长毛,决不可等闲视之。”
谈了这些大事后,韦俊又对曾国藩谈了些太平天国内部的繁琐称谓,如天王的话称圣谕,东王的话称诰谕,翼王的称训谕,英王的称金谕,干王的称宝谕,勇王的称瑞谕等;又如王长女称天长金,二女称天二金,丞相子称丞公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皆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皆称雪等等。曾国藩和众人听了哂笑不已。
此时,陈玉成正率兵五万来救安庆,曾国荃向祁门告急。曾国藩命韦俊率所部渡江援安庆,另派湘勇进驻池州。
待韦俊离开祁门后,曾国藩叫彭寿颐将韦俊所谈的加以整理,题名叫“长毛战术”,誊抄十多份,分发给湘勇主要将领。又派人将李鸿章献的安徽分府地图给曾国荃送去,另附一封密信。
兹派降人韦俊带所部前来援助。此等贼匪,逼迫无奈才降我,其性反复无常,终不可重用。然分化瓦解,自古以来为制胜良策,望弟善于运用;且此辈久在贼中,深知贼情,用之制贼,可谓以毒攻毒,要害在严加驾驭也。韦俊之部,宜放在前沿打四眼狗之援军,令其火并。另据韦俊供,安庆之贼,精锐在集贤关,切切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