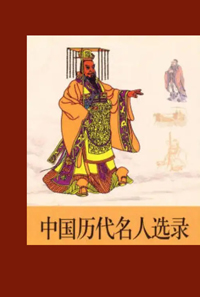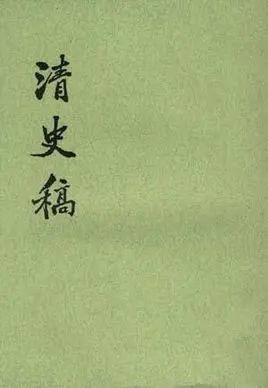夏威夷盛产白檀,由此得别名“檀香山”,抑或“白檀岛”。岛上之白檀皆为夏威夷皇室私产,禁止擅自采伐。
1896年,重阳兵败潜逃至日本的孙文,安排好横滨兴中会事宜后,便只身一人重返夏威夷。翻阅1896年夏威夷群岛的人口普查文献,可知同年华侨人口数多达两万余人,占全岛居民总数近两成。然而1879年,少年孙文初至此处投靠兄长时,岛上华人仅有六千出头,连一成都未有。怪不得孙文其后称此行“短短二十载,恍若隔世”。
孙文方才登陆,便径直赶赴兄长在珍珠港营业的店铺。而店铺中,竟见到一个熟面孔——先前,在香港结识的台湾举人——林炳文。
“林兄为何会在我兄长处?”孙文奇怪道。
“哈哈,家乡被日本所夺,我又不愿屈身于满仔土地,便只得四海为家。流浪至夏威夷,听闻孙先生的兄长定居此处,便前来投靠了。对了,令兄这会儿在茂宜[茂宜岛是夏威夷群岛第二大岛。]的牧场那儿,他托我在此等候,为你引路。”
“汗颜了,回个家竟还要麻烦林兄带路。前日林兄专程造访,只因忙碌起义事宜,未招待周全,还望海涵。”
孙文说完,摘下帽子,微微鞠了一躬。林炳文赶忙脱帽回礼,孙文这才察觉到对方的脑后竟也没了辫子。
孙文所犯的是“诛灭九族”的谋反罪,自然不可能将妻儿留在香山县翠亨村等死。所幸其兄长在夏威夷略有产业,对亲弟弟的家室还是能照顾周全的。孙眉在当地素有“茂宜王”之称,足见其名下牧场之巨,他将孙文的家室妥帖安置在茂宜。
林炳文建议道:“你一定也旅途劳顿了,明天咱俩再一起坐船去茂宜吧?”
孙文没有异议,暂别林炳文后,他独自一人徘徊于街巷中。一路下来倒是遇上不少熟面孔,但就凭他这副行头,也别指望对方能认出自己来。
这不,眼看又要与一位老相识擦肩而过,孙文索性喊住对方,摘掉帽子:“是我呀!孙文呀,孙逸仙呀,你不记得了吗?”
老相识愣了半晌,这才反应过来:“哎呀呀,孙文!……你怎么一副日本人打扮,我差点儿没认出你来!”
在孙文十八岁那年回国后不久,夏威夷王朝便与日本政府签订“官约移民”。自那之后,夏威夷的街头巷尾中,便时常能见到东方人面孔、西洋人打扮的日本人身影。
孙文笑道:“我这趟就是从日本来的,入乡随俗嘛。”
重阳起义前,孙文曾一度返回夏威夷为革命招兵买马,并在当地组织了兴中会。早在当时,他便对海外华人群体之庞大深有体会了。他计划从夏威夷起手,游说于海外华人聚集地,积蓄革命力量。但突逢甲午战败,部分急于求成的同志便坚持要趁此机会归国策划兵变。孙文只能将自己的计划暂且搁置。
在茂宜岛上,孙文与妻儿团聚,杨老太也如愿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家庭对立志舍身救国的革命家来说,始终是块放不下的大石。为不累及亲人,革命家多半得使用假名,孙文在这点上也丝毫不含糊。
难得一家团聚,但孙文仅在茂宜滞留了数日,便有些坐立不安:大事未成,怎能在此悠闲度日?
一同滞留茂宜的林炳文也察觉到了他的异状:“孙先生,怕是这两日便要动身去火奴鲁鲁了吧?”
心思被看个通透,孙文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儿,苦笑道:“到底是瞒不过林举人的慧眼呀。”
“不管孙先生去哪儿,我林某人是跟定了……还有,万万别再唤我‘林举人’了,亡国之下,何来举人?我给自己起了个别名,林遗民。”
“我都忘了,你已算半个日本国籍。讲真,若是没这日本人,我们如何能如此大大方方地顶着个平头在夏威夷与香港的街道上晃悠?话说回来,你要入了日本籍,倒未必是坏事。至少,可以为削辫的华人打打掩护。”
“日本人可并非全为谨小慎微之辈,部分日本人敢于脱离自国枪炮的庇护,离开台湾与日本,到他国白手起家。譬如说吧,我在香港便结识了一个日本人,他在当地开了一家叫照相馆的洋玩意儿,他好像认识孙先生。”
“我晓得了,是梅屋老板吧?梅屋庄吉。”
“正是此人。他声称,曾与您推心置腹地畅谈甚欢。”
“确有其事,我还记得,他主张革命非一国之事,需多国同心协力方可成功。此观点,与孙某不谋而合呀。”孙文颇为感怀道。
两人漫步于茂宜海岸,微风拂面,谈谈革命,聊聊旧事,倒是自在得很。夏威夷算是孙文的主场,他本欲尽早投入于游说工作的,却拗不过天性悠游的林举人,被强拉到这儿来消遣。
夏威夷确是一块宝地,在孙文眼中尤甚。毕竟,他前半截青春记忆便埋藏于此。再者,他虽然是赴港后才接受洗礼,但让宗教信仰在他内心扎根的,还得属这长达五年的夏威夷生涯。
前文亦提及过,孙文进言无果,返夏威夷组建了兴中会分会。其后,在携革命宣传手册返港途中,停靠横滨,将一部分手册交与船小贩陈清。
1894年11月,夏威夷兴中会再组“成立会”,孙文那时不得不回港带领起义,便委任友人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
清国在夏威夷设有名誉领事,想要光明正大地组织革命活动是不可能了。好在,时值融资机构“银会”在夏威夷民间甚为流行,兴中会最初便是以“银会”的形式在当地发起的。入会人投资十个银元,若行情好便有百元利息入账。如此厚利,人们自然趋之若鹜。
集会场所最初设在副主席、主教银行主管何宽的家中,其后因会员数量激增,不得不将据点转移至夏威夷政府通译、会员李昌名下的大宅子中。
在林炳文的极力挽留下,孙文将起程时间推迟了两周。
孙文抵夏威夷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张罗着凑款,将向横滨的冯镜如所借的五百日元悉数寄还。这笔借款,就像卡在孙文鞋里的一颗石子,硌得慌。
孙文心里清楚,横滨对己而言,仅是短暂滞留之地。然而,本应是生命中一匆匆过客的船小贩陈清,却毅然决然地跟随自己赴港起义。
——人情无价,人情难负……
种种经历,让孙文愈发看重对人情义理的经营。因此,孙文自然少不了要逐个拜访远赴广州参与起义的夏威夷同志。邓荫南、陈南、夏百子、侯泉、李杞、宋居人、何早……已返乡者自不必说,未能返乡者,则探望其家属,以表感激之情。
也是多亏了林举人的挽留,孙文得以在火奴鲁鲁的港口与自己的人生导师、就读西医书院时的恩师——康德黎博士重逢。
当初起义失败,孙文潜逃至香港,便当即拜访康德黎,以求今后之策。清廷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要求港英当局立刻引渡主谋孙文。在此危机之际,康德黎又为其引荐律师德尼斯,里外周旋。孙文能全身而退,全赖这位恩师的协助。
临别之际,康德黎难舍道:“我此番如此协助于你,香港怕是待不下去了。我已向学校那头提了辞呈,即日离港。我们师生二人……今后有缘再见吧。”
西医书院创始人名何启,虽在港素有“长老”尊称,事实上仅年长孙文十余岁罢了。这何校长少时曾留洋英吉利,专攻医学与法律,并与一英国女孩儿结缘。学成后归港,从事律师行业,后受聘于政府。不幸爱妻雅丽氏早逝,他悲痛之余,倾尽财产建立“雅丽氏医院”,西医书院作为医院附属学校,也应运而生。孙文为1887年入学的首届毕业生,康德黎博士则于1889年就职于该校的。
首届学生仅有十一人,五年后完成学业者,更只有孙文与江英华二人。孙文舍友关景良推迟一年毕业,其余学生便不得而知了。其后,每年的新生便只有寥寥一两人,其中更不乏如陈少白一般中途辍学者,以至于如今成立十周年,持有西医书院毕业证书的只有十余人而已。
生源紧缺若斯,亦没有必要招聘多余的讲师,甚至连创始人何启也亲执教鞭。因此,孙文与康德黎之间的情谊,远非简单的师生之情。
港口人潮拥挤,孙文仍然一眼便认出了自己的恩师,他手里的玩意儿着实太显眼。
康德黎是个地地道道的摄影迷,当时,伊斯曼公司的柯达相机已问世,康德黎无论到哪儿,都会随身携带着新潮的折叠式相机。扛着照相设备,陪着老师走街串巷的时光犹然就在昨天,孙文激动地招呼道:“康德黎老师!”
康德黎回头,愣了半晌,显然是在纳闷儿眼前的日本青年是何许人。孙文意识到自己的西洋人打扮,忙摘掉礼帽,一手撩起额前刘海儿,一手遮挡鼻下胡须。康德黎这才恍然大悟,展颜兴奋道:“逸仙?你是逸仙!”
提及孙文,康德黎的第一印象便是长袍、额头前秃、辫子。而如今的孙文,不仅头发茂密,鼻下蓄须,还穿着“皇帝”谭有发为其特别定制的洋装三件套。如此巨变,怨不得康德黎一时未能认出,他惊叹道:“哎呀,真是……数年不见,改头换面。这身洋装,与你甚为相衬。”
“见老师依旧如此精神,学生也放心了……您这是打算回英吉利吗?”
“是的。我当初赴任时,走的是印度到新加坡航线。如今返程,便换走太平洋航线,带家小顺道游览一番。此番,计划在火奴鲁鲁逗留五日。你呢?为何在此处?”
“老样子,来做革命宣传。下一站,打算要横跨美洲大陆。”
“再往下,恐怕就要踏入我的家乡了吧?”
“学生早有此意了,可惜,在英华人远不如在美华人那般多……”
“此言差矣,我记得你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条——复兴中国,建立共和。那么,便不能将宣传面束缚在本国国民,必须让国际瞩目才是。而作为世界中心的伦敦,便是再好不过的散播地。若是能得伦敦《泰晤士报》关注,可匹敌百万雄师。哎呀,不说了,不说了,这种话题放在闲适温和的夏威夷假期,太过煞风景。他日你若来伦敦,我们再细聊不迟。”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知老师在伦敦的地址是?”
孙文随即取出纸笔,记下康德黎所说的地址,浑然不知这几个英语单词,其后竟左右了革命的命运。
“那正事就聊到这儿,你现在得空儿吗?陪我聊聊摄影吧。”
那年月,一台相机对旅行者来说,可是傍身不离的宝贝。相传,1902年日本大古探险队探访“丝绸之路”时,便是以京师高官照片为信物,才免于被地方官衙阻挠。而从他们的旅行日记中可得知,探险队沿路拍摄,至目的地时,事先准备的数千张相纸竟所剩无几。
而康德黎对摄影的狂热早已不拘束于摄影技术的层面,甚至连显影工序,都要亲历亲为。
“一遇老师聊起摄影,仿佛又回到了梅屋老板开的照相馆里。”
每逢周日,礼拜结束后顺道拜访“梅屋照相馆”,是康德黎在香港时的习惯。孙文也由此与那儿的老板梅屋庄吉相识。康德黎一旦进了暗房,数小时也出不来,孙文通常会先行离开,或在柜台与店主梅庄闲聊。两人均不擅长对方的语言,仅能用英语交谈,却聊得颇为投机。
话题多涉及时事,两人一致愤慨于洋人对亚洲的轻蔑,并主张亚洲人必须加快文明开化的进程。
“哈哈,不想以洋文咒骂洋人会是这般有趣。”梅屋笑道。
“那接下来,换作用汉文骂如何?”孙文亦打趣道。
不知过了多久,康德黎一脸满足地走出暗房,见孙文竟还在店中,不禁奇道:“哎呀,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瞧你们聊得这般火热,可否让我也插一脚?”
“不成,不成,这是政治机密。”
康德黎略加沉吟,便猜出一二:“我晓得了……莫非是日清联盟,要闹翻天了?”
“正是如此。”在座的两人异口同声地笑道。
时间轴回到现在。临别在即,孙文不舍道:“难得有缘与老师异国重逢,竟聊了一天相机,可笑。”
“无须懊恼,你既有意前往英吉利,届时再秉烛夜谈如何?权当给自己一个盼头。”康德黎宽慰道。
清国开关,直接促成在夏威夷的华人数在近二十年间的爆炸式增长。1896年,美利坚合众国吞并夏威夷王朝。据同年的人口普查,单单记录在案的在夏华人便有两万之巨,然而加上黑户与偷渡者,实际数目数倍于此。
最初,夏威夷王国并无支柱产业,岛民给过往的美利坚捕鲸船提供淡水与燃料,换取物资以谋生,说白了便是资源贸易。卡米哈米哈王朝视岛上自生的白檀为私产,恣意采伐,且无意栽培,坐吃山空是迟早的事。
直到1820年左右甘蔗榨糖技术引进,才打破了这一现状。相传,在岛上发现第一块甘蔗地的,是过往商船上的华人伙计。事实上,残存至今的夏威夷早期制糖器具与清国华南及琉球之地的制糖器具极为相似。
引进之初,仅有在岛唐人三三两两地开坊制糖,难称规模。直至南北战争后,糖价水涨船高,才有岛民陆续掺上一脚。但讽刺的是,此时正逢过往商船激增,外来病菌传播至岛内,缺乏免疫力的原住民遭了殃,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
此现状,直接促成“猪仔贸易”的繁盛。所谓“猪仔”,指的便是被卖到海外,劳作于矿场与铁路建设的华人苦力。
康德黎满足地拍了拍挂在胸前的相机:“你改日到伦敦,便可欣赏到我沿途所记录下的景致了。”
孙文紧握康德黎的双手:“想到不日便能与老师再相见,此次离别倒不显得伤感了,望珍重。”
暂别了康德黎,孙文也不着急动身,继而在夏威夷逗留了数日,以斟酌下一步计划。
孙文曾踏遍脚下的每一寸土壤,即便是阖上眼,前方多远是拐角,何处是村落,犹如映在脑海之中。其他且不说,单是这激增的华人数量,便足以令孙文猝不及防。
状况有变,老一套的宣传手段自然是行不通了。为广州起义招兵买马时,孙文理所当然地将重心放在贫农、苦力等底层人民的招揽上,丝毫未将乡绅显贵考虑在内,这也直接导致数逾千人的起义队伍内,竟挑不出一位拿得出手的名望之士。这样看来,康有为那句“乌合之众”虽有贬低对手之嫌,却也算一语中的。
孙文与陈少白学习西医,电报实习生陆皓东更是志在以科技兴国。三个年轻人无一例外地视科举制度为仇寇,为时代弊病。由此,对以科举上位的士大夫阶层自然也是嗤之以鼻。这种观念显然有失偏颇。
夏威夷是没有举人了,但唐人富豪还是不少的。尤其,有一位名作阿芳的唐人富豪,还与孙文是老乡。是否要拉这个阿芳入伙,倒成了兴中会的主要议题,孙文毛遂自荐道:“这件事,便全权交与孙某来做吧。”
会后,孙文专程拜访了在意奥兰尼学校时的老同学钟工宇,商讨对策。
孙文极为看重自己的这位老同学。为保其周全,甚至未拉拢他加入兴中会,有意保持距离。能令孙文紧张如斯,称其为兴中会的秘密武器亦不过分了。每每谈及此人,孙文的说辞是:“现今,还未到美芳(钟工宇的字)出鞘之时。”
远在香港,另有两人可称“鞘中宝刀”——同为孙文老同学的关景良与江英华。
在孙文看来,真正的英杰,绝非要周旋于枪炮与阴谋之中。让他们在后方运筹帷幄,方能做到人尽其才。
与孙文同届毕业于西医书院的便只有江英华一人。这老同学多次向革命事业伸出援手,尤其是在革命精神传播与筹集资金方面,他深受孙文器重。晚年隐居于婆罗洲[婆罗洲位于东南亚,又叫加里曼丹岛,中国史籍称之为“婆利”“勃泥”“渤泥”“婆罗”等。]山打根市行医,深得当地人民敬仰,与孙文书信往来频繁,同志情谊丝毫未减。
再聊聊这关景良吧,关景良出生于教会之家,其父在伦敦的教会担任牧师。相同的信仰,让孙、关两人的友谊从一而终。另外,关景良同样是西医书院的首届学生,只不过迟了一年毕业罢了。关景良学成后,先在江南沿岸的炮台营就职,担任军医,后移居至香港开设医馆。
最后,该谈谈这钟工宇了。兴中会创会之初,钟工宇因妻子卧病,错过了入会时机。后妻子病逝,钟工宇再娶续房。与老同学孙文重逢时,他名下碾米产业已粗具规模。他常与孙文唠叨:“逸仙究竟打算将我雪藏到何时呀?”
“待局势初稳,主要威胁由枪炮转变为如今的同志们对钱财与权势的贪欲,才是你施展才华之时。”孙文总会如此推搪。
“待到那时,岂不是失去不少乐趣?”钟工宇叹道。
孙文不愿在此事上再多赘言,便转回正题:“如此说,美芳兄是不建议招揽阿芳入会了?”孙文确认道,他对钟的建议还是言听计从的。
照钟工宇的意思,夏威夷数万唐人,富豪何止数百,无须纠结于一人。而钟工宇不看好阿芳的原因并不仅于此。
阿芳,原名陈国芳。唐人入籍海外时,为适应洋人发音习惯,通常会将姓名改为两个字。陈国芳的洋名为“CHUN FONG”,亦就是“陈芳”的发音。久而久之,当地人便习惯唤他作“阿芳”。他本人也不介意,称其为“入乡随俗”,索性将“FONG”改为“CHEN”(陈)。
阿芳绝非一般的土财主,甚至还远负“学者”盛名。他远赴夏威夷的目的很是明确,便就是从商,而非同其他唐人一般在甘蔗地上卖苦力。
后世作家杰克·伦敦[杰克·伦敦(1876—1916年):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生于旧金山。],便以这位传奇华商为原型,创作传记小说Chun Ah Chun[Chun Ah Chun,中文译名为《陈阿春》。]。只不过,作者给阿芳虚构了一段在甘蔗地上受农场主剥削的苦力经历。
另外,阿芳还频繁出现在西方音乐剧中,剧中的他是十三个女儿的父亲。这倒不是夸张,真实的陈国芳,育有四男十二女。
孙文此番回岛后,便尽量避免与陈家人接触,这主要还是出于林炳文的忠告:“且不说阿芳已归国养老,他早已不是单纯的商人了。直到数年前,他还身兼夏威夷名誉领事的差使。虽为虚衔,却是清廷亲手委任的官员。谁能保证,他能死心塌地地站在我们这头……就算他本人有胆子反清,他留着这边的人,会怎么想呢?罢了,罢了,别到时蹄髈没啃到,还惹得一手油腻。”
“据我所知,阿方已入美国籍,清国与他再无干系了……”
“那又如何?孙先生别忘了,他底下还有一群巴望着靠他过活的乡里,上头还有一帮恨不能榨干他油水的官僚,他哪有那般容易脱身?”
“嗯,林兄所言有理。几日悠闲生活,倒令孙某想事情失了计较。”
“孙先生勿要自责,这夏威夷风情,便是这般磨人。连我这外乡人都难以抵挡,这点与我故乡台湾倒有数分相似。”
“唉……到头来,还是得从平民阶层下手。筹集军饷一事,还是暂行搁置吧。”
“学生倒是有一建议……孙先生,不如从洪门下手如何?那帮跑江湖的,虽难堪大用,却可贵在恪守一个‘义’字,绝不会背叛。别对他们抱太大期望,反之,便不会令我们失望不是吗?……您问我今后的打算?这是一块好地方,一时半会儿我还真没打算走。”
两人近乎同时开始蓄发,或许是由于无忧无虑的性子,林举人的头发就是比孙文茂密不少。
“军资何来呀……平民已艰辛度日了,再伸手向他们讨要钱粮,孙某于心何忍。”
自广州起义以来,孙文便暗暗起誓——绝不同士大夫为伍。人才全由各会党中招揽,郑士良的首要工作,便是从“玉石混淆”的会党中“引玉”而“去石”的。
孙文有意将夏威夷兴中会建设为以会党为根基的组织,林炳文亦附议。“洪门”便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夏威夷“洪门”与郑士良先前负责接洽的会党还是大不相同的,归结为二字,便是“温差”。
清廷明令禁止民间人士“拉帮结派”。通常而言,统治阶级为少数人的政权最为忌讳的便是被统治阶级团结一心。称当时清国大陆上的会党苟且于清政府镇压的之下,一点儿也不为过。
相反,远在夏威夷的华人会党,便毫无此方面顾虑。照林举人的说法,美利坚大陆上的华人会党更是“无法无天”。
美利坚在籍的华人,有七成为“洪门”党徒。同乡人结伙,被惯称为“会”,先前提及的“银会”便是典型的“会”。远在美洲大陆,天高皇帝远,自然没有偷偷摸摸的道理。
对这样的“门徒”宣传革命,可非一日之功。毕竟,他们之所以成为“门徒”,为的也仅是在异乡寻求归属感。这样的人,怎会愿意与心中的“归属之地”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