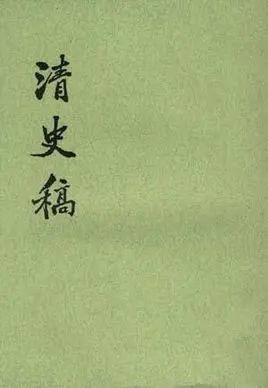谈及“洪门”的“身世”,至今仍未有定论。
“洪门”二字最早为民间地下组织“天地会”的别称。当时,“天地会”归顺于太平天国政权。不知出于何种缘由,民间习惯将入会称为“入洪门”。至于“洪门”这个会党的来历,民间流传着多种版本。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是“洪门”出于自保,刻意捏造多种说法,以混淆视听。
“天地会”又名“三合会”,抑或“三点会”。后世闻名的“哥老会”,实际上亦是“天地会”的分支,只不过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罢了。
“天地会”极重守密,基层门徒对会中情况一问三不知乃是常态。
早在意奥兰尼学校时,孙文与钟工宇便从中文老师盛先生那里听说过有关“洪门”的一些神乎其神的传闻。青年孙文只当是市井谣传,不置可否。
台湾举人林炳文对“洪门”起源的见解,倒算有史可循——“洪门”起源于台湾。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陷北京。翌日,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明王朝灭亡。
然而李自成还未将龙椅坐热,满洲铁骑便敲开了北京城门。满族原为关外女真族,起初国号为“后金”。其后,为与六百年前侵略宋国的金朝划分界线,改族名为“满洲”[1635年,皇太极下令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国号为“清”。入主京师的第一任帝王,为年近七岁的顺治帝。
当时,汉族仅存的反抗势力以台湾郑氏最为强大,其领袖郑成功为中日混血,因功勋卓著受赐国姓“朱”,名“成功”。民间敬称他为“国姓爷”,他却仅改名为“成功”,仍用“郑”姓。如今,还有几人记得他原名郑森,字大木。
常言道“何处有反抗,何处便有团结”,至于这帮志同道合之士为何将他们团结的载体称作“洪门”,就不得而知了。
孙文首次与洪门人士接触,得追溯到去年重阳起义前的号召阶段。记得,直到见面之前,孙文对这帮江湖人士还是抱有防备之意的,一再向对接人郑士良确认:“确保不会出岔子吧?”
“宽心,那帮兄弟可不似士大夫那般奸险。”
孙文的担忧合情合理,毕竟事关起义机密,一旦泄露,则累计数千同志身家性命。然郑士良对久习礼义的士大夫嗤之以鼻,却对这帮草莽之士深信不疑。为解除孙文的顾虑,他讲了一个故事:
曾几何时,一个洪门门徒见财起意,欲将会中机密卖给官差。他暗中来到县衙,称有机密相告。
他被衙役领进一间密室,室内有一男人在等待他,看样子是捕快。他忙开门见山道:“我手头上握有本县洪门的内部情报,衙门愿意花多少钱来买?”
男人摆摆手,示意不着急,让左右先给门徒上了一盏茶。门徒也是渴了,一仰脖子便将茶水一饮而尽。他再欲开口,却发现喉咙已没了知觉。
男人见状笑道:“哼哼,花海如何?怎么,这么快便开不了口了?兄弟近来似乎有些点子不正呀,是否要走一趟万水千山?哎?怎么不给个反应,不至于连声都听不到了吧?”
乍听来牛头不对马嘴的数句话,却令此人一屁股瘫在了地上,眼前的捕快竟是洪门人士。洪门会徒大多是见面不相识的,得依靠特殊暗号,来甄别同伴。
“海花”指“茶水”,“点子不正”意为“运道差”,“千山万水”是“医馆”的黑话。若仅冒出一个“黑话”,还能侥幸地认为是口误,这一连地蹦出三个,眼前的捕快,是洪门门徒无疑了。这杯“花海”入肚,此人下半辈子怕是再没能力告密了。
照林举人的话说,“洪门”的创始人不是其他,正是“国姓爷”郑成功。当年,郑大将军拥兵台湾岛,为来日重复河山,就曾派手下勇武潜返大陆,于各地组织反清团体以里应外合。
17世纪中叶,台湾岛内反清势力愈发不可收拾。台湾郑氏政权虽健在,但要正面进攻日益巩固的清王朝,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郑家只能以反清秘密组织的形式暗中渗透至大陆,这便是“洪门”的原型了。
诸版有关“洪门”起源的传说,多以内地为背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少林寺”起源说。此少林,非“达摩祖师面壁”之河南开封少林寺,而是毗邻于台湾,福建省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九连山少林寺俗称南少林。]。
传言,莆田“南少林”拥僧众一百二十八人,个个身怀绝技。而南少林存在时,清国已至康熙朝(1661—1722年),这与“洪门始于明朝”一说是相悖的。
再者,传言中有云:邻国西鲁侵犯清国边境,清廷招募天下义士以御敌,南少林僧众披甲从戎,大胜而归……此说法亦颇荒谬,反清义士竟助清抵御外敌?
传说还有下文:此一役后,清廷视南少林为隐患,在内奸“老七”马福义的策应下,一把火将寺院烧为废墟。自那后,“七”便成了洪门的忌语。
而幸存于火海中的蔡德忠等五人师兄弟,被奉为洪门“前五祖”,永世受门徒祭拜。其后,更出现了“中五相”“后五祖”等精神领袖。乃至于林举人调侃道:“洪门啥都缺,就是不缺唱戏的与讲评书的。看这架势,是恨不能在所有名人头上都加上一段‘洪门’故事。哈哈,不知百年以后,孙先生与‘洪门’之间,又能发生如何感人肺腑的纠葛。”
“林兄说笑了……”孙文嘴上这样说,心里也犯起嘀咕了。自己早在郑士良的引荐下,与“洪门”旗下组织“致公堂”有过交集,硬要说,也算是半个“洪门”门徒了。只要对革命事业有益,他对这一头衔倒不排斥,反而觉得“洪门”与英语读物中出现的“Freemason”(共济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1905年,反犹著作《锡安长老会纪要》问世,书中诬陷“共济会”为犹太人一手缔造,企图以此征服世界,此作直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犹太民族的仇视。一个组织愈是神秘莫测,便愈引人遐想。“洪门”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致公堂”为“洪门”派系,以美利坚为主要活动区域,夏威夷“洪门”索性便自称“致公堂”。说来可笑,“洪门”如今能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仰仗的还是清政府的野蛮镇压。
林举人笑道:“海外唐人中,错认为‘致公堂’与‘洪门’毫无瓜葛者仍不在少数。真是不知该惋惜,还是该庆幸。长久以往,‘致公堂’在世人眼中,怕是会沦落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江湖组织了。但要是如此,我们这些门徒呀,怕是得处处戒备警察与密探,再无安生日子可过。”
回头想想,孙文倾尽心血,陆皓东慷慨赴死,其目的不就是能过上这“安生日子”?革命宣传与军饷筹集,仅是第一步。
孙文在夏威夷大小算是个名人,有富豪兄长孙眉这把大伞,成日登门拜访者亦是络绎不绝的。老同学钟工宇虽明着不敢有什么大动作,但为了能早日走出亡妻之痛,他也算是一头扎进孙文的革命事业里了。
这一天,钟工宇备好笔墨,来到孙文的宿舍。闻知孙文归国学医期间,仍能不忘从师研习中国古典,钟工宇大为感佩,此番便是专程为讨教而来。
“不日便要与逸仙兄千里相隔,望逸仙不吝笔墨,赐只言片语以做留念,这亦是你我二人同窗情谊的见证。”
“那孙某便献丑了,望美芳兄勿要嫌弃我的‘鬼画符’才是。”
孙文嘴上谦逊,却已迫不及待地磨起了墨。钟帮忙捋着笔尖,摇头叹道:“逸仙过谦啦……是了,勿要太过晦涩,我打算遗留给子孙后代。如今的孩童,哪还读得了祖宗留下的竖版字。”
那年月,愿意将儿女的教育托付于洋学校的华人父母可谓少之又少。孙文依稀记得,自己初至夏威夷时,意奥兰尼学校已开学两周了。入校之初,读一行横版字都得遭老罪。但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后,他的成绩便名列班级前茅了。夏威夷国王亲自颁发奖励。
而同班的钟工宇悟性便没这般高,起初还能与孙文半斤八两,没多久就被孙文远远甩在了后头。意奥兰尼学校采取全封闭式教育,但两人还是逮着机会便逃出校园,到盛先生处求学中文。不出所料,同样是几年钻研,孙文的中文造诣,仍是要比钟工宇高出许多层次。
青葱记忆让孙文一时难以自拔。墨已蘸,却踌躇如何下笔了。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推翻清朝,仅是革命的开始。孙文倾尽一生奉献于革命事业,为的仅是四个字——民族平等。而民族平等的先决条件,为民族“大同”。
孙文正欲挥毫,却犹豫了,单单“大同”二字,是否太过晦涩难懂。“大同”,一言蔽之,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状态。踌躇之间,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入“致公堂”时,郑士良让自己做出的一句宣誓:“尔父母,即吾父母。尔兄弟姊妹,即吾兄弟姊妹。尔妻子,即吾妻子。若违此誓,五雷诛灭!”
孙文略加沉吟,凝心神于笔尖,顷刻间,纸上出现苍劲的“博爱”二字。
一气呵成,不浪费一纸一墨。孙文扫了一眼钟工宇带来的一叠宣纸,意犹未尽道:“来,再取一张过来……这纸墨,都非凡品呀。这纸,怕是上等宣纸吧?”
安徽宣州以当地精湛的造纸技术闻名于世,同时安徽省所造的墨亦是一时无两,时称“宣纸徽墨”。
新的笔墨就绪,孙文这回再无犹豫了,下笔就是铿锵有力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
天下万物,非一人之私产,而为万万民众所公有。此四字,不仅道出了“民族共和”之真谛,亦饱含了孙文的无限展望。
孙文对“共济会”的了解,不仅得于书中的记载。早在学生时代,恩师康德黎便对共济会颇为仰慕,常将其事迹挂在嘴边。据传,共济会成员互以兄弟相称,这正与“洪门”第一誓不谋而合。康德黎本人虽与共济会无干系,其表兄却是共济会成员。
共济会高举“博爱、自由、平等”三面大旗,成员遍布世界。他们所崇尚的“博爱”,特指“全世界人民”的大爱。
“感激,感激。”钟工宇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纸卷起,心中盘算着找一流工匠裱起,悬挂于家中厅堂之上。
“本想加上‘革命’二字的,但考虑到如今的国人,对‘革命’的理解有所偏差,还是先缓缓。”
倒不是说国人对“革命”一词感到陌生,只不过,谈及“革命”,他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易姓革命”。
“易姓革命”,顾名思义,指的便是“上顺天意,改朝换代”。刘汉、李唐、赵宋、朱明,传至清一朝,国姓“爱新觉罗”,而取代“爱新觉罗”的会是什么姓?
孙文各地宣传革命,为的便是告诉普天民众,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万姓”。国家领袖由百姓选举而出,任期数年后轮换,并非天子,而是总统。短短一句话,要让天下百姓心领神会,却是千难万难。
夏威夷真是孙文心中的极乐之地,无论是前番(1894年)以起义者身份到此备战,还是如今作为通缉犯在此避难,悠闲的夏威夷空气,总能让孙文忘却俗世烦恼。见此,钟工宇提醒道:“不要怨我泼冷水,如今的夏威夷可不比往日,你在岛上的一言一行可得留个心眼儿。”
“美芳此话从何说起?”孙文疑道。
“你细想便知,你我上学之时,夏威夷唐人不过数千,如今却猛增至数万之巨呀。当年,数千唐人是一家,大家都知根知底。再看看如今,还有谁管你是谁。再者,阿芳与阿泰的甘蔗地上,每日都会出现新来的唐人,其中不乏些来历不明的家伙。”
“对这些来历不明的新唐人,确实要留个心眼儿。”孙文点头道。
“你这人爱广交好友,好事,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切记谨言慎行。”钟工宇再次叮嘱。
“美芳提醒得是!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最铁不过故交。就怕兴中会内,也混进了什么宵小之辈。”
“宽心,亏得何宽与李昌二人实心用事,又有令兄孙眉坐镇,暂时无此迹象。要注意的,是那些打今儿起,有意无意向我们示好的人……”
“甚是。让你这样一说,我还真有些头绪了。这些日子,有个人在暗中调查我前往旧金山的航班。如此看来,他可没安什么好心呀。不知美芳所指,是否是此人?”
见孙文心领神会的眼神,钟工宇露出个似笑非笑的表情。他一早便觉得那成天绕在孙文周围、名作吴平的新唐人不是善类,既然孙文有所察觉,他也无须多做提醒了。
1896年6月18日,孙文登陆旧金山。同日,光绪帝生母醇亲王福晋辞世,她也是西太后的胞妹。
此时的光绪帝,重用变法派官员,俨然已成为帝党领袖。西太后对此颇为忌讳,但见朝政仍然把持在以自己为首的保守派手中,便暂作观望态势。
但实际上,两派之所以能看似和平地共存至此,还得归功于醇亲王福晋两头周旋。孙文闻知福晋殡天,心中便对接下来的局势有了计较:
——少了那护犊子福晋的呵护,帝党的处境怕是堪忧了。西太后没了妹妹这道顾虑,打压帝党势在必行。当然,帝党也不会坐以待毙,事到如今,只有赶在西太后前先行动,方能有一线生机。
受时势所推动,“起义”“变法”“维新”等新词汇得以在民间传播开来。让孙文倍感安慰的是,会中同志终于习惯了“革命”这一称呼。
孙文从火鲁奴奴登船时,李鸿章还滞留于俄国,加冕礼虽告终,但密盟仍未谈拢。直到6月7日,李鸿章才在其子李经方的陪伴下,于克里姆林宫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辞行。
其后,使团一路西行,6月13日抵达柏林。李鸿章拜见德皇威廉二世,观看了禁卫军军演,并就“三国干涉还辽”一事,对德政府表达谢意。
7月初,使团一行参观克革烈军工厂[这里应是指李鸿章一行于比利时参观克革烈枪炮公司。]。8月5日,李鸿章拜见英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4年。亦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8月28日,一行人搭乘“圣路易斯”号,横跨大西洋至美洲大陆,美总统克利夫兰[格罗弗·克利夫兰(1837—1908年):美国政治家,第22任和第24任美国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分开任两届的总统。]亲自至纽约相迎。李鸿章在美利坚滞留半月余,于9月14日起程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