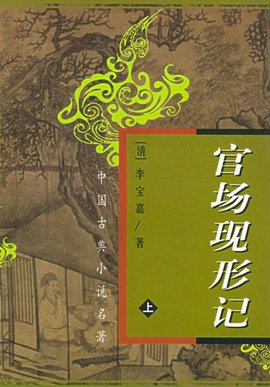本作品以孙文(1866—1925年)为主人翁,活生生地描绘了“中国诞生”这段历史的台前幕后,堪称历史巨著。
描写孙文的文学作品,可谓满坑满谷,但多数是传记,抑或评传。以孙文为主角的小说,别说在异国日本了,即便在中国,也是少之又少。估计是因为普通小说家的功力,不足以驾驭“中国诞生”这一段厚重的历史吧?
当然了,还有另一个见不得光的原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是不太受文学界待见的。有一种说法不知大家是否听说过——试问,革命同志们在国内抛头颅、洒热血时,孙文身在何处?打着募捐的旗号,周游世界。1911年武昌起义,孙文身为革命领军人物,不思临阵杀敌便罢了,还远离战火于丹佛。待革命成功,他才以高姿态“凯旋”现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加身。如此想来,孙文是否有坐享其成之嫌呢?尤其是时下评传将孙文粉饰得如救世主一般,更是令人无名火起。
相较于夸夸其谈的评传,自从拜读了陈老师的《孙文》(单行本改名为《青山一发》)[“青山一发”为本书日文版书名。此篇“解说”原为日文版收录,故在“解说”译文中沿用日文版书名,以方便读者了解。“孙文”为本书日文版原名,后改为“青山一发”。],本人才明白孙文因何受中国人敬爱。通过小说独有的叙事形式,孙文内心的苦恼与纠结展示在世人面前。读者们深感共鸣——原来,孙文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单单这点,便是历史传记与评传无法企及的。
照理说,孙文本可无忧无虑地做他的“国际人”,但时值祖国同胞在清廷与列强的压榨下苦不堪言,他才不得不高举民族主义旗帜。
要说陈老师的精妙之处,先是以史学家不掺杂个人情感的视角,将伟人孙文“降格”为普通人,再运用小说的手法,加之以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残存的海量史料中,精准地捕捉到孙文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历史小说的极致也不过如此了。
孙文所处的时代,正是激荡的历史变革期。放眼中国前的变革史,无一不是“自北向南”,抑或“自内陆向沿海”。悉数成吉思汗、永乐帝、努尔哈赤等征服者,都是顺应此趋势,才成就霸业。就拿孙文的宿敌康有为来说,他与孙文一样是广东出身,坚持老一套,致力从京师朝廷开展改革。
再反观孙文那“自南向北”“自沿海向内陆”的变革方针,纯粹是逆常理而行。正因如此,才会举步维艰,屡屡受挫。但一旦成功,其成果便冲破了“易姓革命”的定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书名“青山一发”,也正隐喻了此方针。
说来奇妙,非士大夫阶级出身的孙文,到头来,竟成了中国历史上首位“社会理念”的领导者。追溯世界革命史,西洋之革命运动多由市民发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主人翁则是下级武士。但在中国,此等中流实务阶级极为势弱。这还得归咎于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一批批实务阶级的人才被迫投身功名。而士大夫阶层多数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好逸恶劳之辈,观念也相对保守。
再说本书的另一大看点——孙文、康有为,两大“先进知识分子”的对决。
早先在海外开馆行医的孙文,算是实务阶级中的佼佼者了。他身为局外人,深知士大夫阶级之局限,因此不愿拉拢其进革命阵营。
再看看康有为,半生投身于仕途,典型的“高风亮节”士大夫。本书对他的性格描写很是贴切,康有为听闻孙文在广州发起革命,神情不屑地说了两句话:
“一帮乌合之众在广东小打小闹,能成何气候?”
“可笑,军中竟无一个举人。”
短短两句话,将自视甚高的士大夫之局限性暴露无遗。果不其然,康有为活了一辈子,也未逃出“朝廷与功名”这一怪圈。
要说结果,孙、康两人都将最初的理念坚持到了最后。孙文屡屡受挫,却初心不改。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则一生誓死护君。要问什么变了?那就是世道……清王朝最后的数年,迫于巨额赔款,国家经济濒临破产。就在此时,停滞了千年的中国社会猛然奋起,眨眼间便将康有为的保守主张淹没;不待孙文反应,革命一蹴而就。如此看来,激流勇进的时代浪潮,才是本书的真正主人翁。
笔者拙见,孙文笑到最后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孙文吃透了散布在国内外的华人关系网(讲明了,就是会党);其二,巧妙利用欧美媒体炒作“伦敦绑架事件”,将国际舆论拉至己方阵营;其三,“三民主义”目标明确。当然,若没有辅以孙文那锲而不舍的乐观精神,说什么也都是空谈。
早在本书问世前,孙文这一主题便在陈舜臣老师心中酝酿已久。笔者有幸,在月刊《中央公论》任职时,就孙文这一话题,对陈老师进行了专访(2003年12月号,后收录至单行本《陈舜臣对话集》)。以下为部分谈话内容:
陈:家父是1898年生人,也就是这本小说开头的次年。那时,台湾已完全在日本“治”下,家父也算是第一批“日籍台湾人”了。1924年2月,家父带着母亲移居神户,这才诞下了我。也就是同年,孙先生来日本,在神户高等女校召开了一次演讲,这算不算是我与他的一种缘分呢?
加藤:若我没记错,那便是闻名中外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吧?孙先生那句“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如今仍如雷贯耳。
陈:那次演讲也是孙先生之绝唱。当时,他已罹患癌症,翌年3月便撒手人世了。我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自然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打记事起,家人乃至周围人,便时常将孙先生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我也将自己与孙先生置于同一时代了,便是《青山一发》所描绘的那个时代。
加藤:也就是说,《青山一发》是您笔下最接近“现代”的历史小说了?
陈:总结得妙!在我看来,故事发生在我出生、记事以后,那就是现代小说……说来,这本《青山一发》出版后,书中人物的子孙后人还专程至信感谢,说是谢谢我为他们的祖上纠正了许多误传。当然了,也有读者指出了个中错误……
“以小说言史”算是我的看家本领——陈先生在后记中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历数以近代为背景的历史小说,陈舜臣文学堪称一枝独秀。
《青山一发》之开篇并非讲述孙文的少年时代,而是谈及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的那段历史,这点不符合创作常理。但细想之下,也有理可循,大概是源自陈老师对自己出生年代的强烈执念吧。在此再次引用访谈内容:
陈:20世纪初,中华受列强蚕食,孙文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与日本民间志士携手共奋,旨在实现亚洲的觉醒与解放。当时,如宫崎滔天、犬养毅一般胸襟坦荡的日本人辈出,估计是东洋人共通的“侠义”精神使然吧。
然而最后呢?观其后历史,日政府离孙文号召的“大亚洲主义”愈行愈远,与中国终生嫌隙,如今两国更是割袍断义。我就想了,若两国能找个时间坐下来,细细品味孙文其人与那段复杂的历史,是否能成为冰释前嫌的契机呢?
在本作中,陈大师已对多位与孙文交好的日籍志士做了不同程度的描写,笔者斗胆再做补充。如文中所赘述,惠州起义兵败,山田良政行踪不明,后被确认为牺牲。关于他的牺牲,坊间传闻野史如下:
山田并非失踪,而是被清军俘虏。那年月,清廷如何敢碰外国人一根汗毛。盘问时,清军质疑山田国籍,但山田几度用中文决绝道:“我是中国人。”最终从容就义。事后,清当局凭山田遗物辨明其日本国籍,悔得肠子都发青了,慌忙处理尸体,并封锁了消息。这才有了“失踪”一说。
山田良政之胞弟山田纯三郎久侍孙文身旁,一直到孙文临终,留下“革命尚未成功”遗嘱时,他是少数在场者之一。孙文辞世后,纯三郎依旧留在中国,并极力撮合中、日政府。“二战”后,纯三郎才不得不回到日本,后蒋介石邀请他赴台。1960年,纯三郎病故,享年八十三岁。
1915年,日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此举让中日关系降到历史冰点。陈老师在长篇小说《山河在》中,描述了孙文晚年的苦恼,国家立场难以与往日情谊共存(特指与宫崎滔天、头山满等)。
再看本作,陈老师于1912年1月1日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处搁笔。如今看来,这不无道理,在那个节点上,中日关系是尚存反转余地的。始于台湾被侵占,终于辛亥革命,精妙的叙事结构,无不透露着陈老师对这本作品的期寄。
曾几何时,日本在全亚洲是何等令人钦佩。无论是“汝为西乡,吾为日照”,还是“长沙如萨摩”,幕末维新志士一直被中国进步人士视若标杆。前有孙文、康有为、梁启超等救国志士选择日本为避难所,后有鲁迅、蒋介石、周恩来等纷纷赴日学习。对这些抑或避难,抑或求学的中国人,日本民间多是敞开胸襟以礼相待,而日本政府则一如既往地冷眼旁观。
拜读了此作,笔者不免扪心自问——如今,经济起伏不定,未来晦暗不明的日本,还是那个受亚洲诸国爱戴的“开明”国家吗?不说政策方针如何,单看我们这些民间人,谁能坦坦荡荡地对外国人敞开胸怀呢?
肩负日本未来的年轻一辈更该静下心来拜读此作,领悟其中道理。